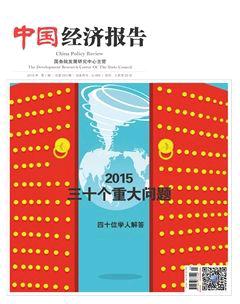求解“钉子户”
党国英
“钉子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工业化前,城市发展极为缓慢,且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按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老城都有保留价值,不仅不能拆,还需要保留,自然也不应该有“钉子户”问题。相反,搞“大跃进”而产生的城市,倒是需要拆迁;如果人们自己不拆,大自然也会拆。
以人力的土地规划干预自然本体的一个经典案例,是日本奈良的城市建设史。公元710年,奈良作为日本首都设想了一个宏伟的造城计划,新都市被定名为平城京。其建造是模仿中国隋唐时代的京城长安,东西长约六公里,南北约四公里。据记载,城市网络格局建设完成了80%以上,鼎盛时期由各地迁入的人口约二十万人之多。公元794年,天皇迁都于平安京,标志着“奈良时代”结束,作为首都倾国力建设八十年之后,奈良不再获得同样的持续投入。在之后漫长的1300年,奈良并未延续宏伟的都城模式,那些被渠化系统改道的河流,鬼魅一般回到自然的漫流形态。辉煌的朱雀大街曾是最繁华之地,现在完全淹没在近似田垄的肌理里面。凡是对河流走向的干预性建设,全部湮灭,恢复了旧貌。反过来说,如果奈良继续作为日本首都,人们为了维护这座城市,要比维护一座自然发展起来的城市,付出更多的代价。
但是,在工业文明前,类似奈良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所以,不合理的城市规划所产生的城市,多会被大自然的力量来解决拆迁问题。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任何“钉子户”都无法抵挡。
工业文明产生之后,建筑垃圾多了,有时候就有了拆迁的必要性。工业文明下的政府会以强干涉性的土地利用规划大兴土木,城市的合理性就难保证。但相对而言,在欧美社会,因为历史上具有地方自治的传统,也有保护私有权的法治实践,城市建造的合理性程度就要高一些。
从欧美的城市建设经验看,即使城市有了什么问题,拆迁也不容易。在他们关于土地规划的立法理念中,有一种“存在优先原则”被政治家与规划思想家所遵守。原住民存在状态优先,是这一原则的体现。以美国涉农土地利用规划的操作为例,农场有自己的作业习惯,这种习惯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土地主人的利益。美国有《公认农业管理习惯》等农事权法规,在司法审判中,法官依法认定对这类农业习惯的保护优先于地方分区规划。此理念的坚守,有助于产生城乡风貌的多样性。如果动辄用后来的土地利用规划否定历史上形成的土地利用现状,非常容易形成反复发生的大拆大建行为,历史遗产难以保护,并使城市风貌千篇一律。这个土地规划理念不仅不会限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城市更加美丽。越是尊重有价值的历史存在,城市就越有多样性,越有可能避免“千城一面”。
建立土地所有者“保持现状优先权”,并不是现状绝对不能改变。通常,如果确实需要改变现状,有可能在土地主人过世之后,发生遗产继承时,才会依法改变现状,例如拆除现有的地面建筑设施。有了这样的理念,政府官员就不容易动心思拆迁,“钉子户”也就不会轻易冒头。
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浪潮中,大面积现存居住区被规划为非居民区,因强行征地、强行拆除民房而导致流血的恶性事件常见,其中,“公共利益”往往被相关方用以论说强征强拆的正当性理由。自然,这个理念很令人怀疑。
从现实看,住房权利边界模糊、城市建筑管理失序、急功近利造城,都会人为地制造“钉子户”。城市土地成为公有土地后,大量城市房屋也就成了公房,或者城市房屋的院落成了公共土地,对建筑的监管就只有靠政府了,民间的产权人不再起任何作用。有了这个条件,“公地悲剧”就开始发挥作用,城市的院落就到处是违章建筑。现在问题出来了。经济力量强大了,有了造城的能力,看见到处堆砌的违章建筑不顺眼了,于是,就要拆旧建新。“钉子户”就这样出现了。
今后怎么办?其实,一些技术性的措施可以减少拆迁量。如果交通枢纽等重要控制性设施先于城市建设,购买土地的市场价格不高。政府出价不仅高于市场价格,还会考虑购买行为对周边利益相关人的影响。一些国家虽然也规定,在关键控制性公共设施建设选择地点有唯一性、不可更改时,政府可以按严格程序强行购买,但现实操作中因为补偿到位,强行购买极少发生。对于此种情形以外的其他建设用地,政府仅仅出台“负面清单限制”,给土地的所有者以选择权利,绝无强行购买的理由。政府不需要担心一条街道上有几个“钉子户”而妨碍城市景观建设。即使多数议员或百姓认为一个“钉子户”的行为所引起的城市景观不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也不会祭出“公共利益”的旗帜,采取“拔钉子”的极端行为。因为人们懂得,公共利益极容易成为多数人的话语霸权,它一旦践踏少数人的权利,最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逃不过“少数人的命运”。
在总体规划中,规划管理部门仅仅对控制性枢纽工程做出强制性要求,而对其他区域的规划只提出“负面清单”,给原住民最大限度的自由选择权。按这个办法,政府可能只需要在约20%的规划区土地上购买土地,其他规划区的土地不需要购买。如果控制性枢纽工程用地选择合适,例如选择在居民少的地方,拆迁量会很小,其他规划区土地基本不需要拆迁,原住民或闲置土地的主人可根据“负面清单”自己建造或改造房产。日本的许多城市在过去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基本没有失去旧的风格,貌似“钉子户”的痕迹在日本大城市比比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日本发展。例如,在东京某繁华街的一段,某人有一块不到30平米大小的土地(长11米,最宽的地方2.5米,最窄的地方60公分),而这块地紧贴街面的是一座大楼。土地主人请了英国著名设计师设计了一座小型建筑,用做珠宝交易,竟然成了街道的一个亮点。规划界有句话说,美是在不经意中创造的,但无疑,这种创造依赖对私人产权的尊重,对个人选择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