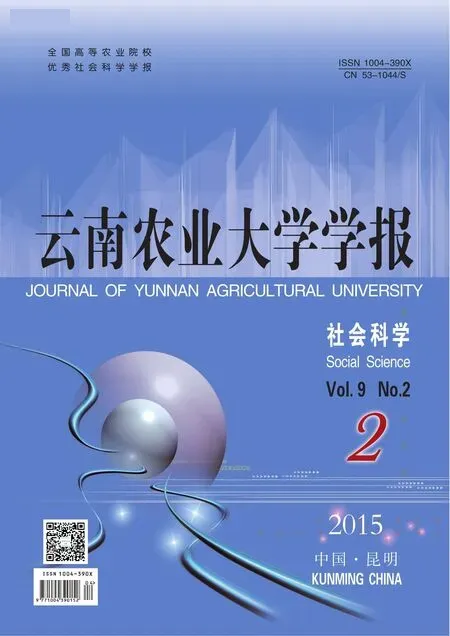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母女关系文化内涵
刘 岩
(西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母女关系文化内涵
刘岩
(西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在美国文坛发声至今,在华裔美国文学内部已经形成了自身清晰可辨的母系传统。由于特殊的移民历史和境遇, 华裔美国文学母女关系书写既不同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书写和主张也不同于其他弱势族的经验。本文选取三位女作家的三部涉及母女关系主题的小说伍慧明的《骨》,任碧莲的《梦娜在希望之乡》和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考察母女关系书写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继承、演变和创新,指出通过调用和调整移民母亲和本土女儿故事的时空架构,母女关系被置于华人移民家庭、族群和社区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加以考量。在跨族裔散居时代,母女关系这一文学母题策略性消解东方主义话语牵引下的传统/现代、东方/西方、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身份认知范式,为母女关系书写增添了跨文化视角。
关键词:母女关系;移民母亲;本土女儿
华裔美国文学执着于母女关系书写在一定意义上弱势族裔的一种生存、身份和发声策略。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文坛发声至今,无论是在文学市场上取得的成绩还是在学界引发的关注女作家都无可辩驳地超过了同期的男作家,华裔美国女性作家前后相继创作了众多聚焦女性心灵,记录女性成长感悟的作品,乃至形成了华裔美国英语文学内部自身清晰可辨的母系传统。与美国白人母系文学一样,华美母系文学关注母亲身份和母女关系,以此来对抗男性文化典籍压制女性言说,忽视女性经验的传统。但是书写和解读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本土出生女儿的故事受到多重话语的牵引,华美文学的女性文本贡献了更多丰富内涵。华裔美国文学母女关系书写既不同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书写和主张也不同于其他也不同于其他弱势族(如黑人女性)的经验。这种差异既体现于华人移民及其后代的跨文化意识,也体现在移民在美国主流社会同化和排斥力量牵引下构建自身主体性的矛盾。美国亚裔学者ELAINE H. KIM[1]较早注意到了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性别意识问题。AMY LING[2]对早期华裔女性文本主题进行了分析,注意到了其中的跨文化内涵。另外两位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LIM SHIRLEY[3]和WONG SAU-lING[4]分别撰文谈及华/亚裔文学中的母女关系主题,后者更是冠之以“美国华裔母系文学传统”之名。国内学者程爱民[5]分析了谭恩美的《喜福会》和《灶神之妻》中的母亲形象和母女关系内涵。陆薇[6]则分析了《女勇士》一书的女性主义叙述策略。石平萍[7]通过对比分析白人中心的主流女性主义话语与美国华裔妇女及其有色人种姐妹的立场差异,肯定了华裔妇女文学在表现母女关系主题上的独特角度。本文选取三位女作家的三部涉及母女关系主题的小说伍慧明的《骨》,任碧莲的《梦娜在希望之乡》和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考察母女关系书写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继承、演变和创新,指出通过调用和调整移民母亲和本土女儿故事的时空架构,母女关系被置于华人移民家庭、族群和社区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加以考量。在跨族裔散居时代,母女关系这一文学母题策略性消解东方主义话语牵引下的传统/现代、东方/西方、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身份认知范式, 为母女关系书写增添了跨文化视角。
一、《接骨师之女》:中国母亲/美国女儿
《接骨师之女》是谭恩美继《喜福会》、《灶神之妻》、《百种神秘感觉》之后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最新力作。作为华裔母女故事系列畅销书作者,谭恩美的母女关系叙事模式准确把握了当代都市中产阶级女性情感需求、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诉求。《接骨师之女》延续了《喜福会》开创的母女故事时空架构:母亲来自遥远的、前现代的东方,历经旧世界的战乱、匪患、父权欺压、流离失所,亲人逝去等等磨难最后辗转来到新大陆安身立命。女儿生活在现代的美国,成长过程中在生活习惯、待人接物上不断受到母亲苛责,渐渐与自己的母亲疏离隔阂。母亲虽然对女儿的境遇了然于胸,但在向女儿用中文传递关爱和表示忧虑时总是感到词不达意,常常欲言又止。母女二人只能各说各话,在各自的辗转反侧中渴望彼此沟通和谅解。女儿成年后,在婚恋和事业上遭遇危机时,母亲的种种预判和老道被证实,母亲的智慧和阅历被重估。母亲战胜苦难的经历重新成为女儿力量和灵感之源。故事最后母女达成谅解,女儿认清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和母爱的无私,母亲也接纳了成熟自知的女儿。《接骨师之女》这部具有较强自传性的作品继续沿用母女故事的时空架构:母亲茹灵小时候历经民国革命、日军侵华,在家族变故后躲进美国传教士开办的育婴堂在美国传教士庇护下躲过了战祸,后又经传教士帮助辗转香港后赴美。女儿露丝竭力扮演现代中产阶级女性角色,在为事业和家人奔忙中渐渐迷失了自我,体现了典型现代都市女性的症候。但是在这一母女故事叙述模式之内,《接骨师之女》一书在设置母女各自的故事时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恰恰更明确反映出谭氏母女故事背后的观念架构和价值诉求。
变化一:女儿故事中母女角色换位。与以往谭氏故事母亲用中国故事或中国格言谚语劝诫女儿不同,在《接骨师之女》一书中,深陷现代生活危机的女儿主动去靠近和追溯完整的母系历史,母亲所经历的磨难帮助女儿完成了在现代舒适生活中对浴火重生的一种浪漫想象,成为女儿所代表的现代都市女性在消费大潮中重新发现自我调适自身扭转困局的契机。《接骨师之女》中的中国母亲茹灵业已老迈,无力为女儿分担忧愁,反而女儿露丝反而为母亲因为失忆导致寡居生活陷入混乱和危机而殚精竭虑。露丝人到中年,一边自己个人生活和事业烦恼不断,一边为母亲的状况寝食难安,不得不拿出耐心像照看孩子一样陪护渐渐丧失记忆、思维混乱言行幼稚的母亲,母女关系周而复始,女儿担负起了母亲的职责。为了与这一角色换位相适应,女儿露丝的故事采取了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叙述声音显得更加成熟冷静。为了帮助母亲延缓记忆,露丝渴望读懂母亲留给自己的中文手稿,但是几经尝试都因为不懂中文而放弃。在母女各自危机不断加剧情况下,露丝终于打定主意请人翻译母亲手稿,随着母亲的过去清晰呈现出来,露丝本人的现实问题也跟着奇迹般解决了:生活中露丝和同居男友坦诚了彼此感受,重新找回往日温情,事业上露丝决定结束替人代笔,倾听自己的内心,书写自己的母系故事。相比之下,在谭氏以往的故事中,母亲为女儿学业、婚恋和事业上的问题忧心,希望女儿出人头地、自强自立,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却保留中国的气质。”[8]227母亲给女儿讲自己如何克服磨难,争取主动的故事,希望能给女儿以警示或激励。如在《喜福会》一书最后,三位母亲都决定打破母女之间的沉默,用自己的力量助女儿们走出困境。在以往的故事中,美国女儿的叙事声音虽然也是成年女性,但是这些女儿似乎都陷入自己的生活里,无力也没有时间去回望母亲的生活。母女自始至终都十分隔阂,母亲不知道自己的人生阅历和遭遇能否给女儿以警示和启迪,而女儿似乎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逐渐步入社会、婚姻和家庭生活后,才开始体悟到母亲的种种良苦用心,母女之间对深入对方心灵的不确定形成以往谭氏故事的张力。
变化二:与《喜福会》里历经磨难痛定思痛的顽韧的母亲不同,茹灵缺乏与命运抗争的智慧和勇气,背负着所谓的命运的诅咒随波逐流,毫不自知。旧式封建大家庭遭遇的天灾人祸映衬着动荡和混乱的中国近代史。在严酷的时代失去了父母庇佑被家族驱逐出去的少女茹灵本已万劫不复,却如有神助般巧遇美国传教士才得以翻开人生新的篇章。在人生跌入谷底之际,巧遇西方庇护和帮助得以重生。在《喜福会》中,母亲懂得利用周围人的迷信愚昧观念摆脱封建牢笼,获得自身解放。在《接骨师之女》中自我抗争被传教士相助取代,一方面反映出女权主义退潮时代女性对自我力量的想象变得苍白贫瘠,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大众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启蒙东方的话语如何牢牢固化了包括华裔自身在内的美国大众的中国/东方想象。
二、《骨》:沟通传统与现代
华美文学新秀伍慧明的第一部长篇《骨》从华裔土生二代女儿的视角,将华裔移民、家庭和社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具化为一个特殊组合家庭三代人的家族史。与《女勇士》和《喜福会》等女性文本中母女故事的时空框架不同,首先,《骨》将家族故事起始时空置于华人移民历史(三代人分别代表自由移民时期——排华时期——二战后新移民时期)和华人社区(美国西部旧金山唐人街),断然拒绝了中国移民母亲讲述的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往事,转而聚焦华裔美国社区内部的变迁。《骨》从本土女儿视角,表达了对奉献了青春和热情的父辈移民的真切同情,对日渐消逝的传统乡土社区和熟人社会进行了温情刻画从而开创性地在母女关系的故事架构中嵌入族群意识和社区责任问题。通过将母系故事与父系故事并置交汇,打破了华美女性文本中父系故事缺失或在美国白人女权主义牵引下担心父系故事与母系故事相互冲突而各自表述的做法。母系故事与父系故事的并置与交汇更贴近华裔美国的现实,体现了华裔美国社会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历史上体制排华造成的华人移民单身汉社会向完整的家庭社区转变,封闭隔离的华人聚居区向现代社区的转变。
《骨》刻画了华人移民社会底层边缘家庭的母亲形象,反映了族裔强势文化牵引下弱势族妇女的命运与经验。由于华人男性长期遭遇排斥与歧视,一直徘徊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条件拮据。华人家庭远不是同时期白人中产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模式。为了养家活口,养儿育女,女性不仅不是丈夫的附庸,相反要与丈夫并肩劳作,女性的付出对于华人家庭的生计不可或缺。母亲是唐人街华人聚居区里为数不多的女性,随同前夫入境美国,被前夫抛弃后带着女儿生活陷入困顿。后来为了绿卡与利昂组织了家庭,生育了两个女儿安娜和尼娜。为了与丈夫一起支撑家庭贴补家用,在唐人街血汗制衣厂当了女工,在缝纫机的突突声里、在堆积如山的衣料里夜以继日青春逝去。通过将家族故事置于华裔美国历史时空,摆脱了母女关系架构中过去/现在、传统/现代的对立。《骨》中的一母三女虽然对应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本土女儿的结构,但是中国和美国、移民前和移民后的时空架构却不是母女两代人的故事架构。换言之,两代人的故事发生在共时而不是跨文化历时背景下。这一时空架构在读者导向上消除了事关“中国”、“中国女人”等话语中的美国东方主义视域。用本土女儿视角中的华人移民在新世界的移民体验取代母亲讲述的旧世界的异域故事,突破了将母女两代人的认知差异简单等同于中美文化差异乃至优劣的书写套路。母女生活在同一时空下,拥有共同的传统,本土女儿的感悟来自亲眼见证和亲身经历,并不外在于母亲的生活。这样的书写立场,摆脱了置身事外的局外人的凝视视角,没有了白人中产阶级猎奇探秘的优越感,华人社区和华人移民的故事得以“去魅化”。小说开篇即写道旧金山唐人街的“三藩”公寓“就是我家最具历史的地方,是我们的起点,是我们的新中国。这就是我们对它的看法。”[9]2
《骨》中的母女也面临着传统向现代的调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让她们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二女儿自杀、三女儿远走就是明证。但是《骨》创造了一个以家庭族群和社区事务为己任的社区缔造者形象莱拉。长女“我”莱拉从小在唐人街的乡土社区里长大,对老一辈移民遭遇的屈辱与挫折感同身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让“我”具备了双重文化意识,工作后做了社区关系专家,在四分五裂的家庭成员和唐人街内外穿梭,调停家庭和社区事务,帮助老移民向当局争取权益,为新移民提供法律和子女教育方面援助,是华裔家庭和社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沟通传统社区与现代社会的代理人。在家庭中,“我”和母亲的位置发生了对调,我成了家庭和社区的代理母亲:父母日益年迈,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越来越像任性赌气的孩子,“我”为他们之间的冷战和冲突忧心忡忡,为二妹自杀自责不已,为之身在外漂泊的三妹感到爱莫能助。“我”在闹分居的父母之间奔波,想方设法调节他们的关系。为了不让年迈的父亲随着衰老而精神萎靡,“我”在做社区工作时把父亲带在身边。“我”背着母亲到东海岸纽约注册结婚不是有意违背母命,是因为同为女性“我”的幸福可能会让母亲更加感觉自己婚恋的不幸。母亲的两次婚姻都缺少爱情:来美国前与我父亲结婚是想改变生活的窘境,先是到香港,后又赴美淘金,用莱拉的话说,“图的是刺激。”[9]10淘金梦破灭后父亲傅满里远走澳洲,母亲和幼年的莱拉滞留华人社区。为了绿卡和生计母亲和单身汉利昂组织了家庭,这一次是为了掩盖自己第一次婚姻失败的耻辱,“图的是方便。”[9]10“我”对母亲经历的理解体谅、对母亲感受的呵护关怀,为母女关系书写范式带来了改变,消解了代际和文化冲突要素,母女情深得到彰显。在工作上,“我”是专职的社区关系专家,负责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从小的经历使“我”对新移民家庭生活的艰辛和劳碌感同身受。新移民家庭的子女与“我”小时候有着相似的经历:狭窄的公寓既是一家人生活起居的空间也是家庭的工作间。我每天在新移民家庭和学校与社区间穿梭往来,承担着这些家庭的“代理母亲”一职。“我”有着明确的族群和社区意识,通过与族群和社区的过去紧紧相连,通过服务社区实现了自我。
三、《梦娜在希望之乡》:消解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立
《梦娜在希望之乡》一书是20世纪9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繁荣期间崭露头角的任碧莲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该书所呈现的故事是任碧莲第一部长篇《典型美国人》的续篇。如果说在《典型美国人》中作者以族裔的视角以戏拟主流强势的口吻讲述了成为先前为自身所贬抑的“他者”的同化故事,在《梦娜在希望之乡》一书中,作者以更宽广的视角观察美国移民社会各个族群接踵摩肩、阶级文化传统参差交错的现实。《梦娜在希望之乡》一书在故事架构上采取了华裔母女关系叙事中从冲突到和解的常见范式,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移民张家通过第一代人的努力,入住了纽约郊区富裕的犹太人社区。父亲拉尔夫和母亲海伦希望女儿们能够好好珍惜社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做优等生上名校并最终跻身美国主流社会,在“美国梦”的阶梯上再上一层。故事整体架构上母女从冲突到和解的范式再次得到重复,但在这一基本架构内母女冲突的缘由、母女冲突背后的隐喻却有了不同意义。首先,《梦娜在希望之乡》一书中移民母亲与本土女儿的矛盾冲突只是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冲突,而不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母亲海伦这代移民出身中国中上层社会,移民前优越的阶级地位使他们先于很多自己的国人接受了西方意识观念的启蒙和现代生活方式,他们身上没有传统与现代的焦虑,移民美国后奉行实用主义价值观追求物质版的“美国梦”,把向上流动作为价值目标和人生定位。对于传统以中国东南沿海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唐人街华人移民社区和华人移民历史缺乏认同感。高中生梦娜就认为在父母眼中“‘移民’一词指的是那些把活鸡带上公共汽车,连个行李箱都买不起的人。”[10]27他们是“新犹太人,‘模范少数族’、美国梦的践行者。他们知道自己身在希望之乡。”[10]1表面上母女冲突是由于文化差异:作为社区里唯一的华裔家庭,父母把张家当成了“堡垒”,竟然谈论是否用围墙围住房前的草坪。在家里梦娜和姐姐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无论是干家务还是去煎饼店帮忙都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也不能像白人同学一样在自己的房间安装电话分机。任碧莲以美国东方主义的口吻写道:“也就是说,梦娜和凯莉就是奴工。随时被叫到餐厅帮忙是常有的事。他们修剪草坪没报酬,用吸尘器清理客厅没报酬,擦防风窗没报酬。尤其是凯莉,她一直就是家里的强力刷。但是即便妈妈的爱女梦娜帮忙擦干碗碟也没报酬。而且这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即是得到了一点报酬,她们也不可能把这笔劳动所得花在买热裤上。毕竟,这就是家庭成员的含义:没有什么事小到你不用征求父母许可。”[10]26相比拥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的白人同学而言梦娜和凯莉简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任碧莲通过有意模仿美国东方主义里有关中国的封建“家长专制”、“东方暴君”等话语,对东方主义本质化“他者”的逻辑提出质疑和结构。小说一开始就反映出拉尔夫和海伦这对移民父母自己已经不再以中国正统文化自居。例如,海伦自己就承认“已经十分西化”,“没有让子女学习中文。”[10]48对她来说同化是生存的必须,“父母应该像竹子,在风中低头,而不是像电线杆了一样僵硬地戳在那儿。”[10]49在有关当代中国的话题上中国移民海伦好像知道的也不比女儿们更多,他们所建构的中国是经过美国主流媒体渲染和过滤过的中国。
不仅如此,任碧莲进一步在文本中消解了将母女之间代际冲突约化为东西文化冲突的范式。如果说在华裔美国文学母女关系书写范式中母女两代人隐喻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权利关系,那么任碧莲则把阶级考量引入这一范式从而消解了母女关系这一隐喻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例如,作为来自中国中上层社会的拉尔夫和海伦来说,大女儿凯莉从大学校园里学来的第三世界联合反殖反帝的话语令他们觉得自己先前的阶级地位被低估了。去国离乡对拉尔夫和海伦这样的移民来说不关乎对过去旧生活的扬弃,反倒是他们先前的阶级地位有可能在新世界不复存在。拉尔夫和海伦在中国的生活可谓是养尊处优,拉尔夫的父亲是城里少数拥有汽车的人,海伦小时候家里摆圣诞树穿进口皮鞋上教会学校。凯莉用从大学校园学来的进步话语“启蒙”海伦,说上海教会学校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者”,他们就是要“接管中国”“拯救那里的异教徒”,但是“你们是文明人”,“他们是要让你们改宗。”[10]42可是海伦用世俗实用的态度轻易化解了凯莉口中的民族宗教大义:海伦说“我们不介意被转化”,“洗礼后我们还是佛教徒,不仅是佛教徒,我们还是道教徒,天主教徒,我们想怎样就怎样。”[10]42由此可见《梦娜在希望之乡》一书中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于母亲希望女儿一代做模范少数族实现物质版“美国梦”,以此收复自己因为移民而失去的先前的阶级地位。本土出生的女儿凯莉和梦娜虽然羡慕白人同学的母女之道,但是族裔意识(犹太社区里唯一的华人家庭)并没有让二姐妹在家庭里效仿自己的同龄人在父母目前抗争自己的个人权益。即便是梦娜与母亲闹翻被逐出家门,也不是因为梦娜忤逆孝道传统不容于东方专制家长。
此外,《梦娜在希望之乡》一书的母女冲突处于特定时空。处于青春反叛时期的女儿们受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种社会运动激进话语牵引和同伴影响,不屑于移民父母做安分守己模范公民的做派,梦娜和一群不谙世事的伙伴在远离西海岸社会运动中心和漩涡之外的纽约郊区富裕犹太社区里参照当时的社会运动实践排演了一出反抗种族不公匡扶社会正义的闹剧:帮助被梦娜父母开除的无家可归的黑人厨师弗莱德私自住进犹太富人的豪宅,并因此引发了白人女孩伊芙和黑人青年弗莱德的恋情。张家父母深知华人夹在黑白贫富之间的微妙处境,自认两边都开罪不起,觉得梦娜的所作所为有可能给他们这个刚刚从平民区搬进中上层社区的华人家庭带来麻烦和灾祸,这次无法再对女儿的胡闹听之任之,母女爆发了争吵梦娜主动离家放逐在外。
通过对三位女作家的三部涉及母女关系主题的小说进行分析可见,母女关系书写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华裔美国文学中得到了继承、演变和创新,通过调用和调整移民母亲和本土女儿故事的时空架构,母女关系被放置华人移民家庭、族群和社区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加以考量。在跨族裔散居时代,母女关系这一文学母题策略性消解东方主义话语牵引下的传统/现代、东方/西方、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身份认知范式。华裔美国文学母女关系书写不仅关注女性个体和群体成长和经历这些女性主义普适话题,更将其还原至具体时空语境加以考量从而丰富了母女关系情感体验和隐喻意义,为母女关系书写增添了跨文化视角。
[参考文献]
[1]KIM E H. “Such Opposite Creatures”: Men and Women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J].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1990, 29(1): 68-93.
[2]LING AMY.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0.
[3] LIM, SHIRLEY GEOK-LIN. Asian American Daughters Rewriting Asian Maternal Texts[C]//Shirley Hung . Asian Americans: Comparative and Global Perspective.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9-248.
[4] WONG SAU-LING CYNTHIA. “Sugar Sisterhood”: Situating the Amy Tan Phenomenon” [M]//DAVID PALUMBO-LIU. The Ethnic Canon: Histories, Institutions, and Interven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174-210.
[5]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07-113.
[6]陆薇.母亲/他者:《女斗士》当中的对抗叙事策略[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17):34-37.
[7]石平萍.美国华裔妇女文学中的母女关系及种族与性别政治[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02.
[8][美]谭恩美(Amy Tan).喜福会[M].程乃珊,严映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9][美]伍慧明(Fae Myenne NG)骨[M].陆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0]JEN GISH.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M]. New York: Alfred A, 1996.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LIU Ya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A recognizable matrilineage tradition can be traced from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1976) garnered national fame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circle in the late 1970s.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ainstream Anglo-Saxon women literature but from that of other ethnic writings due to the fact that Chinese Americans have emerged from a unique immigration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variation of the tradition in the Chinese American texts published in the 199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By invoking and adapting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mother-daughter stories,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there texts is explor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family and communit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the trans-ethnic Diaspora ag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trategically dissolves the cognitive paradigm of identity that highlights the orientalist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tradition / modern, East /West and Self/Other. Thereby a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is added to the traditional mother-daughter motif.
Keywords: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mmigrant mothers; native daughters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2.024
作者简介:杨波(1978—),女,云南保山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文学翻译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4y220)。
收稿日期:2014-10-23修回日期:2014-10-29网络出版时间:2015-04-0210:41
中图分类号:I 2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2-01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