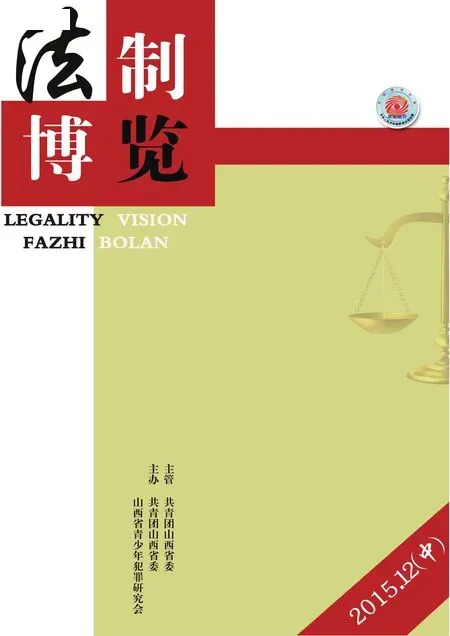论我国《精神卫生法》存在的缺陷及完善
雷 宇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论我国《精神卫生法》存在的缺陷及完善
雷宇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摘要:一直以来我国精神障碍患者都处于被社会刻意忽视或排斥的状态,2012年出台的《精神卫生法》为这一现象带来了转机。作为保障这一弱势群体的专门法律,该法对患者的相关权利及有关部门职责作了详尽规定。尽管如此,由于利益冲突和机构职权等因素的存在,该法还存在一些遗憾,如规定患者权利范围狭窄、权利救济程序不完善等。
关键词:精神障碍;权利救济;精神卫生法;完善
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保护一直是公众关注但并不愿去涉及的话题。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不仅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屡遭侵害,连普通民众“被精神病”的案件也频频见诸报端。如何规范这一混乱现象,进一步缓解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矛盾已经刻不容缓。
一、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基本内容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相继对精神卫生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既往的社会防卫性的司法模式逐步演变成了治疗性的尊重人权的医学模式的精神卫生法。我国于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对于精神卫生立法不能仅仅将之视为“保健与治疗”立法,更应该使之成为保障特殊人群权利的立法。
(一)立法原则
在总结各方意见之后,《精神卫生法》在总则部分第1条,第3条和第4条规定了本法的立法原则,其中《精神卫生法》第3条处于核心地位。《精神卫生法》第3条规定:“精神卫生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预防、治疗和康复相结合的原则。”《精神卫生法》确立了的是以患者预防和治疗为中心,全社会包括医疗机构、社会团体、单位个人等提供帮助为辅助的框架。
在分则中,第26条和第30条确立的在实践中操作的原则,也为精神障碍患者的保护提供了可靠依据。第26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尊重患者人格尊严的原则。”这条原则性的规定是总则第3条的延续,但并不重复,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以保障患者权益为出发点,更凸显了本法的精髓所在。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该条规定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早就成为大家争议焦点,对于是否强制医疗直接涉及到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矛盾的调节。对于社会大众更加希望精神障碍患者能收归医疗,而对于患者权益本身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自由权利的剥夺。《精神卫生法》最终将住院自愿原则保留下来,使得患者在住院与否有了选择权,这是该法的进步,也更表明本法是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保护法。[1]
(二)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
1.隐私权
隐私权的保护体现在第4条,根据第4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条规定在之前公布的草案中并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一新增的规定让患者行使权利更为自由。隐私权的重要性对于每个公民而言不言而喻,尤其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这样的弱势群体而言,缺乏社会的关注,且一旦相关信息被公众所知,其处境只会更加窘困。
2.自愿住院权
《精神卫生法》第44条第一款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由于该法规定有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可以采取强制性住院措施,该条款使得患者能够有选择随时出院的权利,避免了医疗机构因强制住院措施而导致的限制任意性,也免去了患者被动住院后被永远限制自由的尴尬。[2]
3.知情权
除了基本的隐私权和人身自由可能被限制的自愿住院权以外,在具体治疗的过程中,患者最重要的权利是知情权。根据第37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精神障碍患者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告知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这一规定使整个治疗过程更加透明,患者的相关权利和诊断情况能被患者及其监护人所知悉,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责任分配
对于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保护仅从相关医疗机构入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精神卫生法》在规定医疗机构和有关部门的义务基础上,对诸如监护人、用人单位等也做了详细规定。[3]
1.医疗机构的责任
本法在医疗机构的职责方面花了较大篇幅予以规定,主要体现在预防、治疗和保障三个方面。在预防阶段,第17条新增规定:“发现就诊者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符合本法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扩大了医务人员的职责范围。在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阶段,医疗机构除了应具备第25条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以外,还应当履行相应职责。[4]如第28条规定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针对以往医疗机构存在的不合理利用患者从事医疗实验的现象,第42条和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对依照本法第32条第二款规定实施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以治疗精神障碍为目的的外科手术”。在最后的康复阶段,第55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提供相应的药物维持治疗,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和支持。
2.监护人的责任
作为精神障碍患者最亲近的监护人,本法也作了明文规定。如第32条规定在对诊断结论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时,监护人可以提出异议;第40条规定对患者实行强制措施时应当通知监护人。这些命令式的规定让监护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同时更好的落实其对患者在法律上的监督和守护的责任。[5]
3.其他部门的责任
对于其他部门,本法规定在国家的指导之下,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有序规划,建立健全精神卫生协调工作。[6]上至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下至村民委员会和居委会,对于精神卫生工作都应当予以支持和协作。
二、我国《精神卫生法》存在的缺陷
虽然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从起草到正式定稿期间历经二十余年,中间利益博弈使得这部法律日趋完善,其精神与联合国和WHO发布的包括《残疾人权利宣言》和《精神健康立法十项基本原则》在内的宣言相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社会具体情况和相关机构的制约,导致这部法律尚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一)精神障碍鉴定制度的不完善
《精神卫生法》第31条规定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虽然我国并没有规定司法鉴定的委托必须由司法机关进行,但是在实践中,个人委托却是从严控制。绝大多数案件的鉴定都是以公检法等机关委托为主,要个人自行委托必然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在理论上和国外各种鉴定实践模式来看,个人委托符合一般规则,但如果从我国国情出发,这一规定会影响到鉴定结论的质量和可靠性。[7]
(二)精神障碍患者权利及其救济程序的不完善
作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保护法,新法对部分权利的规定比较狭窄,因而实践中权利的行使效果可能达不到立法者的预期,而且部分权利在该法中并没有得到规定,导致部分权利缺乏救济的途径。
1.精神障碍患者权利规定的缺失
由于《精神卫生法》应强调患者的权利本位,认可患者除了精神存在障碍外与其他人并无不同,因而患者不应基于年龄、性别、宗教和种族等受到歧视。我国《精神卫生法》在第4条规定了劳动报酬权和隐私权,第35条规定了患者住院同意权,第37条规定了告知权等。虽然这些基本权利在该法中得到确认,但相关权利的规定却并不完善,如第37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将精神障碍患者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告知患者或者其监护人。[8]
2.精神障碍患者权利救济程序的缺失
除了权利规定不完善以外,该法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即没有规定相应的权利救济程序。在实践中,精神障碍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权利被剥夺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在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中也并没有涉及到相关的救济途径。
(三)与《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84规定,“对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但是由于这些规定在前,与后出台的《精神卫生法》难免会有冲突之处,因此要如何协调这些矛盾也是将来司法实践不可避免的问题。[9]
1.二者的性质不同
新《刑诉》中的强制医疗属于司法性质,根据新《刑诉》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由公安机关写出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再由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申请,最后由法院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从这里可以看出,整个过程都在司法机关之间运作,而对于《精神卫生法》规定的强制医疗则属于行政法的范畴。[10]
2.决定主体完全不同
对于新《刑诉》中决定是否对当事人进行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在法院,且必须组成合议庭并作出决定。由司法机关决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是对相关案件的审慎,且作出的决定更具有说服力。相较之下《精神卫生法》的决定全在相关鉴定机构和医疗机构。根据该法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由医疗机构采取强制措施,并通知患者的监护人。
3.救济的程序不同
根据新《刑诉》287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而且对于强制医疗的程序都由人民检察院实行监督。《精神卫生法》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本级人民政法对本级相关部门予以监督,这种理想上的被动监督方式在实践中并没有效果,也就是说如若患者的权利受到侵害,并不能主动寻求到相关救济。[10]
三、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完善对策
(一)明确精神障碍鉴定制度的内容
如前文所述,既然《精神卫生法》属于行政法范畴,对于该法规定的鉴定应着眼于一些特殊性的问题上。[11]如出台相关解释,协调本法的鉴定程序和司法鉴定程序的衔接,完善医疗机构和有关部门的职责。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整合相关鉴定资源,使得我国的鉴定系统不会太过于庞杂,在利用好有限资源的同时也方便了患者行使其权利。
(二)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
《精神卫生法》对于患者的权利和相关部门的职责规定已经相当详尽,但对于一些程序性的规定则鲜有涉及。这跟我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固然分不开,更多的还是立法者对程序性保障并不重视。因而有必要明确精神障碍患者权利的程序性规定,以确保患者能够了解自身享有的权利以及如何行使权利。除此之外,应当充分肯定当患者的权利被剥夺或限制时,患者及其亲属或代理人通过各种途径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合法性。[12]
(三)协调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
首先要协调好二者对于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由于强制医疗是对于个人人身的限制,世界各国均采取审慎的态度,通行的做法是由法院作出相关的裁定。但由于专业上的限制,法院显然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13]因而要协调二者之间的权限,最理想的最发是由医疗鉴定机构来运用专业知识诊断当事人是否患有相关疾病,然后再由法院按法定程序,结合事实和相关鉴定意见来作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的决定。
其次是要明确相关监督主体。在新《刑诉》中对于强制医疗的监督权属于检察院所有,但在《精神卫生法》中所谓监督权属于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不同于西方的机构设置,我国检察院作为监督机构有其独立的地位,其作为专门的监督机构,加上强制治疗的措施涉及到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将监督权统一收归检察院。虽然可能涉及到职能的变动和检察院工作量的增加等现实问题,但出于对人权保障的考虑,将监督权统一于检察院无疑利大于弊。
四、结语
《精神卫生法》的出台对于我国混乱的精神卫生医疗局面是个重大突破,其涉及到各方面利益冲突和职责分配。作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保护法,本法从权利和程序等几个方面做了规定,但在实践中仍需要包括用人单位、社会团体、患者监护人等各方面共同予以关注和保护。
[参考文献]
[1]王辉.我国<精神卫生法(草案)>立法目的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11(09):177.
[2]裴国玺.关于我国精神卫生法制度构建的若干思考[J].医学与社会,2005(04):48.
[3]孙大明.精神卫生立法中鉴定条款的改进及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司法鉴定,2011(04):38.
[4]左雪梅.我国精神病患者权利的立法保护探析[J].精神医学杂志,2007(06):399.
[5]王永杰.新法的冲突与协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02):75.
[6]管唯.对<精神卫生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与建议[J].中国司法鉴定,2011(04):35.
[7]戴庆康.英国精神卫生法修订评介[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2(03):114.
[8]盛莉莉.精神病人救治过程中的权利保护[J].科教导刊,2010(04):189-190.
[9]蔡军.日本的保护人制度[J].上海精神医学,2002(01):15-17.
[10]彭华民.台湾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制度[J].东岳论丛,2011(06):32-39.
[11]彭少慧.论精神卫生法的基本原则[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6):114-119.
[12]王岳.美国精神障碍患者权利保护历史与可鉴之处[J].海峡法学,2012(06):179-182.

作者简介:雷宇(1991-),男,湖南岳阳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13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5-01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