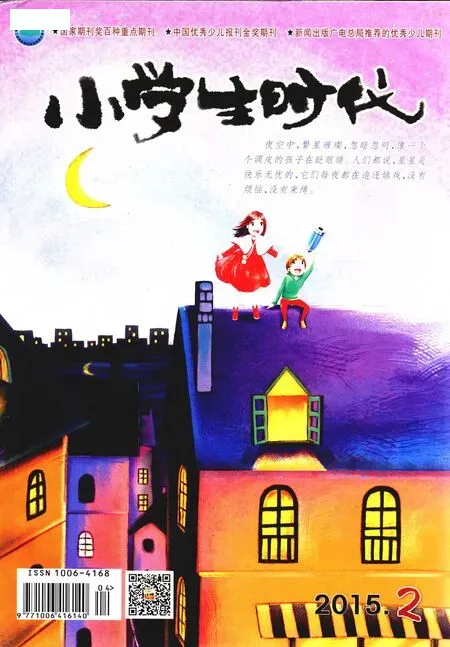朱鹮,东方仙子“起死回生”
□刘伟伟
朱鹮,东方仙子“起死回生”
□刘伟伟
在我国古代,朱鹮被视为“吉祥之鸟”。
日本民间把朱鹮看成“仙女”的化身,它的羽毛是祭祀的供品。
在古埃及,朱鹮则是智慧的化身。它们死后会被制成木乃伊,享受着神灵般的祭祀。
四十多年前,中国、日本还有前苏联的科学家们“上穷碧落下黄泉”,遍寻朱鹮却不得,一度以为这个物种已经灭亡,痛心不已。
然而,33年前,人们在秦岭深处意外地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一时间欢呼鼓舞,甚至设立了专门的保护区——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作为一种鸟,朱鹮显然享受了超规格的待遇!
为什么?
美丽
毫无疑问,朱鹮是一种极其美丽、优雅的鸟儿——如果你见过它,也一定会被它迷住。
正常情况下,朱鹮一身羽毛如雪似玉,脸颊是朱红色的,虹膜为橙红色,腿也是朱红色的,嘴巴却是黑色的,又细又长,还向下打了个弯(有利于它从水田、沼泽、河滩及山区溪流浅水的淤泥中探寻美食,比如泥鳅、黄鳝、蛙类、田螺、沼虾、河蟹等),后脑上长着几十根又粗又长的白色羽毛,看起来如同戴着漂亮的柳叶羽冠。
总而言之,如果朱鹮不发声,无论静止,还是走动,抑或飞翔,都极其端庄美丽,十分符合东方的审美观,估计这也是它们享有盛名的原因。可如果它叫起来,呃,就有点“自毁形象”了,因为它们的声音十分刺耳。幸运的是,它们出声的时候并不多。
温和
“朋友来了有美酒,敌人来了有猎枪。”这句俗语足以用在朱鹮身上。虽然体型不算小,但朱鹮性情友善,极少攻击比自己弱小的鸟儿。此外,它们不仅夫妻忠贞恩爱,同类之间也是和谐共处。即使面对试图“撬墙脚”的第三者,朱鹮夫妇也只是做出亲昵的假动作,使之自动“羞”退。
在食物缺乏的冬季(河流、小溪、冬水田一旦结冰,朱鹮的嘴巴敲不开冰面,吃不到泥鳅等,只好改吃蚯蚓了),它们还会成群结队地栖息在高树上——没饭吃,聊聊天也能打发这漫漫冬夜啊!
然而,如果敌人来犯(在它们生儿育女的时候,老鹰、乌鸦、蛇等总是伺机偷蛋),朱鹮却是坚决对抗,曾有人目击一对朱鹮夫妻为了保护幼子,和一米多长的菜花蛇进行了生死决斗!
变色
很少有人知道,朱鹮还是一种会变色的鸟儿。它们的这种本领多在繁殖期间施展,也就是万物复苏的春天,这时候食物充足,正适合生儿育女。
然而,在生育之前,朱鹮们还要先做点什么,比如,用嘴不断地啄取从脖子上的肌肉中分泌出来的一种灰色色素,涂抹到头部、颈部、上背和两翅等的羽毛上,让自己雪白的羽毛最大可能地变成灰黑色。这使得它们不再那么美丽,然而,这却是朱鹮为人父母最甘心的付出。只有这样,它们才会避免被敌人发现。
慈爱

朱鹮不仅是恩爱夫妻,还是慈爱的父母。在决定生孩子之前,朱鹮夫妻(它们相当有“夫妻相”——同形同色,令人难以分辨)会离开集体,在高大的树上用树枝、草、木棍搭成一个简陋却温馨的家,平平的,中间稍微下凹,有点像一个超大的平底盘子,然后,新升级的朱鹮太太一次生下了几个淡青色的蛋,至于是2个、3个,抑或4个,就看老天的安排了。
朱鹮夫妇轮流趴在卵上,终于,漫长的一个月过去了,孩子们出世了。这些小家伙光着身子,只有很少的糟毛,也不会自己找食物吃,只会张着嘴巴:“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
朱鹮夫妇最忙碌的时候到了,它们要加油干活了!比如,把捉到的食物吞进食道的夹袋里,制成半流食,带回来喂给孩子;再比如孩子稍微大了些后,还要亲自教它们觅食、避开天敌……直到孩子长到3岁,能够成家立业了,老两口才能暂时松口气。

清洁
朱鹮还是一种酷爱干净的鸟儿,和那些吃腐肉的同类相比,它们可以说是有“洁癖”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它们爱吃活食,而且只在没有施过化肥、喷过农药的稻田或清洁的溪流里寻找食物。那些受到污染的地方,根本不在它们的“就餐区”范围内。
几十年前,人类发明了农药,并开始广泛使用,这很可能就是朱鹮们急速减少,以至于濒临灭绝的真正原因。要知道,在历史上,西伯利亚、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东、北部的很多省份都有朱鹮分布的记录。据说,那时候它们的数量堪比麻雀,这样的场景多么令人向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