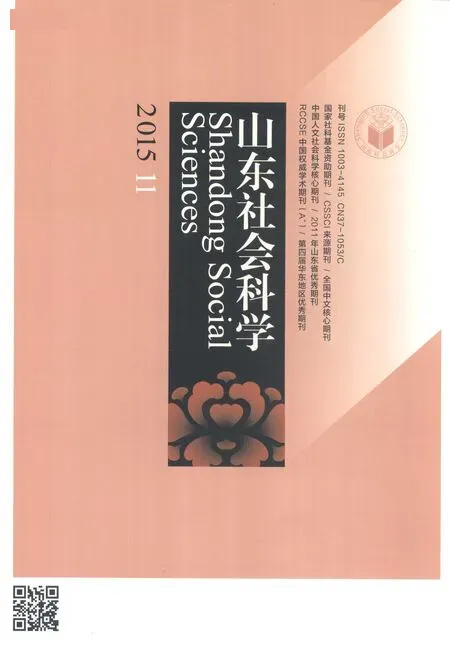乡土意识的艺术呈现
——刘玉栋作品研究
韩德信 韩存远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山东 淄博255049;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 5 0 1 0 0)
乡土意识的艺术呈现
——刘玉栋作品研究
韩德信 韩存远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山东 淄博255049;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 5 0 1 0 0)
乡土意识是产生于农业文明、发酵于工业文明之下的一种文化形式和思维方式。它以感性形式出现,更多体现为人们的一种理性且恒定的认识起点与判断标准。乡土意识是乡土文学的内在灵魂,乡土文学是乡土意识的艺术呈现。刘玉栋的乡土文学以其故乡“齐周雾村”为背景,集中关注了传统文化之精神性内核,包括家庭观念、亲情、责任感、尊老爱幼、和睦乡里等要素在内的一系列传统伦理规范皆在其书写范围之内。他强化了对传统与现代的比较、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以较为全面的视角俯瞰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有的放矢地对其中一些社会现象予以无声的批判,并理性地表达了传统文化在当下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而避免了过分偏激的情感倾向。可以说,他的乡土文学作品在沿袭了沈从文等人的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良、有所超越、有所开拓。
乡土意识;乡土文学;刘玉栋作品
一、乡土意识概述
乡土意识是立足于特定地域、产生于农业社会、发酵于工业文明之下的一种文化形式和思维方式。它是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文化思考的起点。具体而论,乡土意识包括内外两个层面的内容。外在层面包括特定地域中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等,它更多以感性形式出现。内在层面包括文化的认同感与精神的归属感,它更多体现为人们的一种理性且恒定的认识起点与判断标准。内在层面的内容往往要借助于外在层面的内容表现出来。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和思维方式,乡土意识往往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存在。当代作家柯灵为纪念《香港文学》创刊七周年创作了散文《乡土情结》,其中的一段可感性表达出乡土观念与乡土意识的内涵:“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辽阔的空间,悠邈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中情味,离故土越远,体会越深。科学进步使天涯比邻,东西文化的融会交流使心灵相通,地球会变得越来越小。但乡土之恋不会因此而消失。”禹建湘在其博士论文提到:乡土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名词,而是“一个区域里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历史变迁、宗教信仰和其他特质的混合体和聚合体”①禹建湘:《现代性症候的乡土想象》,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45页。。南帆也同样讲道:“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至少在文学史上,乡村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②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在这个文化空间当中,乡土作家“以自己的乡村经验积存为依托,以民间风土为灵地,在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浪漫绘制中,构筑抵御现代工业文明进击的梦中桃源”③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如沈从文、废名等人将乡土世界中的自然形态、日常生活等他们熟知的一切都作为赞美的对象,从而将乡土这一物理空间转化为弥漫于物理空间之中的文化空间。总之,每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这就是他的地理与精神“故乡”。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关中、贾平凹的陕南、王安忆的上海。这些作家们的创作虽然立足于特定地域,但又超越特定地域,最终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符号。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古国。农业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并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文明体系,其中包括遵守四季变化而组织农业生产的轮回观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由对土地的热爱而产生的对家乡、故土的依恋情结,由农业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家族观念与道德信条,由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而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以及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稳固的家族观念与松散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特定地域性相联而形成的对宗法制度的遵守与人伦血缘关系的维护,由农业生产方式而形成的对长幼有序与等级观念的坚守。钱穆特别推崇乡村文明中的艺术人生与宁静专一的世俗生活,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首先建立于农业基础之上,这决定了这种文化形式既有自然性同时又有生命性。由此,他进一步提出农业人生与艺术人生的问题:“农业人生,本极辛劳勤苦。但中国人能加之以艺术化,使其可久可大,可以乐此不疲。又自艺术转入文学。如读范成大之四时田园杂兴,赵孟頫之题耕织图,欧阳修之渔家傲词,亦各十二月分咏。随时随事,无不可乐,人生可以入诗入画者,复又可求。”①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就内在人生而言,都市不如农村,其心比较易于静定专一。……人生能有艺术,便可安放停止,而自得一种乐趣。惟有农村人生,乃可轻易转入此种艺术人生。因其是艺术,便可是道义的,而且有当于人生之正。专利工商业人生,则是一种功利的,必待计较与竞争,把自己的胜利放在别人的失败上,人生大目标不应如此。昧失了农村人生,则终亦不能了解中国人的那一套文化传统与人生理想之所在。”②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30页。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讲,乡土意识往往以集体或个体的记忆影响其文学创作。乡土意识是乡土文学的内在灵魂,乡土文学是乡土意识的艺术呈现。对于乡土文学来讲,乡土意识中的“乡土”决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它在特定地理概念基础之上转化为一种文化概念。
刘玉栋的乡土文学,为读者展示了自己家乡“齐周雾村”的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在现代与传统对比的基础上,以较为中立的立场,以未来发展为基点,在与城市生活对比中,既看到家乡落后的现实,同时也注意到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在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这是他的乡土文学创作不同于20世纪有些乡土作家的地方(有些乡土作家要么单纯地批判,要么简单地赞美,而未能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俯视乡村的现实,并以理性的态度表达对这种现实的反思)。
二、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乡土意识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男女间的经验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的最小单位。有人对家作出了文学式的描绘:家是什么?家是心灵的归宿,家是梦想的乐园,家是驻泊的港湾。当你脆弱的心灵受到伤害,家是抚平伤口的良药;当你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家是重获力量的源泉;当你独自在外经历风霜雨打,家是你温馨的避风港。有人从社会学角度对家庭作出说明:家庭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的重要生产单位,也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单位。为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家庭的维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农业社会为家庭制定了许多伦理观念。比如尊老爱幼、长尊有序、夫妻和睦、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兄友弟恭等。然而,这些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却受到极大冲击。比如在强调人人平等的法制观念下,尊老爱幼与亲情观念受到挑战;在关注个体独立地位的当下,家庭这一最小单位的稳定出现裂痕,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等纷纷出现;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下,妇女冲出家庭走向社会,但由于夫妻双方调适方面的差异而使夫妻关系出现危机。这些家庭观念及形式的变迁,决不能简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予以辩解。同样,上述现象的出现也不能构成对现代化的否定。因为传统文化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惰性的,而社会发展是快速的,特别是经济发展。为此,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总是会暂时出现社会发展与先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这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不合理现象,它们的出现也只是暂时的。当然,传统文化中那些符合人性的观念必将随社会的发展而保持其稳定的形态。有些特定的传统文化则由于其历史性与地域性的限制,而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文化中本来有其亘古不衰的东西,这是文化中得以延续的传统。这除了一些可直观的人文艺术形式、风俗习惯之外,还包括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伦理准则,如孝悌仁爱,不偷盗,不淫乱等。但文化中也存在一些与社会进步不相符的传统,这是现代性需要与之割断的”①陈嘉明:《“现代性”与“现代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刘玉栋在其文学创作中,也特别注重家庭的变化,在他看来,家庭是传统文化中伦理观念的重要传承者。关注家庭也就是关注传统文化,关注家庭的变化也就是关注社会的变迁。正如在《家庭成员》一书的卷首语中,刘玉栋引用马兵的话所讲:“从小处着眼,从家庭着眼,在家庭成员命运的变迁中来辐射醇正温静的传统氛围正在消逝的现实……”于是,家庭成为刘玉栋创作的重要观察点与表现对象。他通过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细微变化,来以小观大,揭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冲击下的变迁。在观察与描写中,浸透着刘玉栋对过去家庭生活的美好回忆、对现在家庭之变的惋惜,以及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在《风中芦苇》中,父亲二九年轻时创业小有成就,却由于私欲膨胀,放弃了对家庭应承担的责任,抛弃与之患难的妻子另求新欢,妻子悲痛欲绝,上吊身亡,女儿小樱由此记恨父亲,远走他乡发誓与之永不相见。即便在5年后,小樱回乡祭拜母亲时,也不想让人们看到:“我不想进镇子。不走柏油路,就是为了不穿过河口镇。我不想碰到认识我的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回来。……当时离开这里时,我发过誓,将永远不再踏上这片土地。仅仅过了五年,我又回到这里。你可以说我没有出息。……在白水城,在没有星星的夜空下,我像个孤魂似的飘来飘去。”但当她听说自己父亲因病将走到生命尽头时,她内心残留的亲情战胜了对父亲的恨,毅然回到父亲身边行儿女之孝:“三轮车停在我们家老宅子门口时,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的急切。我跳下车,几步来到门口。本门虚掩着,我一推,就开了。眼前的景象,让我一下子愣在那里。我看到瘦瘦的小男孩一双墨黑的惶惑的眼睛。我看到父亲坐在躺椅上,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头皮红生生的,就像一团刚洒上水的肥猪肉。他瞪着眼,朝这边瞅着,可一对眼睛空洞无神,两个眼珠就像磨损的玻璃球似的,没有一丝光泽。……父亲果真成为了瞎子。身上穿着的灰色棉袄脏得不成样子。整个院子都是这样,破败、颓废,千疮百孔,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腐臭气。我知道,这个家遇到了大麻烦。想起当年盛气凌人的父亲,面前的这个男人让我感到陌生。但我还是走到他面前,蹲下来,一攥他的手,我就哭了。让我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个男人,哭得更加悲切,涕泪横流,无法控制。”文中作家用了“急切”、“跳”、“几步”等词语,表达了小樱急切想见到父亲的心情,然后又用了“破败、颓废,千疮百孔”等词语表达小樱记忆中家的败落,特别是最后父亲与女儿手握手时的描写,父亲全没了昔日的威严,“哭得更加悲切,涕泪横流,无法控制”。这种人物情感与周围环境的描写,很自然地表达了由恨到爱的转换。于是,亲情战胜了仇恨,宽容战胜了冷漠。这让读者深深感到了家庭的重要性。它可以是贫穷的,可以是对人产生过伤害的,可以是多年未归的,但它却一直深深隐藏在人们心中,让人难以割舍。女儿的到来,让这个败落的家庭又充满了生机,这使深知自己已病入膏肓的父亲,内心充满了安慰。他向女儿忏悔了自己所犯下的人生错误后,毫无遗憾地走向自己的生命尽头:“夜色渐渐深了。睡在我身旁的阳阳竟说了两句梦话。我仔细听着对面小樱的屋里,已经半天没有动静。我悄悄爬起来,穿好棉衣,慢慢地拨开门栓,来到院里。尽管我什么都看不见,但家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轻车熟路。我来到门口,一把便抓住妹子根白天准备好的绳子。放心,我不会上吊的。我害怕吓着孩子们。绳子不长,两端我各拴了一块砖。我掂了掂,还挺沉。我慢慢打开大门,出来后,又轻轻地关上。我站在家门口,长吐了一口气,露气很重,可我觉得特别舒服。我把绳子挂在脖子上,一手托着一块砖,颇有些悲壮地朝村北走去。下午我问过阳阳。阳阳说北大湾里的水好多呢……村路熟在我的肚子里,我走得慢,但脚下稳。”尽管文中语言平实,没有感情的抒发,但读来后却让人内心难以平静。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悔意的父亲对孩子们的爱、对亲情的依恋。为了不再给孩子增添麻烦,他内心已无牵挂时主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读后人们在唏嘘不已的同时会更加珍惜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二九由婚外情而致家庭破裂、妻子身亡、女儿远走他乡的错误做法,刘玉栋并没有进行道德批判,甚至连谴责的话都没有,但这并不代表刘玉栋无视这种道德现象或包容这种现象。相反,作者从其坚守的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对二九的这种做法是谴责的。他只是用亲情,特别是二九面对女儿时无法控制的哭泣,以及女儿的原谅,代替单纯的指责与批判。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处理,更能实现艺术效果,这也是刘玉栋乡土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感、担当意识,在《丫头》一文中也得以艺术地表现。丫头是一个男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丫头特别厌倦给自己起“丫头”这名字的父亲:“他连个名字都不会起,叫什么不好,人家一个男的,非给人家起个名字叫丫头。天底下那么多名字,叫什么不好。弄得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人家的笑靶子”。他很烦别人再叫他丫头,甚至不惜向深爱的母亲发火,证明自己是男人。“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儿,我猛地摆脱母亲的双手,喊道:‘我不叫丫头,我是男的,你们为什么整天丫头丫头地喊我。”为了证明自己是男子汉,他再不愿意跟着隔壁的春梅婶子学织网了:“我的个头这么高了,还整天跟一个女的在一块儿织网,干些女人干的活。我想我该去卖虾酱,该去卖虾酱,卖虾酱了……”“丫头”的心路历程,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成员特别是男人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尽管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多强调男女平等,但由于生理的不同,男人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更强一些。这是一个性别分工问题、一个文化观念问题。丫头在与台阶叔卖虾酱的日子里,以一个孩子的身体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在这个过程中,丫头的身子骨也硬棒起来,心理上也成熟起来了。他对家庭生活重担的承当,让母亲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眨眼年就到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下午,我和母亲坐在床头上数钱,毛票票钢蹦子,花花绿绿地摆成一片,乐得母亲眯缝着眼,一边往手指头吐着唾沫,一边念念叨叨地记着数目。点了好几遍,最后把数目定在六百六十八块七毛五。”丫头在和母亲赶集置办年货时,不仅想着给母亲买件新衣服,而且也给家里的小二小三各买了过年礼物。另外,与台阶叔的一次对话,也改变了丫头对父亲的看法,让他感受到父亲的存在、父爱的伟大。台阶叔说:“丫头,你这名字好啊,你小时候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地生病,你爹怕是阎王爷喜欢你这胖小子,给抱了去,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你还别不信,自从你叫了丫头,你那身体立刻就变好了。要不是你叫这个名字,等我有了儿子,我就让他叫丫头了。”其实在农村,为了孩子健康,给男孩子起个女孩子名字或一种动物的名字是一种较普遍的文化现象。这一方面反映出农业社会家中男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反映出父母对孩子那份难以言表的关爱,决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文化现象与封建迷信等同。起什么名字看似是生活小事,但刘玉栋却不厌其烦地描写。原因就在于生活如流水,在涓涓细流中最能体现出家庭的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与亲情。家庭生活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丽,更没有赴汤蹈火的悲壮,但它却是社会的基础。它不仅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发展,而且也维护着当下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刘玉栋的乡土文学对家庭的描写应该是他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看似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重大社会问题的艺术关注,但却能以小见大。透过家庭结构的变动、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密与松驰,艺术地反映出社会大环境的变迁、社会观念的变化。这反映了刘玉栋创作中独特的艺术视角与浓浓的人文情怀。“刘玉栋在他的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乡村生命对于土地的依恋与热爱,渲染了依附在这种土地上的纯朴情感、人性和温暖。……他不回避乡土世界内的丑恶、苦难和灾难的描写……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苦难和罪恶,不是为了简单地批判,而是为了在冷酷中展现和寻找温暖的力量、人性的光芒。”①吴义勤:《“道德化”的乡土世界——刘玉栋小说论》,《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三、现代文化视野下的乡土意识
时间如同一块过滤布,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将美好的东西保留下来,从而将过去与现代沟通起来。即便是当时令人难过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为一种前进的动力。在刘玉栋眼里,家乡就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是自己精神的归属之地。正如作者所讲:“我的童年是在鲁北平原的农村度过的。那个叫齐周雾的村庄是山东省最北边的一个村庄,就在漳卫新河的河堤下面,漳卫新河是山东省和河北省的分界线,漳卫新河被树林覆盖着的高高的河堤是童年记忆中最美的风景之一。离村子正东二十里,有一座山,在无棣县境内,叫大山,现在叫碣石山,来自于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再往东不远,就是渤海了,其实这是一座小山,只有六十米高,但它是大平原上惟一的一座山,在乡亲眼中,是一座大山。小时候,我们站在野地里、屋顶上,看山很清晰,伙伴们闹着玩儿时,也是互相拽着耳朵喊:‘看,看,看大山,越看越近……’这座山让孩子们产生无边的遐想。后来走的地方多了,发现我的家乡实在算不上美,盐碱地多,用贫瘠来形容也不为过。但就是这片土地,让我魂牵梦萦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有时候做梦还要梦到这个地方。仔细想一想,主要还是因为这片土地留给了我太多的爱,太多的快乐和梦想,当然,还有伤痛。”②张丽军:《刘玉栋:年日如草,在现实纵深处潜行——七○后作家访谈录之一》,《芳草·文学杂志》2012年第3期。对家乡的童年记忆,构成了刘玉栋对当下社会现象的批判力量。过去的美好记忆,成为他审视现在、关注当下的标尺,家乡环境被破坏、遭污染的现象,深深刺痛了刘玉栋。他将文学对现实说“不”的权利转化为一种批判力量,阻止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小说《风中芦苇》中,主人公小樱回到其家乡时看到的景象,反映了刘玉栋对故乡环境变化的深深忧虑,同时也反映出作家对现代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的思考,比如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置环境于不顾的客观现实。同时,作品也反映出当前一些地区领导干部在偏面追求GDP过程中引起的干群矛盾。文中描写道:“我摇下窗子,清冷的风像一盆冷水似的浇在我脸上。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风里夹杂着一股怪味儿,直冲鼻子,难闻得要吐。我忙把窗子摇上。‘什么味儿?这么难闻。’司机笑了,看来他已是见怪不怪,‘造纸厂、化肥厂、炼钢厂、农药厂,多着呢,你还能都把它们停掉。工人吃饭是小事,当官的捞不到油水才是大事呢。’”客观环境的变化,也影响到作品主人公的内心情绪,本应充满温情的故乡如今在主人公眼中却变成了一片破败的景象。“尽管已近正午,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那座上世纪六十年代修的水泥桥已破烂得惨不忍睹,如同是几块水泥板拼成的一样,两边的水泥栏杆就像八十岁老人的牙齿,模样让人恐惧。河的两岸,是一些枯黄的野芦苇,稀稀拉拉的,淡灰色的天空下,风吹过芦苇,特别荒凉。”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生活经验与思想概念的物化形式。在《风中芦苇》中,作家对环境几近白描式的书写,反映出刘玉栋本人以及生活在那一片环境中人们的共同感受。作家为民众代言,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民众生存而奔走呼号,这是新时期以来作家所必须具有的品格。当然,刘玉栋还一直保持着冷静描写的做法,他将自己的愤怒深藏起来,在平淡之中表达出理性的力量;在理性思考之后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保护环境的行动。
刘玉栋在其乡土文学创作中,以其故乡“齐周雾村”为背景,以乡土意识为基点,艺术地表现出他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特别是在现代文明下传统文化如何生存的问题,成为刘玉栋文学创作中着力表现的对象。刘玉栋初入文坛时作品多是以城市为题材,比如《后来》、《淹没》、《蛇》、《向北》、《黢黑锃亮》、《八九点钟的太阳》等,这些作品大都表现主人公对城市生活的困惑与青春的迷惘。然而如何继续创作、朝什么方向走,成为刘玉栋一度苦恼的问题。刘玉栋在回顾自己创作时写道:“1998年冬天,我心里特别迷茫和困惑,我对自己的创作非常不满意,我觉得我的小说缺少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我分析自己,发现我的创作并没有全部发自内心,也说是说,我的情感还没有真正回到内心,它一直游离在生命情态之外。我决定,写离自己内心最近的东西。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童年和故乡,没想到,一下子便激活了我的经验”①刘玉栋:《创作自述》,载刘玉栋:《公鸡的寓言》,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1999年后,我之所以把目光又拉回到农村,首先是个人情感的需要。我从小在农村长大,17岁才离开故乡,但总觉得没有真正离开,我十分想念那段日子,想念那里的花草树木、土地河流,想念那里的乡邻和伙伴,尽管过去十几年,我却始终没有忘掉那段生活”②刘玉栋:《创作自述》,载刘玉栋:《公鸡的寓言》,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刘玉栋开始真正审视这片古老的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的风土人情与伦理风尚。这段乡村生活经历构成刘玉栋乡土意识的重要内容,这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精神之源。他不仅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贫穷与落后,更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价值。多年居住于城市,灵魂却一直飘着的刘玉栋,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归宿。20世纪初的乡土文学大多偏重于批判乡村的愚昧与落后,但也有像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这样的作品,他们多描写乡村民风的古朴淳厚、人们生活的缓慢恬静。刘玉栋延续了沈从文等人的创作传统,但又有所超越。这种超越源于他对传统与现代的比较、城市与乡村的对比,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理性地表达了传统文化在当下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非一味地赞颂或批判。换言之,刘玉栋的乡土意识更多关注传统文化的精神性内涵,包括家庭观念、亲情、责任感、尊老爱幼、和睦乡里等。刘玉栋依据这些传统观念,在全面审视现代社会风气时,对其中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无声的批判,这展示了山东新生代作家继承“文学鲁军”的文学传统,坚持道德感、使命感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责任编辑:陆晓芳)
I206.7
A
1003-4145[2015]11-0053-05
2015-06-07
韩德信,山东淄博人,文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韩存远,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研究”(项目编号:12BZW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