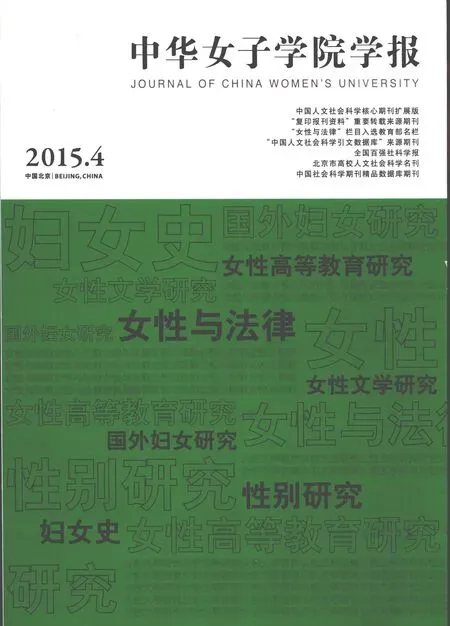“以性易物”与时代的光影——解读“新生代”女作家小说的一个视角
“以性易物”与时代的光影
——解读“新生代”女作家小说的一个视角
李晓丽
“新生代”女作家格外关注当代社会中女性与物质的关系,尤其是女性“以性易物”的复杂形态。她们要么专注于探究女性以身体向物质投诚过程中复杂的心理过程,要么审慎设问女性“以性易物”映射出的道德变动。虽然这些思考尚有深度开掘的空间,但它们对当代社会走向物质化过程中的性别思考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新生代”女作家;以性易物;性别思考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逐步发生全面的变化。中国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走向消费社会、物质化社会的影响。在这宏观文化语境中,物质观念与金钱观念成为这一时代最突出的主流话语。正如西方消费文化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对消费文化的普遍接受,大力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不由自主地投入到物质的消费与生产中,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因为‘受到物的包围’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官能性的人’”。[1]当物质生存与欲望复苏成为当代社会最突出的一个文化特征时,人与物质的关系越来越凸显出来,当代作家在书写当代社会生活时,自然也会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表现与思考。对物质社会和消费文化的表达,性别差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中国“新生代”作家①“新生代”作家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品侧重于反映当下生活的作家的统称,具体范围没有明确的所指,大体包括下列作家:韩东、朱文、毕飞宇、邱华栋、鲁羊、丁天、刁斗、鬼子、东西、李洱、李大卫、荆歌、述平、张旻、刘继明、吴晨骏、艾伟、陈染、林白、徐坤、卫慧、棉棉、海男、戴来、朱文颖、魏微、金仁顺、盛可以等人。的写作当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表现。邱华栋、朱文、刁斗、东西、韩东、何顿等男性作家关注现代都市生活,但从他们创作所呈现的性别场景来看,“新生代”男作家常常把女性写成高度物质化的动物。他们的代表作家邱华栋曾经这样说:“女人的物质性是天生的,很少有女人具有真正的精神指向。”[2]因此,邱华栋把以身体换取物质的女性称为“新美人”,这些“新美人”往往会因为渴望得到男性能给自己带来的丰厚金钱和物质,而义无反顾地投入成功男士的怀抱,这成为他小说的典型模式。“新美人”们性感、妖娆、贪婪,她们只追逐金钱和物质,是现代城市“物欲”的化身,她们不像小说中男性人物那样具有丰富的心灵内容。邱华栋小说中的“新美人”是以符号化的方式存在的,她们被剥夺了应有的话语权,没有呈现出具有个性特征的思想内涵。她们在这些小说中只具有功能性意义,作家仅仅用她们展示现代女性用身体来交换物质,也就是“以性易物”的时代特征。与这些男性作家不同的是,“新生代”女作家则以丰富、细腻的性别思考致力于从不同侧面展示女性以青春和身体做物质交换这一过程,写出丰富、细腻的感受与理解。将这种“以性易物”现象作为一个母题进行多向开掘,既呈现对当代社会物质走向的理性思考,也涉及其中丰富的人性内涵。
一、向“物”投诚的时代困境
“新生代”女作家注意到女性“以性易物”现象在当代社会中更加频发,甚至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要取得合理性的趋势。比如,《奥菲斯小女子》女主人公阿咪“傍大款”,她表面上做公司老板的女秘书,暗地里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交换舒适的物质生活,这是当代文学中典型的被“物化”的女秘书形象;《野草根》的夏小禾优秀聪慧,但为得到更有前途的发展,她不得不选择做集团老总的情人;《惜红衣》的年轻女性董葡萄也同样深谙此道,她使自己的青春资本发挥更大的利益,脚踏两只船,同时从两个男人那里为自己谋取物质利益;《请呼3338》寻呼台小姐于玲为了一份悠闲舒适的工作,也自然而然地选择投入“多金”男士朱先生的怀抱。不过,总体而言,“新生代”女作家对当代女性“以性易物”的探寻并未停留在对这一现象的简单表现上,她们以自觉与不自觉的性别意识关照这一现象,在写作中借助对“以性易物”更加精微细致的刻画,重点展示现代社会人向物质“投诚”的过程中复杂的心理演变过程,这一展示也就具有了对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留下心灵史料的意义和价值。
魏微擅长从世态人心的角度来记录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动,她的小说以“以性易物”为镜,巧妙地折射出当代社会人们物质追求与伦理退让博弈的过程。短篇小说《大老郑的女人》展示“以性易物”的故事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密集登场,以及这一登场对人们带来的精神震动,这体现了传统伦理观念与对金钱合理化追求的对抗逐渐减弱。《大老郑的女人》可贵地呈现出传统伦理道德如何进行变通和妥协。
这是一组在社会转型期,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与“以性易物”现象进行伦理较量的故事,小说设计了三个不同角度的“以性易物”事件来展示传统伦理观念退让的无奈。一个故事写小城中突然出现了新鲜事物——“广州发廊”的姐妹。“发廊妹”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具有隐晦含义的称谓,她们不仅仅给女人们带来新潮的发型,也通过晚上做男人的生意来赚取更多的金钱。即便如此,在小城居民眼中,她们依然是美丽的,是小城走入“现代”的先行者。重要的是,初期发廊女卖春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表面上并没有对小城已有的家庭秩序形成威胁。因此,“发廊妹”因其具有时尚代言人的特殊身份,受到了小城居民宽容的接纳。
第二个“以性易物”的故事并无太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在小说的语义系统中也起到反映时代观念变革的作用。小城本土居民冯奶奶的丈夫多年前抛下妻子和一双儿女去了台湾。丈夫走后冯奶奶没有经济能力,于是用身体来养活自己和孩子,她这样的生存方式在小城里众所皆知。冯奶奶这种“以性易物”的方式因抚养儿女而带来了一丝悲壮的色彩,同时也博得了小城居民的谅解。冯奶奶被谅解的原因并非源于人们对其生存方式的认同,而是在于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一个母亲的伦理职责,顺利地养大了儿女。这一故事说明,时代的变化已经使得原本坚固的传统伦理观念出现一定程度的裂痕,这一裂痕正是中国社会从稳定的乡土社会进入城市化过程中付出的伦理代价。
这一组“以性易物”故事中,最引人深思的是大老郑的女人的故事。大老郑是商品经济初期较早四处闯荡的外来户,他在小城中经营小本生意,后来成为小城居民“我”家的房客。与传统的中国生意人一样,大老郑人品朴实、性情敦厚,与房东“我”一家相处融洽,由此受到房东一家的尊重。大老郑闯荡漂泊的生活使他不能将妻子儿女带在身边,为了解决生理需要,也为了生活的便利,大老郑找到一个看似本分的当地女人一起生活。而大老郑的房东算是讲究体面的人家,房东之所以接受大老郑把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带回来共同生活,也展示出小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受到的渐变式冲击。大老郑是个尽职称职的兄长,他在小城的生意做得本分妥帖,这为人们对他的宽容提供了一个基础。而且,这来路不明的女人对自己尴尬的身份也有自知之明,对房东谦恭有理,精心料理大老郑兄弟们的生活,让常年漂泊在外的几个单身汉过上了像样的家庭生活。这女人被接纳也因其自述命运“凄苦”,她说自己不仅被丈夫无情抛弃,还要含辛茹苦地养活孩子,从道义上讲,她也是值得小城居民同情的弱者。细心审视,我们不难发现,这几个原因都是属于家庭伦常范畴的,这一事件没有太直接、太尖锐地向传统家庭观念进行宣战和对抗,所以小城居民才有可能勉强接纳其存在。
可见,这一组故事中,小城居民以是否维护传统家庭伦理秩序作为前提,来衡量是否应当宽容女人“以性易物”的做法。当其对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颠覆没那么直接时则有可能被接纳;当其对传统家庭伦理秩序构成直接威胁和破坏时,还是会受到抵制和厌恶的。这表明,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早期,女性以身体交换金钱和物质这种方式,还是不容易被传统观念浓郁的小城居民接受的。因此,当大老郑“女人”的乡下丈夫进城来寻找妻子时,无意间将妻子编造的凄惨谎言揭穿,这女人与大老郑兄弟们就都被房东毫不客气地驱逐了出去。
魏微的《情感一种》也是对传统伦理观念无奈地让位于现代人追逐物质生存这一现象的思考。女性“以性易物”已经更大程度地被现代人所接受,甚至普遍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性别交易。与男性作家视点不同的是,魏微试图通过女主人公栀子的选择,来思考当代女性以身体资本向“物”投诚时,呈现出来的复杂的性别意识。栀子是一个女研究生,在毕业前她经人介绍,结识了一家报社的副总潘先生,为了能够顺利地留在上海工作,栀子拿青春作为交换,成为潘先生的秘密情人。按照“以性易物”故事模式的通常写法,栀子在这一交易过程中,理当获得相应的利益,但故事没有遵循这一模式。小说重点演绎了栀子在这一交易过程中,内心展开的物欲与性别自尊的搏斗。
小说中潘先生和栀子的师兄都认可女性“以性易物”的用青春交换物质和利益的原则,并且将其当作这个时代的一种新的生活准则,因而栀子并未直接提起,潘先生已经主动为栀子安排工作。但是,栀子在这个看似“公平”的法则面前却是犹疑的,在这场“交易”中,栀子越来越后悔没有让男人知道自己是个有思想的女孩子,这点小小的痛在她的女性自尊中逐渐被放大,她最终拒绝了潘先生安排的工作。小说细腻地引出这样的思考:在女性“以性易物”的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性有可能被物质追逐所淹没,也有可能像栀子这样用内在的精神力量唤醒女性主体性的追求。小说从女性与物质关系的角度展示女性精神成长的历史,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二、“去道德化”的新物质观念
随着中国社会物质追求合理性的逐步确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传统物质观念中的一些偏颇和缺失。比如,重精神而轻物质的传统是否适应时代的发展?人们是否一面肯定物质追求的合理性,一面坚守“君子固穷”的观念?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一定是不可调和甚至对立的吗?“新生代”作家的一系列创作面对这些质问,颠覆和反思固守贫穷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一种“去道德化”的新物质观念,来表达对“以性易物”的现象进入当代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新生代”男作家们振臂高呼,喊出“我爱美元”的口号,揭开对“去道德化”物质追求的书写。这一时刻标志着清高的传统物质观念在这一时代瞬间崩塌。作家们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开始大书特书金钱与物质追求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强劲动力,由此也展开当代生活中,物质和金钱满足带来的精神空虚与情感缺位。不过,一部分作家表达的急切也容易将这一话题简单化、概念化和模式化。“新生代”部分女作家则以独特细腻的性别感受和体验融入这一思考,对当代物质新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生动的演绎。
朱文颖的长篇小说《高跟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首先大胆地质疑千百年来固化的传统物质观念,将时代变迁与物质观念的走向结合起来进行审视,展示当代社会物质追逐给人们物质观带来的困惑:“将是90年代的中后期,真正的世纪之末,一些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比如说:物质与精神;也有一些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清楚,比如说:究竟要走多久,物质才能抵达精神的边缘,或者换句话讲,精神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得到它赖以生存的基础。”
小说以两个女性,安弟和王小蕊的物质追求来呈现当代物质观念发生的变化。这两个同样认可物质追求合理性的女孩子,在构建自己物质观念的过程中,首先对传统物质观念提出质疑和反思:“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可见,她们朴素地肯定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对个体人成长的正面意义与价值。这也表明,在她们眼中,物质与精神已经不再是紧张对立的关系,对物质的追求已坦然成为新一代人明确的人生目标。
不过,同样是接受“去道德化”的物质观念,两个女孩的接受和理解却具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区别也决定了她们命运的不同发展。王小蕊对物质的理解是简单直接的,她那廉价而醒目的“高跟鞋”具有明确的物质指向性,暗示着王小蕊并不在意物质获取的方式与过程,因而她采用“以性易物”的直接方式来实现物质追求。她后来选择做房地产商人的情妇,以身体资本轻松换取此前可望而不可即的物质生活。在这一过程中,王小蕊主动将自己“物化”,精神诉求被她排除在人生追求之外。但这种依靠青春资本换取物质生活的方式毕竟不具有持久性,精神人格的缺失最终导致王小蕊遍体鳞伤,她最终不得不选择远赴异国他乡重新寻找精神的救赎。
这篇小说更具有价值的是,它通过安弟这一人物,来思考当代新物质观念对传统道德的改写。“物质,在王小蕊是一种终结。在于安弟,则是个过程,一架阶梯。她希望通过它,到达一个她自己都还无法描述清晰的所在。”与王小蕊的“物质至上”相比,安弟的物质追求并不排斥对精神内涵的追求。她与珠宝店老板王建军的爱情,物质因素只是一个必要方面,王建军吸引安弟的是从物质追求中投射出来的精神品味。当王建军将安弟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商业伙伴,精神因素在他们的爱情中被瓦解,安弟也因此义无反顾地抽身离去。安弟自己注重物质过程中的精神内涵,也通过其身边其他人的故事反思物质丰富与精神缺失的生活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心理失衡。她遇到的大卫就是从追求精神走向追求物质,再从物质富足走向精神崩溃的例子。这似乎都在提醒人们,当代“去道德化”的物质追求,并不仅仅呈现为对传统物质道德化的反驳,也在重新思考物质追求中平衡物质与道德的关系的必要性,物质与精神追求双赢的模式可能是更佳的人生途径。
时代在不断地转换,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这其中女性“以性易物”的生存方式,正逐渐被日常化、生活化,社会对这一方式的评价判断也都从道德制高点上后撤下来。“新生代”女作家们以此为起点,思考当代生活中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复杂性,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这体现出作家对当代物质观念理性审视所达到的力度:“看得出,朱文颖在日益强大的物质面前是隐忍而笃定的,或许,正是因着这种带着宽容的隐忍和笃定,使朱文颖在《高跟鞋》里获得了一种眼光,使之得以写出广阔的物质力量,并进一步发现这些物质的生长是如何一步步作用于现代人的精神的。她既不像一些高蹈而抽象的理想主义者那样,竭力地贬损物质,把它视为庸俗和罪恶的代名词加以批判,也不像那些紧跟潮流、向往奢华的现实主义者那样,不顾一切地把物质的力量神化,从而向物质社会的到来全面投诚。”[3]
三、关系置换与性别政治
女性“以性易物”的基本模式为:男性占有更多的金钱和权力,他们在渴望物质的女性面前具有明显的性别优势,女性要得到这些男性手中的金钱和权力,只能够用自身作为资本,与男性进行性交易。如果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反过来,女人拥有优势的金钱与权力,男性处于弱势,那么,这些多金的女性,会不会同样赢得男性趋之若鹜的“献身”以求呢?按照常理,这一现象必然存在。但是,男女进行关系置换之后,或者女性获得经济优势后,“以性易物”过程中女性是否必然会占据性别优势呢?“新生代”女作家对此也进行了一些独特的展示与反思。
徐坤的《杏林春暖》是一则男性“以性易物”的故事:俊俏小生民生年轻英俊,他利用自己的青春向富婆美惠换取奢华的物质生活。他之所以赢得了中年富婆美惠的芳心,在于他无意间导演了一场令美惠感动的壮举,即为了“取悦”美惠,他几乎以生命为代价做了包皮切除手术。由于想给美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民生选择去私人医院做手术,结果伤口感染,险些令他送命。但是这一事件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它与美惠所期待的爱情根本无关。民生的“牺牲”只不过是歪打正着被夸大。这一个看似与女性“以性易物”同构的故事,由于这一动因的偶然,反讽了女性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欺骗。可见,“以性易物”这一模式更倾向于男性占据主动并且获益,看似“公平”的性别法则中隐藏着微妙的性别政治。
现代物质生活常常刻画男性以物质财富的占有来树立其性别尊严。而女性接受“以性易物”的方式,前提是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且渴望以身体资本与男性掌握的物质和权力进行交换。那么,当女性摆脱了经济上的弱势,是否会“扳回一局”,在男性面前重新赢得人格与自尊呢?魏微的《化妆》讲述了女大学生试图用经济上的成功,来洗刷先前被误以为具有“以性易物”企图的感情历史。女大学生嘉丽大学实习时爱上实习单位的科长,虽然科长不大舍得为经济拮据的嘉丽花钱,但嘉丽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嘉丽始终为科长在临别前给她的钱感到痛彻的屈辱。后来,嘉丽努力打拼,成为经济上富裕的知名律师。而此时,久未联系的科长要求与她见面。嘉丽沉积心底多年的创痛再次被触动,她想以落魄的样子去验证一下科长当年对她是出于爱情还是以微薄的金钱来“购买”她的身体。她伪装成“下岗女工”前去赴约,却被科长当作暗娼,这昔日的情人居然理直气壮地在她身上当了一次“嫖客”。故事的结局表明,当女性向比自己更有经济优势的男人献身时,男人心里总是难以抹去女人具有“以性易物”企图的认识。这一认识会成为男性判断女性价值的一个重要凭证,如此的性别偏见给女性带来的精神伤害比贫穷更甚。《化妆》讲述的故事,将女主人公放置在试图通过经济“翻身”而重获性别尊严的语境之中,使得“以性易物”模式具有了人性深度的视角。不过遗憾的是,作家更专注强调这一情节的传奇色彩,却没有在宏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女主人公心灵创痛中具有的性别意味,这也体现出题材开掘的深度还十分有限。
四、结论
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强调精神追求高于物质追求的理念,因而还未有哪个时代像当今这样把个人选择完全暴露在“物质主义”的考验之中。当代社会如此开阔地迎来物质对人性的考验,也给作家表现当代生活带来良好的契机。有学者指出:“90年代都市文学书写呈现出一个逐渐失去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物质话语表现过程,而较多出现围绕生存意义上的物质欲望展开时代动荡心灵的思想和文化写作。”[4]这一表现势必会拓展中国文学物质书写的空间。男性作家对物质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关系进行探讨时,性别视角的思考并不充分。[5]部分“新生代”女作家多角度记录和书写了女性“以性易物”的现象,或探究女性以身体向物质“投诚”过程中复杂的心理过程,或探问女性“以性易物”映射出的道德变动过程,或从性别置换角度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考。但总体而言,“新生代”女作家对女性“以性易物”的考查,尚未深入到以此来构建物质时代精神面貌和人性变异的层面,她们对此类题材写作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拓展。
[1]张一兵.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邱华栋.女人是时尚的寄生虫[J].海燕,2004(,3).
[3]谢有顺,石非.物质生活及其幻觉——朱文颖和她的高跟鞋[J].当代作家评论,2001(,6).
[4]蓝爱国“.物质”的文学及理论的产生方式[J].文艺争鸣,2006(,4).
[5]蓝爱国.当代文学的物质源流及其书写历史[J].艺术广角,2001(,2).
责任编辑:杨 春
Body for Barter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Times: A Perspective of the“New Generation”of Female Writers’Novels
LI Xiaoli
The“newgeneration”of female writer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s and“material”, whose complex patterns they discuss in their novels.These novels express the complex psychologies and changes in ideas of morality when females gain“material”from their bodies.These expressions show the specific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life in gender perspective and might explore their novels toa greater extent.
The“NewGeneration”female writers;bodyfor barter;gender thinking
10.13277/j.cnki.jcwu.2015.04.012
2015-05-20
I206.7
A
1007-3698(2015)04-0076-05
李晓丽,女,中华女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100101
本文系中华女子学院校级课题“‘70’后女作家小说的日常生活的书写”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G2012-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