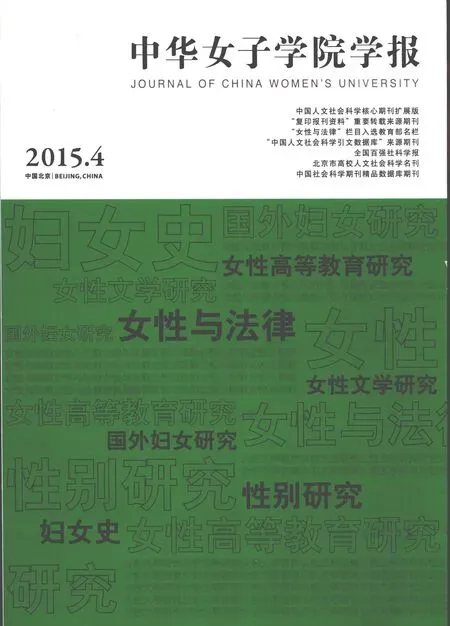施叔青家族小说的不可靠叙述与叙事伦理
施叔青家族小说的不可靠叙述与叙事伦理
王萌
施叔青在所创作的家族小说中,均使用了不可靠叙述策略,其不可靠性表现为多种方式,而且常常又与可靠性相互转换,显示出不可靠叙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独特的叙述效果,有助于作品叙事伦理的构建,使其呈现出丰富性和开放性的状态,给予读者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更多的可能性。关键词:施叔青;家族小说;不可靠叙述;叙事伦理
施叔青是当代华文文坛的重要作家,在她长达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家族小说虽然仅有《寂寞云园》《风前尘埃》和《三世人》三部,但却堪称巅峰之作。尤其是在叙事策略方面,这三部小说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不可靠叙述就是其中之一。不可靠叙述的界定标准最早是由韦恩·布斯提出。他认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叙述者为可信的,反之,为不可信的。[1]178此后,不可靠叙述一直是叙事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众多专家学者不乏独到见解和精深研究,其中,中国学者申丹把不可靠叙述由叙述者扩展到人物。她认为,“无论在第一人称还是在第三人称叙述中,人物的眼光均可导致叙述话语的不可靠。”[2]75这拓展了不可靠叙述的理论空间,更有利于全面深入的分析文本。虽然目前关于不可靠叙述的区分标准、主要类型以及文本表现等问题,学界仍争论不休,但是不可靠叙述策略作为一种现代小说常用的叙述技巧和普遍的叙事现象,通常会使作品具有更大的叙事张力,给予读者伦理取位更多的可能性,却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在施叔青三部家族小说的不可靠叙述策略中,叙述者和人物的不可靠性表现为多种方式,而且时常又与可靠性相互转换,显示了不可靠叙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小说伦理意蕴的展现和读者的伦理取位均起到重要作用,使作品叙事伦理呈现出丰富性和开放性的姿态。
一、家族·女性·不可靠叙述之可靠
在《寂寞云园》中,主要以黄家第四代黄蝶娘的视角,回顾了黄得云的后半生和黄家的家族史,并勾勒出香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到九七回归前夕的历史风云图景。作为家族故事的主要讲述者黄蝶娘,被文本的叙述者“我”描述为爱出风头、放浪形骸、张牙舞爪的叛逆贵族女性。与之对应的“我”,从字里行间可以明显看出是一个历史知识丰富、有着正常家庭、举止符合社会规范的中产阶级职业女性。那么,按照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来看,读者会认为“我”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而黄蝶娘是一个不可靠的讲述者。但是,实际上“我”同样也是不可靠的。作为第一人称同故事的回顾性叙述者,“我”是由“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相叠加而成的。在文本叙述开始的时候,“叙述自我”已经对整个故事了然于心,然而“叙述自我”并没有说出比“经验自我”更多的事情。在“经验自我”一点点地通过黄蝶娘挖掘黄家秘史的过程中,“叙述自我”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黄蝶娘虽然对家族史的讲述带有明显的好恶判断和个人推测,但与此同时,她在讲述自己的生活时,却极为坦率真诚,毫无遮掩和粉饰,并不讳言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率真的态度自然也就影响到了她不可靠叙述的部分,化解了读者的部分不信任和反感。而且,黄蝶娘对曾祖母黄得云的崇拜和赞誉,又与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相近。所以,具有不可靠性的黄蝶娘,在讲述的过程中就具有了某种意义的可靠性。如此一来,她对于曾祖母黄得云和祖母黎美秀截然相反的态度,势必会也影响到读者选择和接受的倾向性。
同样具有不可靠性的“我”,作为一个提问者、考证者和叙述者,不断地对黄蝶娘关于家族历史的某些猜测进行解释、补充和修正,将黄蝶娘的不可靠叙述部分尽力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或者推翻重新演绎,这就使得“我”身上所显示出的可靠性因素,更容易引起读者的信任和认同,而忽略其不可靠性。比如黄得云和西恩·修洛之间的故事,黄蝶娘认为二人纯粹是因为性的吸引,而“我”则认为二人产生了一种生死相依的真挚情感,将黄蝶娘所透露出的黄得云的生活片段连缀,推演而成为一段日久生情、患难与共、凄绝美艳的爱情故事。无疑,这种说法更符合大多数读者的伦理判断和阅读期待,也与隐含作者一贯的价值立场和道德观念相符。
文本中有两个未解的谜团:一是黄蝶娘生母朱融融悲惨下场的传闻,另一个是王福失踪事件,就是利用不可靠叙述中的可靠性,达到独特叙述效果的典型例证。在故事开篇不久,朱融融的传闻就通过黄蝶娘朋友之口说出,其后文本中又多次提到,然而黄蝶娘和“我”始终都没有明确指证黎美秀就是凶手,而是通过其他事件来揭露黎美秀的虚伪和冷酷,以暗示其对朱融融的悲惨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救灾事件,“我”用记者的第一手采访资料,拆解了黎美秀亲自救灾的谎言:黎美秀告诉记者,在香港有史以来最寒冷的冬天,九龙石硖尾发生大火,她率领教会的教友,抱出家中过期不赎的冬衣,去救济九龙石硖尾的灾民。但是据记者查证,香港有史以来最寒冷的冬天发生在1923年,而九龙石硖尾大火却是1953年,前后相差整整30年。史实的错误无疑是最有力的驳斥证据,由此黎美秀在读者的眼中,不可能再被给予丝毫的信任度,而她的不可靠性反过来又强化了黄蝶娘和“我”的可靠性。
不过,黎美秀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她的信仰里作法巫术应该与魔鬼等同,她怎么可能会去相信巫术并用此残害朱融融,“我”对此多少还是持怀疑态度。但紧接着黄蝶娘却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解构了黎美秀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谎言:她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说了一辈子,此生最大的愿望是到耶路撒冷朝圣。……”黄蝶娘把脸对住我,咄咄逼人,“结果她去了没?”
我不自觉地摇了摇头。
“在我们家族的照片簿上,有一张黎美秀骑骆驼金字塔前拍的,她去了埃及、约旦旅游……”
“而居然没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没有。她与那城擦身而过,跑到埃及骑骆驼去了。”黄蝶娘加重语气地说:“黎美秀口口声声她出身世代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3]496- 497
至此,“我”仅存的怀疑已经被彻底打消。即便没有确凿可靠的指证,读者也会相信是黎美秀指使他人杀害或者逼疯了朱融融,这远比直接揭露事实真相具有更大的叙事张力。
与之相反,王福失踪事件则指向和传闻不同的判断立场。首先是黎美秀用坊间传闻拼凑的所谓真相,认定王福死于黄得云的谋杀,其中一个信誓旦旦的证人与黄得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一个被黄得云解聘的仆妇,到街市上指天咒地地说,她最后一次看到王福,像一座山,翻着死鱼的眼睛,赤身裸体大冷天直挺挺躺在那张月洞门罩子床上,臊得她老脸都没处藏。[3]378
这个仆妇因为被黄得云解雇,所说的一切就有可能是对黄得云怀恨在心的污蔑和诽谤。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她的确亲眼看到王福的死亡情形,因而才遭到黄得云的解雇。两种可能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所以该仆妇的讲述也只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此外,愿意相信这一传闻的黎美秀,又与婆婆黄得云不和,自己且已经被证明为不可靠的讲述者。因此,双重的不可靠性,只能使王福死于黄得云之手的传闻不具备任何可靠的可能性。
两个未解谜团不可靠性的不同指向,显示出隐含作者明显的倾向性:有意模糊黄得云行凶的可能性,而处处指证黎美秀罪恶的可靠性。这不仅让黄得云、黎美秀、黄蝶娘等人物性格呈现出复杂性与多面性,也使所营建的阅读空间更为广阔和开放,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历由此而引起的多种情感的交织变化,延长其伦理判断与审美判断的过程和范围。
二、殖民·女性·不可靠性与可靠性的纠缠
《风前尘埃》以横山绫子、横山月姬、无弦琴子、横山新藏、范姜义明、哈鹿克·巴彦、太鲁阁部落退休警察等众多人物的聚焦,扫描台湾被日本殖民后的残酷境地。由于这些人物各自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价值立场等的限制,在叙述过程中与隐含作者有实际矛盾,其不可靠性由此显露出来,且不可靠性几乎都是与隐含作者反殖民反侵略的立场相悖有关联。
隐含作者没有过多描述日本殖民者的残酷暴虐和台湾原住民的英勇反抗,而是重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所推崇的战争暴力文化和对台湾实行的文化殖民主义,带给台湾与日本人民无尽的心理创伤,时至今日仍阴魂不散,横山月姬的遭遇就是最好的明证。
横山月姬的父亲横山新藏为了出人头地、改变自己卑下的身份,不顾妻子绫子的执意反对,来到台湾当警察,结果导致绫子无法适应台湾的生活,以及惧怕原住民的仇恨,而不得不返回日本,当绫子走时,横山新藏竟然不允许她带走年幼的女儿月姬,给母女两人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遣走绫子后,他以为日本殖民同化政策献身的借口,在当地又娶了原住民女子。然而,同化政策对于他来说只是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幌子,所以在他得知月姬爱上了原住民时,他根本不能容忍,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处死了月姬的恋人哈鹿克·巴彦,强迫月姬嫁给一个日本人。如此野心勃勃、残暴和自私的一个人,身为受害者的月姬对女儿琴子说他很受番民爱戴,其叙述显然具有不可靠性:
那时她已成长为少女了,有次从吉野移民村回山上驻在所。下了车,几个番民蹲在路边嚼槟榔闲聊,看到她,其中一个猛然站起来,朝着她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话。
“我当时全身僵硬,胸口怦怦跳,以为要攻击我了,正想拔脚快跑,后来听出那番人口口声声念着我父亲的名字,他的同伴也点头,原来是讲父亲的好话。”[4]112
这一虚假粉饰的话语,或许有些微的亲情因素在内,但更多的却是月姬以此来为自己湾生身份的合理性辩护。只有将男性的殖民统治合理化和正义化,才能确保女性湾生身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她的悲剧由父亲一手造成,却又被迫借助虚构父亲所谓的亲善的殖民行为来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合适的理由,其自我撕裂的严重程度和内心悲苦的无处可诉可想而知。
台湾光复后,月姬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被强制遣返回国,而回到日本的她和女儿琴子又因为湾生身份被本国人歧视。绫子对外宣称月姬是被遗弃在日本本土、自己收养的孩子,由此月姬在台湾的生活被生母一笔勾销。在自我被割裂的煎熬中,月姬只能私下告诉琴子一些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台湾生活经历,原本以此缓解痛苦,然而却往往造成自己和琴子更多和更大的痛苦。
当月姬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身为病人的她原本应该是一个理论上的不可靠讲述者,但患病对于她来说却是一个新生的契机,她开始向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可靠讲述者接近。她听凭自己内心真实自我的召唤,借用真子之名逐渐吐露自己在台湾的真实生活,包括与哈鹿克·巴彦的情感经历。不过直至生命的结束,她的叙述都没有不具有完全的可靠性,她没能摆脱身份认同的困扰,不敢揭开琴子的身世之谜。
相对于横山月姬的悲苦命运和认同困扰,番民后裔、太鲁阁部落退休警察的文化选择更令人痛心。退休警察出场时,自称致力于帮助族人适应现代生活,以及搜集整理部族历史文化:“我们没有文字,可是我们有历史,不能被遗忘。”[4]3让读者会以为他的叙述是可靠的。然而,随着日军种族屠杀的雾社事件被他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与之相反,对日本人的小恩小惠他却感恩戴德: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很感恩日本人的,安部先生帮了我们一家,还送我姊姊去学校学日文……”[4]4
就个人经历而言,他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叙述的可靠性应该毋庸置疑。可是,将此放在太鲁阁部落几乎被日本灭族这一惨痛的历史大背景中,就显得格外刺目锥心,他的叙述在读者的眼中已经滑向不可靠性。
至故事结尾处,他彻底暴露出其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的丑陋嘴脸,成为一个毫无争议的不可靠叙述人物:
“如果不是出生太晚,没赶上战争,”退休山地警察望着图片,喃喃地说,“也许我也会立下血书加入高砂义勇军吧!”[4]240
“高砂”一语为日本古籍对台湾之称呼,后日本以“高砂”称呼原住民,目的在于加强同化。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台湾原住民族部落遭到日军近乎灭绝性的血腥屠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以诱骗和强迫的方式,征召2万余原住民青年入伍,远赴南洋作战,称之为“高砂义勇队”。他们大多被派赴战场的第一线,故死伤极为惨重,生还者仅余三分之一,且多数为伤残。
青壮年男性被送往战场九死一生,留在家中的不少原住民年轻女性又被迫成为慰安妇,给原住民带来巨大的苦难和无法消弭的心理创伤。[5]如果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热衷搜寻部族的历史,即便不能全然知晓历史真相,但对“高砂义勇队”及原住民慰安妇的遭遇,也不可能一无所知。然而,在根深蒂固的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下,他对不利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历史真相选择视而不见,自动过滤。在他的眼中,“高砂义勇队勇敢敏捷,涉渡山间,到南洋菲律宾丛林开辟战争道路,不畏艰苦忠心耿耿,军夫背着日本人的米粮,宁愿自己饿死,也不敢私自食用军粮。”[4]240显然,这与真实的历史形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在他的叙述中,个人经历的可靠性和民族历史的不可靠性始终是对立的。换句话说,正因为他个人经历的可靠性,导致了他对民族历史不可靠叙述的选择。
从日本女子横山绫子到湾生的横山月姬、无弦琴子,再到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台湾原住民慰安妇,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给女性带来的除了苦难,别无其他。而男性叙述者,无论是本族的,还是异族的,都无一例外将她们排斥在可靠的历史叙述之外。
三、衣服·女性·不可靠倾诉者的选择性聚焦
与《寂寞云园》和《风前尘埃》不同,《三世人》不再以女性人物为故事主轴,而主要以男性的遭遇展现从日据时期到“二二八”事件爆发50多年间里的台湾风云变幻。女性人物王掌珠的故事穿插其间,成为男性时代记忆和历史叙事的一个绝佳注脚。隐含作者在王掌珠的聚焦中,将男性眼中惯常出现的政治事件安排为少量点缀,反而别出心裁地把衣服这一和女性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却不被关注的物品加以凸显,以此揭示时代的变迁和王掌珠的心路历程:
王掌珠她要用自己的故事,写一部自传体的小说,用文言文、日文、白话文等不同的文字,描写一生当中换穿的四种服装:大裪衫、日本和服、洋装、旗袍,以及“二二八事变”后再回来穿大裪衫的心路历程。[6]27
从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乡下养女,到独立自强的职业女性,王掌珠不向命运低头、勇于进取的精神,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完全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规范。“生命操在她的手中。她是自己命运的主宰。”[6]70她立志成为一个作家,“想描写一个处在新与旧的过渡时代,却勇于追求命运自主,突破传统约束,情感独立,坚贞刚毅的台湾女性。”[6]23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她的奋斗经历和价值立场无疑具有隐含作者赞同的伦理判断,但是浅薄、虚荣、盲目追求时髦的性格缺陷,又造成她叙述过程中的不可靠性一直存在。
她初到城市时,毫无见识,惊诧于都市和乡村二者生活的天壤之别。让她以为这一切都归功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且在日本殖民时期日本人远比台湾当地人高贵,因此她被日本文化所迷惑,艳羡不已。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认知错误和殖民地实际存在的等级制度,导致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都出现令人遗憾的偏差。她拼命模仿日本人,连日本人雇佣的台湾下女悦子与之交往,她都觉得是高攀,自愿为悦子代劳粗重家务。在悦子的指引下,她开始学习日语,“成为日本人,到帝都朝圣,是她这孤女一生的愿望。”[6]180与象征养女身份的大祹衫相比,和服自然也就成为她幻想变成日本人的一个载体:
开放自己。进入日本人的浴衣,让身体的各个部位去迎合它,交互感应,紧贴粘着在一起,填满空隙,感觉到和服好像长在她身上的另一层皮肤,渐渐合而为一。[6]63
穿上和服,掌珠与过去割裂,她变成另外一个人,另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由和服所创造出来的新人。透过身穿的和服,掌珠觉得幸福,从碎裂中感到完整。[6]180
不过隐含作者将和服取代大祹衫,放到王掌珠由于养母逼婚而被迫逃亡以及日本当局废娼举措使养女重获自由的背景下,部分抵消了读者对她一厢情愿沉迷于日本文化的举动可能产生的不满和指责,反而还会对其生出同情之心。另外,在日本警察欺负台湾摆摊老者时,她敢于仗义执言;为了生存,她宁愿吃苦受累的做工,也不愿走上出卖肉体之路;当身穿和服、说着日语的她仍然被日本人孤立、歧视的时候,她也感到孤独,因而开始模仿中国电影里的女明星穿旗袍。这些都毫无疑问地拉近了她与读者的距离,减少对其不可靠性的质疑。
王掌珠的衣服更替、聚焦和叙述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交织缠绕,传递出的是台湾人对历史身份和国族认同的混乱与茫然,以及内心深处无以言说的悲哀。
施叔青的这三部家族小说在不可靠叙述策略的运用上,圆熟、别致,叙述者和人物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可靠性,以及不可靠性和可靠性之间的相互转换,既修订和改写了男性的正史叙述,又使人物塑造更为复杂,揭示出在历史发展混乱、无序时期人性的多面性,引发读者对故事、人物和历史进行更深的思考和探索,也为华文女性文学想象和重构历史提供更多的可能。
[1](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施叔青.寂寞云园[A].香港三部曲[Z].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4]施叔青.风前尘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台湾慰安妇报告[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
[6]施叔青.三世人[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责任编辑:杨春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Narrative Ethics in Shi Shuqing’s Family Novels
WANGMeng
Unreliable narration applies to all of Shi Shuqing’s family novels.This unreliability—which is reflected by various expression forms—can be transformed into reliability so that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feature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help writers to form special narrative effect and construct narrative ethics of novels.Unreliable narration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for readers’ethical judgment and aesthetic judgment by the novels’diversity and openness.
Shi Shuqing;familynovels;unreliable narration;narrative ethics
10.13277/j.cnki.jcwu.2015.04.011
2015-02-20
I206.7
A
1007-3698(2015)04-0071-05
王 萌,女,蒙古族,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文学。450002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3BWX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