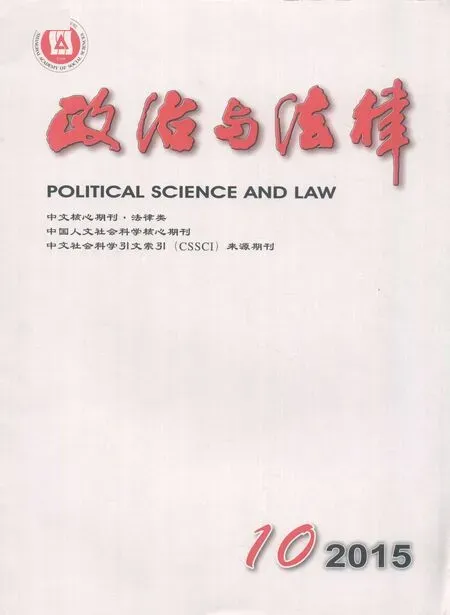为公民基本义务辩护*
——基于德国学说的梳理
王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100191)
为公民基本义务辩护*
——基于德国学说的梳理
王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100191)
基本义务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义务。基本义务自法国1795年宪法首次规定,此后影响了德国宪法。1919年魏玛宪法专章规定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德国基本法之所以抛弃了专章规定的做法,仅保留了个别的基本义务,一方面是对纳粹时期滥用公民义务的反应,另一方面是认为公民承担基本义务是不言自明的。根据是否会产生宪法或法律上的制裁,可以将基本义务分为道德义务、不完全的法义务和完全的法义务三种。基本义务中的作为义务需要通过法律来贯彻,但不作为义务和容忍义务则无需通过法律的中介。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间是非对称的关系,但基本义务也有其独立的宪法地位,因为基本义务就是公民身份中公共性的体现。
基本义务;基本权利;道德义务;法义务;公民
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的章名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此产生了公民基本义务的宪法范畴。①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虽未直接出现“基本义务”的用语,但是,其一,从汉语形容词的使用规则来看,如果两个名词具有相同特征,可以用同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两个名词,比如“红色的大衣和帽子”,所以也可以称为“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由于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短语,所以省略了“的”字。参见刘月华、潘文娱、故韡:《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79页。其二,从宪法史来看,“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沿袭自1954年宪法,作为1954年宪法亲历者的许崇德教授一直坚持使用公民基本义务的术语。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第786页。当然,公民基本义务的入宪,并非现行宪法的“独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部宪法中都有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甚至往前追溯,自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开始,中国的历部宪法中都有臣民或人民义务的规定。可见,公民基本义务在我国宪法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范畴。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对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②姜峰:《宪法公民义务条款的理论基础问题:一个反思的视角》,《中外法学》2013年第2期。然而,这些论证或有缺陷,③对张千帆教授观点的批评,参见王世涛:《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吗?——与张千帆教授商榷》,《时代法学》2006年第5期。或有误解,④比如朱孔武教授和姜峰教授都认为,1949年德国基本法删除了或者废除了基本义务条款。参见朱孔武:《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同前注②,姜峰文。本文拟在梳理德国基本法上有关公民基本义务的相关历史和学说的过程中,为公民基本义务的宪法意义进行辩护。
一、基本义务(Grundpflicht)的概念
不同于魏玛宪法第二章“德国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1949年德国基本法中并未提到基本义务的概念,这让人产生了基本法已经完全放弃了基本义务的印象。但实际并非如此。学界的通说认为,这只是宪法对纳粹时期滥用公民义务的一种反应,⑤Hasso Hofmann, Grundpflichten und Grundrechte, in 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X,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1, S. 700.同前注②, Randelzhofer书, S. 614。基本法中仍然保留了一些义务条款,比如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的教养义务、第14条第2款第1句的财产的社会义务。至于州宪法中基本义务的规定就更多了,在基本法之前制定的许多州宪法,比如巴伐利亚州、不莱梅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萨尔兰州,都模仿魏玛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所以,准确地说,基本法反对的只是纳粹时期公民承担无限的义务,而非反对基本义务。⑥Thorsten Ingo Schmidt, Grundpflicht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99, S. 46.
那么,什么是基本义务?由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只在个别的判决中提到基本义务,⑦BVerfGE 61, 358(372); BverfGE 47, 34(37); BVerfGE 84, 239(269).所以法院至今还没有形成对基本义务的定义。最早对基本义务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施托贝尔(Rolf Stober)认为,基本义务是宪法规定的个人针对国家所负的义务。⑧Rolf Stober, Grundpflichten und Grundgesetz,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79, S. 13.格茨(Volkmar Götz)认为,基本义务是宪法要求的义务人对于公共利益所负的义务。⑨Volkmar Götz, Grundpflichten als verfassungsrechtliche Dimension, VVDStRL 41(1983), S. 12.卢赫特汉特(Otto Luchterhandt)指出,基本义务包含两个层面,首先它是宪法上规定的,其次它的主体原则上是个人。⑩Otto Luchterhandt, Grundpflichten als Verfassungsproblem in Deutschland: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und Grundpflichten unter dem Grundgesetz,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88, S. 49-50.施密特(Thorsten Ingo Schmidt)给出的定义是基本权利享有者向国家所承担的宪法上的义务。①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36。兰德尔茨霍夫(Albrecht Randelzhofer)认为,基本义务是个人在基本法上所承担的、向国家共同体履行的义务。基本义务既包括基本法所明确规定的,也包括基本法中所隐含的。②Albrecht Randelzhofer, Grundrechte und Grundpflichten,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d. II,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6, S. 605-606.由此可见,德国学者的定义大同小异,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基本义务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基本义务是宪法规定的,不同于法律上规定的义务。基本义务完全是一个纯粹形式的实证概念,个人的法律义务在形式意义上并非基本义务,③Detlef Merten, Grundpflichten im Verfassungssystem, BayVBL 1978, S. 555; Peter Badura, Grundpflichten als verfassungsrechtliche Dimension, DVBL 1982, S. 868; Herbert Bethge, Grundpflichten als verfassungsrechtliche Dimension, NJW 1982, S. 2146; Christoph Gusy, Grundpflichten und Grundgesetz, JZ 1982, S. 657.即使这些义务基于其本质内涵和影响也自称为“基本义务”,比如德国《士兵法》第7章规定的士兵的基本义务。当然,这能否得出宪法上的义务就比法律上的义务更“基本”呢?卢赫特汉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一些法律义务也拥有基本的“实质”,比如作证义务,虽然基本法上没有规定,但它对程序法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④BVerfGE 49, 280(283f.).同时,宪法上的基本义务也不能拒绝不成文的宪法义务的存在,比如承担风险的义务。⑤Hasso Hofmann, Grundpflichten und Grundrechte, in 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X,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1, S. 700.同前注②, Randelzhofer书, S. 614。
第二,基本义务的主体是公民,所以它不同于先于国家的人的义务(Menschenpflicht)。首先,人的义务是自然法上的义务,而基本义务是实证法上的,所以比人的义务更体系化。其次,人的义务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再次,人的义务适用于任何人。①Herbert Bethge,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Problematik der Grundpflichten, JA 1985, S. 259.再其次,人的义务针对其他人,而基本义务是针对国家。最后,人的义务产生国际法问题,而基本义务是国内法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说基本义务的主体是公民,但是否仅限于公民?施密特认为,基本义务主体的更准确表述是基本权利的享有者(Grundrechtsträger),即除了公民外,还包括私法人和某些公法人,前者如私法人要承担纳税义务,后者如《巴伐利亚州宪法》第111a条规定的广播电视机构的真实义务。②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36-37。
第三,基本义务的对象是国家,不同于针对国家机关或者公共行政的义务,虽然后者也是宪法上规定的。比如德国基本法第44条第2款的向调查委员会的提交义务,第33条规定的州对联邦的义务,第43条、第53条、第58条规定的联邦机关之间的义务,乡镇之间的友好对待义务。德国学者还区分基本义务和基本权利义务(Grundrechtspflicht),前者是公民向国家承担,后者是国家对公民承担,③Peter Häberle, Grundrechte im Leistungsstaat, VVDStRL 30(1972), S. 93, 112.国家如果违背基本权利义务,将产生侵犯基本权利的效果。④同前注③, Bethge书, S. 2148。
第四,基本义务不应限于宪法上明确带有“公民有……义务”的字眼,还应包括从宪法中推导出的基本义务。有时宪法文本规定的是特定人的义务(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的义务、第31条第1款的州内德国人的义务),有时规定的是特定对象的义务(基本法第14条第2款第1句财产的社会义务),有时用接近义务的名词,比如任务(Aufgabe)、照顾(Fürsorge)、强制(Zwang),有时用动词,比如克制(ist gehalten)、“应有利于”(soll dienen)、“是神圣的”(ist unantastbar)或者“被委托”(ist anvertraut)。那么,到底从哪些词中可以推导出基本义务?Schmidt认为,这要看公民违反该义务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宪或者是否会招致宪法制裁(丧失基本权利)。⑤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38。
因此,兰德尔茨霍夫将基本义务分为三类:(1)宪法直接规定的义务,包括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义务、第12条第2款的公共服务义务、第12a的服兵役义务、第14条第2款的财产的社会义务、第26条的和平义务、第33条第4款的忠诚义务;(2)从宪法中间接推导出来的义务,包括服从法律的义务和纳税义务;(3)宪法上没有规定的义务,比如受教育义务和接受名誉职位的义务。⑥同前注②, Randelzhofer书, S. 610-615。
二、基本义务的理论基础
基本义务的概念是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费德尔(J.G.H.Feder)发明的。费德尔从法律平等中导出了个人的消极义务,即不能去侵犯他人的自然权利。这种义务与自由权的内在限制是同义的。⑦Florian Dühr, Prinzip und System der Grundpflichten, LIT Verlag, Münster/Hamburg/London, 2002, S. 3.
基本义务正式见于1795年8月22日法国宪法的《人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宣言》,⑧同前注③, Badura书, S. 861-862。当时规定了四个基本义务:服从法律的义务、纳税义务、财产牺牲义务和服兵役义务。⑨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51。其实早在1789年召开国民会议的过程中就讨论过基本义务的问题,旧政权的代表——主要是教会要求补充基本义务的规定。会议的多数人承认公民自律和针对其他公民的责任,但认为针对国家的独立的义务规定似乎背叛了自由的理念,①Hasso Hofmann, Grundpflichten als verfassungsrechtliche Dimension, VVDStRL 41(1983), S. 48.议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 Rat)是德国1949年基本法的制定机关,共有65名成员,由西德各州议会议员依照特定程序互选产生,外加5名无投票权的柏林代表。参见叶阳明:《德国宪政秩序》,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1页。最后会议以570票对433票否决了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发布,②同前注⑨,Götz, S. 65.所以法国《人权宣言》仅在前言中提及义务。至于法国1795年宪法专门规定基本义务的原因在于理论上是受到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即社会的维护要求公民认识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政治上是热月党人对雅各宾派所鼓吹的人民的不可置疑论调的一种反对。③同前注③, Badura书, S. 862。
法国宪法上的规定影响了南德和中德地区的宪法,它们也将服从法律的义务、纳税义务、财产牺牲义务和服兵役义务作为基本义务。④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52。1849年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会议首次引入了受教育义务,但当时该义务是指给孩子上课的义务而非上学的义务。1919年的《魏玛宪法》在德国宪法史上首次对基本义务进行了全面规范化。一方面它延续了之前的宪法传统,规定了纳税义务、服兵役义务和财产牺牲义务。同时,它又有新的发展,包括将受教育义务规定为上学义务,并通过在宪法文本中规定父母的教养义务来予以补充。源自于乡镇法上的担任荣誉职位的义务也进入了宪法。⑤荣誉职位(Ehrenämtern),比如荣誉法官、竞选助手、人口普查员等等。彼得斯(Hans Peters)将其视为国家支持政治、经济领域的自我行政的重要表现。同前注⑨,Götz书, S. 27。魏玛宪法的最主要意义是首次承认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义务,特别是财产和土地的社会义务、对无补偿的征收的容忍义务和劳动义务。但是,由于魏玛宪法只实施了14年,同时缺少宪法法院,所以基本义务的教义并没有充分形成。⑥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53。那么,魏玛宪法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规定基本义务?学者认为,它的根本诉求是通过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来塑造文化国家和社会国家。⑦同前注⑨,Götz书, S. 10。
纳粹时期基本义务的特点是:首先,义务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中心地位,个人对公共福利(Gemeinwohl)负有无限的义务。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称之为义务的总体方针(das totalitäre Programm der Pflicht)。它为每个人设定了对民族总体的内在义务。这个内在义务取消了个人的私人属性。每个人都要对民族的命运负责,无论是他的公共活动还是家庭内的活动。⑧Ernst Forsthoff, Der totale Staat, Hanseat Verlag, Hamburg, 1933, S. 42.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必然导致义务的优势地位。⑨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54。其次,纳粹时期还提出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理论。在自由法律体系中,权利和义务、公民和国家、个人和集体是相互独立和对抗的。而纳粹时期提出的成员地位(Gliedstellung)则认为权利和义务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由此义务变得内在。因为个人的生命只有在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中才有意义。民族成员(Volksgenossen)的权利只有为了更好履行他的集体义务的时候才能被授予。国家对个人利益,比如名誉、生命、财产的保护与此并不矛盾,因为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集体的一份子存在,因此只有在领袖(指希特勒)所定义的集体利益的框架内才能得到保护。⑩同前注⑨,Götz书, S. 360。
基本法之所以保留了个别的基本义务条款,从议会委员会的讨论过程就可见,①基本义务虽未成为原则,但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议会委员会的发言人曼戈尔德(Hermann von Mangold)简明扼要地指出,基本权利构成个人在国家中地位的前提,个人的基本义务也是一样。①同前注⑧, Stober书, S. 19。施密特(Carlo Schmidt)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制宪者们仅仅规范了一些意见一致的义务,这些义务来自于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民主共识。②Ernst Benda, Grundrechte-Grundpflichten, Vortrag gehalten am 9. Mai 1981 in Esslingen am Neckar, S. 7.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也间接承认了基本义务存在的必要性:基本法中人的形象并非一个孤立的、自主的个人,基本法更多地是在个人与集体的紧张关系中来决定个人的社会关联性和社会约束性,否则将损害基本法的内在价值。③BVerfGE 4, 7(15f.); 47, 327(369); 50, 290(353); 65, 1(44).当前,德国学者对基本义务正当性的论证主要基于以下四个理由。
第一,基本义务是为了国家的存在。其代表人物之一是古斯(Christoph Gusy)。根据他的观点,国家的存在先于宪法,国家权力对应个人的义务。因为国家权力要以统治的可能性为基础,而统治要想变得可能就要对第三人提出行为要求并辅之以制裁的威胁,这就是在为受众设定义务。④同前注③, Gusy书, S. 657。所以,古斯将服从义务作为国家的理论前提。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施托贝尔,他认为,国家强力就表现在听任主权机构设定基本义务。⑤Ralf Stober, Grundpflichten als verfassungsrechtliche Dimension, NVwZ 1982, S. 473, 474.与古斯不同,施托贝尔并不认为国家能够设定潜在无限的义务,他认为,自由原则上是无限的,而服从国家原则上是有限的。人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是通过权利、义务来确定的,在民主国家,权利、义务是不可分割的,基本义务是为了强调社会因素,基本义务的功能是作为保护自由、生命和财产的前提。
第二,基本义务是来源于社会国原则。巴杜拉(Peter Badura)认为,社会国原则可以被视为基本义务的概括条款。它不仅具有伦理上的意义,而且是对个人式自由主义的否认,它反映了基本自由的社会约束性。⑥同前注③, Badura书, S. 869f。施特恩(Klaus Stern)也认为,基本义务是与社会国交织在一起的。⑦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1,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77,S. 880f.但是在后来的《德国国家法》第三卷中,施特恩则回到巴霍夫(Otto Bachof)的论证轨道,⑧巴霍夫认为,每个人都有义务不作出伤害社会的行为,这种团结义务向上追溯到与国家性相联系的服从义务。Otto Bachof,Diskussionsbeitrag, VVDStRL 41 (1983), S. 98, 100.将基本义务作为团结(Solidarität)的最低标准,社会国原则也是由此导出。这种团结义务不是自然法义务或者先于国家的义务,而是一个基于国家的法义务。⑨我国学者王晖博士也试图从团结的角度来论证公民基本义务的正当性,但是她认为基本义务与宪法义务不同,前者“先天有效”、“不需要来自国家的实定化”,而宪法义务是宪法规定的其他义务,与基本义务不同,“它们的义务范围需要来自法律的说明,效力来自实在法的规定”。参见王晖:《法律中的团结观与基本义务》,《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这种区分不仅在德国学界未见先例,因为从德国学者的论述来看,他们认为宪法规定的义务肯定是基本义务,有争议的是宪法没有规定的义务是否基本(比如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不成文的义务),而且她所列举的一些基本义务,比如纳税义务和兵役义务,也并非不需要来自国家的实定化或者法律的说明。当然,如果这种区分的目的是想反映某些基本义务比另一些基本义务“更根本”,倒是有意义的。比如德国学者施密特就把基本义务的体系分为外部体系和内部体系。外部体系由规则组成,内部体系是基于规则的内容联系,由少量指导原则组成。他将后者称为“母义务(Muttergrundpflicht)”。但他认为,在不同时期,母义务是不同的:在魏玛时期,国籍或者民族理念成为所有义务的化身;在纳粹时期,忠诚义务成为所有民族成员义务的来源;在东德宪法中,共同决定和共同形成发挥着母义务的功能;在二战后的自然法复兴时期,一些学者将爱社会作为母义务;在现阶段,施密特引用伊森泽(Josef Isensee)的观点认为,形式的母义务是服从法律的义务,实质的母义务是和平义务(Friedenspflicht)。参见前注⑥,Schmidt书, S. 288。
第三,基本义务来源于与基本权利的对等性(Gegenseitigkeitsprinzip)。霍夫曼(Hasso Hofmann)认为,个人的社会性以及服从合宪法律的义务在宪法上的理由是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对等原则以及基本法第3条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在宪法上竞争、并存,都需要保护和组织保障。①同前注⑤,Hofmann书, S. 74f。
第四,基本义务来源于人性尊严。卢赫特汉特认为,人性尊严构成了基本义务的根源。②同前注⑩,Luchterhandt书, S. 444。其中,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1句构成了与公民有关的基本义务的根源,第1条第1款第2句构成了与国家有关的基本义务的根源。第1条第1款第1句首先要求人们不去侵犯他人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义务,其次人们有义务去忍受其他人的发展,只要这有助于他的人格尊严的自我发挥。不侵犯义务并没有在忍受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中耗尽,相反它将人的一般道德义务转化为帮助他人的义务。对于国家来说,不侵犯义务在两个层面上展开。首先,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1句通过实证的刑法、民法和程序法制度来使平等的人格尊严保护变得可能。这就为服从法律的义务奠定了实质的基础。其次,国家负有保护人格尊严的义务。这种与国家相关的义务包括和平义务、防卫义务和纳税义务,国家让公民承担义务本质上是在履行国家目标——保护人格尊严。
三、基本义务的性质——道德义务抑或法义务
基本义务到底是道德义务还是法义务?③笔者用“法义务”而非“法律义务”,是因为本文中所讲的“法律义务”都是相对于宪法义务而言的。伊森泽认为,伦理性的基本义务本质上是在基本权利所有者之间生效。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尊重其他人的人性尊严。容忍是多元社会并存和共同生活的条件。人越是把基本自由权作为实现个人性的机会和一种基于真实的不平等的权利,这个社会的多元性越大,那么对容忍的需求就越大。同时,既然是道德义务,那么就不可能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落实这种道德性的基本义务的重要手段是教育。公立学校的教育任务超越了法律,还包括了道德,即宪法中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共识。④Josef Isensee, Die verdrängten Grundpflichten des Bürgers: Ein grundgesetzliches Interpretationsvakuum, DÖV 1982, S. 615-616.笔者认为,伊森泽的观点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正确的成分就是,基本义务是道德义务还是法义务的关键在于,落实这种义务的方式是什么。比如施托贝尔认为选举义务是道德义务,因为它既未在法律中规定,也没有规定惩罚措施。反之,纳税义务就不是国家的一种道德预期,因为它必须通过法律来贯彻。需要商榷的是,如果我们把基本义务定义为公民针对国家的义务,那么公民针对其他公民的义务还能称为基本义务吗?⑤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父母对子女的教养义务并非公民对公民的义务,也就是说,该义务仍是父母向国家承担,子女只是受益人而非权利人。同前注②, Randelzhofer书, S. 622。
关于基本义务是否具有法效力的问题,德国学者间存在分歧。施托贝尔认为,基本法之所以没有规定对违反基本义务的惩罚,部分是因为这在基本法上既不可能也没有效率和意义,部分是因为基本义务仅仅是立法的标准,因此它的法律后果和法律保障都要通过法律来具体化。⑥Rolf Stober, Grundpflichten versus Grundrechte?, Rechtstheorie 15 (1984), S. 56.但是,兰德尔茨霍夫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将导致从法治国原则中得出的服从法律的基本义务只有在立法者制订了具体的法律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服从法律的基本义务并不以每一个具体的法律为前提,为了独立于法律,所以它存在于宪法。基本义务的规范效力不需要通过法律,而是直接来自于基本法。⑦同前注②, Randelzhofer书, S. 621。但是,兰德尔茨霍夫并没有解释基本义务的这种规范效力到底体现在哪里。相对地,贝特格(Herbert Bethge)区分了五个等级的规范效力,包括道德义务、序言和教育目标中的义务、不完善的法义务、具有规范效力的基本义务和自我执行的基本义务。道德义务不是真正意义的法义务,但是它可以被法文本所规定。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具有制裁性的不完善的法义务。位于两者之间的是作为过渡形式的序言和教育目标中的义务。具有规范效力的基本义务和自我执行的基本义务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法律的转化。①同前注⑥,Bethge书, S. 258。巴杜拉将魏玛宪法中规定的基本义务分为描述性、劝告性、为立法者提供准则以及具有直接效力四种。②同前注③, Badura书, S. 867。
施密特综合了贝特格和巴杜拉的分类,将基本义务的效力分为道德义务、不完全的法义务和完全的法义务三种。(1)道德义务,是指不会导致法制裁的义务。有些义务明确地称为道德义务,比如魏玛宪法第163条第1款的劳动义务;有的是被解释成道德义务,比如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第1句的财产义务;有的基本义务是以劝说为目标,比如巴登-符腾堡州宪法第26条第3款的选举义务和表决义务,也只能看作是道德义务。(2)不完全的法义务,是指目前没有规定法制裁的义务。比如从基本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的财产的社会义务或者从社会国原则中得出的连带义务。(3)完全的法义务,是指不履行会导致法制裁的义务。③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120-122。法制裁包括宪法层面的制裁和法律层面的制裁,在法律层面还要区分刑法、违反秩序法、纪律法、行政法和民法上的后果。其一,宪法层面的制裁就是基本权利丧失(Grundrechtsverwirkung)。④Michael Sachs, Bürgerverantwortung im demokratischen Verfassungsstaat, DVBL 1995, S. 891.比如德国基本法第18条规定,凡是滥用表达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讲学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信、邮政和通讯秘密、财产权和避难权来攻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的人,将丧失这些基本权利。这一制裁主要是针对公民的忠诚义务的。此外,德国基本法第26条第1款第2句规定,可能扰乱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和具有此种意图的行为,特别是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均属违反宪法。对此种行为应予以惩处。这是针对违反和平义务的,同时也对立法者提出了制裁违反该义务行为的义务。其二,违反基本义务的最大制裁来自于刑法。尽管所有的刑罚都可以被视为对不履行服从法律的基本义务的制裁,但是刑法上仍然存在着针对违反单个基本义务的制裁。比如德国刑法典第113条是针对公民的和平义务的,第353b条是针对公务员的忠诚义务的。此外,高校教师不履行忠诚义务,不履行服兵役义务和纳税义务、父母的教养义务、自卫义务、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义务都将成为刑法制裁的对象。其三,违反秩序罚是作为刑罚的补充。这个主要是针对接受荣誉职位的义务和受教育义务。其四,纪律罚主要是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公职人员,包括警告、财产损失以及一些特定的纪律手段。其五,特别行政法上的制裁,比如州的学校法规定,对不履行基本法第7条第4款的义务的私立学校撤回其办学许可。其六,民法上的制裁。虽然基本义务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基本义务的受益人是其他公民的时候,也会产生民事制裁。比如和平义务在民法上就转变为不侵害他人的要求,民法典对此规定了损失补偿请求权、赔偿金请求权以及对侵犯的防御请求权。⑤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126-129。
同时,施密特认为,基本义务的这种规范效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义务之前被认为是道德义务,之后则被解释为法义务,比如财产的社会义务;有的义务对于不同的主体性质不一样,比如劳动义务,对于公民来说劳动义务是道德义务,而对于罪犯来说劳动义务是法义务。
四、基本义务的宪法定位
最早对基本义务进行宪法定位的是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他在《主观公权利体系》一书中将基本义务界定为一种公民对国家的被动地位,从而与基本权利作为公民对国家的消极、积极、主动地位相对应。①[德]格奥尔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9页。但是,可能限于该书的主题,耶利内克并未对被动地位进行具体的阐述。那么,基本义务到底在宪法上具有什么意义?目前德国学者有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将基本义务作为基本权利学说的分支,隶属于基本权利教义学,另一种则将基本义务视为独立的宪法范畴,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是平行的。
(一)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的关系
首先,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是非对称关系。②根据施密特的观点,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间有三种关系。(1)非对称但义务优先,此时公民根据义务的履行来享有权利,权利并非自由地行使,而是带义务地行使。比如纳粹。(2)对称关系,即权利本身也是义务。比如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既是权利又是义务。(3)非对称但权利优先。民主国家的宪法首先塑造了一个先于国家的原则上无限的自由范围,这个自由受到全面的保护,反之基本义务原则上是有限度的。这种非对称关系是为了追求人性尊严和自由的目标。其中,基本权利是直接实现该目标,而基本义务是间接实现该目标。参见前注⑥, Schmidt书, S. 48-49。值得注意的是,王晖博士提出了另一种对非对称关系的理解,她认为,这种非对称是因为基本权利并不构成国家的基础,作为一种宪法保障,它无法证立国家,相反,基本义务并不必然需要宪法上的证立,它先天有效,并且必然发生在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之前。同前注④,王晖文。这种理解类似于施密特所说的非对称但义务优先,与本文所讲的非对称但权利优先不同。这种理解的正确性在于看到了基本义务所蕴含的“政治性”,但问题在于,首先,如后所述,主动的基本权利,比如参政权,也具有政治性,对于国家的构建同样是重要的;其次,在她列举的几项基本义务中,比如财产的转让义务(笔者译为牺牲义务)难道能先于财产权而存在吗?再次,正如伊森泽所说,义务只是手段,权利才是目的。因为国家是为了人,而非人为了国家。Vgl. Josef Isensee, Freiheit ohne Pflichten-Zum verfassungsrechtlichen Status des Bürgers im Staat des Grundgesetzes, Eine Veröffentlichung der Freiherr-vom-Stein-Gesellschaft e.V., Münster, 1983, S. 29-30.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基本权利都对应一个基本义务,③同前注②, Randelzhofer书, S. 614f。因为如果说公民有义务行使自由,那么自由就会丧失其核心,而自由的本质是选择做或不做什么的可能性。认为每一个权利都对称地存在一个义务的观点会掏空权利,导致最后剩下的仅仅是义务。④Carl Schmitt, Freiheitsrechte und institutionelle Garantien der Reichsverfassung, in ders.,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 Materialien zu einer Verfassungslehre,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58, S. 167.例外是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所规定的“抚养和教育子女是父母的自然权利,也是父母承担的首要义务”,该条的意思是父母教养子女的权利中并不包括不教育子女的权利。⑤Detlef Merten, Negative Grundrechte,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d. II,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6, §42 Rn 60.父母的义务并非对父母权利的外在限制,而是说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它具有双重性:父母无法选择是否行使教养孩子的权利,但他们可以决定如何行使该项权利。同时,父母必须为了孩子的幸福行使该项权利。⑥Willi Geiger/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Kraft und Grenze der elterlichen Erziehungsverantwortung unter den gegenwärtig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n: Elternrecht-Recht des Kindes-Recht des Staates, Aschendorff, Münster, 1980, S. 67-69.
其次,基本义务和主动地位的基本权利一样具有高度的政治内涵,它关系到国家目的——法律和谐、社会均衡、后代教育、满足国家的财政和土地需求——的实现。⑦Peter Saladin, Verantwortung als Staatsprinzip: Ein neuer Schlüssel zur Lehre vom modernen Rechtsstaat, Verlag Paul Haupt Bern und Stuttgart, 1984, S. 217.虽然基本义务在内涵上与主动地位的基本权利相关,但在法律结构上则与社会基本权类似,是一种宪法方针条款,即基本义务不能像基本权利一样具有直接效力,必须通过法律的转化,行政机关不能直接依据基本义务来做出有效力的命令。⑧同前注⑤,Hofmann书, S. 725。对此,伊森泽的说法更直接,他认为,如果没有法律来具体化基本义务,宪法上的基本义务对个人来说不过就是一个道德上的呼吁。⑨同前注④,Isensee书, S. 613。基本义务通过法律来实施还具有另一个意义,即表明了基本义务的有限性。在此,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能在没有法律中介的情况下直接从基本义务得出法律后果。①同前注③, Badura书, S. 868。同前注⑥,Schmidt书, S. 46-47。目前,基本义务的法律中介性是德国国家法学的通说。②Hans H. Klein, Über Grundpflichten, Der Staat 1975, S. 155ff.同前注③, Badura书, S. 868。但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义务要求并不一样。施密特认为,服从法律的义务必须要以法律的制定为前提,否则该法律的内涵就是空洞的;对于作为义务,比如纳税义务,法律要提供最低的规制;对于容忍义务,比如财产的社会义务,就不需要法律的规定;对于不作为义务,比如和平义务,同样不依赖民法和刑法的规定,民法、刑法的规定仅仅在制裁违反不作为义务的行为时才有必要。③同前注⑥, Schmidt书, S. 124-125。容忍义务与不作为义务的区别在于,容忍义务是指对他人的作为不予阻止或防御,不作为义务是指单纯放弃自身的作为。
再次,基本义务并非基本权利的反面。有学者认为,规定基本义务是反自由主义的,它来源于绝对主义的专制国家。④Hans Bayer, Entstehung und Bedeutung wirtschaftlicher Grundrechte und Grundpflichten, Diss., Frankfurt, 1937, S. 14.对此,伯肯福尔德(Ernst Wolfgang-Böckenförde)敏锐地指出,基本自由权不再必然是自由主义基本权理论上的单纯自由,而是一种制度——客观意义上的自由的实现,自由的范围和保护要随着行使自由的方式和目的而改变。因为它属于一种法律上的自由,所以由国家通过确定的规则来履行该项任务(自由的保障——笔者注)以及对由于国家侵犯而无法履行或者减损或者对保护自由的拒绝进行惩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⑤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Grundrechtstheorie und Grundrechtsinterpretation, NJW 1974, S. 1532.兰德尔茨霍夫也认为,这种认为基本义务是反自由主义的观点的关键还在于人们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理解为对称关系,这种误解可以通过非对称关系的理解得到消除。基本义务的存在并非宪法有缺陷,而是对宪法的理解问题。⑥同前注②, Randelzhofer书, S. 618-619。
最后,关于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关系,传统上认为,基本义务是作为基本权利的限制而存在。⑦同前注③,Gusy书, S. 662f。但是这种观点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判。霍夫曼认为,人们把基本义务理解为如同容忍原则般构成自由权的内在限制,但这窄化了与国家相关的人员和事务上的给付和忍受义务。因为基本义务不仅仅是防御性质的,而且还带有给付性。⑧同前注②,Dühr书, S. 76。同时,基本义务不是针对特定基本权利的,而是涉及多个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比如纳税义务不仅仅与财产权保障有关,还涉及职业自由。同样,服兵役义务不仅影响职业自由,还影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请愿权。⑨同前注⑤,Hofmann书, S. 726-727。施密特提到了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另外三个不同。(1)基本义务是针对作为,而基本权利限制是针对不作为。(2)基本义务主要涉及公民对国家和集体的关系,而基本权利限制是说自由的行使要和其他人的自由相协调。⑩兰德尔茨霍夫提到,限制基本权利并非基本义务的本来目的,基本义务的目的是个人为了集体的利益去给付和忍受。迪尔(Florian Dühr)也认为,基本权利限制的目的是使其他基本权利与他人同样受限制的自由相协调,而基本义务的重点是促进公共利益,从而实现共同体的统一、整合和社会形成。同前注②, Randelzhofer书, S. 620;同前注②, Dühr书, S. 11。(3)尽管基本义务和基本权利限制都以基本权利的界限为目标,但通过不同的路径来实现。基本权利限制首先要确立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然后再谈基本权利的保护。而基本义务是直接为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划定界限,比如和平义务。①同前注③, Badura书, S. 868。同前注⑥,Schmidt书, S. 46-47。有人担心基本义务的规定会清除基本权利限制上的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限制。但是,巴杜拉认为,这可以通过基本义务的法律保留来预防,同时,基本义务本身就是宪法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基于基本义务的有限性,过度禁止也得以保留。②Hans H. Klein, Über Grundpflichten, Der Staat 1975, S. 155ff.同前注③, Badura书, S. 868。
(二)作为独立宪法范畴的基本义务
近年来,德国学者开始挖掘基本义务在宪法上的独立价值。比如施托贝尔就认为,基本义务属于宪法的结构原则。①Rolf Stober, Entwicklung und Wandel der Grundpflichten, in Norbert Achterberg/Werner Krawietz/Dieter Wyduckel (Hrsg.),Recht und Staat im sozialen Wandel: Festschrift für Hans Ulrich Scupin zum 80. Geburtstag, Duncker & Humblot, Berlin,1983, S. 643.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本义务作为国家主权的产物,在功能上,其在现代国家是保护自由、生命和财产的前提条件。这其中的关系可以从纳税义务上看出来。税是国家财政的前提条件,尤其对社会国家履行宪法任务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国家主权的自由就取决于它的宪法是否规定了基本义务。第二,基本义务作为解释规则,比如忠诚义务,不仅具有宪法位阶而且也是宪法任务,原则上公职人员必须遵守。同时,立法者不能通过宪法修改来废除忠诚义务,因为它是不可修改的。对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来说,忠诚义务成为解释公职时的规则和指导方针。问题是:基本义务提供了何种解释标准?仍然以忠诚义务为例,首先,必须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公职人员的忠诚义务,因为它的具体化必须符合公职传统;其次,宪法史必须区分不同的公职传统,因为立宪君主和魏玛共和都规定了公职人员的忠诚义务,但是后者所讲的不可废除的忠诚义务与前者所讲的全力以赴的义务需要区分。在民主国家,公职人员应当维护行政的合法性,它必须取代传统的职业生涯原则。第三,基本义务作为主观义务,其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个人的一种主观宪法义务。施托贝尔指出,过去人们用被动地位来理解基本义务是不太准确的。本质上,基本义务应当采用与基本权利相同的标准。比如要求公民不作为的服从法律义务是一种消极地位,要求公民进行实物、金钱或者服务的给付义务是积极地位,以政治参与为目的的接受荣誉职位义务是主动地位。②同前注①,Stober书, S. 51。
施密特也对耶利内克的地位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耶利内克的理论存在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一方面,耶利内克采用了行为方式标准,由此区分了不作为请求权的消极地位和给付请求权的积极地位。另一方面,耶利内克又把权利所要实现的目的作为分类标准,他强调主动地位是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反过来则没有权利形成。同时,施密特对“地位”这个词本身也提出了质疑。耶利内克用“地位”是来说明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更多是用法律关系或者个人对国家的联系,反之用“地位”则混淆了作为法律关系主体资格条件的身份(Eigenschaft)和法律关系本身。所以,施密特建议回归法律关系的概念来说明基本义务。在基本义务关系中,直接参与人是公民和国家。公民是义务主体,国家是权利主体。同基本权利区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样,基本义务也有必要区分义务能力(Grundpflichtfähigkeit)和义务履行能力(Grundpflichtmündigkeit)。义务能力就是成为基本义务主体的资格,义务履行能力就是能够独立和自负其责地履行基本义务的可能性。义务能力原则上与权利能力是相关的,义务履行能力则取决于年龄。比如儿童要承担纳税义务,但是只有成年人才需要缴纳。在基本法律关系中,间接参与人包括负担人(Belasteter)和受益人(Begünstigter)。负担人是指履行义务将导致经济上受损的人,比如接受荣誉职位的义务对于其他劳动者构成负担,因为从收益的角度阻碍了他的劳动力的行使。再比如纳税义务对顾客构成负担,因为税提高了商品价格。原则上国家是基本义务的受益人,但是除了国家之外,基本义务还会使其他公民受益。比如和平义务、财产的牺牲义务。特殊的是尊重人性尊严的义务,国家并不会从中受益,受益的仅仅是其他公民。基本义务的受益人并不限于本国公民,比如公民的和平义务也对外发生效力,国际法义务对外国和国际组织有利。③参见前注⑥,Schmidt书, S. 82-86。
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出发,施密特阐述了基本义务的三种功能。(1)对国家来说,基本义务意味着自我证明和自我维护。它使国家教育的目标变得可能,唤醒公民并形成公民意识。基本义务作为整合的手段,①同前注④,Isensee书, S. 618。使公民形成宪法理解和宪法意识。基本义务在国家权力的所有领域发挥作用,它赋予立法者立法义务、为行政和司法提供解释指引。②同前注⑨,Götz书, S. 118;参见前注⑩,Luchterhandt书, S. 543ff。(2)对于国家和公民来说,基本义务将宪法中的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连接在一起。一方面,它使公民直接与国家发生联系,排除了中介的权力。如果说基本权利是一种消极的权能规定,那么基本义务就构建了一种积极的权能规定。它敦促基本权利行使的节制、减少个人的放任。就此而言,它提醒公民注意在国家中的共同责任。另一方面,通过基本义务的承担,强化了负责任的民主参与的政治要求。鉴于公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基本义务构建了集体生活的规则样板。(3)在国际法领域,通过公民的和平义务,国家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的任务,侵略战争被禁止,国际法义务也被接纳成为宪法的一部分。③参见前注⑥,Schmidt书, S. 295-297。
五、为公民基本义务辩护
在笔者看来,目前有关公民基本义务的争论,主要原因在于公民基本义务并未在宪法上取得一个稳固的理论基础。即使在德国,人们对基本义务的理论依据也提出了种种批评。比如对于古斯的基本义务是为了国家存在的观点,有学者就指出,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古斯认为国家的存在先于宪法,但是无论如何立宪国家是以宪法为基础的。④同前注②, Randelzhofer书, S. 607-608。对于基本义务是来源于社会国原则的观点,由于社会国原则的内涵不够明确,更多地是一种国家目标规定(Staatszielbestimmung)。所以,一些反对意见认为,将其作为基本义务的来源是不可能的。⑤Ernst Forsthoff, Begriff und Wesen des sozialen Rechtsstaates, VVDStRL 12 (1954), S. 25ff.; Karl August Bettermann,Grenzen der Grundrechte,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1968, S. 18f.对于基本义务来自于与基本权利的对等性的观点,卢赫特汉特认为,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和第3条第1款并非在正当化基本义务,而主要是防御国家的自由权和平等权。⑥同前注⑩,Luchterhandt书, S. 443。对于基本义务来源于人性尊严的观点,施特恩反对说,人格尊严并不属于内在的义务。⑦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1994, S. 1024.由此可见,德国学者对于基本义务的理论基础并未达成共识。为此,有必要为基本义务寻找一条新的论证思路,而这条新的论证思路的核心就在于对作为基本义务的主体的公民身份的理解。
什么是公民?通说认为公民就是享有一国国籍的人。但这种完全形式化的理解并不符合公民概念产生以来的历史。公民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因为公民(citizen)源自拉丁语的civis或civitas,其中civis指古代城邦,而civitas是希腊语polites一词的拉丁语翻译,意指某个希腊城邦的一个成员。⑧商红日:《公民概念与公民身份理论——兼及中国公民身份问题的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⑨刁瑗辉:《当代公民身份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2页。古希腊的公民资格并不仅具有归属性,还具有参与性。也就是说,参与城邦事务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充满了道德意味,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为了换取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美德。⑨所以,在古希腊或者古典公民观中,公民与城邦是结合的关系,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不该认为公民拥有其自身,因为所有的人都属于城邦,每个人都只是城邦的一部分。但是,近代公民观却是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随着享有自治特权的自由市的出现而出现的。如法文的citoyen、意大利文的citadino、德文的bürger以及瑞士所使用的bourgeoisie都具有相同的意涵,即个人离开乡村进入自由市,从而得以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由自由市民所组成的市民社会成为一个自治的领域,不受政治势力管辖。①陈淳文:《公民、消费者、国家与市场》,载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民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第282页。因此,近代公民观其实是市民观,市民与公民的区别在于,市民关注的是其个人利益,而公民关注的是公共利益。所以,市民要求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不干涉,尤其是经济活动上的自主,强调政治(国家)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区隔。这种市民主义的公民观导致权利成为公民身份的象征,从18世纪的自由权利到19世纪的政治权利再到20世纪的社会权利,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的“公共属性”的减弱,即过分强调公民个人享有的权利而忽视公民对共同体或国家应尽的义务,从而使国家内部产生了离心力,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从结合变成了区隔。这种市民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缺陷导致了现代共和主义公民观的复兴。②[美]彼得·雷森伯格:《西方公民身份传统——从柏拉图到卢梭》,郭台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5页。共和主义公民观就是要恢复古希腊或者古典公民观中的道德成分,强调公民身份的公共性质。这种公共性质一方面体现在公民身份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一个好的公民在受到吁请时会承担起这些责任——从遵守交通规则、尊重他人权利这些日常的要求,一直到纳税、服兵役这些更为繁重的义务。另一方面体现在公共参与,好公民在受到吁请时固然会承担公共责任,但是他们不会总是被动地等待别人发出吁请,相反,他们会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③同前注⑨,刁瑗辉书,第109页。因此,现代公民是一个蕴含着公私两面的概念,④高全喜:《论公民——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野》,《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从私的角度讲就是强调个人权利,从公的角度讲就是强调公共义务和公共责任,阿克曼称其为私人公民(private citizen)。⑤[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326页。由此可见,公民身份是由各种认同、义务和权利组合而成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⑥[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17页。更准确地说,承担基本义务就是公民区别于私人的地方,也就是公民概念中“公”的部分的体现。
当前我国宪法学界对公民基本义务的质疑或者担心,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1)有的发达国家宪法上没有规定基本义务,比如美国,可见基本义务并非宪法所必需的;(2)宪法规定了基本义务就容易强调基本义务而轻视基本权利,这对于保障基本权利本身就不足的我国容易使人不放心;(3)宪法即使规定了基本义务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基本义务仍然要靠法律来实现,既然如此,义务由法律来规定就可以了。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这基本上是个伪问题。因为美国宪法上没有规定基本义务并不代表他们认为公民不应当承担基本义务或者美国公民实际上不承担基本义务;⑦霍夫曼指出,美国联邦宪法不规定基本义务是出于一种自然法的思想,同前注⑤,Hofmann书, S. 47-48。基于同样的思想,美国联邦宪法最初也没有规定基本权利。但是,美国州宪法中有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比如弗吉尼亚州《人权法案》第15、16条,马萨诸塞州宪法第18条。同时,德国宪法上规定了基本义务也不代表德国就不重视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或者德国对基本权利的保护程度不如美国。因为现实是,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基本义务,有些没有规定,而且也无法比较到底是规定的国家多还是不规定的国家多。⑧比如,1788年至1945年的22部宪法中没有规定纳税义务的是90.9%,而从1946年至1955年的14部宪法中规定了服兵役义务的是78.6%。参见[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所以,无论是拿别的国家宪法有无规定还是拿有多少国家宪法没有规定来论证我国应否规定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对于第二种观点,同样是个伪问题。诚如前述,德国基本法规定了基本义务也没有导致轻视基本权利的现象,反之,难道将我国宪法上的基本义务条款全部删除后我国的基本权利保障水平就自动提高了?笔者认为,这是另一种否定文本的极端,即企图把所有的现实问题都归咎于文本。从德国基本义务发展的历史来看,宪法上有无规定基本义务与是否重视基本权利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主要还是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就是说,即使宪法上同时规定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但两者之间孰轻孰重是可以通过解释来解决的。德国学者所提出的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间的非对称关系的思考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这是个真问题,值得讨论。关于基本义务与法律保留的关系,首先,有些基本义务,比如作为义务,的确需要通过法律来实现,但这并不是说用宪法来规定基本义务没有意义,这恰恰反映了具有直接效力的基本权利相对于不具有直接效力的基本义务的“优越地位”,同时也防止了国家依据抽象的宪法规定让公民承担无限的基本义务。其次,不通过法律来实现的基本义务也是存在的,比如容忍义务和不作为义务。同时,不通过法律来规定制裁的基本义务也是可能的,比如直接用宪法来规定制裁。这又恰恰反映了宪法上的基本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区别。
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一致性”学说,这种学说如果被滥用将导致用基本义务来否定基本权利的后果,①参见林来梵:《论宪法义务》,《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第二辑。从德国学者的讨论可见,所谓“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一致性”并非是指“每一个基本权利都对应基本义务”或者“公民负有行使基本权利的义务”,②德国的例外是父母对子女的教养义务,学者认为,这是说父母不享有不教养子女的权利。对于我国来说,例外就是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劳动义务和受教育义务的内涵,参见王锴:《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法学家》2008年第4期;王锴:《从一则案例看在家教育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兼谈我国宪法上受教育权与受教育义务之内涵》,《判解研究》2007年第4辑。而只是对公民相对于国家既享有基本权利又承担基本义务的身份的说明,就像我国宪法第33条第4款所规定的,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责任编辑:姚魏)
DF2
A
1005-9512(2015)10-0116-13
王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研究——以我国宪法第51条为中心”(项目编号:11YJC82011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