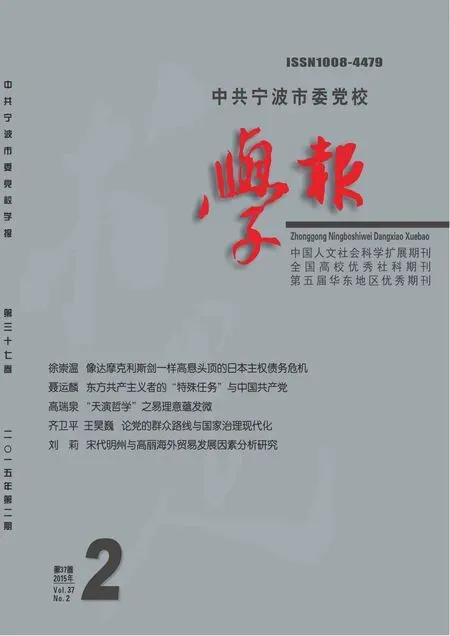提升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研究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
提升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研究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
政治效能感意指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政府的回应性抱有一定的信心。它影响着人们是否参与政治和如何参与政治,也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即公民自身政治知识水平偏低、政府回应性不足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导致了公民的政治冷漠、政治不信任,将民众引向暴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追求和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其路径在于,提高公民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加强回应型政府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平台的建设与管理。
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作为公民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个人对其能够影响政治的信心,这种信心将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一个人的行为。列宁曾经这样批评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1](P218),列宁的批评恰当地揭示了无政府主义者对自己和政治毫无信心的心理状态,也即政治效能感的严重缺乏所导致的极端心理。当前,一些人在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时,不是诉诸法律,或通过其它正常途径向党和政府提出要求,希望以此获得党和政府的重视。这些人政治效能感的有无或高低,能对这一现象作出某种程度的解释。
一、政治效能感的内涵与功能
政治效能感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被认为是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态度变量。艾布拉姆森曾经认为,在美国,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仅次于政党认同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学者们对政治效能感内涵虽有不同认识,但其影响公民政治行为的重要变量却在学者们中间达到了共识。
1.政治效能感的内涵
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坎贝尔(Campbell)等人最先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研究,他在研究美国公民的选举行为时发现,政治效能感是除政党认同、问题取向和选民取向之外的第四个影响公民选举行为的因素。在他看来,政治效能感“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也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觉。是公民感受到政治与社会的改变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在这种改变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感觉”。[2](P187)阿尔蒙德和维巴提出了公民能力感这一概念,表示公民对自己影响政治的能力的感知。他们发现,在其所研究的五国中,那些具有较强政治能力、更多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他们也更倾向于表达对选举的满意度,并确信自己对地方政府的活动是有影响力的。可见,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政治效能感是指向公民自身政治能力的。戴维·伊斯顿和丹尼斯以儿童政治社会化为视角探讨政治效能感,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概念,“政治效能感是以三个彼此独立但又紧密关联的要素表现出来,即作为规范的政治效能感、作为心理学倾向或感觉的政治效能感和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政治效能感”,伊斯顿指出,就作为一种规范来说,政治效能感是指民主制度中的成员应当能够影响政府,政府也应当具有回应性;就作为一种感觉来说,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必须感觉到自己在政治自我认同上是有能力的,是感觉自己能够影响政府,政府能够回应个体;就作为一种行为来说,是在政治上的行为表现,也就是其在政治活动中形成真正的影响。[3](pp25~26)莱恩(Lane)认为政治效能感包含两种不同的成分:一是与他人相比,个人认为自己对政府具有影响力;二是面对政治体系而言,个人认为政府会对自己的要求有所回应。据此,莱恩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影响政府的感觉,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个体相信当权者或者政府应该回应民众的感觉”。[4](pp141~143)国内学者李蓉蓉在研究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时,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内在政治效能感划分为“了解型”和“影响型”,将外在政治效能感划分为“重视型”和“回应型”[5](pp79~85),以此测量不同类型的政治效能感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论述,我们将政治效能感初步界定为公民觉得自己了解政治,并对自己能够影响政治的能力抱有信心,同时,公民对政府重视和回应自己的诉求也抱有信心。
2.政治效能感的功能
政治效能感之所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是因为它的有无和强弱,对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李蓉蓉认为,政治效能感对个体政治行为起到的主要是一种指导或引领作用,而非必然导致行为的发生。台湾学者郭秋永也认为,在英美国政治系统中具有政治效能感的公民中,只有部分公民诉诸实际的政治参与行为,而较多的具有政治效能感的公民并没有转化为参与行为。[6](pp320~322)尽管如此,政治效能感内外两个层面的交叉组合,影响着公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选择。公民良好政治效能感影响着他们的政治参与、政治态度,从而对政治稳定产生影响。
首先,政治效能感影响人们是否参与政治。坎贝尔认为,“对于选民是否卷入选举更为深入的考虑应该是其政治价值和态度,不同个体参与选举程度不同,是因为其基本的政治态度不同,政治效能感就是这样一个基本概念”。[7](P187)因此,学者们将政治效能感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指标。日常经验告诉我们,那些觉得自己不了解政治,也不可能影响政府及其官员决策,或觉得政府也不会重视自己和回应自己要求的人,不大可能选择政治参与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或提出自己的要求。而那些具有较高政治效能感的人,则更倾向于参与政治。之所以会如此,安东尼·唐斯等人所开创的理性选民理论可对此作出很好的解释。理性选民理论认为,“每一选民都将他的票投给他相信将比任何别的政党提供给他更多利益的政党”。[8](P33)选择投票意味着公民感觉自己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其选票能够为其带来收益;而那些政治效能感较低的人,则会觉得投票影响不了官员,也改变不了政策,参与政治对他们来说“得不偿失”,不如不参与政治。
其次,政治效能感影响人们如何参与政治。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虽然公民觉得自己能够影响政府和实际对其产生影响不一样,或者公民试图对政策施加影响,但政府及其官员可以不为所动,但是,公民“对发挥政治影响的能力的感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公民将尝试用什么方式影响政治,公民的“尝试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9](pp224~226)那些对感觉自己了解政治、能够影响政治,并且觉得政府也会重视和回应自己的公民,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化行为去参与政治。而那些认为自己了解政治,并能影响政治,但却觉得政府及其官员不可能理会自己的公民,更有可能采取非制度化参与行为,如建立黑社会组织作为替代性选择,或制造谣言以向政府施压。查尔斯·蒂利用“信任网络”来描述人们的替代性选择,“信任网络”会用多种方式逃避公共政治的整合,从而危及社会稳定。谣言则被当作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10](pp120~124)那些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很低的人,则会沉默,待到“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候”,则会爆发或“揭竿而起”。亨廷顿所说的“钟摆式”农民,便是从“沉默”到“爆发”的最好例证。而那些对自己影响政治的能力持有较低信心,但对政府抱有较高信心的人,则更有可能选择服从政府及其官员。
再次,政治效能感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政治效能感的两个层面告诉我们,它表明的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国公民政治效能感较高,则说明该国公民不仅自认为有可能改变本国的政治决策的程度越大,也表明该国公民感觉到本国政府和官员对他们的重视和对其要求的回应,这些都说明了一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因此,政治效能感成为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当前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原因及影响
1.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之原因
政治效能感研究在我国虽然历时不久,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当前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总体偏低①,致使一些人要么对政治“敬而远之”,要么则采取一些非制度化参与方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首先,公民自身能力偏低是其内在政治效能感偏低的首要因素。政治效能感首先意味着公民感觉自己了解政治,能够影响政治。其首要条件便是公民个人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一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人,也会很难感觉到自己对政治能够有所影响。此外,社会分层也是当前我国公民内在政治效能感偏低的原因之一,一个社会当中,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普通民众。处于政治权力外围的公民,很难说对自己了解政治、影响政治的能力抱有多么强的信心。而我国又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尽管改革使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们仍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一群人,在陆学艺所划分的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中,农民处于比“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好一点的第九层。[11](P47)其他群体虽有政治效能感较高者,但并不能改变中国公民政治效能感总体偏低的现状。
其次,政府及官员的回应性不足是导致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偏低的重要因素。公民具有外在政治效能感,意味着其感觉到政府及其官员重视自己和自己的诉求。而一个对公民的诉求不予理睬的政府及其官员,是很难塑造公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领导的政府也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目标的政府,本质上讲,中国的民众应当具备较高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随时准备倾听人民的意见,回应民众的呼声。但实际生活中,党和政府的回应性不足常有发生,原因在于,一是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人们的利益意识觉醒且更加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变迁要求政治体制的变革,但无法保证二者会同步变化。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与政治体制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便突显出来,当前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回应性不足,这种“体制性迟顿”是主要原因。二是少数党员干部宗旨意识不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薄,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对民众的诉求不放在心上,或者等闲视之,或者胡乱回应②,造成了民众外在政治效能感偏低,也即感觉不到政府及其官员对其诉求的重视和回应。
最后,政治参与路径不畅是当前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一般认为,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朱妍借用Rodgers和Huber等人的观点认为,“参与议政渠道越是畅通,政治参与机会越多的群体,政治效能感越强,也就是对自身有政治影响力的信念越强;反之,如果参与渠道很少,经常在政治上被排斥,参政议政受到阻碍,便可能引致较低的政治效能感,也就是说认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是很弱的”[12](pp84~9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理论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我国民众提供了广阔的参政议政平台,应当说,公民在这些领域的政治参与为提高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且不说这几个根本的政治制度无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这几个平台本身,也不可避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例如,人大制度中农民代表有限,农民阶层的声音得不到有效表达;政治协商制度相对来说具有高端性,一般民众难以接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最贴近普通民众,但有时候因一些地方政府的干预,自治组织行政性有余,自治性不足。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从而影响到其政治效能感的增强。
2.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之影响
政治心理学理论认为,一定的政治心理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效能感作为政治心理的一种,无疑对人们的政治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阿尔蒙德和维巴提出人们某种程度上的“臣民能力”是稳定民主的重要条件之一,“作为有能力的臣民,他们认为……他们将受到当局公正的对待,其观点也将得到考虑,这并不是由于其试图施加他的影响,而是由于政府官员是由一套束缚其专断权的法则所控制的”。[13](P265)政治效能感偏低的公民更易于形成这种臣民能力,这种臣民能力对政治体系的益处在于,它有助于防止民众的“参与爆炸”,从而维持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但政治效能感偏低除了有这样的正面作用外,更有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政治效能感偏低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和对政治的疏离。民主社会需要公民对政治的参与,而参与政治的心理前提则是人们觉得自己对政治有一定的影响力,或政府及其官员对自己的重视和回应。而政治效能感偏低,或者说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有较低评估的公民则更可能选择远离政治,或对政治持一种冷漠的态度。杨光斌认为,政治冷漠有四个方面的缺陷,一是那些没有参与政治的人没有合适地被代表,二是广泛的政治冷漠给那些为所欲为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政府的机会,三是政治冷漠不利于培养人们的判断水平,四是广泛的不关心政治,不仅是政治制度软弱的表现,也是政治制度软弱的原因。[14](pp99~104)政治上的冷漠或疏离有时候还迫使人们进行替代性选择,这在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察中体现出来。熊易寒对上海的调查发现,就维权方式来说,同乡支持网络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首选方式,有23.7%的受访者表示优先选择向同乡或亲友求助。同时,本应在经济纠纷和维权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工会组织和党团组织并没有得到劳动者的认同,只有11.4%的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选择“工会组织”、“党组织”和“团组织”。[15](pp90~104)民众如果长期远离政治而做出替代性选择,必将对社会秩序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政治效能感偏低导致公民政治不信任。莱恩的外在政治效能感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对民众的需求不仅要重视,还要及时回应。当前我国公民不仅内在政治效能感较低,外在政治效能感更由于一些官员的回应性不足而呈偏低状态。公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偏低与其政治不信任直接相连,甚至是相互加强。民众对政府政治信任度较低,则其认为政府重视和回应自己的可能性则较小;反过来说,民众越是认为政府不可能重视和回应自己的需求,则越不信任政府。当前,公民尤其是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治不信任感较强,如肖唐镖通过对江西、江苏等省农村的调查,发现农民对党和政府的评价中,“中央的威信是最高的,次为省,再次是县,然后是乡,最后是村”,“在他们看来,遥远的、抽象的上级政府是好的,而身边的、常接触的政府是差的甚至是坏的”。[16](pp10~17)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对福建、浙江等省农民进行的调查问卷研究显示,农民对于上级政府的信心比对下级政府的信心要高,越是低一级的党委的威信越低。[17](pp209~226)民众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诉求未能得到地方政府及官员的重视和回应,或民众觉得他们的诉求不可能得到重视和回应,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偏低,加强了政治不信任。
最后,政治效能感偏低将民众引向暴力。政治效能感较高的公民更倾向于用温和的手段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如通过参加会议、投票、竞选等制度化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相反,政治效能感较低的公民更有可能采取非制度化方式去达成自己的目标,一些政治效能感极低的人,开始时可能会选择容忍和沉默,一旦达到了心理承受极限,这些人将不免采取极端方式以发泄自己的愤懑和怨恨。政治效能感偏低的人之所以容易走极端,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不仅自己不了解政治,也无法影响政治和通过政治的途径满足自己的要求,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感觉到政府及其官员根本不会考虑他的感受,也不会回应他的诉求。传统社会中,农民要么忍受,要么爆发,在“忠顺”与“反叛”之间摇摆,便是专制政治下,政治效能感极低的民众的典型行为方式。当前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用极端方式以引起其他人或政府关注的人③,这些人的行为结果虽严重程度不同,但其原因却有相同之处,当事人都表现出了极低的政治效能感,即对自己能够影响政治的可能性,以及政府重视和回应自己诉求完全丧失信心,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均极低的组合,将这些人引向了用暴力,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之路。
三、提升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之必要性与紧迫性
我国公民偏低的政治效能感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如能够缓解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与政治参与体系发展不完善的矛盾。但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的负面作用后果更加严重,它不仅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或一些弱势群体远离政治,更让他们不相信政治,遇到问题时不寻求正当途径去改变于己不利的政策或决定,而是选择暴力或违法手段,这些行为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我们身边的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告诫人们,当前,提升我国公民,尤其是处于较为弱势的民众的政治效能感已经迫在眉睫。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要求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首先,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优越性在于,它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强调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和人民的权力,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8](P1031)。与之相反,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则在于,人民只是精英主义者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一种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19](pp395~396)在熊彼特那里,民主不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人民选择谁来统治自己。此时,人民的政治冷漠对精英主义者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状态。卢梭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有尖锐的批判,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在评价英国的议员选举时指出,“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以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20](P121)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因此,必须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政治、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唯有如此,掌握权力者才能有所忌惮,真正知道权力属于谁、掌握权力应当为了谁、掌权者应当向谁负责等根本性问题。只有切实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他们才有可能了解政治、关心政治和参与到政治中来,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同时,也有利于真正将权力关住。
第二,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要求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公民政治效能感高低不仅影响公民是否参与政治,同时,也影响其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我们知道,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政治参与有序,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只有在一个和谐社会中,公民才有可能真正的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一个动乱不堪的社会恐怕很难保证其公民享有政治参与权利的。④公民较好的政治效能感是有序政治参与的基础和前提,较好的政治效能感意味着公民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回应性抱有较高的信心,这种信心能够促进人们选择更加温和的方式介入政治,而那些对自己的能力和政治均抱有较低信心的人则更有可能选择暴力去介入政治。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利益和权利意识觉醒,维权意识增强,维权行动增多,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让他们了解政府及其官员的决策过程和方式,提高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使民众不仅感觉到了解政治,而且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影响政治,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公民引导到有序政治参与的轨道上来,而非总是以“散步”、参与“无直接利益冲突”和制度网络谣言等这些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方式去影响政治。
第三,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有两大历史使命,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此两大历史使命,无数仁人志士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各个阶级及其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救世方案,以期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但都未能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其武装全党,最终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实现了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使命。现如今,在和平建设的年代,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实现第二个历史使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无论是已经完成的第一个历史使命,还是即将要完成的第二个历史使命,都不是中国共产党能独自完成的,而必须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一项人民群众袖手旁观的事业是很难得到完全实现的。这就要求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让他们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参与到这个伟大事业中来,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四、提升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之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已经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要求我们进一步认清公民政治效能感的积极作用,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引导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提高公民经济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增强公民内在政治效能感。已有研究表明,那些具有较高的经济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公民,更倾向于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政府对自己要求的回应性抱有信心,政治态度也更加地温和,他们在遇到问题时,也更可能采取正当途径或者说体制内途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我国公民总体政治效能感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受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相对于成熟理性的公民要求来说,还有一些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为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现阶段来说,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提高农村居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使他们掌握基本的政治知识,从了解政治做起,提升他们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同时,由于我国有上亿农民工生活工作于城市,这些人的政治心理状态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加强这些人的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和就业保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使他们融入城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使他们摆脱“游离”和“边缘”的状态,增强他们影响政治的信心,即政治效能感。
第二,加强回应型政府建设,提升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公民遇到问题时,从政府及其官员那里得到的重视和回应是影响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重要环节。政府及其官员对公民的问题做到及时有效地回应,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效能感,而对公民诉求的漠视则会使公民对政治失望和拒斥。卢坤建认为,及时反应是回应型政府的一个典型特征,“回应型政府要求政府对于社会诉求,不能不(回)应,也不可久拖不(回)应,而必须及时、有效地予以回应,否则,就是失职,就不能称之为回应型政府”。[21](pp66~70)但是,陈国权和陈杰认为,“我国政府回应性的缺失是普遍存在的”,其原因在于,“民主政治缺失、政府制度的不健全和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22](pp36~41)。除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外,我国政府回应性缺失的原因还在于少数官员的官本位思想。因此,当前加强回应型政府建设,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政府回应社会诉求的法律法规,政府及其官员必须及时有效地对民众诉求作出回应,对因不能及时回应或胡乱回应民众诉求而引起不良社会后果(如群体性事件等)的官员不仅要追究行政责任,而且要追究法律责任;其次,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网络平台,政府可以利用网络传播及时有效的优势,对民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做到及时澄清,有效回应。这就要求政府和官员加强学习,不仅要学习新兴媒体的有关“硬知识”,更要学习如何在新兴媒体上如何发声、如何回应民众诉求的“软知识”,而不至于像个别官员那样,一在网络上发声、回应就被民众揪住辫子。只有政府及其官员及时有效地回应民众的诉求,才能使民众相信政府和官员,从而增强他们的外在政治效能感。
第三,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提升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能增进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其原因在于,参与能够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政治,掌握参与政治的知识和技巧,卡罗尔·佩特曼认为“一定的参与经历使个人更好地适应未来进一步的参与活动”。[23](P44)我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基本保障了公民在各个层次上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这些制度的顺利实施,将广大人民群众从以往那种毫无政治地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但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并不代表其已经完善,当前,需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增加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群众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比例,赋予他们以更多的发声机会,将他们的声音传递给党和政府。同时,关注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改变城市农民工既不能在乡参与政治,也无法在城市参与政治的“边缘”状态,放宽基层政治参与的户籍限制,使他们能够通过制度化途径为自己的权益“呼吁”,只有民众能够通过制度化途径实现自己的利益时,才能促进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忠诚”和“信任”,而“制度信任”是建构公民长期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
第四,运用和有效管理现代网络技术平台,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增强政治效能感。网络技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平台,网络民主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态”⑤。网络为民众提供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平台的同时,如人们经常所说,它也是把双刃剑,有的时候,表面看网络上“民意滔滔”,实际上只是少数所谓的“意见领袖”⑥在发声,在“代表”着,甚至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意见。有的时候,所谓网上民意,只是有失偏颇的个人观点。[24]这种参与本质上讲不仅不能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反而导致人们真正的无力感,感觉被裹挟于网络舆论的洪流之中,更不用说政治效能感的增强了。因此,加强对网络政治参与平台的管理是增强公民政治效能感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严厉打击利用网络传播谣言,谋取私利的行为,构建平等、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平台,才能真正提供公民政治效能感。
五、结语:信心是政治稳定的基石
简单地说,政治效能感即是公众对自己和对政府抱有信心,而信心是政治稳定的基石。之所以如此,在于只有对自己的别人抱有信心的人,他的眼光才会长远,采取行动时也才会更加温和与理性。而一个对自己和别人都丧失信心的人,其态度和行为中的极端和非理性恐怕不可避免。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自身能力不足、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存在的不完善性等造成了我国民众政治效能感偏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民众过度参与导致政治体系不稳,但也使一些人对自己和政府信心不足,对政府和官员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个人的信念不足,遇到问题不能心平气和,情绪容易极端化,给他人和自己都造成了伤害。因此,当前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增强他们对自己和政府以及整个制度的信心,是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举措,可以说,信心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石。
[注释]
①这一结论性观点由如下一些学者的研究得到证明,李蓉蓉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进行了实证调查,认为“历时30年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于农民而言,只是具备了最为基本的政治效能感”。李蓉蓉还对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进行了实证调查,发现居民的社区内在政治效能感较低,相对来说,其社区外在政治效能感较高。熊光清对两代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进行了调查,并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两代农民工在政治效能感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两代农民工的内在政治效能感都不算太高,而外在政治效能感都比较低”。学者们的调查虽然零散,但涉及到中国社会几个主要群体,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可以说,有较高的代表性,我们在此加以采信。具体论述分别可见:李蓉蓉:《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0卷第4期第79~85页;李蓉蓉:《城市居民社区政治效能感与社区自治》,《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3期第53~57页;熊光清:《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分析——基于五省市的实地调查》,《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32~37页。
②例如,四川阆中市国土局在回复民众有关“商品房产权只有40年,是否意味着40年后还要当一次房奴”的担忧时,居然回应说“40年后,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个世界,不要考虑太长远了”,被网友戏称为“神回复”。
③如2013年6月7日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制造者陈水总、2013年7月20日首都机场爆炸案的制造者冀中星等人。
④2013年7月以来的埃及便是最好的例证,公民走上街头,抗议、流行、示威不断,看起来像是全民参与政治,实际上大多数人只是被“卷入”政治,在混乱中“被享有”着所谓政治参与的权利。
⑤叶敏:《中国特色网络民主形态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3月20日。
⑥所谓“意见领袖”,指“在每个领域和每个公共问题上,都会有某些人最关心这些问题并且对之谈论得最多”,这些人影响甚至塑造别人的意见。见[美]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伯纳德·贝雷尔森、黑兹尔·高德特:《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唐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1]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Warren E.Miller.The Voter Decides,Row,Peterson and Company,1954.
[3]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s Political Efficacy[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1,No.1,1967.
[4]转引自:Paul R.Abranson.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M].W.H.Freeman and Company,1983.
[5]李蓉蓉.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6]郭秋永.抽象概念的分析与测量:“政治效能感”的例释.方萬全、李有成.第二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文集[C].
[7]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Warren E.Miller,The Voter Decides,Row,Peterson and Company,1954.
[8][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0]郭小安.络谣言的政治诱因:理论整合与中国经验[J].武汉大学学报.2013,(3).
[1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2]朱妍.中产阶层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有效性的评价——比较中国与越南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J].青年研究,2011,(4).
[1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4]杨光斌.政治冷漠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3).
[15]熊易寒.新生代农民工与公民权政治的兴起[J].开放时代,2012,(11).
[16]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17]Lian Jiang Li.Polit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Petitioning in Chinese Countryside,Comparative Politics,Vol.40,No.2(January 2008).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1]卢坤建.回应型政府:理论基础、内涵与特征[J].学术研究,2009,(7).
[22]陈国权、陈杰.论责任政府的回应性[J].浙江社会科学,2008,(11).
[23][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4]谢新洲、王秀丽等.网上民意,能否代表主流民意?[N].光明日报.2010-6-10.
责任编辑:刘华安
D668
A
1008-4479(2015)02-0073-08
2014-06-13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方向”)和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编号:10JZD0001)阶段性成果。
王可园(1981-),安徽庐江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农民政治行为、执政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