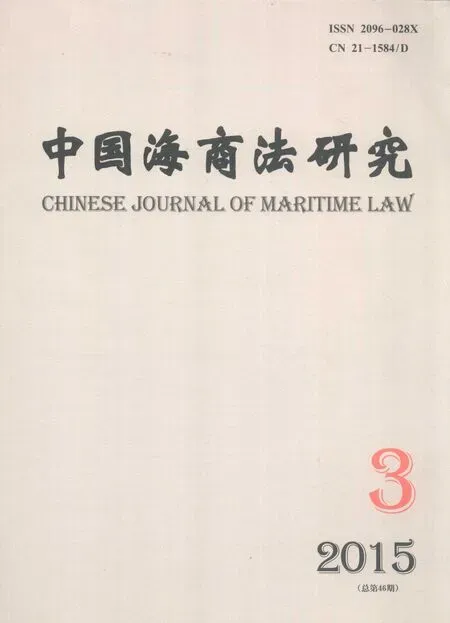海法概念的国际认同
初北平,曹兴国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海法概念的国际认同
初北平,曹兴国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海法概念始于罗德海法,是指所有与海有关的法律规范,其在中世纪得到普遍认同和运用。虽然近代海商法、海洋法等概念的发展以及陆上立法的兼并使海法概念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海洋法律所呈现的碎片化使海法概念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回归价值。建设海洋强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使海法概念对中国的价值更为突出,即在海法这一国际认同的概念统合下,通过海法体系的构建,完成体系化完善中国海洋法律的目标。
海法;国际认同;海商法;海法体系
近年来,为保障和促进中国海洋权益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学界关于构建海法体系的呼声日高,海法(sea law)的概念愈来愈频繁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但值得研究的是,国际上是否也存在海法的概念?海法和与之相近的海商法(maritime law)、海事法(admiralty law)及海洋法(the law of the sea)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海法概念回归的价值何在?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清晰界定海法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必要前提,也是海法概念能否在当代获得广泛认同的重要支撑。有鉴于此,从海法概念的历史认同开始,通过对海法文本内容以及演变历程的梳理,界定海法概念的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海法概念在当代回归的现实价值。
一、海法概念的历史认同
海法这一概念并非学者在当代的创造,其作为调整海上事务的法律形态不仅在历史上客观存在,而且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
(一)海法概念的萌芽与出现
海法概念的出现源自海法文本的出现,海法文本的出现则源于海洋活动对法律调整的需求。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自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780年的汉莫拉比法典开始,就已经出现调整海上活动的立法内容①汉莫拉比法典第234条至第240条以及第275条至第277条规定了有关船舶建造、船舶租赁、沉船责任分配、船舶碰撞责任分配、雇用海员应付工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与苏美尔法律手册(SumerianLawsHandbook,约公元前1700年)②苏美尔法律手册第(a iv42-v11)部分规定了背离船舶原定航线的责任问题;第(b v12-20)、(v21-26)部分规定了在租用船舶时破坏船舶及船舶沉没的责任;第(c v27-31)、(v32-36)部分规定了船舶碰撞的责任;第(d v37-44)部分规定了船舶租赁的租金支付。、摩奴法典(TheLawsofManu,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0年)③摩奴法典中相关的立法内容包括货物交易中禁止的行为与惩罚、国王定价、货物的重量和规格(第399条至第403条),航海专业人员薪酬与运费(第156条、第404条、第405条、第407条),船舶损害共同赔偿的规定(第408条至第409条)。以及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Justinian’sDigest—BookXIV,公元529年至公元565年)④查士丁尼时期编纂的学说汇纂中相关的法律内容包括两大部分:向船东提起诉讼的问题以及关于罗德海法中有关弃货的规定。一起为此后内容更丰富、独立性更强的海法奠定了基础,可视为海法的萌芽。
而海法概念在历史上的最早使用,可追溯到罗得海法(TheRhodianSea-Law)。罗得人是创设、整理和颁布海洋法律制度最早的民族。早在公元前约900年,他们就是当地的海上主宰,以其强大的海上舰队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著称于世。他们的航海法作为国家间通行的法律(law of nations),不仅被雅典城和爱琴海各岛所接受,而且得到整个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认可。虽然他们的法律没有在当时被记录下来,但以《罗得海法》命名的法律汇编于1561年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后又于1596年在法国的法兰克福出版)。尽管这两个出版的汇编的历史真实性受到学者的质疑,但罗得海法对后世的影响却无人置疑:其不仅是笔者搜集到的海法概念的最早起源,而且对许多海法制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⑤罗得海法分为人法、物法和债法三个部分,对船上工作人员的薪酬与职责、乘客与货主的权利义务、船舶所有权、货物所有权、海运借款与担保物权、海事合伙、海盗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对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海洋法律影响深远。同时,罗得海法可基本满足调整、规范当时海上活动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拜占廷帝国时期的皇帝安东尼才有“朕是陆地上的君王,但法乃海上之王,……与海事有关的问题应根据《罗得海法》做出裁决”的说法。[1]
(二)海法概念的普遍认同
如果说罗得海法是海法概念在历史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则中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相继出现的海法文本表明海法这一概念在当时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同。根据笔者的查证,当时直接以海法命名的法律文本就至少包括维斯比海法(TheSea-LawsofWisby)⑥维斯比海法共有70条。该海法对当时船长的权力,船员雇用和管理,运费的支付与货物管理,船舶引航与船舶碰撞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佛兰德海法(Sea-LawsinFlanders)⑦佛兰德海法共有24个条款,主要由判例法而来,涉及船长权力、船舶管理、货物处分、船员管理、引航、港口规定以及托运人权利等方面的规定。、苏格兰海法(ScotlandSeaLaw)⑧苏格兰海法共有十五章,由一个总则和十四个章节组成,其对船舶所有人的权利、商业买卖、水手、引航员甚至海盗行为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以及哥特兰海法(GotlandSeaLaw)⑨哥特兰海法在内容上与同一时期的佛兰德海法和苏格兰海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三部海法同源于奥列隆判例集(The Rules of Oleron),只是翻译的文本内容有所不同。。这些海法文本虽然多为民间的惯例编纂成果,但由于当时商人习惯法在海上贸易中所具有的支配地位,[2]这些海法在当时得到广泛遵守,具有等同于法律的效力。
而从文本内容来看,上述海法的调整事项从船东与货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到船长船员的权职与管理,从船舶的所有权到货物的所有权,从引航员的职责到船舶碰撞的责任划分,再从船舶的融资建造到对海盗行为的规定,囊括现代意义上民事、行政、刑事性质的法律规范,几乎涉及当时海上活动(主要是海上运输)的方方面面,能够满足独立调整海上活动的需求。同时,这些海法都出现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其并非当代国内法上的概念,它所包含的内容,承认并实行的地区范围不单纯地局限在一国之内。也就是说,这些海法的内容在当时的地中海地区具有很强的共通性,并得到广泛认可。正如学者所总结的:“海法实行商人自治,它自成体系,不受陆法和国家权力或者领土的管辖。在接近5 000年的时间里,它独立存在——不是由君主制定,而是逐渐地被编集成典并得到大家遵守。”[3]
因此,海法作为一个在中世纪得到普遍认同和运用的概念,其在当时所指称的是所有调整海上活动的法律规则的集合,是一个十分广义的概念。
二、海法概念的近现代演变
至17世纪,法律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民族国家和主权意识开始有机体化,国家主导的立法开始逐渐取代过去自发形成的跨越国界的习惯法。这种演变也逐渐渗透到海洋立法中——各国纷纷从保护本国海洋、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了属于各自国家的海洋立法。这种过程在丹麦1561年腓特烈二世的海事法典中就已经开始出现,随后在丹麦、瑞典和法国等国的海事立法中一起达到了顶峰。[4]同时,伴随着国际公法作为一个学科独立出现,新的法律学科不断细分,海商法、海洋法等概念相继从海法概念中剥离出来,中世纪普遍认同的海法逐渐走上演变之路。
(一)海商法对海法主体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在海法的演变过程中,海商法(maritime law)继承了其主体内容。maritime一词源于“mare”,其在当时仅是“海上”之意,[5]亦即泛指海上一切相关事宜。换言之,在早期,对maritime含义的理解仍是十分广义的,其与海法之间并无太大差别。以法国1681年路易十四颁布的《海商条例》(OrdonnancedelaMarine)为例(其名称中的marine即为法语的maritime),其内容包括海事审判人员、管辖权、船员、船舶、海事契约、港湾、海洋警察、渔业等,囊括与海有关的大部分法律规范。但此后,随着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maritime”一词慢慢演变为仅指当代意义上的“海商”事宜,而且此后有关海商的立法也逐渐将有关公法方面的内容排除:例如以1681年《海商条例》为蓝本制定的1807年《法国商法典》“海商编”就缩减了很多公法方面的内容。而发展到当代,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maritime law”是指调整海上贸易和航行、海上旅客及财产运输、海上事故以及在水域上进行商业活动而发生的合同、侵权以及雇员赔偿关系的法律规范。[6]
不过具体而言,对于“maritime law”含义的理解,目前世界各国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
在美国,“maritime law”的研究范围,除了实体法的内容之外,也可能包含一些程序法的内容。其中实体法一般包括:1.狭义海商法的一般内容:引航合同、共同海损、海上保险、船舶物权(船舶留置权、船舶优先权)、拖航合同、海难救助、海上货物运输、船舶碰撞、油污、残骸打捞、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2.海上劳动法:船员人身伤亡。程序法的内容则一般包括:1.海事管辖权;2.海事诉讼程序(包括对人、对物诉讼)等内容。[7-9]
而在英国,有学者将海商法(maritime law)的组成分为海上运输法(law of carriage by sea)、海上保险法(law of marine insurance)和海事法(admiralty law)。[10]3与美国法相比,英国法下的“maritime law”的研究范围通常并不涉及海上人身伤亡,但涵盖船舶买卖、建造、登记以及船舶安全管理方面的内容。[11-12]
另外在北欧,海商法学研究的领域除船舶物权、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租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上污染、船舶碰撞、海难救、共同海损、海上保险合同以及时效之外,还包括如下内容:1.船舶的国籍与登记,船舶的公共控制与入级;2.船舶的建造与修理合同;3.船舶买卖;4.航运企业的组建及公司的责任;5.船员的法律地位,雇佣合同、合同期限、船员的法律地位;6.海上侵权法,包括损失的种类及因果联系,侵权人的疏忽责任、严格责任、船东的转承责任和船东的合同责任、人身伤害索赔;7.海事调查等。[13]北欧学者认为,“‘maritime law’一词,通常是指适用于航运的一些法律规则,包括与海事(admiralty)和海上保险(marine insurance)相关的一些规则,尽管后者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主题区。这些规则是非常广泛的,它们也能包含合同成立及解释的一般规则。为避免该问题,最好将‘maritime law’界定为航运(shipping)所独有的那些法律规则。当然,在实际解决海上争议的时候,经常需要大量的合同法和侵权法的基本规则。海商法包括私法规则,也包括公法规则。即便是国际法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与之相关,例如,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以及国有船舶在外国港口扣押的豁免权。[11]1
此外,在研究“maritime law”这一概念时,不得不提海事法(admiralty law)这一概念。在美国,很多学者认为admiralty law与maritime law没有本质的区别,许多教材中也直接用“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来共同表述海商法①如Thomas J. Schoenbaum、Robert Force以及David W. Robertson、Steven F. Friedell、Michael F. Sturley等关于美国海商法的著作都是以“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命名的,他们对admiralty及maritime的含义不再做区分。。但英国学者在对“admiralty law”下定义时,认为其是指那些英国海事法院在行使其对与海有关问题的管辖权时所发展的法律,包括程序法在内。[10]1其具体内容可包括:海事诉讼的性质和范围、船舶物权请求权、船舶优先权及其他责任、一般海事请求、海事扣押程序、扣押后续程序、基金的分摊、船舶碰撞案件的程序、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事仲裁等。[14]
总而言之,海商法继承了中世纪海法的主要内容,其或以单独立法的形式(综合型或分散型),或以商(民)法典一部分的形式在当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也应注意的是,与中国通常认为海商法只是实体私法的认识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海商法的认识显然更为广义。在他们看来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公法和私法的集合,[15]其不仅包括海事程序法上的内容,而且也涉及很多通常我们认为属于行政法性质的内容。
(二)海洋法的独立与发展
在海法的演变历程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分支是海洋法(the law of the sea)。在中世纪前,虽然也有一些国家有将与之相邻的海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排斥其他国家使用的倾向(如在有关的同盟条款中写进“统治海洋”、“成为海上主宰”等字句),[16]但由于当时人类对海洋的利用能力仍十分有限,海洋自由、航行自由的观念仍占支配地位,因此,当时对海洋法的需求并不迫切。发展到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君主对土地的领有权开始向海洋方面发展,欧洲诸海中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分是处于某种权力的要求之外的。[17]在这种背景下,“邻接海域”等海洋法理论开始出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海洋法还未完全从海法中独立,有关船舶捕获方面的争议仍属于海法的调整范畴,有关海盗的规制也常在海法中出现。
海洋法里程碑式的发展出现于格劳秀斯于1609年发表的《海洋自由论》,该著作在理论上为“公海自由”奠定了基础,也由此引发了关于各国对海洋权利的论争,使得海洋法的相关理论得到跨越式发展;领水、有效统治等概念和原则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海洋法逐渐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得以独立发展。此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达,人们利用海洋的能力不断提高,各国之间对海洋权利需求的冲突使得法律调整势在必行,海洋法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有关海上航行、海洋渔业等国际公约的制定以及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国际海底制度等新海域制度的提出推动海洋法逐渐发展为国际法的一个独立分支。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则标志着海洋法(laws of the sea)这一概念正式在国际范围内得到统一和确认。至此,原本属于海法一部分的海洋法已经完全从中独立,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研究范畴。
(三)陆上立法对海法内容的兼并
除去海商法和海洋法对海法的继承和发展,很多的海法内容在其演变过程中未能得到独立发展,而是被陆上立法所吸收,或成为陆上立法的一部分,或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忽视。这一点在大陆法系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受法律部门划分的影响,有关海上刑法、海上行政法等的内容更多地被纳入一般刑法和行政法的研究范畴,以陆上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而设计、制定的陆上立法开始广泛地适用于海洋领域。而在这一过程中,海法内容的特殊性并未在被陆上立法吸收兼并的过程中得到完全重视,这也导致了相关海法内容的“死法化”。以海上刑法为例,各国在制定刑法典时很难注意其在海上适用的特殊性:比如有关非法悬挂国旗、船长不尽力救助海上人命等犯罪易被刑法典所忽视,船舶价值和海上清污费用的高昂也使得以陆上交通肇事罪的标准来定罪量刑不尽合理。因此,陆上立法对海法内容的兼并虽是各国立法发展中较为统一的趋势,但其负面效应亦引人反思。
总之,随着海上活动的频繁以及内容的多样化,中世纪粗线条的海法未能得到延续:其部分内容得以独立发展而保留其历史渊源的特殊性,另一部分内容则被陆上立法所兼并,并伴随着“死法化”的危机。
三、海法概念的当代回归
虽然粗线条的海法文本因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而未能得延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海法这一概念也应随之成为历史。恰恰相反,当前碎片化的海洋立法和理论研究现状需要海法概念的回归。
(一)海洋法律关联性与碎片化之冲突
海洋活动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必然要求相应的海洋法律日益精细化,因此,粗线条的海法在世界范围内被调整对象更为具体、研究内容更为专一的海洋法、海商法等取代,甚至海上货物运输法、船舶法、船员法、油污法等更为具体的单行海商立法以及关于领海、大陆架等的单行海洋法立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国法律体系中。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出于对海洋活动日新月异的法律需求的灵活回应,因为单行立法相比于内容庞大的综合性法典更具时效性;另一方面则是受部门法和学科分类的影响(尤其是大陆法系),民事、刑事、行政、国际等法律关系的划分以及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的分类使得“诸法合一”的海洋立法难以符合法学理论的标准。应当肯定的是,海洋立法模式的该种变化使得海洋法律的数目大大增加,海洋法律覆盖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但同时又不可否认的是,该种立法模式使得海洋法律的碎片化现象加剧,海洋法律之间的关联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
具体而言,所谓海洋法律的碎片化是指各海洋法律的规范和制度之间没有形成有机联系,“它们相互冲突、彼此矛盾,就像堆积在一起的‘玻璃碎片’”。[18]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分散式单独立法模式固有的缺陷所致,因为各分散式的单行立法可能由不同的行政部门主导制定而缺乏立法主导思想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并更倾向于关注该单行立法所调整的特定海洋法律关系的特性而忽略与其他海洋法律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但事实上,由于海洋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都是在海洋这一特定的空间环境之下,这些法律制度间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叉与联系:例如,有关船舶安全的行政规定与海商法下承运人适航义务的判断存在密切联系,因此有关船舶安全法律制度的出台(如ISM规则)通常会在实质上给私法下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带来变化;又如,海上行政执法程序对内而言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但对外而言属于海洋法的范畴,因此相关程序的制定必须综合考虑两个层面的效果;再如,为达到保护海洋环境的目的,与之相关的各项法律制度,包括政府的应急管理和执法机制、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制度、公众参与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际合作机制等,都应以有利于海洋环境保护为制度设计的首要目标,继而达成制度间的内部协调。所以,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海洋法律关系之间是动态联系的,[19]9这种关联性要求我们必须克服海洋法律碎片化所带来的冲突和矛盾,这就需要对为数众多、涉猎广泛的海洋法律进行统合。
(二)海法概念的统合作用
统合海洋法律,事实上就是将所有调整海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的梳理,进而使之形成一个内容全面、结构合理、体系协调的整体,以法律的调整空间为划分标准构建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体系。同时,纵观现有的海洋法律概念,无论是海商法、海事法还是海洋法,传统上对这些含义的理解使得它们都不足以统摄整个海洋法律体系。因此,海法概念就成了我们统合海洋法律概念体系的首选,不仅因为海法曾经被广泛用于命名当时囊括所有海洋法律规范的法律文本,而且历史上对其概念的理解是普遍认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属于海法的回归。尽管国际上目前并不普遍使用“sea law”来表达海法的涵义,但鉴于海法理论研究的需要,欧美学者经常使用“maritime law”或者“maritime law and ocean law”来表达统合海洋法律之意。从长远来看,随着海洋法律体系研究的兴起,一个能够准确指代海洋法律的“海法”概念,也将逐渐被国际学界所接受并重视。
进一步而言,海法概念的回归将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层面起到统合作用:首先,在法学研究层面,海法概念的回归有助于海法研究体系的构建:在海法概念的引领下,原本分散的海洋法学研究得以整合,这不仅有利于明确各分支海洋法律学科之间的界限和区别,更有利于发现它们相近的传统、原则、制度和特征,使它们在同一体系下交叉、互动,进而达到优势互补,促进相关学科的良性发展;其次,海法概念的回归有助于海法体系的构建:在海法概念的引领下,碎片化的海洋立法应当进行重新审视,以体系化的思维梳理现有立法存在的冲突及遗漏,使海洋法律内部之间以及海洋法律与陆地法律之间形成有机的衔接。[20]特别对中国而言,在国家相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背景下,海洋法律的完善是海洋法治乃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传统上“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涉海法律法规多采取分领域、分事务、分行业的分割式立法模式,以单项活动为调整对象,相互之间存在着交叉和冲突,缺乏全局性和协调性”的现状,[21]中国海洋法律的完善任重而道远。海法概念的回归以及建设海法体系理念的提出恰为中国海洋法律的完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四、结语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战略地位的凸显使得海洋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也日显其重要性。在海洋法律呈现碎片化的大背景下,中世纪获得广泛国际认同的海法概念到了回归的时候。海法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和认可有助于纠正在立法领域也存在的“重陆轻海”观念,有助于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是陆上法律体系和海洋法律体系的有机结合的认识,[19]7从而为海洋法律体系的完善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同时,海法概念在中国的建立有助于统合中国当前碎片化的海洋法律规范,即通过海法体系的构建,完成体系化完善海洋法律的目标,从而使各海洋法律间实现上下有序、内外协调、动态均衡。另外,国际层面客观上也缺乏一个统领海商法与海洋法的上位概念,中国“海法”概念的提出和研究,也将在在国际层面产生影响并得到逐步认同,这不仅会对国际海洋法律的立法统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亦会助力当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
(References):
[1]王小波.《罗得海商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225. WANG Xiao-bo. A study of theRhodianSea-Law[M].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11:225.(in Chinese)
[2]WELWOD W. The sea-lavv of Scotland shortly gathered and plainly dressit for the reddy vse of all seafairingmen[EB/OL].[2013-10-30].http://quod.lib.umich.edu/cgi/t/text/text-idx?c=eebo;idno=A14934.0001.001.
[3]何勤华,李求轶.海事法系的形成与生长[J].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5(5):365. HE Qin-hua,LI Qiu-yi.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law system[J].Journal of China Lawyer and Jurist,2005(5):365.(in Chinese)
[4]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下)[M].何勤华,李秀娟,郭光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917. WIGMORE J H.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Vol. II)[M].translated by HE Qin-hua,LI Xiu-juan,GUO Guang-dong,et al.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4:917.(in Chinese)
[5]余甬帆.试探名词“海商法”之源[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8(1):381. YU Yong-fan.Tentative study on the etymology of “maritime law”[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08(1):381.(in Chinese)
[6]GARNER B A.Black’s law dictionary[M].9th ed.Eagan: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9:1055.
[7]FORCE R.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M].Washington DC:Federal Judicial Center,2004.
[8]ROBERTSON D W,FRIEDELL S F,STURLEY M F.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cases and materials[M].Durham: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8.
[9]MARAIST F L,GALLIGAN T C,MARAIST C M.Admiralty in a nutshell[M].6th ed.Eagan: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10.
[10]胡正良.海事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HU Zheng-liang.Admiralty law[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2.(in Chinese)
[11]BAATZ Y.Maritime law[M].2nd ed.London:Sweet & Maxwell,2011.
[12]STARFORTH H C J.Maritime law[M].6th ed.Virginia:LLP,2003.
[13]FALKANGER T,BULL H J,BRAUTASET L.Scandinavian maritime law:the Norwegian perspective[M].3rd ed.Oslo:Universitetsforlaget,2011.
[14]DERRINGTON S,TURNER J M.The law and practice of admiralty matter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5]MUKHERJEE P K.Maritime law and admiralty jurisdiction: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emerging trends[M]//Ghana Shippers’ Council 2012.Accra:Ghana Shippers’ Council,2012:3.
[16]华敬炘.海洋法[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14. HUA Jing-xin.The law of sea[M].Qingdao: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14.(in Chinese)
[17]高维新,蔡春林.海洋法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9. GAO Wei-xin,CAI Chun-lin.Tutorial of the law of sea[M].Beijing: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2009:9.(in Chinese)
[18]古祖雪.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J].法学研究,2007(1): 139. GU Zu-xue.Diversity,fragment and orderlines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J].Chinese Journal of Law,2007(1):139.(in Chinese)
[19]汤喆峰,司玉琢.论中国海法体系及其建构[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3). TANG Zhe-feng,SI Yu-zhuo.On China’s system of laws of sea and its construction[J].Chinese Journal of Maritime Law,2013(3).(in Chinese)
[20]司玉琢,曹兴国.海洋强国战略下中国海事司法的职能[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4(3):14. SI Yu-zhuo,CAO Xing-guo.Functions of China’s maritime judicature under sea power strategy[J].Chinese Journal of Maritime Law,2014(3):14.(in Chinese)
[21]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4)[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266. Institute of Ocea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China’s ocean development report(2014)[M].Beijing:China Ocean Press,2014:266.(in Chinese)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sea law
CHU Bei-ping,CAO Xing-guo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The concept of sea law,which refers to all sea related regulations, originates from theRhodianSea-Law, and was generally recognized and used in the middle age. Although it faded away withthe development of land legislation and concepts like maritime law and the law of the sea, the fragmentation of sea-related legislations makes the return of the concept of sea law meaningful.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China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sea law under the strategies of Sea Power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to systematize sea-related regulations and build the legal system of sea law.
sea law;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maritime law;legal system of sea law
2015-09-0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电子港航法律制度保障研究”(15BFX19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海洋强国战略的海法保障”(3132014313)
初北平(1972-),男,山东莱阳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海事大学海法研究院院长,国际海事法律研究中心成员,E-mail:chu_beiping@163.com;曹兴国(1989-),男,浙江绍兴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E-mail:caoxingguo89@163.com。
DF961.9
A
2096-028X(2015)03-0016-06
初北平,曹兴国.海法概念的国际认同[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6,26(3):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