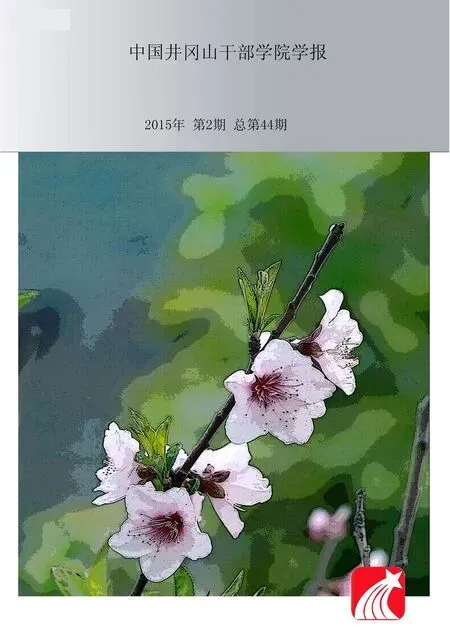试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试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共产国际、联共(布)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一口号执行中的扩大化会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经济基础,为此要求中共中央坚决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富农问题
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始终关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土地问题。对这一问题,史学界一般只作为土地革命的背景之一而只做简单概述。其实,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深入理解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土地革命的中心是土地的分配,其中尤其以富农问题为焦点。而富农问题又必然牵涉到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或领导权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问题,以期增加学术界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学术认知。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意义的强调
共产国际、联共(布)早在中国土地革命开始阶段就关注并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1927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弗赖耶尔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建议:南昌起义部队,应该“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并将其交给耕作这些土地的农民,公开积极地为实现这一口号而斗争”。这一纲领包括两个要点:“在革命部队中作战的军官及其家属的土地,低于一定的限额不应予以没收;革命军士兵的家属首先应分得一块没收来的土地。”[1]P100尽管这一建议还只是针对起义官兵的待遇,但已经明确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这一原则性要求。1927年10月14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希塔罗夫严厉指责南昌起义军:“仍像过去那样不敢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的大胆口号,而仍竭力加以削减。例如,他们要求超过200亩的土地才没收”,[1]P132可视为是对上述建议的回应。1927年10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明确提出:由于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已不存在,所以中共“现在必须提出无条件没收土地的口号”。[1]P130
为更科学地指导中国的土地革命,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十分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1928年1月3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1]P222这一论断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1928年1月,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从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角度阐述中国土地革命的必然性。首先,苛重的地租剥削加剧了中国农民的贫困程度:“支付地租是收成的50-70%,中国农民又生活在经常性的税捐、掠夺、高利贷资本重压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农户不得不交出自己收入的70-90%,生活在贫困线或者贫困线以下的水平上。”其次,比例过重的土地租佃率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农村土地占有的主导地位:“根据中国1917年的官方材料,自耕农占50%,佃农占28%,半佃农占22%。这样看来,佃农和半佃农占着总农户的50%,而自耕农也是50%”,说明“农村的封建农奴制关系占着统治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再次,“在外国资本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关系很快渗透到中国的农村”,以安徽芜湖地区为例,“农业经济的商品量大约相当于54%,也就是说农户收入的54%表现为货币形式,而其余46%则是农产品的实物消费”,尽管并不能全面概括全中国的农村经济,但仍然“说明农业经济的根本摧毁”。最后他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农业危机的实质是封建农奴制关系在缓慢地痛苦地被摧毁”,另一方面“这种危机不可能在封建资本主义中国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因此,“中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是确凿的事实”。[1]P268-2731928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总结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和农民阶级的革命主力军作用:“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它是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全部中国史实质上就是周期性的农民暴动史,经过多年的农民战争后造成了全部土地的重新分配。现在农户的极端严重状况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提上了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1]P317-318这一基于王朝周期律的认识,与现实经验相结合,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1930年4月14日,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人员、前苏联驻华军事顾问马马耶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认为中国农村空前的经济危机是平分土地政策最直接的社会基础:“危机、内战、歉收、沉重的捐税负担,这一切使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不是饿死,就是起来造反,要求废除赋税、徭役,消灭一切封建农奴制关系,平分土地。”[2]P944月15日,在另一份报告中,他重申了这一观点:“危机格外猛烈地打击了农民。粮食作物少收30-70%,这实际上是由压迫中国人民的一切封建残余的压迫造成的,使农民不是慢慢死去,就是为土地而奋起斗争。争取废除一切徭役、不堪负担的赋税和封建农奴制关系的斗争最终使农民走上了夺取土地的斗争。对中国这方面的形势应该这样说:今天农民已拿起武器,奋起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农民要求平分土地。”[2]P105
在上述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
1928年4月7日,共产主义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瓦尔加在为中共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提出:在农村应该“无偿地没收地主、寺院和资本家的一切土地并将其国有化。将剥夺来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首先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小租赁者和复员士兵、农民无偿地使用(取消一切租赁的中介形式)”。[1]P407这一土地政策的主旨是在剥夺大地产的基础上推行土地国有化。但是此草案对分配原则没有提及,也没有说明对其他拥有土地阶层的土地政策,更没有涉及到产权问题,只是一般提及无地少地者对没收土地的优先使用权。1928年7月10日,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在其书面报告中,肯定了中国部分苏区平分土地工作的成绩:“在湘西南几个地区和在陆丰分了田地。分田之前对现有土地和对它的需要量作了统计。在其中的一个地区,分田后中农得到的土地比他原有的要少,因为无地的农民也分得了土地,但所有人都是满意的。”他认为在平分土地的条件下,“贫农和佃农的情绪是如此鲜明,以致中农自愿作出让步”[1]P509。但他的结论并未说明农民分得土地后是否同时获得产权,这使他的关于中农态度的描述值得商榷。1928年7月25日,共产国际“六大”关于中共任务的决议要求:党在农民运动中,应该“没收所有地主土地,并将其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1]P519。1930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电告中共中央:“党在苏区应普遍实行平分土地,尽可能在分地上不损害中农的利益”,强调:“土地国有化仍是一个中心口号,实际上只有在全中国革命和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实现。”[2]P173综合考察平分土地时不损害中农利益的提法和仅把土地国有化作为口号的建议,隐约透露出共产国际有在平分土地后尊重土地所有权的动机。1930年7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电令中共中央:“党在苏区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以及寺庙和其他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给贫农和中农,尽可能不要把没收土地的原则扩大到富裕农民的身上。”[2]P2161930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致函中共中央,批评在中央苏区的部分地区存在歪曲平分土地原则的现象:“地方的同志不知怎么把地主阶级看得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主被划分成‘好的’和‘坏的’。‘坏的’是那些积极同我们作斗争的地主。他们没有得到土地。‘好的’是不同我们直接进行积极斗争的那些地主,他们同劳动者一样得到了土地”,结果,“分给‘好’地主的土地不是荒芜,长满了草,因为地主不想自己耕种,就是被地主出租。”远东局指责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和任何革命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地主阶级对土地或苏维埃政权部分地保留自己的特权的时候,论证这种做法的荒唐性是多余的。应该没收地主的所有土地以及他们的建筑物和财产。”[2]P4511930年12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致函别尔津,也提到给地主分地的现象:“善良的地主在分配土地时也可以分得自己的一份。好地都给了富农,而坏地分给了贫农和雇农。有些地方的雇农的境况相当凄惨,他们分得了土地,但没有农具。”[2]P518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近东部部长马季亚尔则一方面表示:“没收土地的原则不应扩展到富裕农民。我们只没收地主、寺院等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实行平分土地时我们不仅应当重新分配所没收的地主土地,而且应当重新分配所有土地。”[3]P301931年3月28日,远东局致函执委会,反映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存在所谓“抽多补少,但不抽肥补瘦”的问题:“一方面,土地是根据数量进行分配,而不考虑其质量。另一方面,不抽‘好的’富农、大地主和绅士的土地来补给‘坏的’贫农或农业工人。”[3]P202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原则的强调,还通过对中共“立三路线”的批判而表现出来。1930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等在土地问题上的超前做法:“对当前时局要求的不理解也表现在苏维埃政府纲领中的一些超前的社会主义措施上和关于类似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的土地问题的一切错误建议上。”[2]P332
尽管共产国际、联共(布)原则上认为应该在中国土地革命中贯彻平分土地原则,但是又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他们担心这一口号可能会因为执行中出现扩大化而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1930年12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米夫在批判“立三路线”时指出:“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普遍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强加给农民。用平均分配土地来取代没收地主土地的表述,这是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出发的。”之所以不该强制实行普遍平均分配土地,是“因为这在许多地方会损害我们与中农的联盟”。具体而言,“在平分所有土地和只平分被没收的地主土地的情况下,中农的利益会被触动。在第一种情况下,中农在财产和租佃方面会受到打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中农作为地主土地的承租者只会部分地受到损害。”他接受1930年7月29日的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指出:“党应该没收所有地主、半地主、寺院和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按照平均的原则分给贫农进而少地的中农,没收的原则不运用于中农,其中包括富裕中农。党无论如何不应该从上面强制推行普遍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只有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要求实行这个原则并且在不威胁与中农断绝关系的时候,才能支持这种做法。”[2]P507-5091931年2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虽然肯定平分土地的作用:“在贫农、佃农和农业工人占农村人口多数的地区,我们在…农民和农业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经验表明,这一口号如果实行,它就是消灭封建主义残余的最激进的办法”,但是他同时担心:“一旦把这个口号在中农势力很强的地区作为主要口号…推向全中国,在分地时中农所分得的土地就会比他们迄今所拥有的要少,就存在我们把中农推向富农一边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只能根据每个省的具体条件采用平分土地的口号,以便使农民相信进行这种形式的土地革命的必要性。”[3]P103-1041931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主任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时,仍然从中国社会的性质出发,强调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阶段上,我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中农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中农将得到比在半封建制度条件下曾经有过的多得多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这将使中农得到加强”。但他同时认为:为防止新富农倾向,必须“经常不断地同内部,而首先是农民内部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作斗争”。[3]P241-242为此,共产国际要求稳定农民对分得土地的所有关系。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中央:“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4]P354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富农问题的指导
富农问题是困扰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主要理论问题,其中对于富农性质的认定尤其棘手。因为这一性质势必影响到土地革命中阶级路线的贯彻。
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批评中共对富农性质的认定:“党的领导长时期认定,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农业阶层和资本主义阶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意见分歧。对富裕农民的态度和把富裕农民分成封建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分子的倾向同样都是错误的。”[5]P1941930年9月28日,埃斯勒致函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对待富农的策略上,我们在目前的革命阶段,还不应采取像对待封建主和地主那样的政策。”但是他同时提醒中共中央:“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富农会越来越多地变成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估计到这一点。”[2]P3531931年3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编辑、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部长库丘莫夫在其书面报告中批评:“在很多地方直到最近土地仍然在小地主和‘开明’绅士手里,平分土地只有利于富农,而损害贫农和中农、雇农和苦力的利益。”[3]P171
1931年5月16日,在共产国际东方处中国委员会会议上,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萨发罗夫批评库丘莫夫的把夺取富农部分土地交给贫雇农的做法:“如果把富农出租的土地同似乎是他们自己耕种的土地分开,而实际上这部分土地是他们积累的源泉,那么我深信,这就有点像是维护私人资本主义因素”。他建议:“单凭地主的土地我们是不能满足农村贫农和无产者的要求的。我们应该提出不致被曲解的方案。”言外之意,他不满意现行中央苏区等苏区实行的不剥夺富农土地,而只对富农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认为保留富农原耕土地就可能“维护私人资本主义因素”。[3]P287-288在此基础上他重申了平分土地原则:“平均分配是消灭封建土地残余和地主对土地的垄断的最根本的形式。”他进一步解释:“所谓平均分配应该理解为把全部没收后的土地交给农民支配,并根据这里阐述的原则进行分配。所有土地都要在我们认为有权得到土地的人中间分配。”[3]P302马季亚尔则变换了一种表述方法。他指出:“我们将夺取富农土地的封建主义部分。富农将得到份地。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没收他的土地,但我们也不会再给他什么。”[3]P297其实,在得到份地之前,富农的土地一定会先被没收。库西宁则总结性地指出:“我们必须澄清中国富农的定义。我们应该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富农的基本特征。”他明确认定:“现在的这种兼有封建特性和高利贷者性质的富农不同于新型的富农,新型富农很可能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产生出来。”[3]P308
总之,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的经济基础,认为为了推进土地革命,争取广大贫雇农、中农群众,富农的土地应该和地主的土地一样被平均分配,只不过富农还可以得到劳动份地以维持生存。这一看法势必影响到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的土地政策,特别是查田运动的价值取向。果然,1931年12月28日,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地主土地应立即无偿没收,并根据平均原则在苏维埃领导下,在贫农和中农、雇农、苦力和红军战士中间进行分配。富农的土地也应进行分配,只给他留下劳动的份地,只要他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没收的范围不应扩大到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自有土地。”[4]P85
与富农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共产国际、联共(布)要求中共中央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早在1928年7月25日,共产国际“六大”关于中共任务的决议就要求中共应该采取如下阶级路线:“主要敌人是地主、土豪、劣绅;无产阶级在农村的支柱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盟友。”决议提醒中共:“在现阶段加剧反富农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抹杀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但是,“一旦农村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同富农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党应该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剥削者阶层。”[1]P5191930年4月15日,马马耶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报告称:“独立的农民运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这领导阶级的领导,永远也解决不了土地问题。”[2]P106他重申了书记处1929年6月致信中共中央信的主旨,即:“富农是我们的敌人,决不能同他们结成联盟。对党内的富农情绪应给以坚决打击。”[2]P1181930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电告中共中央:“除雇工工会外,请在苏区着手成立贫农团,贫农团应将苏维埃的一切措施用来为贫农和中农的利益服务。”[2]P1731931年1月17日,马季亚尔致函远东局,指责洪湖苏区领导人邓中夏等:“农村的贫农团还没有组成,赏赐给地主土地,散布关于苏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富农和资产阶级理论,等等。而邓和邓之类的人物除了关心对地主寡妇和孩子怎么办以外,没有其他可关心的。在这方面他制造了小脚女人应当比大脚板女人分田少之类的混账理论。”他建议:“首先需要将农业工人组成工会建立乡村贫农团并在其中讨论分配土地的问题,争取中农并把他们聚集在苏维埃周围,只有到那时才能分配土地。”[3]P29-311931年3月18日,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吸取富田事件的教训,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开展反富农斗争,“建立乡村贫农团和农业工人工会,并在将要这样做的地区同富农和其他剥削分子开展群众性的斗争。”[3]P177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联共(布)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尽管共产国际、联共(布)在原则上坚持平分土地的立场,但是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一口号执行中的扩大化会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土地革命政策的态度基本是科学的,所确立的平分土地的原则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的需要,其关于富农问题的分析也基本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对中共的相关政策指导也十分及时到位,因此对起步时期的中国苏维埃土地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可是,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经济基础,为此要求中共中央坚决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因此仍然促使中共在查田运动中执行了比较严厉的富农政策。这使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相关指导仍然与中国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实践结果存在一定的距离。这与前苏联国内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政治气氛,特别是消灭富农阶层的强硬政策对中共执行富农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存在因果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共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由于中共中央领导层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客观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相关指导的影响。但是,不应该因此忽视中共自身对土地革命相关规律的探索。首先,在平分土地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均出现过到底是按照人口平分土地还是按照劳动力分配土地的争论;其次,在富农问题上,中共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个不断深化对富农在土地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的认识问题。中共最终明确了对富农封建性性质的认定,并在此基础上确定革命的阶级路线,即通过反对富农和落实按人口平分土地,以实现对农村最广大群众的社会动员。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贺文赞)
O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s Guidance over the CPC’s Agrarian Revolution
WANG Ming-qian
(SchoolofMarxism,Xiamen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China)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emphasiz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 working out the land policy suitable fo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gave timely guidance over the land policy made by the CPC in the soviet agrarian revolution,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equally distributing lands.Nonetheless,they always kept a cautious attitude over the slogan of equally distributing lands,and worried that this slogan,enlarged in implementation,would affect the class alliance strategy toward middle peasants.In respect of the rich peasants,they asserted that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rich peasants must be eliminated,and therefore aske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uncompromisingly carry out the revolutionary class route of opposing rich peasant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CPC;agrarian revolution;the rich peasant issue
2015-03-09
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
D231
A
1674-0599(2015)02-00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