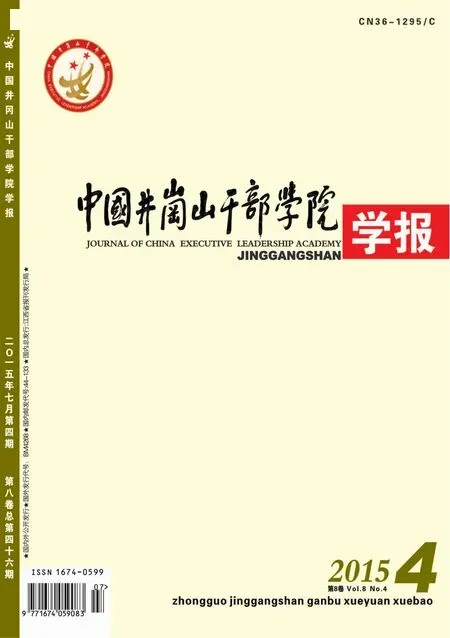浅析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沟通机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
□蔡 丽 冯 云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沟通机制,如沟通渠道、沟通内容、沟通阶段以及这种沟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的影响等,可以从一个微观的层面探寻这一阶段二者的关系变化。本文将依据已公布的1937年8月至1943年5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300余份档案文件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疏理和解析。
一、沟通概况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沟通,无论是沟通渠道还是沟通内容,无不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明显时代特征。
(一)沟通渠道
1.电报、书信往来,以电报为主,内容多简短。这里的电报、书信往来大致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较为间接,中共中央发电报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或者中共驻新疆代表,转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8月到1939年4月2日主要是这种情况;第二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直接电报、书信往来,1939年4月2日以后主要采用这种方式。
2.互派代表直接沟通。代表的派驻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意见中转作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时有变动,情况如下:1937年10月前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是王明、王稼祥和康生,1937年11月13日,季米特洛夫在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后,决定“把王稼祥暂时留下作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1]P62。次日,王明和康生动身回国。1938年至1940年间,周恩来和任弼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回国后,中共代表空缺。第二种是莫斯科方面派代表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了解中共的工作并进行帮助。1941年2月,苏联工作组到延安,“目的是研究日中情况和向中共提供帮助”[2]P221,毛泽东和朱德2月3日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表示,中国方面将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材料,包括最重要和最秘密的材料,供他们研究和向季米特洛夫进行传达;1942年,弗拉索夫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派往延安;1942年5月14日,去到延安的苏联同志向毛泽东转达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不久,毛泽东托返回苏联的斯克沃尔佐夫转达一些事情给季米特洛夫。第三种是中共代表赴莫斯科进行报告,这种报告通常篇幅较长,内容较为详尽,是共产国际了解中共各方面情况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如1938年5月8日,任弼时在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和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中共的活动和中国的国内形势,共产国际对这两次报告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3.成立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形势的通报,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5天内制定出具体建议”[3]P5;1939年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利亚耶夫请求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资料研究小组,并获同意。这种方式虽然不是直接的沟通方式,但两个小组内都有中共成员的参与,例如专门委员会里有邓发、康生和王明,中共中央资料研究小组里有林彪、刘亚楼、任弼时,这样的方式有助于加深共产国际对中共所开展活动的了解程度,从而做出正确的指示。
4.在新疆、兰州、蒙古人民共和国设联络地及信使,主要起中转物资和传递消息的作用。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上述联络地进行包裹和邮件的转递,并通过信使转交双方交办的相关事项。
(二)沟通内容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沟通内容大都围绕抗战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双方最重视的问题。总的来说,沟通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援助事宜。资金、武器、无线设备、医疗、技术人员、文化用品等,主要是中共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一内容占比重较大;第二,中共自身情况。包含中共关于召开七大的系列问题、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情况、中共对敌斗争状况、边区问题、党的发展问题、中共开展的工作等;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许多摩擦,国共摩擦是主要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经常就国共关系、国民党的动向和政策等问题进行沟通;第四,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双方就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对中国抗战形势产生的影响进行沟通,并据此表明自己对形势的态度;第五,新疆问题。从1942年7月5日开始,围绕中共在新疆工作的同志的困难情况,双方进行了比较频繁的电报往来;第六,其他具体问题。包括学习联共(布)党史和马列主义问题、联络问题、王明问题、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双方曾就是否保留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行讨论。1939年7月5日,在共产国际内部的中共中央资料研究小组的会议上,莫尔德维诺夫①莫尔德维诺夫1938-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与任弼时就承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地位是否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莫尔德维诺夫主张承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地位,认为这有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弼时则持相反意见。
二、沟通阶段
共产国际与中共这一时期的沟通成效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二者在沟通的次数以及质量方面不断向良性互动方面发展。从总的情况来看,沟通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指1937年8月到1939年上半年,此时双方沟通较少,且沟通方式多为间接,相互间的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
1.沟通的次数较少,且不是直接的方式。从已公布的档案文件来看,从抗战爆发直到1939年4月2日以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才开始比较频繁的直接电报往来,毛泽东在1939年4月2日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里说:“现在我们已经联系上了。可否开始工作。”[3]P130在之前一年半多的时间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报往来大都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或者中共驻新疆代表(这一阶段是邓发)转发的,并且仅仅只有8份,内容多集中在援助事宜方面,对中共的活动情况报告得比较少。
2.沟通的内容不详细。在这期间,双方沟通缺乏详细的情况通报,除了1938年5月8日任弼时的报告比较详尽外,共产国际对中共情况的了解大都来源于较为简短的电报或其他方式,所得到的信息相对而言是零碎、片段化的。
这一阶段的这种沟通状况使得双方相互了解不多,一方面共产国际不够了解中共的实际状况,因而在援助方面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中共不了解共产国际的真正指导思想而给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曾有文章指出,1937年11月,肩负着共产国际重要使命的王明回国以后,“表达的一系列思想,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共产国际的思想,也有一部分并不能真正代表共产国际,而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因为披着共产国际的外衣而给共产党的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4]P73
(二)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指1939年下半年到1943年5月。1939年4月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沟通次数明显增多,尤其是双方领导人的直接沟通;从1939年6月4日开始,中共经常给共产国际发送较为详细的情况通报。
1.定期通报制度的建立。中共中央经常转发一些内部通报给共产国际以助其更全面了解中共的现状。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里表明:“在随后的电报里我们将开始定期向你们通报国共关系、军事形势、八路军和新四军状况、中共在全国的活动问题。”[3]P1341939年6月4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发送了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第1号通报;此后,中共陆续发送了较多详细的情况通报给共产国际,例如1939年7月17-30日发送了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简报、1940年2月22日发送了关于中国当前的形势的说明、1940年5月25日通报了国民参政会第五次会议的相关情况等等。此外,中共也希望了解共产国际方面的活动情况,在1939年5月17日的电报里还恳请共产国际方面指定专门同志编辑相关通报材料并定期寄来,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及其主要支部的活动情况”[3]P134等等;共产国际方面经常请中共从重庆寄给他们关于中国的报刊资料,这样的方式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从而使共产国际做出的指示更符合中共的实际情况。
2.协商程度的加深。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容易形成错误的印象,似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是居高临下的,以命令式口吻来发号施令。其实,共产国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尊重中共意见的,只在少数关键问题上语气较“硬”,在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文件结尾,多有询问中共意向的字句,如“请告知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等。例如,1940年2月19日,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对中共中央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讨论结果是,同中国同志一起制定了以下决议草案……”[2]P21说明共产国际是比较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的。再如,1940年3月17日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说:“周恩来会亲自向你们通报我们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所有情况。这些都需要你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完全独立地作出最后决定。如果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请速告我们并说明理由。”[2]P62从中共方面来看,在很多电报中都向共产国际作情况通报并请其作指示。例如,1940年11月7日毛泽东发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电报中,汇报了与蒋介石摩擦的主要状况,在结尾说到:“虽然我们现在在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但最后的决定还没有作出。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解决不好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特向你们作出通报并请尽快作出指示。”[2]P98-P99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也对共产国际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1941年4月20日,斯大林谈到共产国际是否应继续存在的问题时提到:“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独立地解决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5]P727并总结指出:“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5]P7284月21日,季米特洛夫就开始向爱尔科利和多列士提出应讨论下列问题:“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5]P728这些考虑都对共产国际更加尊重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产生了积极影响。
3.联络工作的扩展。在1942年1月13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里指出:“形势要求紧急实行补充措施,扩大和改进联络工作。”[2]P248并对此提出了五点建议,包括由毛泽东选派一名常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联络问题;中共向共产国际派遣一个小组,学习联络技术等等。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沟通机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沟通机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积极的,不仅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积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早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就在报告中指出:“所以我赞成我们英勇的中国兄弟党的倡议,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6]P437在随后的进程中,共产国际也用行动支持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对此评价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和季米特洛夫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确定与发展上给[中共]中央以极大帮助。”[3]P19
(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做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决定
第一,主张维护统一战线内各政党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在1938年6月11日的决议里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也不能是以限制参加这一战线的政党,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其他抗日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目的。任何这种企图只能导致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和对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破坏。”[3]P97并认为“党的加强、党的独立性和团结正是进一步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进而胜利地继续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保障”[3]P99。对此,中共表示认同,在 1938 年 6 月24日《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里提到“中共必须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坚持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7]P525,1938 年10 月 12 日至 14 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性的东西”,“但同时,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7]P646而这一做法在后来的抗日统一战线实际中被证明是正确的。
第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少数民族问题。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共代表作的报告通过的决议里提到“在吸收中国少数民族,蒙古人民和穆斯林参加全国自卫斗争方面,必须开展广泛工作”[3]P100,中共十分重视这一项工作,先后于1940年4月25日和7月发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阐述了这些民族的特征、国民党对其的政策和中共争取他们的工作方法问题。
第三,关于投降派问题。1939年5月21日,季米特洛夫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指出:“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中的投降派。”[3]P138对此,中共中央在1939年6月4日的电报里表明:“你们关于同投降危险和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指示以及关于巩固和扩大民族战线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和及时的。”[3]P145
还有诸如另派代表取代邓发赴新疆以缓和和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关系等等。
(三)成立专门的中国问题小组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1939年5月23日,共产国际内部的中共中央资料研究小组获准建立,并在随后的时间召开了三次大小不同的会议专门研究中共相关的问题,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1939年8月19日莫尔德维诺夫向季米特洛夫上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小组的工作结果的书面报告,对四个问题进行了研究:“1.如何制止投降的危险和加强中国的抗战。2.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3.如何加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4.在国民党投降和国共合作破裂成为事实的最坏情况下如何继续抗日战争。”[3]P250这个小组是在详细分析中国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体现出了共产国际对中共指导工作的慎重性。
(四)及时劝阻中共的不合适做法以维护统一战线
在皖南事变问题上,对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与中共的关系危机,共产国际并不是消极地指示中共要忍耐,不要破坏统一战线,而是为这一事件想了很多缓解的办法。首先,对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1941年1月17日,季米特洛夫“打电话给莫洛托夫,告之中国发来的电报。莫答应把问题向斯大林反映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5]P715次日,季又亲自给斯大林写信,信中表明了他对此事的性质判断,“蒋介石显然认为目前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总攻的适宜时机”[5]P715,并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办法,例如要苏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在英美等国开展运动、外国报刊揭露反动派罪行以及由中国各种协会、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向蒋介石发出抗议信等来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其次,劝中共方面保持克制,不要首先采取军事行动。194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发电报告知皖南事变发生,并说:“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2]P116-117中共的进攻态度十分坚决,可能进一步加重危机的发展。1月20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电报,告知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此事视为地方上的军事事件,并保证此事“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2]P124,试图缓解中共的激动情绪,避免军事行动。但是季米特洛夫对国共两方都不放心,在电报结尾嘱咐毛泽东及时向他通报政府对八路军和特区的行动及毛泽东采取的措施。21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发电报,表示在政治上要“彻底揭露蒋介石在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方面的反革命阴谋”[2]P125,军事上“决定暂时进行防御战,今后,如有必要,将采取反攻步骤”[2]P125,态度较之前的电报有所缓和。1月29日,毛泽东回复季米特洛夫1月20日的电报,对蒋介石的说辞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反驳,鉴于蒋已经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将军长叶挺交由法庭审判的事实,认为蒋介石说新四军事件不影响国共合作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我们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我们不得不走上决裂之路,这也是因为蒋介石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已到极限”。[2]P128-1292 月 1 日,毛泽东再发电报给季米特洛夫,认为虽然从事件的开始到关系破裂还有一个过渡时期,“但是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2]P132。对此,季米特洛夫在2月4日的电报中表示:“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要“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2]P133并要中共“重新考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2]P133,语气是比较严厉的。2月13日,毛泽东发给季米特洛夫电报,表示中共做出的决定符合季的指示,双方没有分歧,并表示“我们认为,国共分裂将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现在”[2]P151,但是中共希望用一种“硬”的方式来应对蒋介石,因为他欺软怕硬,而这种“硬”的方式恰恰就是中共维护统一战线的表现。在这样来回沟通后,最终确定了对国民党“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策略,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发给周恩来的《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指示》里就说:“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8]P50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对于维护国共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努力,在事件发生的最初阶段对中共的情绪反应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也对中共最终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在反蒋会议问题上,施加必要的影响。1942年6月15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听到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组织反蒋会议,认为这种行为会使国共关系紧张,因而要求中共“采取紧急措施使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执行坚定地、始终如一地、旨在改善共产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政策,并从自己方面避免发生一切可能导致这种关系更加紧张的做法”。[2]P285毛泽东在6月24日的电报里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建议,表示:“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已通知周恩来,让他彻底执行您的指示。”[2]P287
四、结论
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沟通是一个逐步走上良性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因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后期沟通较多,双方理解增多,因而沟通较为顺畅,共产国际所作的指示也基本符合中共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成熟的回应方式,不卑不亢。这两个方面共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和发展。
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在共产国际对中共指导的指令性与指导性问题的区分上:一方面,在国共关系或者统一战线有危机时,共产国际会对中共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虽表面上不是强制性,但中共是必须遵从的,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共产国际是带有某些“指令性”的,但是这种指令性是在比较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的,总体来说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平时,共产国际不大会干预中共的内部事务,虽会在党内问题等方面提建议,但是是比较温和的,没有严厉敦促的味道,从这一点上来看,又是“指导性”的。总而言之,共产国际并不是事无巨细地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只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带有指令性的味道。周恩来对这一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评价为:“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9]P692因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沟通还是比较好的,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持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中共方面来看,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成熟的回应方式。在中共中央发往共产国际的很多电报中都可以看到“请作出指示”的字样,体现出了对其的尊重,但在这些请示中,中共并不是毫无主见地请共产国际给意见,而通常是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再请共产国际作指示,这种“请示方法”体现出了中共的成熟性。例如在193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将国民党提出中国统一党的问题后国内的不同观点向共产国际汇报,第一种观点主张解散除国民党以外的所有政党,第二种观点主张解散所有政党,第三种观点主张建立各党派的全国联盟,中共在电报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当然,我们不能同意前两种观点”[3]P39,然后请共产国际对可否同意第三种方法作指示。这种坚持自身正确主见而又尊重共产国际正确建议的沟通方法对于二者的沟通起到了好的作用,从而又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复杂的环境中得到了维护和发展。
当然,这种沟通机制是在特殊的环境中不断建立起来的,由于战时形势往往骤变,这种沟通机制有时也有明显的弊端。如滞后性和协商讨论的不充分问题,在新疆工作的中共人员的撤退问题就是明证。由于沟通不及时和不充分,导致中共在疆工作人员没能及时撤出,不少骨干惨遭杀害;早在1939年6月4日中共就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第一份通报,但1939年8月19日,莫尔德维诺夫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里说:“而我们却得不到来自中共中央的全面定期通报,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一年来,除了电报,没有收到一份通报材料。”[3]P263说明这种沟通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容易延误问题的有力解决时机。
[1]〔俄〕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4]徐玉凤.抗战初期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再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14(9).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0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6]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7卷[Z].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