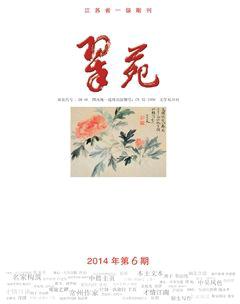艾米内斯库国际诗歌节行记
1
一架波音777大飞机,带着我们,跟着地球上移动的黑暗部分,上海、安徽、河南、青藏高原,一直到乌鲁木齐,飞出中国版图,然后折向西南,飞往黑海方向。海洋和陆地、平川和高原、语种和时差……这所有的切换,在我而言,就像是一次陌生、新鲜、刺激,充满未知,但又满怀期待的来自语言内部的深刻转换。
8月31日14:03分,我收到署名Ion Deaconescu的邮件。
邮件同时抄送给著名翻译家、诗人海岸,和比利时诗人杰曼·卓根布鲁特(Germain Droogenbroodt)。这封来自罗马尼亚南部重镇克拉约瓦(Craiova)的邮件中,有一份设计精美的罗马尼亚语邀请函,郑重邀请了我和太太陈洁,参加9月16日至9月18日在克拉约瓦举办的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国际诗歌节。
米哈伊·艾米内斯库(Mihai Eminescu,1850~1889)是罗马尼亚历史上最富盛名的诗人,被称为“现代罗马尼亚语之父”。在他33岁那年不幸染上梅毒,不久又雪上加霜地罹患抑郁症,可谓是疾病缠身、饱受折磨,当时距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的1928年还有40多年时间。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被迫用当时的土方法注射水银来治疗梅毒,因为水银是重金属,对神经伤害极大,使用这种方法治疗“不死也要半条命”。因此,可怜的诗人终死于他39岁那一年的夏天。但这并不影响罗马尼亚人对他的尊敬,据说其代表作《Luceaf rul》在罗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为了纪念这位“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罗马尼亚诗人”,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和索因卡在克拉约瓦创办了“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国际诗歌奖”,至今已颁发16届,两年前开始同步举办相应的“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国际诗歌节”。这个给我发来邀请函的伊昂·迪肯内斯库(Ion Deaconescu)正是该国际诗歌节的主席。
这一切都缘于著名翻译家、诗人海岸先生的无私推荐。我依稀记得,大约2004年左右,我们在位于上海都市路的撒娇诗院某次朗诵会上见过一面。因为现场人太多,嘈杂不堪,因此记不得有什么交流。后来,是2009年他主持的《中国当代诗歌前浪》编选并翻译了我的两首诗,我是在书出版后,才意外地看到我忝列其中的。第二次见面,则是去年,因为上海社科院孙琴安要研究上海的先锋写作,找海岸打听我的联系方式。海岸受人之托,费了一大圈周折,七弯八绕终于联系上我。那时正值海岸要去美国波斯顿,于是我们相约在他出发前夕到上海港汇广场的一个酒吧和孙琴安见面。当时还有徐慢、王晟,艺术家韩北石。此后,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和交流。海岸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教授,但他却义无反顾地坚持把自己归于民间写作,让我很是感慨。与一些应聘进去做大学生辅导员后就开始自称“青年教师”,并千方百计把自己乔装成“学院派代表”的诗人有本质上的区别。海岸对于写作的认知和立场,多少有点与1964年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声明:“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有点异曲同工。
诗歌节主席伊昂使用的是罗马尼亚语,不谙英文,因此生于1944年精通佛兰芒语、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的比利时诗人杰曼(Germain Droogenbroodt)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海岸和诗歌节沟通的纽带。杰曼不仅是诗人,同时还是翻译家和国际著名出版社POINT的拥有者,2009年海岸和杰曼编选并在欧洲出版的《中国当代诗歌前浪》一书中,我成为那本书的最后一个诗人。后来在诗歌节第二天晚上和杰曼一起去酒吧喝酒,杰曼说他和北岛、多多,台湾的向明都是好朋友。我说多多和向明都和我很熟,相识好多年了,而北岛则没见过,但我知道北岛最近在国内忙于到处向小学生们推销他新编的书,在各种网络消息上,轻易就能看到他系着红领巾和孩子们一起行少先队礼的照片。他哈哈一笑说,他曾经和北岛、多多一起发起了一个名叫“新感觉主义”诗歌运动。次日,他送给我一本由台湾诗人龚华和北岛为他翻译的中文诗集《逆光》,说向明为他写的序。回国以后,向明告诉我说杰曼“对中国人特別有好感。”因此,当海岸通过杰曼的中转向组委会推荐我时,我很快就获得了通过,并收到了邀请函。
9月14日22:45从浦东机场起飞,由伊斯坦布尔转机,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于当地时间15日上午7:50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机场和中国的机场反差巨大,人也少,据说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齐奥塞斯库时期,一直使用至今。伊昂的儿子开着一辆越野车来接我们,要把我们接到227公里外的克拉约瓦。沿途到处都是大片的农田和电线杆,远处偶尔有一些淡淡的小山丘。这个全国人口都没有上海多的国家,公路也比较初级,车辆和人烟一样稀少。村庄疏散,整个感觉色彩明快,空气好,天很蓝,屋顶是大红的,墙大都是白的,夹杂着一些黄的,树木一簇一簇地从房子和房子之间冒出头来。伊昂的儿子不懂英文,我们几乎只能靠微笑来表达友好和谢意。伊昂的儿子非常为我们着想,甚至在布加勒斯特机场到克拉约瓦的途中,特地停车,用手势告诉我们,可以下车休息、抽烟。把我们送到下榻酒店后,他就离开了。后来我们受到邀请,参加19日下午在克拉约瓦影院举行的中国电影节成龙电影《十二生肖》首映式时,伊昂再次安排他的儿子开车,全程陪同我们。这是仅有的两面,但这个东欧小伙子的热情、友好、善解人意却给我们此次罗马尼亚之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地时间下午两三点钟,终于到了位于克拉约瓦城东北的下榻酒店Europeca,相当于中国的四星级,但在当地已被认为是极尽奢华的了。和伊昂见面,第一印象,气度雍容,兼具中年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风范,显然是经过东欧社会数十年沉淀的贤达之士。言语不通,驴一唇马一嘴地寒暄了几句,送上一幅我的左笔书法卷轴,内容写的是我的《渡·爱》。稍事休息。晚餐时分,各个国家的诗人陆续到来,总共有三十个国家的38位诗人应邀出席。号称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阿多尼斯传来消息,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出席诗歌节了。当地的饮食以牛肉和土豆为主,也有一些烤鸡肉、素菜沙拉。关键是,红酒很棒,不限量畅饮。
克拉约瓦位于多瑙河支流日乌河中游,是多尔日县(Dolj,相当于中国的省)首府,罗马尼亚西南部的重镇,也是罗马尼亚最大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进入城市,随处可见2021年建设成为欧洲文化之都的标语和户外大牌,有点类似于上海世博会之前的宣传。16日上午10:00在克拉约瓦的ART MUSEUM举行开幕式并颁发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国际诗歌奖时,多尔日省长普雷奥蒂萨和克拉约瓦市长奥古塔-瓦希莉斯库,都特别强调这一点,该国际诗歌节之于当地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由于语言障碍,除了海岸偶尔用英语和与会诗人有所交流以外,我几乎像一个局外人,甚至在开幕式上伊昂介绍与会嘉宾时,用罗马尼亚语连报了我两次名字我都没有入神。幸亏海岸及时提醒,我连忙站立向大家致意,才不至于失礼。倒是这个艺术博物馆,气势非凡,有着气派的楼梯、拱顶、白色墙面上凸起的圣经人物、天使,辅以鎏金花饰。从建筑的外形特征和内装饰来看,起码有数百年的历史,每个建筑细节都流露着拜占庭帝国的印记,也许在若干年前本来就是一座东正教堂。
开幕式结束后,所有人步行到不远处的市政厅。这一段路应该是最繁华的核心区域了,行人和汽车也非常少,到处都是古老的欧陆三段式建筑,几乎见不到任何新建筑,黑色的几何形屋顶,灰白色墙面,看上去粗壮森严的基座。整个街面上你能感受到一种骨子里的安静,让我这个久居东方喧嚣都市中心的人内心深受洗礼。市政厅大楼也是一栋年代久远的老建筑,外面悬挂着好多红黄蓝三色国旗。门前是一个开阔的广场,一个不是很大,但恰到好处的喷水池,零零落落地有一些市民,不远处是一座雕像:白色基座,上面一个手举战斧的骑着战马的骑士,乍一看像是苏北盐城市中心的那个新四军雕像。作为多尔日省首府的克拉约瓦市政厅,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个站岗的士兵或警察,当地社会的平和、宁静可见一斑。
年轻、漂亮、充满智性魅力的女市长奥古塔-瓦希莉斯库和国际诗歌节主席伊昂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一个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的西方议会开会的样式,主席台背靠迎门的墙面,上面挂着罗马尼亚三色国旗和欧盟旗帜,三面呈弧形环绕的听众席。我们走到发布会现场时,那里早已架好了记者们的长枪短炮。短暂的发布会后,美女市长亲自给与会诗人发放礼物,人手一份。一只白色环保布袋,上面印着克拉约瓦的市标,就是门外那个举着战斧的骑士雕像,里面装着宣传克拉约瓦到2021年要建设成为欧洲文化之都的宣传光碟,还有帽子、玻璃茶杯、纪念胸章等各种物件。
2
“一颗颗稻种,活生生的在地下
被深深地埋葬
风暴呼啸在泥土之上
悬浮的星河,更高、更久长”
这四句诗节选自海岸写于2005年的组诗《江南·河姆渡》中的一首,名为《稻种》。17日下午,我们走进克拉约瓦的罗马尼亚歌剧院之时,天上下起了毛毛雨。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国际诗歌节的第一场朗诵会在这里举行。之所以把诗句引用在这里,是因为这首诗在更为深刻的生命认知的层面上,如此贴切地对应了海岸自身的命运。这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活跃于上海先锋诗界的先行者,在当下喧嚣的诗歌语境中,似乎被与日俱增的泡沫和浮渣遮盖。然而正如他笔下的“稻种”,虽然活生生地被这个年代浮皮潦草的诗歌江湖“埋葬”,任由“风暴呼啸在泥土之上”,由于那股“不灭的心火”,你可以没读过他的长诗《挽歌》,你也可以不了解这个人,但那“悬浮的星河”预表着“更高、更久长”的锲子般的力与光芒。如果没有海岸三十年如一日的努力,狄兰·托马斯这棵“稻种”,在“汉语中复活” 又如何成为可能?海岸跟我说,同样付诸了他三十年时间的另一部心血之译《萨缪尔·贝克特诗选》也即将正式出版。
与尼采所言的“大优伶之喧闹与毒蝇之营营”的国内诗坛对他的认知完全不同,海岸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声誉。2004年应邀参加UNESCO全球和平文化合作研究项目,并有论文及诗歌入选《UNESCO-EOLSS维生系统百科全书》。这些年来,应邀出席“第15届阿根廷-罗塞里奥国际诗歌节”(2007)、“第48届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等,让他在国际诗坛上获得了很多好评。我在罗马尼亚歌剧院时,忽然之间就深切感受到了《稻种》最后几句的深刻含义:“一切似乎都汇入长眠/忘却了诞生与死亡/拒绝出土的种子色泽金黄”。在与上海有着6个小时时差的克拉约瓦,海岸“拒绝出土”的决绝和自信,恰如其分地喻示了他在国内不争名,不逐利,潜心诗歌翻译和诗歌写作的态度。然而,诚如诗中所示,这一切并不能掩盖种子的“色泽金黄”。一个宿命般的巧合是,海岸作为第一个出场的中国诗人,所登上的舞台,由6扇顶部呈圆弧形的金色屏风作为背景,每扇屏风的视觉中心都是一枚鸭蛋形的浮雕,周边缀以镂空的雕刻花艺,在一盏水晶吊灯的照耀下,到处流溢着这种深沉、内敛,透射着达基亚人穿透历史的庄严和岁月古老而雄浑的金色光芒。
诗歌节特地为朗诵会配备了一男两女3名翻译,在诗人朗诵完之后,立即由翻译朗诵一遍罗马尼亚语。在其他诗人都选择用母语朗诵的时候,海岸展现了他作为翻译家,和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的专业底气,用英语朗诵,翻译耗在台上,足足等下面掌声响完,才能开始罗马尼亚语的朗诵。当海岸踩着罗马尼亚语的“遮蔽的日子真实又彻底/大地的子宫孕育着另一种梦想”的节奏,走下台来时,我不失时机地用相机记录了这一刻的海岸,记录下海岸“色泽金黄”的一瞬间。
与海岸的朗诵相比,其他国家的诗人,可能是年龄的原因,相对而言,显得有点老态龙钟。那种英语世界里的抑扬顿挫,我并不是很入心。中国另一位诗人郁郁,在这场朗诵会上也是峥嵘毕现。郁郁应该属于我越来越反感的“第三代”中的一员。当然,在今天的郁郁看来,第三代或许也是令他反感的。韩东曾在一篇名为《<他们>或‘他们》中提到:“记得有两位上海诗人来访,自称是从长江源头一路走来的,要走回上海(入海口)。但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像,两人干干净净,衣服几乎一尘不染,而且也没带行李。坐下后就大谈哲学,试图让我折服。即使你请他吃饭也得心悦诚服地请,化缘的和尚也没有这样的呀!”我不知道这两个上海人中,有没有郁郁,但无论如何,就像韩东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南京一样,郁郁所在的宝山也是八十年中国诗人在上海的一个老码头之一。三十多年坚持地下写作,主编的《大陆》诗刊广有赞誉。在伊斯坦布尔飞往上海的飞机上,他告诉我,上一期《大陆》他从500万字的来稿中,遴选出50万字刊行了,因为读稿,眼睛读坏了。仅此,我觉得郁郁在罗马尼亚歌剧院收获的掌声,还是太稀薄了、太吝啬了。撇开罗马尼亚人不了解中国当代诗歌不谈,就说今天的中国诗坛,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郁郁这一点。写到这里,我的耳际再次想起了海岸《稻种》的开篇:“一颗稻种,活生生的在地下/被深深地埋葬/没有空气没有声音/黑暗断送了可能发生的向往”,在我看来,郁郁同样是被第三代的喧嚣和浮渣埋葬在地下的一颗稻种,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和海岸一样有着金黄的“色泽”。
这场朗诵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Ataol Behramoglu,这个来自土耳其的诗人,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告诉我,曾经两次来到中国参加过诗歌节。当我问他是否尝试过用双语进行诗歌写作时,伊斯坦布尔人爽朗地大笑起来连说:“No! No!”他用英语说道:“我用我伟大的母语写作!”那一刻,罗马尼亚歌剧院的金色灯光像是一道闪电烙在他灰白的头发上,显得意味深长!
Vladas Braziunas捧着个专业相机,在舞台前像幽灵一样,不时“咔嚓咔嚓”几声。前一天开幕式间隙,我中途跑到门外抽烟,看到他正在那里抽,白发白胡子,像个戴了近视眼镜的圣诞老人,在人中位置一撮因为抽烟而被熏染成黄色,我觉得很有趣,于是和他搭讪。两个都只懂一点点英语的人,在那里连估带猜,才搞明白他是立陶宛人。当时台上一个打着领结、带着礼帽的老绅士模样的挪威诗人Knut·degard正在朗诵诗歌,Vladas捧着相机在朝着我的方向拍,我于是跟他打手势,让他帮我们拍一些。他给了我一个ok的手势,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友好的立陶宛人,像个专业而尽职的雇佣军一样,终日无声地游荡在我们周围。等到我们回国后,他通过电子邮箱发过来精挑细选的就有96张照片。尤其是他抓拍海岸的几张照片,我认为是我见过的海岸的最好的照片,深刻地展现了这个立陶宛诗人的高超摄影技术。虽然语言不通,在短短几天之内我们还是建立了无比融洽和通畅的沟通,甚至他还特地给我夫人送了一盒立陶宛巧克力。我想这样的离开语言的交谈,也只有在诗人之间,才能够进行。
我被告知,我的朗诵安排在第二天的克拉约瓦大学。次日上午,先是在克拉约瓦的图书馆安排了几本新书的发布会,紧接着是一个研讨会,一群诗人们上台自由发言。因为语言的关系,我只是零星地知道他们“咿咿呀呀”地在发言中谈到了网络时代,他们诗歌的版权经常会受到侵犯之类的。甚至因为担心版权问题,而有人引申到批判年轻人的写作。本来我忍不住想上台去讲几句,轰一下他们部分人的陈腐观点。后来转念一想,我满口中文,官方翻译也不一定翻译得了,思虑再三最终放弃了上台的想法。
按照我和海岸的猜测,估计研讨会结束后,就该安排午餐了,朗诵大约会在下午,或者傍晚。谁知道,大巴直接把我们从图书馆拉到了克拉约瓦大学,先是在一个大教室里,伊昂和两个大学里领导模样的人分别讲了一会儿话。然后直接上楼,到朗诵的大厅。我们上去时,才知道朗诵直接开始了。由于估计错误,海岸都没有带录像机,以至于这成为最大的遗憾。容纳数百人的朗诵大厅,门外拥挤着很多人。进入大厅,中间一条过道把听众席分为两个部分。后一个部分已经坐满了克拉约瓦的大学生。前一个部分空着,等诗人、各媒体记者都到位后,再放进堵在门外的大学生,到最后,甚至连过道上几乎都站满了人。
台上一男一女坐着两个人,一个担任现场翻译,一个担任主持。中间空出来诗人朗诵的位置。海岸仍然是中国诗人中第一个出场的,再次用英语朗诵了他的《现状》一诗。“我未能完成写作,就像/无法完成我的生命……我也是进入思想内核的汗珠/是想象回归到火变得尖锐的地方”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在于把写作、生命、想象都安置到一个相对深刻的涉及命运本质的层面上,从而实现一种涉及到诗人最本源的精神“回归”,火是物质燃烧过程中的强烈氧化反应,而“火变得尖锐的地方”让全诗在一种骤然紧张起来的压迫感中找到了一种“现状”的坐标,并让想象回归到这一坐标。可以说这首诗是在平静、理性的叙说中隐藏着巨大的爆发力,因此在海岸朗诵结束以后掌声比前一天在罗马尼亚歌剧院朗诵《稻种》时显得更为热烈。在郁郁上台朗诵时,坐在我后排的意大利诗人Laura Garavavaglia找我说话,海岸正好在她旁边,她请海岸帮忙翻译,意思是要我用我的相机在她朗诵的时候,帮她拍一些照片。一来一去之间,当我在一片掌声中把头转过来时,郁郁已经朗诵完了,正站在台上等着听翻译的罗马尼亚语朗诵。后来据说,因为15日晚宴上郁郁和参加诗歌节的俄罗斯诗人Veaceslav Samoskin在一张桌子上进餐,而俄罗斯曾有过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历史,于是他就选择了朗诵一首名叫《十二月》的诗,我甚至亲耳听到过那个俄罗斯人最后干脆就称呼郁郁为:“Dec.”。
3
当主持人报幕邀请我登台朗诵时,跟在开幕式上一样我又没听清楚,幸亏海岸及时提醒。站在朗诵的麦克风前,关于朗诵篇目问题,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此前,主办方曾要求我提供四首英文版诗歌,我实在没有英文版,只能拿了《中国当代诗歌前浪》中海岸早些年翻译的《思维方式》和《再彻底一些》,在网上下载了一首2004年被英译的作品《广场》,加上复旦青年诗人秦三澍在我临行前英译的“诗歌船”同题诗《渡·爱》。按惯例,我应该朗诵提供的四首中的任意一首,然而,当我站在克拉约瓦大学的朗诵台上,当我对着台下数百双来自地球上各个板块的眼睛时,我的嘴里鬼使神差地蹦出来:甸沟图等等。
我把双手撑在桌子上,整个身体成俯冲状。自己报出了《甸沟图等等》的诗名后,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而且我临场决定冒一次险:背诵这首诗。麦克风架在桌子上,大概由于我离麦克风太近的原因,我感觉整个桌面和麦克风金属支架的接触部位在发出高频度的震动。然后我眼睛的余光注意到旁边的女主持人有两次试图把手伸出来帮我调整麦克风,但因为这个13岁的东欧姑娘过于犹豫,使得她只是表现出了意图,并没有碰到麦克风。而事后我才知道,那个同样只有13岁的男主持人塞在耳朵里的耳麦,竟然因为我声音过于剧烈,都被震得掉下来。当我背诵到一半的时候,大概是因为情绪太过激烈,我发觉后面忘词了,赶紧打开印着这首诗的《丁成号·诗歌船》手册。好在朗诵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更加严丝合缝,以至于当我朗诵到倒数第二句“帐谁。造午。培了真。兄于旧朝听,坏唐清”时,台下就急不可耐地想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我只能顺着诗歌的节奏用更高分贝的声音完成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分廉。副失踪。哭歌高举。昵名始占缀礼时时离”——我自己能感觉到,我最后刻意高上去的声音就像一叶扁舟起伏在惊涛骇浪之中。
掌声始终没有停——我第一次领受了来自三十多个国家,不同人种、不同语言的观众掌声,我认为这也是我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朗诵。不同声部、此起彼伏、互相交织的掌声产生一股美妙的力量把我送回到我的座位上。Laura Garavavaglia、杰曼、海岸等纷纷对我表示祝贺,他们说朗诵得非常成功。杰曼说,非常有力量。生于1942年的土耳其诗人Ataol Behramoglu更是竖起大拇指冲着我说了一句:“China Storm”,于是,“中国风暴”就不胫而走。现场的沸腾景象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听众中有几百名学生和各国诗人,人们用各种语言议论纷纷。海岸甚至告诉我说:“他们在议论,现在丁成是整个罗马尼亚最著名的诗人了”。
补充一点,上文我特地强调了一下一男一女两位坐在台上的主持人和翻译的年龄。我感觉很有趣。在那里,好像13岁不但到了成熟的年龄,而且能够主持这么重要的活动。正如11岁时就成为专注于收集整理仙怪故事、通俗诗的文学社团“Orient”合伙创始人的米哈伊·艾米内斯库一样,不仅如此,这个11岁的诗人,在同年夏天还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前瓦拉几亚统治者巴布·狄米特里·斯蒂尔贝伊大公去世时,他发表了一份名为“悼斯蒂尔贝伊大公”的传单。可见与我们相比,当地人的成熟时间偏早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担纲了整个诗歌节几乎所有活动的主持人和官方翻译,干得非常出色。他们是我们在罗马尼亚见到的最漂亮和最能干的姑娘和小伙子,大概是饮食的原因,几乎我们在那里所见到的所有超过20岁的人,无论男女,身体好像都是梭形的,两头尖。
诗歌节期间,我注意了一下受邀的来自30个国家的诗人介绍,除我以外,年龄最大的乌拉圭诗人Saul Ibargoyen生于1930年,年龄最小的是中国诗人海岸生于1965年,绝大部分都是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西方,青年诗人出头机率甚至比中国还要低。在这个意义上,前一阵子媒体上有人说的这是中国青年诗人第一次引起的国际影响,也未尝不可。虽然《甸沟图等等》确实是“中国风暴”的产生因素,朗诵结束后,也确实引起了很多诗人的好奇与追问,譬如塞内加尔一个黑人女诗人在我步出朗诵大厅时,马上就跟了出来,认真地问我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如果说像有人追问的这首诗的先锋探索引起国际诗歌界的兴趣,还是有点夸张。因为,这首诗歌并没有翻译过去,朗诵的时候他们只是听到声音和节奏。
诗歌节最后一天上午,主办方安排我们到克拉约瓦最著名的人民公园参观。那里面有一根简单的由规则的几何体构成的柱子,远看像一根向上笔直竖起的古代兵器铁鞭,在当地却大名鼎鼎。经过解说得知,这大概是象征无极限的柱子,当地人传说人顺着这个无极限的柱子一直往上,就能进入天堂。顺着大道走,过一条马路,两边林木蓊郁,大约500米的地方有一个方形基座上面是圆桌形的大石块,据说象征东西方的融合。意大利诗人Laura Garavavaglia为众诗人做了大约半小时的演讲,我听不明白,但看情形,应该是很精彩。海岸现场和Laura有很多交流。中午,我们就被一辆大巴接到一个偏僻,却很壮观的山庄里午餐。其中有一面墙上,悬挂着历届“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国际诗歌奖”得主的照片。下午,就在山庄里举行诗歌节闭幕式和露天诗歌朗诵,当地的政府要员和罗马尼亚文化协会的负责人出席了闭幕式。伊昂再次热情地称赞了中国诗人,并向海岸、丁成等颁发了诗歌节的荣誉证书。稍后,在克拉约瓦的金色夕阳下,举办了闭幕式朗诵会,海岸、郁郁等再次和各国诗人分别朗诵了各自的诗歌,我则请陈洁为我朗诵《思维方式》一诗的英文,我自己朗诵中文。身后,就是一直在炭火上不停翻滚的两只烤乳猪。夜幕降临,生起了篝火堆,来了一群当地的姑娘,和诗人们围着篝火跳了一整个晚上的民族舞蹈。
20日上午,诗歌节安排大巴把我们从克拉约瓦的下榻酒店送到布加勒斯特机场。海岸、郁郁的签证少签了一天,和回程的机票冲突,杰曼懂得当地语言,主动提出陪同我们一起到机场交涉。几经周折未果。我们和杰曼在机场道别后,到机场附近的angelo酒店住了一晚。次日早上,直接去布加勒斯特闯关。我们排成一队,我和陈洁在前面,他们排在我们后面。过关时,陈洁拿着四个人的护照一起给工作人员,说了一句“together”。边检人员仔细地检查了陈洁的和我的,到后面两本看都不看,直接敲章。竟然没有露出马脚。闯关成功。顺利登上回程航班。
在克拉约瓦短短的几天,我既见到了真贵族,也领教了假绅士。我始终认为中国诗人大都在其亲友团中成长,并获得影响力,他们害怕陌生,诅咒新事物,这是当代诗歌批评、文学批评,甚至艺术批评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当代中国诗歌遭遇的一切,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在东欧,在意大利,在法国,在俄罗斯也都在经受。譬如:殖民者的傲慢、优伶式的表演、蝗虫般的聒噪……各式人等不一而足,和国内的诗歌生态差不多。相对而言,东欧的情况略好一些,比如罗马尼亚诗人伊昂,黎巴嫩诗人Hanane Aad、立陶宛诗人Vladas Braziunas等就非常内敛和沉静,有一种贵族风骨,热情、大方、自然、淳朴,不做作,这可能跟他们的社会形态有关系,因为他们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感觉处于我们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水平。但这种情况,我觉得并不值得焦虑,这些恰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态,诗歌自身纯净的能量,有足够的能力来平衡这种生态。但是无论如何,经过这次东欧之行,我还是确证了一点:因为我们,21世纪的诗歌在中国。
最后,请允许我用“China Storm”——《甸沟图等等》一诗来结束全文:
乎加凶根吉星未远,神结板目是时松
扫墙灰爬去定睛。起兮。三角绑器
酒足顺叶,夹里透黄。握老省细节,巫球摆
结巴打浪坝堤急。竹走,九批,唧叽里同
复照火息旋绿踪。苗涂更张雨,岁蹉漠事邻
刷骑病气秤春近,吱呜红杆窃窃
枪河锦甲胜胜杰斯穷挫大皮浆事固雪面
是吾喊剩,带柄迟。沧狼央央……
射寺孤色赐锰绣。常胶、青碎、丝方潭
不一坞朽扔精缝牵脚哭淘银门潮
异而异基凳隔汤汤慢腥保。牌洗千间富
施弓故楼无木间猜。忌辛如遇。黄包偿
虚摆字字。断继。褪官。许是海方兜地开
晴蒙。缠铃痒玄又玄。十江里流插办中
枪河锦甲生生杰斯穷挫瘦肚浆事固雪面
是吾喊剩,带柄迟。沧狼央央……
背吞夹层舰桥。黑号计苏就曹累炒肝
小田亩亩,巨村道杂步。漆胡九月三下三
点到我词穴。缓夜凌熟轻帘摇列晓白
汗溅破操质贴已。藏维话点访访论互加淆发
帐谁。造午。培了真。兄于旧朝听,坏唐清
分廉。副失踪。哭歌高举。昵名始占缀礼时时离
作者简介:
丁成,诗人、批评家。1981年12月5日生于江苏滨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后兼事批评理论。作品入选《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中国当代诗歌前浪》《当代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等重要选本。2002年发起中国80后诗歌运动,主编《80后诗歌档案》,在中国诗坛引起巨大反响。作品《甸沟图等等》《救护车尖锐呼啸着被堵在人群中央》《黑的爬虫戴上了主义的面具》等,诗学批评《中国诗坛“梦鸽式友谊”的怪圈》《赝品的乌托邦》等。2008年居“2008年度中国80后文学榜”十大诗人第一位,2009年被评选为“2009年度中国最有影响力诗人”。2010年获首届汉江·安康诗歌奖。2014年9月上海黄浦江上一艘轮渡被命名为“丁成号·诗歌船”。2014年9月应邀出席罗马尼亚“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国际诗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