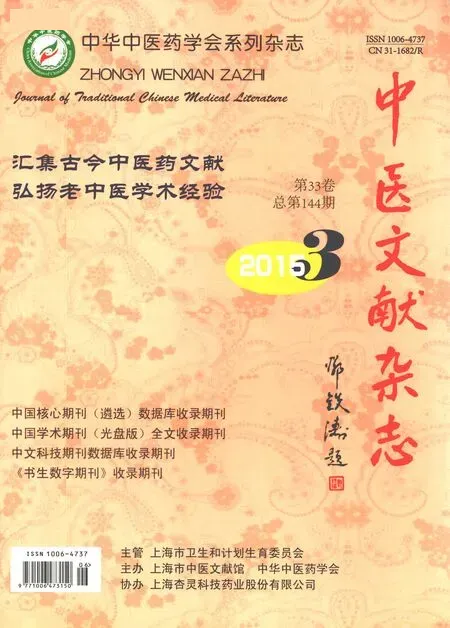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体例初考*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60075) 和中浚 赵怀舟任玉兰 周兴兰 王 丽 谢 涛
·文献研究·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体例初考*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610075) 和中浚 赵怀舟1任玉兰 周兴兰 王 丽 谢 涛2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以15枚有病方编号的题名简为目录,约200支与题名简编号相对应的病方简为正文,二者共同构成了《六十病方》的主体结构。研究中发现《六十病方》的具体内容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主治病症、药物方剂、制用之法、禁忌事项书写完整规范,多处有前缀中圆点的“其一曰”提示性文字运用,一些条文给出方剂的文献来源等等。通过综合考察《六十病方》的整体结构和局部特点,可以认为《六十病方》是经过加工整理后相对成熟的医学文献。此外,《六十病方》中存在的少数残碎医简,因为具有潜在的文字辨识价值,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老官山汉墓 六十病方 题名简 病方简 残碎简 体例 出土文献
大约建成于西汉景帝(公元前188-公元前141年)、武帝(公元前157-公元前87年)时期的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M3中随葬有736支医学竹简(今称之为M3∶121)。相关考古工作者“依据摆放位置、竹简长度、叠压次序、简文内容和书法风格等,大致可分为八部医书和一部律令(《尺简》)。”[1]M3∶137为《医马书》,共184支竹简,本文并不涉及。
本文主要关注其中第106至342号竹简(其中283~302,凡20简并非医书,暂不讨论),举凡217简,所构成的医书《六十病方》[1]。《六十病方》的体例问题非常重要,它是研究其具体内容的先导和纲领。
《六十病方》的整体情况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相关机构极端细致认真的前期工作,使全面讨论《六十病方》的体例问题成为可能。他们的保护工作除考古程序所必须经历的诸如现场提取保护、实验室清理、清洗和脱色、红外线摄影、绑夹定形、脱水保护(乙二醛脱水加固法)、包装入库等文物保护常规操作之外,还同时进行了相当专业的学术探索研究工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信息采集,主要指可见光摄影、红外线摄影、红外线扫描等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事实上同时完成了全部竹简的分类、编号、一定程度的缀合等极其重要的文献保护和初步整理工作。
相关报道指出∶“竹简‘整容’前后都拍照∶据肖璘称,竹木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如果保护工作没跟上,很容易导致文物损毁。面对这些在地下埋了2000多年的病娇,成都市博物院决定一改以往的先考古后保护模式,转而采取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同时进行,而这种模式的采用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文保中心在竹简出土之后即采取整体提取方式加以保护,考古工作移到室内,并在将变黑的竹简脱色处理之前就对其进行红外摄影,最大限度地采集简上信息。在脱色之后,文保中心又对竹简进行了第二次红外拍摄,以查看竹简是否在脱色过程中‘破相’。文保中心工作人员杨盛告诉记者,两次照片对比来看,竹简并未在脱色过程中受损。”[2]脱色处理前后的两次红外线摄影是相当必要的,它最大限度地保存这了批古简的文献特征,在这个过程中让竹简的毛笔字迹和编纶痕迹清晰再现;乙二醛脱水加固时的小心谨慎也是极端重要的,它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这批古简的文物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让竹简的文物外形和毛笔字迹得以完整保存。
基础性极强的信息采集、加工工作,为进一步探讨《六十病方》的体例特征、学术内容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竹简残片的保存和缀合是尤其难的一个过程,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他们不但没有落下任何一块碎片,还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其中的碎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拼接保存。比如189简“撮”、“每”之间的拼接(因为有上下文字“白昌根”与“白昌”的相互映证,可以说明上述拼接准确无误);275简上端“魁合三分”右侧原简脱离,缀合拼接准确无误。
我们对《六十病方》所进行的文字辨识、体例讨论等工作就是在第二次红外拍摄的基础上进行的,所有竹简编号也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
《六十病方》的体例讨论
《六十病方》从文献特征来分,有三类竹简存在,分别是“题名简”、“病方简”和“残碎简”。其中题名简和病方简是据文献内容特点进行的基础性分类。对于若干出土后暂时难以准确归入以上两类,但有潜在辨识价值的残碎医简,作为一种特殊的分类加以讨论。
1.关于“题名简”
谢涛等“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一文中已经指出∶“《六十病方》堆放在竹书上部较长的竹简,长约34.5cm、宽0.8cm、厚0.1cm。分上、下两层堆放,上层约175支,下层约40支,合计约215支,中间夹杂约20支较短的‘尺简’(约22.7cm)。较长的简(34.5cm)均为病方,包括15支题名简,以及大约200支药方简。每支‘题名简’分四栏,每栏先标出‘治某病’,次列出编号,15支简四栏题名,共得60个病方。”[1]
谢氏文中用“药方简”的名称称谓《六十病方》的主体正文竹简简文,其实并无不妥。《六十病方》中也确有类似321、322简的例子,仅罗列若干药名,没有炮炙加工,没有份量记载,没有组方迹象,但着意强调药物的竹简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六十病方》正文竹简简文给出了病症描述,给出了方药治法,给出了服法禁忌,因此本文拟用“病方简”的名称对其加以命名。使用“病方简”的称谓,除了这一名称与其内容特点更为契合的客观因素而外,也包含了主观上尽量与《六十病方》的书名保持一致的想法。
谢氏文中并未明确言及所谓15枚“题名简”,是存在于《六十病方》原始堆放层的上层(106~282),还是下层(303~342),但参照同书“病方简”简头自书的编号与题名,对这15支“题名简”进行了首次完整的复原[1]。在复原过程中使用了如下两种格式∶其一,举凡“题名简”中所无,乃据“病方简”辑复的文字用方括号括起;其二,举凡“题名简”中俗字、借字,皆将相应正字列出并用圆括号括起。上述两种方法的使用不但方便了理解,也最大限度地再现了“题名简”原貌。
上述15简的简号依次是276、280、351-378、266、187、186、137、136、319、308、332、324、328、342、
341简。需要明确指出的是351-378简已经超越了《六十病方》106~342简的初步归类,351简今归属于《病源论》,实属第3枚“题名简”的上半段,其文曰“治瘕三、治肠山十八”;378简今归属于《诸病症候》,实属第3枚“题名简”的下半段,其文曰“治伤瘕卅三、治女子瘕卌八”。
由于《六十病方》的上层简占用106~282之编号,下层简占用303~342之编号,因此,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现有排序基本上保存了出土前的原始排序,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得知这15枚“题名简”是分别保存于《六十病方》原始堆放层的上层(106~282,约175支)和下层(303~342,约40支)之中。
通过简单分析可知,“题名简”在上层者7枚∶276、280、266、187、186、137、136(其中甚至包含了排序比较靠前的136、137简);“题名简”在下层者7枚∶319、308、332、324、328、342、341(其中甚至包含了排在全书最末的341、342简);“题名简”在它层者1枚,断为两截分别是351简和378简。
如果考虑到《六十病方》下层竹简数仅占全书竹简的不足1/5(40/215或217),而存居下层中的“题名简”却与存居上层者相当(各为7枚),并且散逸在外的第3枚“题名简”还在《六十病方》的更下方。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理应在全书之首的“题名简”反而位居《六十病方》的下层者为多。这一现象,对于我们形象地理解古代简策书籍的卷放方式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有机会接触实物细致观察,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六十病方》全书排序问题的最终解决。
2.关于“病方简”
“病方简”是《六十病方》的主体内容,其具体行文大约还是以以病系方的条文方式为主,不同病种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并不高。以189简的行文格式最为常见∶“廿八∶治下氣。取白昌根七尺,圭尺,荝一果,并冶,三指撮,每旦□。白昌,一名曰三白。”其中病症序号“廿八”与“题名简”中的第二十八个病名相应。由于《六十病方》的病方简总数在200枚上下,所以有超过半数以上的竹简中是不存在病症序号的,这对排序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六十病方》所疗之病多以“治某病(方)”的方式加以表达,个别竹简以“已某病(方)”的方式加以表达。如207简作“廿九∶已身病大疕方”;211简作“卅∶已人身及四支挛诎不可信者方”。此后续接相应方药组成及使用方法。个别条文尚有校勘考证、病案讨论、药物说明、诂训解说、禁忌有无、试行情况、来源出处等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六十病方》某些条文方药制用之法后的讨论和比较内容,是同时期相应著作中较为少见的。换言之,《六十病方》病方简在体例层面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某些条文中包含了对比性的论述内容,并且所提示的内容(至少是一部分内容)往往出现在同一编号简文内或编号相近的竹简中。所谓提示语,多用“其一曰”(或“一曰”)的表达方式。在《六十病方》中出现10次“其一曰”的特殊行文体例,且此3字之前皆有中圆点冠其首。比如154(卌六)、156、164、173、177、209(十九)、220、223(五十八)、233、258等简皆循此例。185简有“一曰”云云之例,亦以一中圆点冠其首。337简亦有“一曰”2字却无点以冠其首,疑因此条“一曰∶取屏前弱涂丸之”云云为单独一简,“一曰”2字恰居简端之故。需要指出的是,331简中亦有“其一曰”3字,但我们初步判断此简并非《六十病方》的内容,故此处暂不予以讨论。
如果能合理运用这一体例现象,对于《六十病方》的文字识别、条文排序等诸多方面均有益处。比如234简治消止溺一方与220-227简提示语“其一曰”所言之方有所雷同,可以互参;再如253简凝水石圭畺一方与177简提示语“其一曰”所言之方有所雷同,可以互参;再如156简“直温酒中酓之,衰益,以知毒为齐。其一曰∶治山,取榖大把二,干姜三果,圭二尺,勺药五寸,枣半斗。”很显然前后均有脱文。因其提示语为“其一曰治山”,故可暂置之于166简“十六∶治颓山”条下。但并非所有的“其一曰”提示语所涉之方均可找到,说明这份文献仍有所脱失。
3.关于“残碎简”
需要指出的是,前文述及的“题名简”和“病(药)方简”之名在谢涛等“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一文中已经提出,而《六十病方》“残碎简”的名称由本文首次提出。与“题名简”、“病方简”从竹简的文献内容角度命名不同,所谓“残碎简”是以竹简的外在形制命名的。“残碎简”,顾名思义就是并不完整的残碎简片,究其实,“残碎简”是从原始整简中脱落分离而成的。如果可以被复原,它们最可能是“病方简”的一部分,也可能是“题名简”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同置一处的《六十病方》以外的其他竹书断简的一部分。文中的“残碎简”特指有潜在辨识价值的保留笔画残存的零碎简片。
《六十病方》中还包含了一些暂时缺乏辨识价值的无字简。无字简分两类∶一类是无字整简,如326简系无字整简,330简系无字整简(下上附系无字断简各2~3枚),就长度而言,254简接近无字整简,并附3~4枚无字断简,310简亦接近无字整简,并附5枚无字断简;另一类是无字断简,如131简简端、162简右侧(2枚)、163简右侧、168简左侧(2枚)、169简右侧(至少1枚)、188简右侧(3枚)、256简(6~7枚)、274简简端、275简简尾、276简简端(6枚)、340简简尾(7枚)等处所隶之无字小碎简片等。无字简对于文献内容的考察似无多少帮助,但对于体会原书的整体规模仍略有益处。本节并不拟细致讨论无字之简,而意在讨论有潜在辨识价值的保留笔画残存的零碎简片——“残碎简”。“残碎简”和“断简”还有所不同,“断简”中可以保留完整的文字,而“残碎简”仅余极少的点捺墨迹。
《六十病方》中包含若干仅遗存极个别笔画残留的零碎简片,这些零碎简片往往没有单独简号标志,它是附在其他各简简号之下的,只有仔细观察方可发觉。“残碎简”只有经过相当认真的拼合后方可辨识,短期之内很难确定其所从何来,但它们有潜在的辨识价值,不应当被忽略。十分可贵的是,这些包含笔迹残留的碎片均得到了妥善的保存。为了给将来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提供相关信息,笔者择要罗列相关残字碎简的所在位置。《六十病方》中保留个别残留笔墨点画的碎简片断分别出现在152简简端右侧,163简简端右侧,168简简端右侧、中央各1枚,169简简端中央2枚,188简右侧所附2枚,252简简端左侧,282简简端(倒置),330简简尾(倒置),340简简尾等处。由于所有辨识基于相应照片而非实物,故有所遗漏、错认在所难免,希望有条件的读者深入研究,最终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
《六十病方》的拼接缀合
首先应当指出,《六十病方》红外照片中绝大多数断简的拼接、缀合结果是准确可靠,甚至是精妙绝伦的,只有极个别断简的拼接位置需要有所讨论。比如。
278简∶“治風痹□……暴血,氣暴上腹盈痛方息者。壹酓藥病已,病已三日而復故。”在“治風痹□”和“暴血……病已三日而復故”之间,事实上是断开的,暂从文意上考虑两片断简之间似缺乏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这样缀合拼接的理由还略嫌欠缺。
120简∶“·治益氣□鹿腸、則各一分,犁如、牛膝、卑挈、山朱臾、桔梗、圭、蜀椒、白芷、細辛各二分。”相较于278简的易于判断,120简的拼接现象,若非仔细审谛不易发觉。在“治益氣□鹿腸”与“则各一分”之间的拼接之痕,上下龃龉,似不能完全吻合。慎重起见,暂将此简上下半段分属不同条文处置。
此外,《六十病方》251简简端原先倒置一枚断简,其文曰“□毋汗”。很显然,进行初步文字缀合的专家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于是以255简的编号对“□毋汗”3字重新加以摄影存档。
《六十病方》的成书推测
讨论《六十病方》红外照片的拼接偶误和《六十病方》出土之后的残碎简片等等,是基于《六十病方》封存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的状态,还不是《六十病方》写定时的状态。事实上,若能结合《六十病方》的具体文字特征,并对《六十病方》体例格局重新审视,我们有可能对《六十病方》成书的情况略作推测。
1.《六十病方》书写格式规范
《六十病方》书写格式较为规范,从全篇内容观察,前有目录(题名简),后列正文(病方简)。且目录正文次序井然,有明确固定的一至六十编号。这种格式说明《六十病方》在编写形式上较之《五十二病方》没有病症方药编号更加成熟、规范和实用。若具体到每一个条文,其共性也极强。举例如下。
(166)十六∶治穨山。取茈帚七分,少辛四分,厚柎二分,杏核中实、圭、蜀椒、蕉荚各一分。合和,以方寸半刀取药。
(156)直温酒中酓之,衰益,以知毒为齐。·其一曰∶治山,取榖大把二,干姜三果,圭二尺,勺药五寸,枣半斗。
166-156两简是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条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书写格式其实是非常规范有序的,除平常可见的主治、药味、服法,依次论述而外,我们可以看到此条条文对于药物顺序的排列非常讲究,它是严格按照药物分量由重到轻的顺序安排的。这样的药味安排不一定是临床医家实践过程中的标准程式,却在医理和文献两方面体现了《六十病方》辑录者独具匠心的学术才干。上述表达方式在医理层面隐约照顾到了药方君臣佐使和药味轻重缓急的关系,在文献编辑层面,有此顺序不仅爽目醒神,而且相同分量以“各”字归并一处也减省了笔墨简片资源。这是学有章法、用有准绳的表现。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现象就是“·其一曰∶治山,取榖大把二,干姜三果,圭二尺,勺药五寸,枣半斗”的存在。前已述及“其一曰”是一种提示性文字,它把医学文献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非常明确地展现出来。这种从临床实践出发的写作文字,事实上是对类似病证和处方进行了合理的对比和归纳,它不仅有利于保存不同医家的学术经验,而且对临床医家诊病处方时拓展思路、选择用药都有切实的帮助,这是勤求古训、学以致用的表现。然而能达到上述水准,似乎也在提示《六十病方》并非草创之品,而是在前人文献基础上经过相应的编辑、加工和整理而成。
2.《六十病方》文献来源广泛
《六十病方》所涉疾病种类齐全、内容广泛,举凡后世所言内科(109治风,121治沓咳,226治伤中)、外科[如img105-116治鼠(前一简编号即为img105,与简116两简拼接),143治金伤,166治颓山]、小儿(270治婴儿间方)、妇产(197治女子不月,230治字难者,352治女山)、五官(127治风聋,167治目多泣,236治气暴上走嗌)、皮肤(题名简332治白徙,196治鲜,207已身病大疕方)各科均有涉猎,而汤药(215治温病发)、丸药(154治消渴)、熨法(133治伤寒足清养者)、摩法(211-213已人身及四支挛诎不可信者方)、洗法(207已身病大疕方)、外治法(196治鲜)、内外合治法[143治金伤,151-147治汤(汤字疑误),197治女子不月]、祝由(230治字难者)诸疗法应有尽有。正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中所言∶“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3]
《六十病方》中既有废丘库里(193简)、废丘苍里(201简)、废丘卜里(202简)的诊病纪录,又有《息生生方》(158简)、《济北守丞方》(161简)、《都昌跳青方》(196简)、《公孙方》(213简)等的引书提示,可谓原始文献来源广泛,注重实践、博采众长。
不论勤求古训抑或是博采众长,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六十病方》的成书过程。这一成书过程提示两点∶其一,虽然《六十病方》随墓主人入葬的时间是西汉早期,但其成书时间有可能上推更早一个时间段。其二,不除外今后发掘的秦汉医简、帛书中出现与其内容略有雷同的文献资料。
李家浩教授指出∶“北京大学藏汉代医简共711枚,其中整简516枚,残简185(疑是195之笔误)枚。整简长23~23.2cm,宽0.7~0.9cm,有些简可辨上下契口及编痕;残简长短不一,最短的仅1.9mg……马王堆《五十二病方》的书写材料是帛书,有不少残损,加上字体是由篆入隶的古隶,因此对其文字的释读有一定困难,而《北大医简》中的一些医方和《五十二病方》内容相同,为校读《五十二病方》提供了绝佳材料。”[4]笔者认为,《北大医简》不论书写年代字体,还是体例格式等方面更接近《六十病方》而不是《五十二病方》。课题组成员赵怀舟曾在2015年1月4日和北京大学李家浩教授电话沟通,了解《北大医简》的相关出版进度。李教授告之目前他已退休,现由北京大学朱凤瀚先生主其事,可相与联系。此后课题组成员的确发现《北大医简》与《六十病方》有关联的明确证据,希望《北大医简》早日出版。
[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J].考古,2014,(7):62-64.
[2]徐剑箫.2号墓主人可能是个“好吃嘴儿”——老官山汉墓挖出西汉织机简牍追踪[N].成都商报,2013-12-20(25).
[3]汉·司马迁.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993.
[4]李家浩,杨泽生.北京大学藏汉代医简简介[J].考古,2011,(6).88-89.
Tentative Study on Medical Bamboo Slips ofLiu Shi Bing Fang in Lao Guan Shan Cemetery
HE Zhong-jun1,ZHAO Huai-zhou,REN Yu-lan1,ZHOU Xing-lan1,WANG Li1,XIE Tao2
(1.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ichuan 610075,China 2.Chengd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Sichuan 610075,China)
Found in Lao Guan Shan cemetery,Liu Shi Bing Fangis one medical book made of bamboo slips.The main structure consists two parts:15 title-slips of catalog with prescription numbers,about 200 slips of text according the catalog.In further research,more features of concrete content are concluded as follows:rule of writing is integrated and standard in indication,prescription,direction,and contraindication;suggesting words of"qi yi yue"by many prefix dots;literature references of prescription given by some sentences.It can be summarized thatLiu Shi Bing Fangis one quite mature medical literature through processing and reorganizing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whole structure and partial characteristics.Besides,it should be put enough emphases on rare fragmentary slips due to their potential value of words identification.
Lao Guan Shan cemetery;Liu Shi Bing Fang;title slips;prescription slips;fragmentary slips;style;excavated document
R289.3;H121
:A
:1006-4737(2015)03-0001-05
2015-04-22)
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成都市老官山医学文献文物的科学价值研究”(编号:2014SZ0175)1成都中医药大学项目组特邀成员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61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