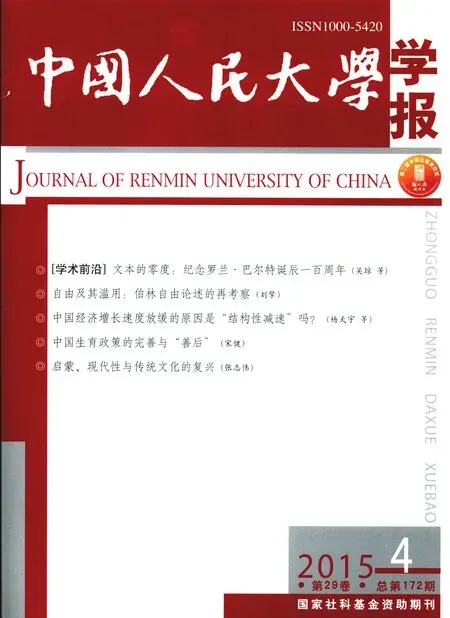论和平主义
曹 刚
论和平主义
曹 刚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关于和平主义的一些重要伦理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包括:(1)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问题。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是基于合意的契约关系还是内在的共生连带关系?(2)和平主义的性质问题。积极的和平观是否必然带来绝对的和平主义?(3)和平主义的公民主体问题。作为一个世界公民需要何种自我意识?我们的基本主张是: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是共生连带关系而不是契约合意关系;积极而相对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更合理的立场;应该做一个具有内在的普遍意识的地球公民。
和平主义;共生;地球公民
和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平主义是人类活动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但目前的伦理学研究并没有为和平主义的基本伦理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和答案。本文试图表明: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共生连带关系;和平主义是为正当暴力预留了空间的、相对的道德原则;和平义务的主体应是具有内在普遍意识的地球公民。
一、共生连带关系是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
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伦理问题,是一个事关和平主义作为道德原则的有效性问题。相关论证中最常见也是最有影响的思路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契约论思路。霍布斯认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要走出这种极其糟糕的自然状态,“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1](P96)在和平的激情,尤其是在死亡恐惧的推动下,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为了走出自然的战争状态,彼此签订以“寻求和平,信守和平”为第一条款的和平契约,并由此进入文明社会。可见,霍布斯的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是一种契约关系。和平主义的有效性取决于契约关系中所内涵的值得珍视的人类价值。(1)契约关系是一种合意的关系。契约主体是自愿而不是被迫地签订契约的,契约的和平条款是当事人自愿施加的一种约束。这种自愿施加的约束是当事人同意和允诺的结果。(2)契约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缔结契约的双方或多方是彼此独立和平等的。彼此的人格是平等的,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也是公平的。在契约的和平条款面前,不存在任何身份贵贱的差别和规则之外的特权。(3)契约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契约关系本是一种交换关系,人们能够用于交换的东西,都是能够满足对方需要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交换的过程也就是彼此满足从而实现互惠的过程。和平便是孕育在交换过程中并有利于契约各方的共同善。可见,把契约合意关系作为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与契约论的思路不同,另一种思路是把生命共同体的共生连带关系作为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池田大作在谈到佛教的“缘起”思想时说:“万物存在于相互的‘由缘而起’的关系性之中,独自能单生的现象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佛教的世界观。”[2] (P226)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彼此依赖,共生共存,每个个体的生命本质的实现程度都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所以佛教强调万事万物的和谐。从这一基础出发,在对待和处理各种关系时,必以慈悲为怀,信奉和平主义的道德要求。当然,把共生连带关系作为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不只是佛教的主张,也是儒家和道家的价值理念。事实上,很多西方学者,如狄骥、涂尔干等,也主张把社会团结建立在社会连带关系之上。把共生连带关系作为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也具有相当的理由:第一,共生是所有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共生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自然万物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彼此共生的命运关系,这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在人类社会中,连带关系是根本的社会存在,任何个体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在连带关系的结构中实现,这也是一个人类学的事实。第二,共生不仅是一个生物学和人类学的事实,同时也是人们共同追求的价值。人类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普遍联系着的链条之中,共生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础。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是在彼此依赖中成长的,共生关系是个体实现自我完善的一个前提和基础,破坏了这个基础,每个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就会受到釜底抽薪般的毁灭性打击。可见,共生对于人类发展和自我完善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是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好处的共同善。第三,人类社会的竞争关系不可避免,但这种竞争是在共生关系的基础上的竞争。倘若竞争关系破坏了共生关系,社会必将崩溃。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内在目的就是要保护和促进有利于共生的和平秩序。菲尼斯把共同体区分为抽象的共同体与具体的共同体。[3] (P135)诸如家庭、企业、宗教团体、国家乃至国际社会,都是具体的共同体。虽然具体的共同体各有其不同的具体目的,但任何具体的共同体都内在地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也即都可以想象成一种“联合或者走到一起”的秩序。因此,各个不同的具体共同体都共有一个内在的目的,即维护和促进使共同体得以存在并完成其使命的内在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共生的秩序是所有共同体的内在目的,而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共生连带关系之上的约束人类行为的基本道德要求。
综上所述,两种思路各有其合理性,但我们认为把共生连带关系作为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更具有说服力。原因有三:(1)契约关系是一种可撤销的关系。在契约论的思路里,由于契约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为对象的外在关系,社会将成为一个为自利目的而进行合作的外在结合体,因此,人们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遵守和平契约,同样也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抛弃和平契约,从而再陷入战争状态。与此不同,共生关系是不可撤销的关系。每个个体都是共生连带关系之网上的一个纽结,没有了这种关系,也就没有了个体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共生连带关系是内在于主体的构成性要素,是一种不可撤销的关系,以这种不可撤销的伦理关系为基础,和平主义的道德要求就具有了不可动摇的基础。(2)契约关系更多的是理性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它很难约束群体之间、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也不可能关注人对自然的暴力问题。所以,在霍布斯看来,国际社会仍处于自然状态,为保护国家安全,各国可以不择手段。至于以人和自然的和平相处为主题的绿色和平问题,更不在其视野之内。与此不同,共生关系是开放的关系,“我们所说的共生,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限于内部的共生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4] (P120)共生连带关系不只存在于群体之间、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人和自然之间,和平主义要求的不只是社会和平,还要求国家之间的世界和平,甚至要求人和自然之间的绿色和平。池田大作就主张把和平的理念贯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认为人和动物并不依赖毁灭对方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人们只有善待地球、珍爱自然、关照未来,才能实现彻底的和平主义状态。(3)契约关系的互惠性质决定了和平的消极状态,但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的消极状态,还包括互帮互助的秩序。正如池田大作所言:“所谓和平,是相互之间不加任何恐怖于对方,相互衷心信赖,相互爱护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和平状态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唯有这样,才可以称之为人类社会。”[5](P250)因此,共生连带关系包含了对陌生人的责任的维度,建立在共生连带关系基础上的和平主义必然包含平等尊重、利益共享、友爱互助等基本要求。总之,把共生连带关系作为和平主义的伦理基础是更合理的思路。
二、积极而非绝对的和平主义
积极的和平观认为,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秩序状态,还是没有暴力、贫困、饥饿、生态破坏以及一切不人道的行为的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
积极的和平主义认为,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暴力行为都是恶的,是应当禁止的不正当行为。有些学者,比如池田大作,就主张积极而绝对的和平主义。他指出:“人类所要解决的课题,不单是实现没有战争这一消极的和平,而是要实现积极的、一种能从根本上改变威胁‘人性尊严’的社会构造的和平。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明白并享受到和平的真正意义。”池田大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倡导慈悲与宽容的绝对和平主义。“现在不可能有什么保卫正义的战争,就是说战争本身已消灭了正义。”[6](P235)与此不同,我们赞同积极的和平观,但不同意绝对的和平主义,而主张一种积极而非绝对的和平主义。这个主张在运用和平主义原则来处理各种价值的、利益的和情感的社会冲突中自然地呈现出来并得到印证。
(一)和平主义主张以平等尊重的原则解决价值冲突问题
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处境是多元价值的存在,价值观冲突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和战争屡见不鲜。恩格尔哈特曾用道德陌生人和道德朋友的概念来描述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既与道德朋友共处,又与道德陌生人打交道。道德朋友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内的成员,他们共享着同样的核心价值观,遵循着同样的基本道德原则,彼此之间有共同信奉的价值纽带来维持他们的和平共处。与此不同,道德陌生人之间的相处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道德陌生人之间由于缺乏根本的价值共识,没有共同接受的道德原则,彼此之间的冲突就可能是一种对抗性的价值冲突。恩格尔哈特认为解决这种对抗性的冲突有四种途径,即征服、论证、改宗和同意。前三者,或者不可欲,或者不可行,只有“同意”是唯一合理的方式。池田大作持有类似主张,他认为,和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善,要建立一个“和平与共生的世纪”、“和平与共生的世界”,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进行“对话的文明”。“对话是打开和平的钥匙”。可以说,通过“对话”解决价值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这个主张不但得到了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在理论上的充分论证,也在处理国内外各种社会冲突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印证。“对话”之所以是打开和平之门的钥匙,是因为在“对话”这一貌似形式正义的程序中,蕴含着实质性的价值标准,即平等尊重的原则。(1)对话意味着对话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彼此平等、相互回应的关系。处理这种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是他者本位,彼此之间的相处之道取决于自己如何回应他人的要求。换言之,他者的立场和需求,而不是自我的立场和需求决定了彼此的相处之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人既不是无需回应的工具性的存在,也不是彼此敌视的异化性存在,对话者需要理解和接受他人的差异性,并尊重他人作为无可替代的特殊性个体的存在。(2)对话意味着对暴力压制的排斥。对话意味着用非暴力的途径解决彼此之间的价值冲突。对话者可以对对方的立场和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但不能因此就用强制性力量来限制和压制对方,剥夺对方说话的权利。事实上,只有在主体有能力对异己进行干预而不诉诸暴力压制时,才真正体现了平等尊重的伦理精神。(3)对话之外仍需保留有限度的暴力。对话既然是以平等尊重为基本价值诉求,其宗旨就是促使差异主体共同生活、和平共处。但“宽容的理由,同时也是对宽容的限制,宽容不能惠及那些拒绝尊重他人的人”。[7](P12)对于那些拒绝对话而突破了平等尊重底线的人,必须有限度地诉诸暴力。
(二)和平主义主张以公益优先的原则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只要承认人的社会属性,就必然要认可共同利益和个别利益的区分,而不同的个别利益在实现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矛盾、冲突和斗争。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基础,就要以公益优先为原则来解决利益的冲突和斗争。当然,在不同的语境中,公共利益和个别利益的“所指”有所不同。在处理国内的利益冲突时,公共利益是指国家所代表的国内人民的共同利益,个别利益是个人利益中区别于共同利益的那一部分私人利益。在处理国际冲突时,公共利益是指人类的普遍利益,个别利益是指国家利益中区别于人类普遍利益的那一部分自我利益。不过,这种区别并不影响利益冲突的性质以及解决这种冲突所需的公益优先的道德原则。利益冲突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私人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的冲突,还是国家自我利益和人类普遍利益的冲突,都应该优先保护公共利益。理由很简单,因为无论是从质上还是从量上讲,公共利益都优先于个别利益。公共利益是所有人或多数人的利益,在量上要大于个别利益;公共利益是个别利益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损害了公共利益,必然导致个别利益难以得到实现和发展。因此,公共利益在质上要优先于个别利益。显然,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应置于优先保护的地位。这里的保护当然不排斥通过暴力的手段来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二是个别利益之间的冲突,包括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国家自我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主义要求以公共利益为基础,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妥协是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双赢的方式。达成妥协的要点是:(1)承认利益冲突的双方和多方之间有共同利益。妥协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妥协,事实上,也只有为了共同的利益,相关方才会作出个人利益上的让步。(2)承认对方的利益有其正当性。妥协要求超越自我中心,肯定对方利益的正当性。如果只认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是正当的,他人的利益诉求都是不正当的,妥协是不可能达成的。(3)要愿意放弃自己的部分利益。妥协要求放弃的是部分私人利益。如果大家都不愿有所舍弃,妥协也无法达成。但妥协所放弃的只能是利益主体不同于其他利益主体或多数利益主体利益的一种个别利益。如果以放弃公共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个别利益之间的妥协,是不被允许的。可见,妥协有其底线,突破底线的妥协行为将被禁止,当然也不排除用暴力的手段来禁止这种行为。
(三)和平主义主张以互助友爱原则来化解社会敌意
当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里,容易产生普遍的冷漠和敌意,一个充满冷漠和敌意的社会是不可欲的,也不是和平主义的题中之义。和平主义主张用友爱来化解敌意,实现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和平。池田大作认为,用“同苦”的情感来巩固社会的连带关系,是走向和平的最确实的道路。[8]他认为,“同苦”是人类共有的心理特质,人们会因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由此可以激发出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有“有了这种‘同苦’的根基,才可能建立起人类的集体连带关系”。[9](P419)池田大作的主张继承了自古以来很多思想家的共识。亚里士多德就主张,友爱不但是个体幸福的重要构成要素,还是把政治共同体凝聚起来的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这根情感纽带的断裂将会导致共同体的种种敌意和冲突。当代学者小林正弥也认为,友爱是比自由和平等更重要的价值。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将友爱的价值置于自由、平等等价值之前,优先得到珍惜和保护,战争就难以发生,而和平有望实现。因为我们可以说“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战”,但说“为友爱而战”却是道理之上的。[10]
我们认为,友爱原则之所以成为化解社会敌意的基本原则,原因有三:(1)友爱具有向陌生人开放的维度。友爱的对象是与之发生关系的他者,是血缘亲情等特殊关系之外的社会个体。如果说亲人是被先天的血缘关系所确定的,那么朋友却是后天选择的。友谊具有将没有先赋性关系的陌生人联结在一起的特质,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友爱是最具平等性的情感。朋友之间的友爱和父子兄弟之类的情感不同,友爱没有辈分之别、长幼之分,是扩展到所有朋友间的平等之爱。(3)友爱意味着朋友之间的和衷共济。朋友之间就是要在对方陷入困境时,伸出援助之手,有福共享,有难同当。(4)友爱还是理性之爱。与由自然情感所致的亲情之爱、异性之爱不同,友爱是理性的产物。亚里士多德就区分了作为德性的爱与作为情感的爱的友爱,这种区分在于前者是包含了理性成分的,后者则仅受情欲的支配。可见,和平主义主张用友爱来化解社会敌意,实现的不只是一种非战争的消极状态,而是一种互助友爱的积极状态,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和平观。
和平主义的道德实践告诉我们,我们不必宽容不宽容者,也不必向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妥协,因此,暴力的正当运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暴力的运用是为了根除暴力,最终实现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积极的和平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积极而非绝对的和平主义。
三、做有普遍意识的地球公民
爱和平不只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共识。公民意识是国内和平的前提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实现世界和平需要什么样的自我意识呢?这是和平主义内含着的一个逻辑起点。牧口常三郎认为人要认识到自己的三种身份,即根在社区的“乡土居民”、形成国家的“国民”、以世界为人生舞台的“世界公民”。他认为人应该超越地方利益,应作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拥有为全人类服务的意识与素养。池田大作提出了地球市民的概念,努斯鲍姆也提出和论证了世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根据这些学者和思想家的提示,我们认为把人的身份分为居民、市民和地球公民三种,更有利于说明和平主体的自我意识问题。
居民的自我意识是边界意识。居民是指居住在某个特定族群共同体的成员。这些共同体是人们在现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交往、共同活动的关系和形式的总和。它们都是由地缘或血缘连接起来的、具有确定时空边界的利益共同体。由于时间的距离,现代人和遥远的后代人之间不能形成现实的利益共同体;由于空间的距离,当地人和遥远的外域人不能形成现实的利益共同体。总之,在族群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中,尽管天然的地理整合力量呈现出弱化的趋势,但总难摆脱自然的和人为的各种界限,从而使利益共同体的边界成为共同体成员的边界意识。而这种边界意识往往具有道德边界的意义,由此决定了我们和他们、朋友和敌人的区分对待:边界内的人是自己人,相处之道是互助共生,实现和平;边界外的人是他者,占有、利用、消灭敌人是维护“我们”的利益的必然选择。可见,只具有边界意识的“居民”是无法承担起实现世界和平的重任的。因为居民的边界意识使得人们总是以“我们”为出发点,从家庭、血缘、地缘群体等等特殊的方面来谈论和平问题。尽管这种边界意识可以借助人际互动产生稳定的地方和平,但这种地方和平不能推及整个社会,更不用说实现世界和平了。
市民的自我意识是“市场人”。市场人意识使得市民成为一个抽象而普遍的身份,其身份意识突破了居民的边界意识。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吉登斯所谓的“脱域机制”发生作用了,在现代社会,地点和地域的概念已经变得模糊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不同场域的“市民”也不再具有边界意识,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是契约而不再是血缘、地缘等自然因素。显而易见,具有自我意识的市民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互为对象性的关系,社会和平只能是市民之间为了自利目的而进行合作的外在秩序。这种外在的和平秩序是脆弱的,因为它去除了和平的伦理根基,即人与人之间互助共生的内在统一性。即便这种和平秩序得以维护,它也只是一种消极的和平,因为从市民的自我意识出发,无法逻辑地推导出对陌生人的积极责任。因此,市民是无法承担起世界和平的重任的。
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普遍意识的地球公民。池田大作曾描述了地球市民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深刻认识生命相关性的“智慧之人”;二是对人种、民族、文化的差异,不畏惧、不排斥,而是去尊重、理解,并视这些差异为成长资源的“勇敢之人”;三是对受苦受难的人,无论远近,都能给予关怀提携的“慈悲之人”。[11]这三点的基本精神就是一种对地球共生关系的内在普遍意识。我们之所以具有地球公民的身份,是因为我们都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仅超越了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等等边界,而且进一步突破了代际的边界,甚至突破了种际的边界,使得在世的所有人、后世的所有人以及其他的生命存在都成了“地球村”的一员。宇航飞行员尤金·塞尔南谈到在太空中俯瞰地球时的观感时说道:“当你在地球的轨道上向下看时,你会看见湖泊、河流、半岛……各种各样的地貌在你的眼前飞快地变换着,白雪皑皑的高山、茫茫无际的沙漠、广阔无边的热带地区……你问自己,在宇宙的时空中,我在哪儿?你看着太阳从美洲落下,又从澳洲升起。你再回头看着自己的‘家园’,却看不到任何将这个世界四分五裂的肤色、宗教和政治上的壁垒。”[12](P10)这段话语显现出的就是地球公民的内在的普遍意识。它预示了一种全球共同体的形成,同时又把人类作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通过对“我在哪儿”的追问,超越了居民的边界意识和市民的自我意识,洞见了万事万物的内在一体关系。可见,在地球公民看来,和平不只是群体内的和平,它应该具有普遍性,其范围不但包括世界和平,还包括涉及人和自然关系的绿色和平;和平不只是自利而理性的个体之间的同意和承诺,其根基是内在于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共生关系;和平不只是消极的没有冲突和战争,还应该是通过正义和友爱联系起来的人类生活的积极的有秩序的状态。池田大作认为:“只有彻底地探讨和理解身边的现实,才能让我们自由地联想到更大的现象。假如我们能培养出这种活生生的想象力,一种对生活和生命的敏锐感觉,就不但能爱自己的邻人,甚至可以把素未谋面的异国人民,以及他们的产物、风土和文化感同身受。对培育出这种感觉的人来说,没有比掠夺国土、令人互相残杀的战争更为可恨的事……这才是走向和平最确实的道路……要和他人共有这种人道意识感觉,不被马塞尔所讲的‘抽象化精神’侵蚀,就要去珍惜和培育自己的内在普遍意识。”[13]
总之,人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但人与其他存在不同,人不但有意识,还有自我意识,对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之间的彼此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的意识,对人类社会的连带关系的意识,也就是内在的普遍意识,只有具有这种内在的普遍意识的地球公民,才会尊重生命,热爱和平,并最终承担起实现人类和平的重任。
[1]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池田大作、戈尔巴乔夫:《20 世纪的精神教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John Finnis.NaturalLawandNaturalRight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4] 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5][6][9]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7] 转引自瞿磊:《作为政治伦理的宽容——个人、社会和规则的维度》,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2)。
[8][13] 池田大作:《人道主义竞争──历史的新潮流》,载《东方论坛》,2009(3)。
[10] 小林正弥:《深层和平与友爱世界主义》,载《太平洋学报》,2008(12)。
[11] 池田大作:《“世界公民”的教育》,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lect-columbia-1996.html。
[12] 林恩·马古利斯等:《我是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李 理)
On Pacifism
CAO Gang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Peace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themes of the era,but concerning pacifism there remain several important ethical issues to be explored. One is which is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pacifism,the concede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or the inner symbiotic? Another is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pacifism,that is,whether the positive idea of pacifism would inevitably lead to absolute pacifism? The last issue is the civil subject of pacifism: what kind of ego should people have if they were the global citizens? We claim that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pacifism is the joint symbiotic relationship,rather than the conceded contractual. We prefer a more reasonable position which is positive and relatively pacifism. We should become global citizens with inner common sense.
pacifism;symbiosis;global citizens
曹刚: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