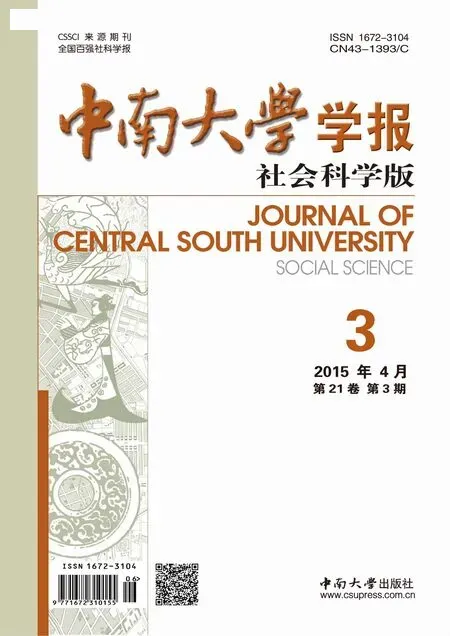《笨花》:民间与革命的双重传奇
王艺,程金城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笨花》:民间与革命的双重传奇
王艺,程金城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笨花》是铁凝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它试图将民间文化和革命伦理结合起来,把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统一起来,探寻历史和人性的真相。它一方面表现着“中国凡人”的家国情怀,实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另一方面,又揭示出革命伦理的某些暧昧属性,表达了对“革命”诉求的绝对性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新的想象空间。
《笨花》;民间文化;革命伦理;融合;冲突
铁凝在《笨花》发表时曾说:“这部作品是一部与以往任何作品均无可比性的大书。”[1]实际上,无论在铁凝自己眼中,还是在读者和评论者心目中,《笨花》在铁凝的创作中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分量和重要性。在《笨花》中,铁凝在日常化、生活化的叙事中展开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努力挖掘出蕴藏于民间的正义力量和英雄品格,在充满生活智慧和生命质感的叙述中表达着崭新的意识形态诉求,体现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雄心和抱负。因此,虽然《笨花》的批评热度随时间推移已经有所冷却,但对这部作品的深入考量和剖析却永不会过时。
一、民间文化与革命伦理的融合对接
甫一开篇,《笨花》就缓缓展开了一幅具有浓郁冀中乡土气息的风情画卷,无论西贝牛一家封闭勤勉的日常生活,还是缓慢流转的黄昏图景,都昭示着冀中平原上这一普通村落里日常生活的传统性和稳固性。铁凝用结实细密的笔触不厌其烦地描绘着笨花村的生活图景,倘若没有外力打破平衡,这琐碎平凡的北方平原生活似将恒久绵长地持续下去。然而,这表面轻盈柔和的素朴日子并不能满足铁凝的野心,想象、还原历史和探寻民族前景才是铁凝这部作品的真正志向所在。所以,笨花村是一个具有“集大成”意义的地点,以它为起点,向喜投身军营,开启了壮阔跌宕的家族史,历经几十年沧桑变幻,又以向有备最终的出走笨花村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铁凝笔下的笨花村是一个优劣杂陈的世界,这里既有如西贝牛一家的本分节俭,也有如向桂一般的不拘小节;既有文成、秀芝夫妇数年如一日的相敬如宾,也有小袄子们“钻窝棚”的荤素不忌。笨花村生存状态的多样是自在自然的,铁凝以欣赏和认同的态度描绘这泥沙俱下的凡俗生活,而并非批判和审视,她曾说过:“我认为不真正地了解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村,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理解中国这个民族……在乡村你不能有屈尊的感觉,但你也不该仰视。最终我觉得我的小说,我要表现的不是审判,不是居高临下,也不是俯视。”[2](16)民间自有它完备的道德秩序,在基本的生存追求之外也有它的尊严与操守,比如“喝号”的风俗。“人老了就要有个号。小时候大人为孩子取名随意:小猫、小狗乃至把把撅子都可以叫;但是这些名字对于一个老年人便不再适宜。……那么,人到了这个年纪就该有个尊称,这尊称便是‘号’。”[3](534)为老人们撰号、喝号的场景是那么激动人心,老人们紧巴已久的生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舒张,乡野的智慧和人情在此刻放射出了庄严的光芒。“喝号”的村风体现了民间道德的雅致与体面,“钻窝棚”的野俗则彰显了民间道德的驳杂与暧昧。向桂与大花瓣儿、佟继臣与小袄子等都曾在窝棚里偷欢行乐,但这种行为在笨花村毫无道德上的约束,反而得到了人们心照不宣的默许乃至鼓励。与之相类的是走动儿和元庆媳妇明目张胆的私情,当每个黄昏走动儿“潜入”元庆家的时候,元庆和儿子奔儿楼便从家里“溜”出来。这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却成为笨花村的常态,“懂得自重的笨花人,谁也不去了解和打探,他们只在等待新的黄昏的到来”[3](13)。民间的道德秩序在男女之事上显出了格外的宽容,它的暧昧态度包容乃至纵容了这些略带邪性的、为正统道德所不容的越轨行为。
作为世俗生活的民间是自由活泼的,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的自由自在。它混合着勤劳、诚实、淳朴、利己、狡黠、目光短浅等复杂的精神基因,在张扬生命力的同时也保留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铁凝对之的表现不是完全原生态的,而是在全局上掌控了一种写作氛围,既充溢着民间生活样态的活力与生机,也反思了既有生活方式中的滞后和愚昧,闪烁着哲理情思的光芒。“小说的民间精神是作家基于民间文化及其传统,融构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所形成的一种审美底蕴与价值取向。”[4](105)铁凝提炼和确定了《笨花》中的民间素材,同时熔铸进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人文追求,形成了极具审美底蕴和超越意义的民间文化视角。
“如果说兵荒马乱是《笨花》的布景,那么世俗烟火则是《笨花》的主词”[5],铁凝试图透过兵荒马乱与世俗烟火的共时相处,编织中国乡土生活的细密纹理,在民间文化的世代相传中发现民族脚踏实地和超越苦难的生存韧性,将“世俗社会的民间精神提升为审美世界的民间精神”[4](105),获得具有普世意义的写作情怀。她将多年的沉淀和培育投注在《笨花》这部大书里,在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里映射出国人的精神气度,探寻复杂人性和民族前景。《笨花》在无数绵密结实的细节叙述中贯穿了中国现代史的寓言,用一种体贴入微的方式去捕捉天道人心的永恒意义。尽管铁凝自言:“《笨花》不是一部风云史,不是传奇,也不是猜奇,也没有刺激性的悬念……我的人物就在我的面前慢慢地活起来。”[6]但向氏家族的兴衰变迁和笨花村人的悲欢离合分明折射着历史风云的沧桑变幻,演绎着中国凡人的传奇命运。
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作者指斥“《笨花》=《棉花垛》+向喜传奇”[7],这样的结论未免武断,但向喜这个人物的传奇经历的确是贯穿作品的主线,他的从戎、升迁、隐退和死亡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而他的处变不惊和全身而退,则体现了铁凝对于沉稳敦厚的中国气质的赞赏。向喜入伍后,随多次交战不断升迁,却终保持着对战争的疑虑和对死亡的敬畏。中庸内敛的气质和骨子里的仁慈让他无法做到“无毒不丈夫”,他虽在实质上参与了影响中国局势的诸多重大事件,却达不到如孙传芳等当初同侪的显赫地位。《笨花》煞有介事地描写了向喜与王占元、孙传芳、曹锟等人的交谊,使人感到不像虚构而更像传记,有迹可循的历史透过一幕幕日常情景浮出地表,虽对正面战场着墨不多,但尔虞我诈中的残酷和血腥也足以令人毛骨悚然,向喜最终的卸职归隐也就是顺理成章了。真正促使向喜回归原乡的是民族战争爆发后日本人的笼络乃至逼迫,“他想,先前我领兵打仗,从北打到南,从南打到北,弟兄们恩恩怨怨几十年,可那都是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现在呢,坐在我眼前的是个日本人,是日本人要和我探讨华北和保定……这就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了,并且让人不寒而栗。”[3](305)由此,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革命意识被正式引入,基于国家民族冲突的仇恨心理使向喜的返归故土带有几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色彩,也使他最终在粪厂与日军同归于尽的壮举在人伦道德和爱国主义两方面都得到了解释和升华。
向喜半生戎马,深刻地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龟山之役促成“南北议和”、直皖战争后诱捕皖系吴广新、任职浙江助孙传芳称雄东南……但正如他自己所言:“那时我在军中也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我的清楚和我的糊涂也算是天时地利的转换所致吧。”[3](305)历史潮涨潮落,旧式军人向喜以服从为使命,他并不清楚自己在革命历史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只是被潮流所裹胁参与进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战斗之中,宏阔的民族国家历史以一种不由分说的姿态将向喜卷入其中。尽管忠孝节义的传统文化基因赋予向喜令人感佩的谦和气质,但军阀混战的残酷历史分明偏离了“义以为上”的人间正道,因而作家也就面临着一种难以将其定位的尴尬。然而,民族危亡关头,向喜拒绝日军笼络而毅然返乡的抉择,张扬了他的民族气节,自此,向喜的行为具有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性”,他的回归既彰显了对生命原乡的眷恋,更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无限忠诚,他传奇英雄的形象就此得到巩固。待到他晚年在粪厂为保护他人牺牲自我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情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笨花村注入他血液里的生命原动力和无私献身的革命伦理相结合,谱写了民间道德和革命伦理最后的传奇乐章。
“革命伦理是以革命的无私、献身、牺牲等价值观念为经脉的个体或群体所应当遵循的革命道德规约与准则,并以服务国家利益为其趋向,彰显了神圣崇高的生命意识与感觉。”[8]《笨花》意欲重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革命历史,但它既不同于“新历史小说”的有意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希图为历史翻案,彻底解构英雄情结,也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通过抽象概念式的说教表达对政治信念的绝对信仰,而是将民间文化与革命伦理结合起来,把历史风云嵌入笨花人的日子和灵魂,挖掘民间文化中有益于生命意义建构的人生事相,将民间文化与革命需求结合起来。实际上,对于向喜而言,他的日常生活和传奇经历是互相渗透的,一切经历都构成了他总体性的日常生活。铁凝并不为了反叛宏大叙事而故意消解他的英雄本质,并不刻意回避他传奇经历中的血腥诡谲,而是将社会历史和各色文化元素嵌入他保守浑朴的生活图景,从而展现出高密度的生命信息。即使是在向喜生命最后的悲壮时刻,铁凝的描述笔触仍然是节制的,“他知道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弄死个日本人,这大半是个以命抵命的结局。开始,他并没有想和那个日本兵以命抵命。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随人愿。”[3](499)一生酷爱清洁的向喜最终倒毙于粪池,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这几年我寻思来寻思去,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3](320)他最终彻底回归了农民的本分,还原皈依于家乡的土地。这里并没有英雄主义的滥情,源自笨花村的古老道德承继和文化基因渗入了革命时代的精神内涵,民间英雄本能的复仇意识与萌发生长的国家民族观念以一种电光石火的姿态交汇,完成了自我牺牲的壮举。
相对向喜,向家其他成员对于革命的参与更加主动和自觉。向喜与正妻同艾的儿子向文成、与二太太顺容的儿子向文麒、向文麟、与三太太施玉蝉的女儿向取灯,还有他的孙辈们向武备、向有备等都是怀着明确的救亡意识加入革命队伍。向文成在家乡办学行医,支持革命,虽然他并未真正加入任何政党,也没有明确接受过谁的指派,然而他却以阔大的全局意识和敏锐的细节感知热切而又无畏地参与进各项革命任务中,在他身上既有民间杂学家的睿智悲悯,又有革命英雄的坦荡豪迈。向取灯以脱产的方式加入革命队伍,她最终的惨死令人扼腕又让人感佩,为实现革命利益而付出的惨烈牺牲正反映了神圣崇高的革命伦理。向文麒、向文麟、向武备、向有备更是奔赴革命根据地,直接加入抗日政权。向家的儿女们勇敢地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义务,忘却个人的安危,有组织、有谋略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加入革命是完全正义正当的,抵御外敌侵侮的目的压倒了个人的恐惧和担忧,所有人在救亡革命的大目标下达成了彼此的谅解和统一。然而,相比向喜传奇生命的塑造带给读者的巨大冲击和扑向历史现场的执着耐心,向家青年一代的“革命”“抗日”描述略显滞涩和板正,缺乏新意。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们依循革命伦理,按照革命的原则与标准行事,他们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和对光明前途的憧憬,紧紧联结着“学潮”、进步书籍、抗日根据地等程式化的符号。究其原因,这些革命符号都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似乎从新文学伊始,它们就被反复使用,无论是用来反抗“吃人的礼教”还是反抗异族侵略,都屡试不爽。这些革命符号与笨花的民间风情贴合得并不自然,拘泥于既定的政治历史框架而失去了丰腴的阐释活力。反倒是一向卑琐黯淡的瞎话和西贝二片的革命义举更加令人难以忘怀。瞎话不顾个人安危,为保护乡亲独自与恼羞成怒的日军周旋,被日军砍头。西贝二片不惜引燃身上的炸药,灭了几个日本兵的命,自己也成了个半截水缸一样的血人。他们渺小卑微的人生在革命反抗的刹那爆发出热烈的光彩,他们奋起捍卫的不仅是民族国家尊严,更是生民素朴永恒的日子,革命激发出了他们人生中最庄严的时刻,笨花人坚韧不屈的精神也正反映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精魂,他们的故事中“蕴涵着一整套关于民族、国家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认知体系”[9],他们与革命互相成全,成就了民间与革命的双重传奇。
铁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笨花〉与我》中是这样说的:“这部小说有乱世中的风云,但书写乱世风云和传奇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情感也不在其中,而在以向喜为代表的这个人物群体身上。虽然他们最终可能是那乱世中的尘土,历史风云中的尘土,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这个民族的底色。我还侧重表现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这群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不败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类,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闭塞环境里开阔的智慧和教养,一些积极的美德,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的种种艰难选择,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10]铁凝始终关注着世俗烟火与兵荒马乱的冲突与汇合,她怀着对民族和历史的敬畏之心,以更为宏阔的精神境界来观察历史变迁和人生命运。《笨花》中的人物大多生活在乡野大地,于他们而言,乡土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块土地真实而极富生命力,既有活泼直白的乐趣,又有苟且狡黠的晦暗,既有不由分说的义气,又有两败俱伤的私利,它以宽广的胸怀承载和接纳着一切沧桑变幻。他们是深深植根于土地上的人情之美孕育出的一批仁义正气的“中国形象”,他们质朴而又高贵,面对生活苦难和人生悲剧,表现出坚忍不拔、执著顽强的民间精神。对于他们而言,脚踏实地的生存诉求和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救亡”救的不是政体、政府、政治,而只是家园、乡土、故国。
铁凝在《笨花》中的叙事导向是明确的,就是将民间文化和革命伦理结合起来,把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统一起来,探寻历史和人性的真相,勾勒出一部完整自足的乡土中国的革命历史。然而这一努力过程中,铁凝又不能完全摆脱革命话语的束缚,作品中无论两性秩序、家庭关系还是生活道路都受到革命伦理的影响。郜元宝将这种价值取向称为“柔顺之德”,认为铁凝作品“不变的价值核心,都是呼唤与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国家理念和利益高度一致的柔顺之德”[11](23)。而被这“柔顺之德”所掩蔽的民间文化与革命伦理间的相互悖逆和相互解构,也值得进一步深思。
二、革命伦理与民间文化的潜在冲突
铁凝曾表示:“我希望我有个大善,不是小善,不是小的恩惠。我认为作家应该获得一种更宽广的胸怀和境界。”[2](17)《笨花》实现了铁凝创作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与总结,它钟情于广阔而深远的时空领域,力图在关心灵魂的同时反映大千世界的沉浮变化,将民间的人性人情之美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利益相结合,使革命历史言说也充满简朴温润的生活质感,努力实现本土文化资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
铁凝试图拨开民间生活的表象,寻觅与自己的文化理想相吻合的民间文化价值内容,借助革命话语,使民间美德升华为从容壮烈的民族大义,从而实现民族国家诉求的回归。因而,肯定革命政权的政治正当性,是《笨花》将民间道德与革命伦理相统一的必要前提。我们可以将政治正当性理解为“基于某种正当的理由,广泛的社会阶层对于红色政权政治秩序的一种自愿赞同和认可”[13]。民族危机的加剧使原本封闭素朴的民间生活荆棘丛生,笨花村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民风遭遇了极大的冲击而难以为继,为了保全朴素自足的生存价值,人们以投入革命斗争的方式来重获失落的生活,人们从革命话语中获得了生命意义,也就对革命政权表示认同。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抵御外侮的需要超脱了诸多复杂的国民内部矛盾,生命原欲和反抗意志高度统一,人们的生存想象被严格限制于民族国家内在的价值边界。《笨花》肯定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当性,它强调了革命政权的合法起源,维护了革命理想和革命价值观的神圣性,它以温柔敦厚的气质书写着华北平原上的革命,斗争不可谓不残酷,牺牲不可谓不惨烈,然而文本却有意避开了暴力场面的直接描述,而代之以不乏节制的片段描写,以坦白却不张扬、沉郁却不悲恸的笔触勾勒了民族革命过程中的曲折跌宕。但与此同时,铁凝并没有回避对革命话语中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的隐忧,她拒绝表露明确的道德决断,小心翼翼地揭示了革命伦理与人性道义的不相容之处,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新的想象空间。
《笨花》的确在着意寻求自然人性的美好和顺服于革命需要的“政治觉悟”的综合,但她并不甘于只通过描写和赞颂民间文化美质来宣扬民族国家的最高理念,而是以传统情爱伦理为切入点,探讨革命伦理对民间原本自在、野性的两性关系的改造。如何处理“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是革命的历史主体必然遭遇到的个人困惑,铁凝以超然的历史理性态度对这一矛盾进行了揭示,也体现出她对于革命伦理绝对权威的思考和质疑。
西贝时令和向取灯可谓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然而他们始终在感情线上徘徊,从未有过实质性的发展。他们的个体欲求仿佛遭遇了无形的遏制而显得畏首畏尾,自然欲望和社会身份的冲突使他们难以任由情感发展,从而在两人之间营造出暧昧和朦胧的氛围。这氛围在西贝时令推荐向取灯脱产参加革命的那个夜晚达到了顶点,二人在言语上互相试探,彼此的称呼“邻家”“同志”“战友”都被附着上了无限的革命意识形态意味,将二者的情感基础设定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当取灯系上由时令那里动员来的皮带时,女性身材的凸显让时令心旌摇曳,却立时又想到“战争年代,人还是暂时忽略一下自己为好”[3](386)。以“革命”的名义排斥“恋爱”,正反映了革命伦理对于人性力量的束缚,原本自由自在的两性关系服膺于革命宏大而美好的解放目标,“革命”成为两性关系的基石,革命伦理的约束力置换了两性关系的自主性,革命美好愿景的大目标下埋伏着人性扭曲的危机。
与此相类的还有向有备与董医助,有备在董医助的讲解启发下对于两性身体有了初步的认识和隐隐的企盼,待到他与小董同宿,一夜辗转难眠,对男女之事的不断想象反映出他内心的冲动和渴望。同样,小董的“细睡”、带有暧昧色彩的言语,也都是她对有备发出的欲望信号。但天亮后两人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对前夜的暧昧气氛绝口不提。革命的理想追求,走向一种禁欲式的表达,两性关系成为革命伦理的宰制对象,呈现出政治化、革命化的特征。
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革命话语将作为两性关系纽带的‘情爱’置换成‘阶级’与‘革命’,带来了男女双方自我的沦丧,使情爱关系沦为‘革命’的空洞的隐喻。”[12]“恋爱”被冠以阶级定性,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尚且要为革命使命约束个体行为,更不用说阶级出身不同的男女情感,天然的阶级鸿沟注定了这类情感的失败。相比《笨花》中的其他青年女性,小袄子野性得多,也放肆得多,她受着佟继臣的吸引,在花市上跟他以手唱价,并到底在窝棚里行了男女之事,然而她和佟继臣的“相好”却并非只为了拾花,单从她拂晓钻出窝棚后,“背对着东方的鱼肚白,面朝着佟继臣和他的窝棚深深鞠一躬说:‘撒哟那拉!’”[3](334)就可见出她是真心向相好的人告别,真心钦慕佟继臣那漂洋过海而来的风度。然而佟继臣却并不这么认真,他答应与小袄子在窝棚约会的初衷不过是“和她无拘无束地寻点儿开心,说点儿脏话”[3](331)。即便是他们发生了性关系,在他看来也是在小袄子的挑逗下“就了范”。佟继臣家境殷实,本人还出洋留过学,在笨花村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小袄子和她母亲大花瓣儿则是靠“钻窝棚”维持生计的笨花贫民,阶级出身造成的经济背景以及人生哲学上的差异是他们无法跨越的鸿沟,这种情感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佟继臣与小袄子的你来我往仅仅算是情场游戏,这两个阶级背景不同的人合在一起,事实上是无法调协的。因而佟继臣可以依凭医术加入后方医院救死扶伤,成为革命力量的一份子,而小袄子却只能和金贵等人“靠着”,凭借出卖肉体来换取物质满足和各种情报。值得注意的是,佟继臣出身背景比较暧昧,父亲佟法年曾是向文成们斗争的对象,他本人的处世为人也高傲优越,与纯粹的狂热的革命保持着半游离状态,这样的身份设定使他在窝棚里与小袄子暗度陈仓显得较为合理,不至与正统革命的道德观过分龃龉。
相比之下,另一位革命者西贝时令对小袄子的感情就显得更加扭曲和残酷了。时令在笨花村的夜校上表现得严肃生硬,极力表露对小袄子的鄙夷漠视,甚至要求夜校把小袄子拒之门外。待到他利用小袄子从事革命工作时,面对小袄子的风骚挑逗,他却没有表现出如之前般决绝,只警告小袄子:“咱俩是执行任务,可不是钻窝棚。”[3](410)他对小袄子美好外形的观察和不那么坚硬的警告已经反映出他潜意识中对欲望的渴求。取灯牺牲后,革命者时令看待出卖者小袄子,“就像看见一头发情的、一心一意正在等待交配的小母兽”[3](489)。小袄子的打情骂俏让他怒火中烧,这怒火不仅源于为取灯复仇的信念,也源于无法发泄性欲的恼怒。小袄子对他的羞辱让他恼羞成怒地处决了小袄子,然而这处决却显得诡秘而猥琐。他把革命权利当成了自我放纵的保护伞,掩盖自己隐秘欲望的动机大于伸张革命正义的目的。自然欲望和革命伦理彼此纠缠,尽管最终他还是压抑了性欲,遵守了革命伦理的道德标准,但革命不能够消灭性别的相互吸引,不可能消灭人的自然欲求,他的自我压抑就显得扭曲狰狞、违背人伦了。
《笨花》中的许多情节在铁凝198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棉花垛》里已经出现,所不同的是,《棉花垛》里抗日战士国想到了“战争中人为什么非要忽略人本身?”[14]国对汉奸小臭子的先奸后杀,将人伦的扭曲表现得更为越轨和极致。相比之下,《笨花》里时令对性欲的最终克制,笔致就含蓄得多,因而有学者认为“《笨花》则是把《午后悬崖》、《大浴女》和《棉花垛》中所看到的龌龊与刺挠包容起来”[10](22),它的批判姿态减弱了,在对人性与历史的大胆揭露方面是一种倒退。从写作手法和艺术气质上看,《笨花》和《棉花垛》一样,都氤氲着泥土的气味,充满了极具民族精神特质和地缘活力的物象,但叙述策略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对革命伦理价值判断的差异悬殊。《棉花垛》更多是从人性欲望的层面来推动事件进展,而《笨花》似乎被“政治正确性”所挟制,收敛了革命者阴暗面的揭示所带给人的强烈冲击,将革命话语被滥用曲解而造成的悲惨丑陋予以淡化,虽然不完全符合革命伦理的完美要求,但也没有超脱革命年代的道德规约,它小心翼翼揭露了革命话语庇护下的暴行,又坚定地站回维护革命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立场,从总体上凸显了革命叙事伦理对权威的捍卫,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显得循规蹈矩。
《笨花》希冀将民间文化资源纳入革命伦理,在浑朴平实的氛围中,折射出人们热爱凡俗生活的坚定信念,在油画般昏黄暗沉的生活图景里,体现人们渴求岁月无恙、安稳度日的人生理想。它发掘和歌颂那种心悦诚服地与革命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柔顺之德,着意寻求自然人性的美好和顺服于革命需要的“政治觉悟”的综合,维护革命理想的神圣性。但这不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条件臣服,它传达了对于革命历史的新的理解,在暗中质疑着革命遗产的某些内在价值,具有一定的暧昧性和复杂性,包含着美学表达的多重空间。
“革命”利用着女性身体资源,却阻滞着女性对革命的参与和体验,让她们游离于主流之外,不得不选择边缘生存状态。小袄子的经历便是以身体为工具去实现革命目标的革命伦理故事。在为革命献呈身体之前,她身上体现更多的是身体原欲的躁动,她懒散而狡黠,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情感和物质的满足,出于自由狂野的天性而认同反帝反封建,招摇而自在地生活在笨花村。革命利用她的声名狼藉来突破封锁、获取情报,她那为一般村人所鄙夷的轻佻招摇得到了革命工作的默许乃至鼓励。革命伦理对传统道德进行了颠覆,却没有给予她加入革命事业的可能,革命在利用小袄子的同时并不认同和尊重她的贡献,她曾经的张致风流使革命对她身体的一次次利用仿佛理所应当,对她的脱产要求却采取敷衍、警惕的态度。革命伦理一方面颠覆着民间传统道德,要求小袄子出卖身体以换取情报,另一方面又与民间传统道德相接,对她的行为嗤之以鼻,不曾给予她加入革命事业的可能。革命事业从未打算将小袄子纳入其中,因而也从未在思想上熏陶和引导过她。革命的至高利益演变为一种权威性的宰制力量,它的正义性被无限夸大,在此之下的人的情感焦虑和失落却显得无足轻重。
革命政权不仅将小袄子这样的边缘女性排除在外,对向文成这样的民间志士也抱有既团结又警惕的暧昧态度。向文成既具传统美德又具现代意识,身处乡土之中而改造乡土生活,推动了乡村的开明之风。他深明大义,先后引导和鼓励妹妹取灯以及他自己的两个儿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带领全家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笨花村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理想型的人物。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人物,依然被革命政权排除在外,革命政权的代表西贝时令不仅在笨花村夜校当众指责他讲课跑题,向取灯交代脱产事宜时还刻意回避他,主要原因就在于“在组织和不在组织就是有个内外有别”[3](383)。革命的政治力量轻而易举瓦解了民间智者的权威地位,向文成在遵循革命政权指挥和调遣的同时,却又遭遇着革命政权的排斥和戒备,不在“组织”的隔阂感使他难以真正被革命政权所吸纳,从而处于被革命冷遇的尴尬境地。尽管在向文成这般近乎理想化的人物灵魂里,涌动着乡村的智慧、古老传统的道德秩序和人性善的神韵,革命秩序仍然以严苛的“组织性”作为判断政治觉悟的首要标准,这隐隐透出革命伦理某种程度的僵化和不近人情。革命利益的一方独尊压制了本应邃密深沉的文化选择,过于强势的革命立场抵触着人性的多变复杂,人们的自然属性和个性自由被极力淡化,完全为革命伦理所教化和规范。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向家几位投奔革命的后辈——向文麒、向文麟、向武备,在雁北相聚时,居然只对向取灯举行默哀仪式,却无人提及悼念向喜。虽然取灯和向喜的死因袭了同一种模式,都在与日军的正面交锋中惨烈而悲壮地牺牲,向喜却没有得到如取灯般的敬意和怀念。本想提议悼念祖父却未能开口的向有备只“本能地感觉到,向喜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或许只存在于另一个主题之中:当他们为自身的缺点挖掘家庭根源时”[3](531)。这里也许隐含着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可能——“出身论”“血统论”等荒谬的阶级话语顶替严肃的革命话语、外在的政治定性遏制内在的礼俗生活的可能性。一向被视为正义凛然的革命具有鲜明的排他性特征,旧式军人出身的向喜虽然为抵抗日军付出了生命,但红色政权依然难以承认和接纳他暧昧的出身背景,革命伦理对阶级出身的纯正要求削减了民间品德与智慧的包容力,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冲突关系。
检验革命的标准在于它破旧立新的深度与广度,而不是看它的手段、态势之激烈,对于一心以乡土故事反映浩大历史的铁凝来说,暴力搏杀与军事斗争不是她进入历史的主要方式,她所依赖的价值根基还是对于仁义理想的不渝追求。革命在蓬勃、激情与豪迈之中羼杂着偏执、幼稚与残酷,如何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障,审视它复杂斑斓的面目,铁凝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她没有过多纠缠于大的历史事件和场面,没有对革命意识形态亦步亦趋,而是返归丰满鲜活的民间生活,更感性化地记载历史中人的心灵、情感的历史碎片,在摄取和提炼民间文化美质的同时融注作家主体的审美理想和人文追求,有意将对仁义之心的思索与关注置于民族国家话语框架之下,将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
《笨花》对民间文化与革命伦理的融合与潜在冲突的揭示,对现代历史进行了富有创意的独特艺术表现,是铁凝个人艺术创作的新境界,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着新时期中国小说在宏大叙事之后的新动向。
就铁凝来说,这部“无可比性的大书”,建立在她对历史富有哲理性和超越性的思考中,她说:“‘笨’和‘花’这两个字让我觉得十分奇妙,它们是凡俗、简单的两个字,可组合在一起却意蕴无穷。如果‘花’带着一种轻盈、飞扬的想象力,带着欢愉人心的永远自然的温暖,那么‘笨’则有一种沉重的劳动基础和本分的意思在其中。我常常觉得在人类的日子里,这一轻一重都是不可或缺的。”[10]“笨”的滞重沉实与“花”的轻飏飞升达到了圆融合一的状态,半个世纪的风云际会紧紧贴合着踏实细密的生命觉悟,跌宕起伏的历史波澜里映照着国人的生存态势和灵魂震颤,宏大激扬的革命历史嵌入丰富厚实的民间文化之中,使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包容性力量,而这力量里透出的,是我们民族亘古不变的生存韧性,是对“中国凡人”的理解和善意。大巧若拙,《笨花》里的地界和人物平凡地栖居于历史的褶皱深处,他们不断被变故冲击,却又不断巩固自身特征,谱写了民间与革命的双重传奇。
就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说,在破除了对历史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之后,在“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各种重新解读现代历史、包括革命历史的尝试层出不穷,各种历史观在文学中也有多样的表现。因此,如何更加客观地、全面地艺术表现中国近现代以来波澜壮阔而内涵丰厚的历史,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是随意涂抹历史,不是按照某种理论图解历史,实际上是当代文学面临的重要课题。正是在这里,体现出铁凝的智慧与超越,她不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而是以“直观把握”的整体思维,冷静地融通和直面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将其转化为艺术思维,以“笨花”的象征隐喻,创造了符合现代历史精神的立体历史画卷。它的“无可比性”正是它的不可重复的艺术创造性,也是历史叙事的不可还原性。《笨花》因此代表着在这一题材领域内文学的新动向和新水准。
[1] 铁凝. 《笨花》卷首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2] 铁凝, 王尧. 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3): 16−17.
[3] 铁凝. 笨花[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4] 赵德利. 民间精神与民间文化视角——以20世纪中国小说为例[J]. 文艺争鸣, 2005(5): 104−107.
[5] 胡传吉. 世俗烟火与兵荒马乱的叙事伦理——论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5): 55−61.
[6] 铁凝. 《笨花》里的世俗烟火[N]. 新京报, 2006-01-20.
[7] 程桂婷. 未及盛开便凋零——铁凝的《笨花》批判[J].当代文坛, 2006(5): 100−102.
[8] 孙红震. 指向崇高意旨的身体献呈——《我在霞村的时候》革命伦理解读[J]. 名作欣赏, 2007(11): 44−46.
[9] 邵波. 论铁凝小说《笨花》的叙事伦理[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0(1): 9−12.
[10] 铁凝. 《笨花》与我[N]. 人民日报, 2006-02-16.
[11] 郜元宝. 柔顺之美: 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J]. 南方文坛, 2007(1): 22−23.
[12] 蔡栋. 从生命意义的维度理解延安红色政权的政治正当性[D].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3.
[13] 李跃力. 论“革命话语”对情爱伦理的重构及其本质[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0(2): 94−104.
[14] 铁凝. 永远有多远[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Benhua: the double legend of folk and revolution
WANG Yi, CHENG Jinc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Benhua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weighty book in Tie Ning’s literary career, which attempts to combine folk culture and revolutionary ethics, to connect everyday life with the grand narrative, and to explore the truth of history and humanity. On the one hand, it demonstrates the sense of domestic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China mortals” and realizes the convergence with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n the other hand, it reveals certain ambiguous property of revolutionary ethics, expresses her skepticism on the absoluteness of “revolution” appeal, and to some extent releases a new sphere for imagination.
Benhua; folk culture; revolutionary ethics; convergence; conflict
I206.6
A
1672-3104(2015)03−0205−07
[编辑: 胡兴华]
2014−09−10;
2015−01−1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4LZUJBWYJ011)
王艺(1987−),女,甘肃武威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程金城(1953−),男,甘肃泾川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