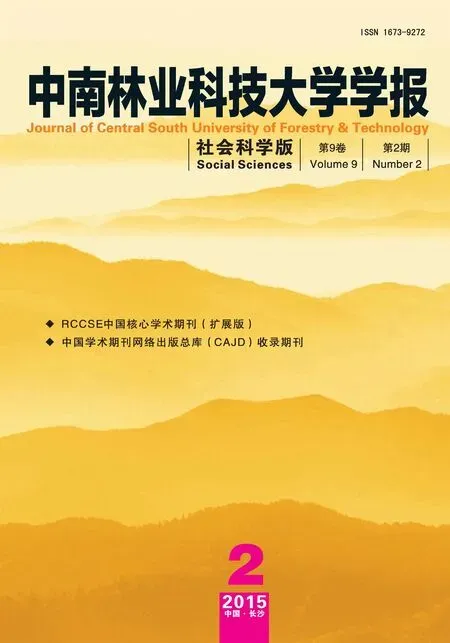生态中心主义视域下的西方环境运动研究
张念念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000)
生态中心主义视域下的西方环境运动研究
张念念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000)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环境运动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源泉,后者对前者起到思想指导、理论规范的作用;而西方环境运动的发展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动“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品质与时俱进,使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温和化转变。
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环境运动;邻避效应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环境运动始于20世纪六十年代,是由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结果,也是人类对生态价值的认识愈加深刻的结果。在严峻的环境危机面前,人类见证了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和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反作用力,继而开始了对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观点进行反思的历程。在1960年代兴起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环境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环境运动具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基础,旨在对政府的相关环境政策产生影响。随着深生态学、生态主义观点的发展,“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西方环境运动新的理论和思想源泉。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圭臬,西方环境运动呈现诸多新特征。
一、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在人的自我价值认同方面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即推崇人的理性和人对于自然的目的。也由此形成了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驱动下,一方面,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迅速迈入现代工业文明,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侵略性和扩张性,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性,都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在上世纪中期不断爆发,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围绕如何消解生态和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出现了大量的绿色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等思潮展开了全面的批评。
安德鲁·多布森认为:“如果有一个术语能够概括激进绿色运动对世界上现存的人类行为方式的反对范式,那很可能是“人类中心主义”。[1]“人类中心主义”即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对其他生命利益给予反对的排他性的、人为偏好性的错误。”[2]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西方传统哲学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人具有天然的主体性,非人自然是“为我所用”而存在的客体。一种强内涵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非人自然仅仅是一种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1]可见非人自然对于人类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性价值而存在。反观“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一种把非人类自然的价值放在中心位置的理论主张,它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作为其理论基石。
美国学者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诞生的标志,其代表作《沙乡年鉴》系统阐述了生态中心主义思想,成为现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思想来源。该书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认为,生态是一个有机整体,没有等级之分,人们应该保护自然,而不是享用自然。“大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3]人与自然之间没有等级之分,自然甚至是一切价值的中心。罗尔斯顿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结合对工业社会的反思提出整体主义生态论和自然价值论。“他强调自然价值是由自然系统的内在结构所决定的,自然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由不同系统(例如:生物系统论等)所组成,而每个系统正是其价值存在的基本单元。”[4]他强调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不依附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存在,人对于价值只是一种翻译,而不是投射。“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视为一个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必须服从生态规律。”[5]“生态环境价值论,就是人类在生态本体论时代对人与自然万物及其生态系统的价值关系的独特新颖的基本看法和观点。”[6]承认人类以外的非人类物质的存在具有内在价值和权利,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思,也是对工具理性的极大否定。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是先在的和客观的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属性是人的基本属性。[7]人类作为生物圈中最有力量的、也是惟一的道德代理人,赋有考虑他们自己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的双重责任。
戴维·佩珀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者并不反对技术本身,他们只是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缺乏信任。相对于政治上的右翼,“生态中心主义”者强调极限的观念,主张对人类繁衍、资源消费水平和接近自然“共同财富”的强制性限制。[6]“生态中心主义”者反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人类生活的入侵,导致生活的异化,他们反对奢侈消费、过度消费,倡导简单绿色的生活方式。“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同于生物中心主义对于动物权利的强调,也不同于自然保护主义对自然环境的简单维护,它具有更广阔的生态伦理关怀。
深生态学就是关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非人类生物及生态自身价值的一个理论,其宗旨是生态中心主义。“深生态”这个词由挪威的哲学家、活动家阿恩·奈斯(Arne Naas)在1970年代初首次提,他主张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的繁荣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价值与其是否对人类有用无关。[8]深生态学是面对世界问题的一个全面的方法,它汇集了思考、感觉、灵性和行动。它超越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的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只是是地球的一部分,而不是主宰,主张万物有灵论,这导致一个与任何生命都有关的深层次联系。1990年代的英国反道路运动被认为是联合了激进的生态主义视野和更有限的改革环保主义。[9]生态主义是一种基于自然价值认可观念的对工业经济和社会制度全面变革的政治思想。[10]自1980年代生态主义已经成为英国绿色文化的一部分。一些出版商,如绿色印刷(Green print)、舒马赫社会以及绿色阵线(Green Line),都参与了生态哲学、生态价值观的扩散工作。一份来自英国绿党成员价值观的调查表明,95%的人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独立于人类价值判断之外的。追根溯源,生态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受到深生态学理论的影响,深生态学为公众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环保视野,影响着人们看待和对待世界的方式。
在中国,也存在类似于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例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传的自然崇拜。自然崇拜通常指的是远古时期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大自然进行保护的行为,它突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11]
二、西方环境运动发展历程及特征
对于环境运动的定义,英国基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卢茨给出的观点是环境运动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由不同正规化程度的组织以及没有组织归属的个人与团体甚至是政党包括绿党组成的非制度化网络;它从事由共同的环境关心激起的集体行动,而这种集体行动与环境关心的形式与强度在不同国家与时间可能有着重大差别。[12]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代,一系列生态和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基于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政府环境治理不力,早期环保运动应运而生。西方早期的环境运动是由一群自觉的环保主义者以环境保护、生物保护为主要目的自下而上展开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基本的集会游行、环保宣传,并涉及部分暴力活动。早期的环境运动还包含着强烈的经济利益诉求,工人把对恶劣生存环境的不满与对雇主剥削行为的愤恨结合起来,举行包括罢工、暴力损毁机器、楸斗雇主等形式在内的运动。这一时期,对动物生存权利的维护和争取也成为运动内容的主要部分,相当一部分环保运动家持有强烈的非人类道德关怀,形成“生物中心主义”观。
战后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的环境问题激增,震撼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大部分出现于这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现代环境运动产生的关键性时期。随着环境公害事件不断爆发,一系列与生态环境问题相关的著作问世,包括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以及《生存的蓝图》等等,这些著作皆以惊世骇俗的笔触揭露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促使当时仍沉醉于战后繁荣景象的一部分人的觉醒。最初,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以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1]实际上仍然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在最大程度满足人类生存利益的前提下做出的对非人类自然的“安抚性”措施。
20世纪7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生态保护阶段。大量的环境运动组织、团体甚至绿党都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根本立场,努力为自己营造深绿的形象。“生态中心主义”者常常是激进运动、直接行动中的旗帜人物。包括英国“地球第一”创始人詹克·伯布里奇和贾森·托兰(Jason Tuolan),二人均以直接、激进的行动方式而闻名;德国自然保护联盟在环境运动实用主义战略失败后承认“我们在关键时刻过于温和了”,当然他们并不主张重新回到战斗性大众抗议阶段,转而关注“生活方式”问题,从“生态中心主义”角度出发,提倡绿色、低碳的生活消费方式;在美国,许多草根环境团体日益脱离了主要环境团体和主流环境游说团体,发展为以环境直接行动为主要抗议方式的环境运动组织。
“生态中心主义”为西方环境运动注入了新的理论动力,它改变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知。“生态中心主义”者指出:如果人类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错误的主客体认识论,便不能从源头解决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以生态利益为归宿,诸多环境运动团体和组织在抗议内容和运动方式上都打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旗帜,环境抗议事件的议题也较为突出地集中在了污染/能源、交通/建设、自然/生态保护以及动物权利/选择性生产方面。其中英国在自然/生态保护和新兴议题中处于领先地位。[13]1990年代的英国反道路运动较为突出地反映了环境运动团体和组织的自然生态保护立场。反道路运动参与者普遍受到深生态学的影响,赞同“生态中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90年代初在英国兴起的反道路运动(Anti-roads campaigns)①Anti-roads campaigns根据不同的翻译习惯,可以写作“反道路建设抗议运动”、“ 抗议道路建设运动”、“反道路抗议”,本文使用“反道路运动”这一翻译。把大型道路、机场、轨道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和汽车的增长作为抗议的主要对象。1990年代的英国反道路运动旨在对政府的道路政策霸权提出挑战,[10]它突出强调公众在环境政策、道路交通政策领域的直接参与价值和影响,以及个性化的参与方式;强调维持地区的生态和物种平衡。1990年代的英国反道路运动也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世纪之交英国环境运动中最受瞩目的运动类型。以特怀福德镇抗议(Twyford Protest)为开端,经历纽伯里抗议(Newbury Protest)、M11公路抗议以及众多收回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运动的历练,反道路运动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至今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三、“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发展——以西方环境运动为土壤
任何形式的思想理论,一旦离开了实践这层土壤,便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和成长的养分,“生态中心主义”也不例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与西方环境运动之间也已经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之后,由于西方社会环境问题整体上的转变,经济政治方面发生诸多变化,环境运动在组织方式、行动内容、运动形式等方面也相应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在组织方式上,大量的职业化、专业化运动团体相继出现,其中不乏经常向政府献言献策的环保组织;另一方面,伴随着大量环境直接行动组织的出现,环境运动不可避免呈现出更多的激进主义、直接行动特征,也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环境运动的发展。在行动内容方面,对新兴环境问题予以持续关注,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对跨国环境问题进行抗议并影响政府决议,都成为新时期环境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运动形式上,大众的抗议性方式在一些国家已经过时,另一方面,环境运动又不能太过实用和温和,如何在激进化和实用性之间进行适当取舍,已经成为环境运动家们思考的难题。这些变化都推动着“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演变和发展。近些年来,“生态中心主义”已经向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不可置否的。在德国,职业化与非职业化环境运动团体与大公司的合作,致力于把最新的环保技术应用到产品中的现象屡见不鲜。又由于西方环境问题在整体上趋向缓和,而社会经济持续倒退,生态中心主义者也把可持续发展理论纳入“生态中心主义”思想体系,力图建立一个把环境保护跟经济发展相融合的持续的、健康的绿色发展观念,使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温和化转变。
四、结论
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较早的优势,而在环境运动、环境治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以生态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借鉴其中合理、有效成分的同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不断的积极探索中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又充满生态关怀的环境治理和公众参与之路。重视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治理中的基础和主体作用,将是中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当前,我国社会中出现的与环境污染、破坏相关的“邻避效应”事件,与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式“邻避效应”的产生折射出许多问题,作为一种“制度外”和“非制度化”的抗议,它显示了在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的参与和意见表达渠道不畅通的现象。在大量的“邻避效应”事件面前,许多学者从如何优化公众参与、优化政府职能方面进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将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向我们展示了党和政府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力量。
[1] (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M].郇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25-26, 35-38.
[2] T.海瓦德.人类中心主义:一个误解的难题[J].环境价值,1997, (1):35-37.
[3] (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5-47.
[4] 刘爱军.生态文明与环境立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44-45.
[5] 余某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5-39.
[6] (美)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28-29,32-33.
[7] 郭 蓉,李 伦.生态伦理:从生态理想到生态文明[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7(6):23-26.
[8] (挪威)阿恩·奈斯.深生态运动的基础[J].施经碧译.鄱阳湖学刊,2010, (4):22-34.
[9] Doherty B. Paving the way: The rise of direct action against road-building and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ism [J]. Political Studies, 1999, (3):22-25.
[10] 李 垣.从“浅绿”走向“深绿”——生态主义视阈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J].学术论坛,2013, 1(1):33.
[11] 刘俊宇,邹 巅.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态伦理学意义[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8(2):40-42.
[12] (英)克里斯托弗·卢茨.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M].徐凯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55-57.
[13] 郇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118.
On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from the Eco-centric Perspective
ZHANG Nian-ni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Jiangsu, China)
In the modern sense of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s based on “ecological centre doctrine” theory source, the latter to the former have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he practical level constantly promote the “ecological centre doctrine” theoretical quality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ecological centralism theory brings out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to some extent is a gentle transition ecological centre doctrine.
ecocentrism; anthropocentrism;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djacent to avoid effect
F205
A
1673-9272(2015)02-0006-04
10.14067/j.cnki.1673-9272.2015.02.002
2015-01-16
2014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气候变化伦理——从利益冲突走向气候公正”(14C1194);2014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气候变化伦理问题研究”(14YBA406)。
张念念,硕士研究生;E-mail:niannianlovely@163.com。
张念念. 生态中心主义视域下的西方环境运动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9(2): 6-9.
[本文编校:徐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