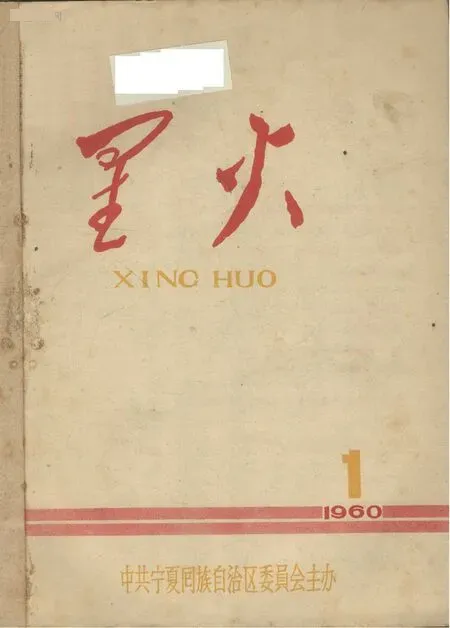“新的长篇已基本写好”
——阿乙访谈录
兆正(广西师大研究生)
阿乙
“新的长篇已基本写好”
——阿乙访谈录
徐兆正(广西师大研究生)
阿乙
关于作品
徐:在《寡人》这本书的一组随笔中,有着如下故事:一帮异乡人拿着剧毒气体喷射张老板,但也跟着倒地。小镇后院人们下井探查不幸绳子断了,可是人没有事还促成一段好姻缘。公安抓住小偷逗乐,小偷后来跑了却又被公安抓住,等等。这些大多类似于新闻报道的变体,你记下了它们,却没有太多情感表达:记录,似乎也就是完成一项任务。是这样么?
阿:无聊正在被荒谬取代。原来我们生活中充斥的无聊(形而上地说是“虚无”),都是一团难以辨识的荒谬火焰。《寡人》是大量的自然写作,当时纯粹是写,不想到发表。我经常写点,以后还会写。
徐:我很喜欢你的这一组随笔,让我先读几段好么?
阿:(笑)好的。
徐:“当我碰到和我说一种方言的人时,总会想到,在小城,人们像树木被砍削,最终只剩权力和钱两种价值观。一个人如果在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还坚持理想,就会变成一只可笑的像得了癔症的鸡。成批的人在年少时有过这样那样的激情,最终幡然醒悟,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投身于小城价值观的泥潭。八年前我辞去县城公职,赴外打工,一直清楚自己是小城里言说的傻子,只是今天才第一次听人亲口说起。所幸我早也不想证明什么。”(《县城的活法》)
“无疑是噩梦。我不知脑子搭错哪根筋,答应回县城生活,而且在县纪委谋到位置,说是三月后正式调入。父亲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你总算回来了。我却在家人亲切的目光中晦暗下去,好像北京永远地关上大门。县城那些过去的同事朋友来探望,说要得要得你回来要得。二〇〇二年我不打招呼逃出县城,这次他们一定会看死我。‘小艾,这次不跑了吧?’‘不会,不会了。’我说得眼泪出来了。”(《梦里的哭泣》)
“在噩梦里,我回到公安局,和过去同事饮酒,像是亲戚兄弟。后来在回家途中,不知干了一件什么自卫的事情,干掉也就忘记了。但在一天我的姐姐接到电话:国柱在家吗?我意识到,这是前同事打来的电话。他们为什么不打给我?怕打草惊蛇?我正要暗示姐姐别回答,善良的她已迫不及待地说:在,在啊。我听到话筒里的他们一起哦了一声。我逃亡到邻居家后,透过窗户看见他们穿着墨绿色制服,举枪蹲在我家门口,像上演哑剧一样无声地移动。”(《背叛》)
书中屡次出现的意象。你似乎写出了世界的尽头。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中也有相近的地方,绥惠略夫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阿:说得很对。现代人已经发昏了。
徐:这些不断重复的动作,是要论证什么?
阿:论证爱的反面是冷漠。
徐:你对于简化琐碎叙事的偏爱,在我看是出于一种反向叙述的心态。在这种心理下,之于日常生活的观察有时达到了神经质般的专注。我发现你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这是夸奖。
阿:谢谢。我有焦虑症,篇幅的控制比较狠。写的时候还算自我,写《寡人》那样的小随笔,发表的可能性很低,因此没什么功利心,不会想到去迎合谁。我是说这个念头是压根不存在的。
徐:我懂。今年要出一本新的随笔集么?
阿:是的。《阳光猛烈,万物显性》。也是如此;写短篇,不如长篇来得机会好。现在写的长篇,写了之后可能一生都不写了,我比较缺乏控制长篇的能力,虽然现在比原来强一些了。小说是有功利心的。
徐:已出的三本小说集,你最喜欢哪一部?
阿:《鸟看见我了》。
徐:(笑)我喜欢下一部。
阿:多谢鼓励。我的短篇不会太亏待人。以后出的更不会。十篇里总会有一两个是还好的,剩余的有掉线的,但不会掉得太深。我从来没放弃对小说的尝试。我经历过很多失败。我想证明一种可能。也许这个没写好,但下次我写别的一个故事时就能成熟地采用这一结构。
徐:你目前争议最大的一部作品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下文简称《下面》)。读这本书时还不认识你,当时我写了一篇《谁都不是楷模》,那是我读的你第一本书。
阿:这篇评论我还没看过,你发表了么?
徐:那时还没有系统开始写书评,纯粹是被小说“镇压”了才写的。
阿:我很看重这本书,它提供给写作更多的可能性。这部作品会成为我早期作品的终结。此前我出版过《灰故事》《鸟,看见我了》,它们和这本书组成递进关系,从灰一路走到黑,终于伸手不见五指。
徐:七月份我去南京,在玄武湖公园躲雨,又把这本小说读了一遍。非常喜欢。这本小说的后记再版时你应该加上。
阿:会的。它是我模仿得最狠的一次,也更克制,和认真。每一步怎么写都运营得很仔细,也很刻板。
徐:我认为从《下面》起,你开始了虚构之旅。换言之,个人素材逐渐让位于虚构能力。这是成熟的发端。
阿:恩,我自己有经验的事情写起来可能顺当一点,(这本书)所以写得苦,可能与此有关。但是我尊重这次写作。
徐:你在接受《中国之声》的访谈中提到:自己修改好作品就交给编者,再由编者交给印刷厂,直到送入读者手里。脱手之后,就不会再为作品考虑任何事情。这话怎么讲?
阿:这是一个作家该有的素质,既不看轻自己,也不贬低读者。作品在读者手里,甚至是时间手里,才自有另一番命运,并且后者的命运才是它的真实价值。读者有权用他们的想象扩写作品,而作者在出手之后,作品也就与他们无关——他们无权扩写作品的世俗意义。
徐:能谈一下你的小说主题吗?
阿:对“上帝不要的人”的深刻同情、对“得不到”的宿命般的求证,以及对人世的悲凉体验。
徐:《下面》写的是犯罪,《春天》写的是永远的客者,谁也接纳不了她,谁也关心不了她,只有她自己。
阿:兆正,你是第一个把《春天》当作长篇的人。
徐:它本来就是长篇的手笔,长篇的主题,并且比《下面》写得更成熟。我在《疲倦之徒的感情溯往》里将它一笔带过是偷懒,但心底对这部小说充满敬意。你将来会把它真正写完么?
阿:也许。我已经说过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很多原因,让我当初粗暴地将它放进《春天在哪里》了。
徐:不提这件事了,虽然我还是希望你将来能把它写全。现在来谈谈《下面》的主题吧。
阿:犯罪事件是戏剧冲突的天然舞台。你看戏剧里的大悲剧,都有杀人、背叛、疯癫等等,都有尸体,都有命。而一走出剧场,你会发现这并不是生活的常态,也许这正是你要去剧场的原因。犯罪故事就像是一个化学实验室,能将人性里的东西,最尖锐的东西,最不可溶解的东西和最容易蒸发的东西,都清晰地淬炼出来。我写作时并没有放弃这一块,《下面》只是它最极端的表现。
徐:你在很多场合都提起将来要写一部“温暖到让人战栗”的作品,能仔细说说吗?
阿:你看《旧约·传道书》里说的“虚空”:“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作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光明’原文作‘在他头上’);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记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憎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第2章12—17节)我容易在光明和温暖里看到更大的虚空,有时我觉得痛苦和绝望反而有质地。我感触得到,它就是实在的。
写作是有阶梯性的:第一层是自我欺骗,有的人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世界本来的面目,就说这个世界很美好,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第二层则可以直面一些黑暗的东西。当我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不可能回头写一些自我欺骗、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我以后会写温暖的作品,但我说的温暖是再往前进一步的温暖。就像加缪写的西西弗斯,不断把石头推上去,石头还是会滚下来,这是在极度荒谬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我选择的温暖。
关于主题
徐:期待这部作品。我先读一段江耀进先生在《恋人絮语》前言中说的话。
阿:好。
徐:“真正为爱情而痛苦的恋人既没有从这种妥协中获益,也没有能成为这种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爱情不可能构成故事。”
阿:不错。
徐:《猎人》这一篇,虽然不像小说,只是一些无法构成故事的片段,但是似乎更肺腑——将之前在《隐士》等小说里出现的,尤其是“互相伤害,然后老去”的意思,来了一次淬炼。
阿:嗯。我有很多年都痛苦,但是这痛苦现在想,毋宁说是蜜饯,反复吃的蜜饯。真的痛苦,这几年经历的,会比爱情深刻得多。爱情只是一场闹剧。
徐:有点类似于叔本华的“苦行主义”。
阿:只能说:减少对它的奢求。
徐:所以,你将它安排在《春天在哪里》这个集子的最后一篇,是蓄意为之?
阿:是,我将它视为对爱情这类子题的某种告别,它们写得太多太多,已经完成了叙事的目的。
徐:什么是叙事目的?
阿:对我来说,它们意味着弥补亏欠。
徐:我大致理解你的意思。欲望是一种否定性行为,我们欲求某人某物,总是建立在欠缺之上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阿:可以。写作弥补了生活曾出现的那些空缺,而且生活本身也在偿还。如果个人之爱圆满地完成,追忆或救赎又有什么必要呢?普鲁斯特认为当我们想要从自我经验中提取普遍意义上的解释时,必须尽量多地积累体验和体验痛苦。他显然有意倒转了生活和写作的前后位置,好像他的写作早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刻薄点说,好像作家爱情的败仗是为了书写这败仗。这个解释既不诚实,也丝毫不能令人信服。
我的经历污七八糟。有很多复杂的地方,现在看来写作正慢慢趋向纯粹。诉说自己的欲望减少了,探查人世的想法变多了。
徐:是你在《寡人》前言里写到的么——“我习惯在一件事或一个场景刺伤或者严重影响我时将它记录下来。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正常的人,因此觉得那些事也会刺伤和影响别人。我很孤独,也很坦诚,我剖析别人,也剖析自己。”
阿:是的。
徐:既然提到人世,不妨谈谈城市与乡村。这个话题你在不同场合都讲过,我注意到你蛮乐于用“暧昧”这个词来形容城市里人与人关系的,并且因此难以把控这类题材的写作。可是《正义晚餐》写的就是城市生活啊。我非常喜欢这一篇。
阿:谢谢。需要更正一下,与其说它暧昧,毋宁说是缺乏了解的机会,人和人之间几乎从不掏心掏肺地讲话、敞开,而且房屋建筑的模式、关系纽带的组成也充当了暧昧的合谋。除了唯一例外的性关系,每个人都被符号化了。《正义晚餐》写的就是后者。
徐:我认为你在今年新作《虎狼》中表明的,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生存感受,它已逐渐代替感情受挫经验在素材中的位置。
阿:我信任你,因为你看得很准。我认为它们需要(必须)被替换。
徐:那么正在写的这个长篇也是如此?
阿:是的。这个长篇已基本写好,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名字暂定为《早上九点叫醒我》。将近二十万字。那个《下面》的宣传语如果重印一定要删了(按:“这是我写得最苦的一次”)。新的长篇讲述了“一个农村的恶霸,在他长年控制乡村之后,在一场酒宴时假死并被自己的亲人埋进地下。整个村庄充满对他的回忆。而他要在棺材里苏醒,并再次死去”的故事。我寻找的是讲述的方式与角度,我最终还是要讲某件事。实际上每次,我都是有一个故事,然后再来考虑用什么方式去讲它。而不是相反,不是先有一个形式,然后再去设计一个故事。讲述方式很重要。
徐:你认为文体(或语言)应该让位于内容(或情节)吗?
阿:肯定的。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有关后现代作家的评论,意见大抵相符。他们对形式的操控已经远远大于对故事的关注。在小说里,语言的功能就是承担对事情的推动作用,它要服从于情节的发展,否则存在的合理性就不够。
徐:新长篇里文体有变化么?
阿:非常大。我之前的写作,都要感谢意外看到的《新闻报道与写作》,它是一切写作的教科书。那个时期执行的写作原则,比如用短句子、文字简洁、多用动词以及时刻注意文章使命等等,都得自于它。我早期的作品充满了视觉感,我喜欢写那些眼见为实的东西,我喜欢写出来的字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画面。但与此同时我会注意保持句子底下的张力,会对这些场面进行压缩和择选。我理想中的作品是,字面一行行,像冰面一样清澈,一览无余,每个字大家都熟悉,平白,易懂,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冰面上起了浓雾。
徐:比如《小人》?
阿:(笑)对,那个结尾隐藏得很深,我比较满意。
徐:那么新长篇呢?
阿:过去我是一个简洁派的信徒,只要看到长句子我就很恶心。一夜之间,我就不要那个财产了。在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必然要维护的。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说出来一个观点,仅供大家参考。因为,我明天可能就背叛我的观点。
我觉得长句子,可以把我的很多东西带出来,其实我心思很细密,不是很简单。多用动词或短句,读起来方便快捷,作者自己也会形成写作惯性,一个事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我想写得慢一点,句子长一点,把细节和想法带得更深一点,把我的另一部分东西抒发出来。我是想尝试一下,因为每个人称的角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徐:你认为这是先锋性的特质么?包括阿丁最近写的长篇,我觉得“中间代”里你俩是对形式做最多探索的人。
阿:谢谢。可能我们的“先锋性”在于每次叙事时都注意方式。有的作家叙事只有一种方式,拿起笔就写,一辈子一个调性。由于新情况的出现,先锋就是在为叙事提供继续存在的意义。
徐:我明白你的意思。而且我与丁哥聊过,他也很反感后现代作家那种形式大于一切的油滑。
阿:嗯。本质上都是为了讲一个故事,但如何讲,如何让读者能更快建立这个形象,非常关键。我最近在尝试那种不可转化的语言。文学语言和电影语言,很多时候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现在不停地给自己的小说增加难度,让别人改编时无从下手,他很难用影像表达小说里的某些意思。有的语言是不可翻译的,不是说不可翻译成外文,是不可翻译成电影。我在小说里增加难度,不是我在拒绝电影,而是我觉得我在给读者增加难度,我不能惯着我的读者。我现在写的文本特别难读,标点符号有,但是我经常也不断句。这也是在给自己增加难度。
徐:(笑)就像你打三副牌,拿个笔在旁边记跑了多少分?
阿:(笑)这个比喻太差劲了。但的确是如此。需要你勇敢地用你的经验与推理能力去演算,去设计。还有,保持阅读,就是保证自己不会枯竭。我有很多经历,但是我差一个致命的经历,就是福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等到经历用得差不多了,才是检验小说家成色的时候,就像听觉之于盲人,虚构之于作者。不是完全的虚构,尤其要避免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的匮乏,虚构出来的物品要能接受合法性与逻辑性的审查。
人都会有一段遭罪的时间。我有时会把这几年写作的失败归结为抑郁症,但实情是这几年我写得很多,质量没下降太快,暗自里它在保持进步——也就是说,我的手段和方法现在更多,对事物的理解也深入了。这几年鼻青脸肿的尝试,在中篇和一些架构上的尝试已经使我能去写长篇了。
徐:您的作品现在的海外版权如何?
阿:《下面,我该干些什么》(APerfectCrime)已经和ONEWORLD(英国)出版社及Stock(法国)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短篇集《鸟看见我了》已经和日本勉诚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
徐:好的。关于主题与写作我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用一句话总结?
阿:过去,我的经验是对一些事的经历;现在,我的经验是对世界的看法。
关于生活
徐:明年寒假我还会去北京找你和丁哥玩。
阿:(笑)好的,只要不喝酒。
徐:你对城市生活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阿:沉默。人是难以应付巨大的沉默的,好在这几年结婚了。否则的话,你听到的蚂蚁的呼喊声有多大,那么世界听到你的呼喊声就有多大。你得到的就是巨大的沉默。沉默像一记巨大的耳光。
徐:写作与你的生活关系紧密吗?
阿:既紧密又疏离。写作是我最后一个和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手段,我试图用很多方式来与世界发生关系,但仍然无法填补与它的陌生。后来我想,不如将这种陌生感写进去。我现在对生活还充满敌意。生活是个什么东西?就像是有五匹马,从五个方向拉着你,你团团转。
徐:这种情形发生在“写不进历史”的时候吧?
阿:(笑)没错。写开了,我会很风情。但有时写不进去,我会把很多人视作是和我无关的人,我在心里面和他们划清界限,不和他们纠缠更多。你知道:答应对方的总要尽力做到,但来自他人的承诺最好勿信。要降低依赖感,包括对素材也是如此。我努力做到人情物理都懂得一点,然后自给自足。
徐:你很喜欢看电影?
阿:有时为了放松一下,我会去电影院,因为那里的光线、屏幕以及音响足以使你神游进另一个世界。你可以专注地阅读一个故事。但是——即使观众再少——总会有人掏出手机,让荧光照射到你的眼球(像手电照射做梦的人)。或者干脆接起来,喂,喂,喂。一定要让自己的声音大过电影的声音好让对方能听清。这时我便走神,咬牙切齿地幻想自己是希特勒。
关于读书
徐:现在还读博尔赫斯么?我注意到你刚才提到“博尔赫斯的匮乏”。
阿:很少。博尔赫斯的语言已经到了一个化境,但是,它缺乏生活来支撑,只有无穷的意境、想象、迷宫。我热爱聪明,坚持读书就是为此,学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验的亏空,但一直要告诫自己,聪明不是终点,至少它不处于小说的核心位置。
徐:这是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比吗?
阿: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本身即象征着素材。你没有他那种人生,你没有在快被处决时给拉下来,你没有被流放,你的思想上就很难有那么激烈的挣扎,他是拿命来迎接这个世界的。我只读过陀思妥的《罪与罚》,很吃惊一个人能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写得那么长,骨架是一个青年杀了放高利贷的婆婆,然后躲避、逃亡、自首。剩下的全部是心理,而且那心理永不重复,这是不可想象的难度。我就想这又和写作者本身的经验有关。
徐:我有意做了一个对比: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下一个是马尔克斯——福克纳。
阿:先说马尔克斯吧。马尔克斯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马尔克斯,就是他本人。他的技法,以及他一惊一乍说书的能力,小若吸铁石、冰块,也能在他那里得到飞毯的效应。
徐:(笑)这不是化腐朽为神奇吗?
阿:但伤害他的也正是如此。
徐:怎么说?
阿:这是一种较荤的写法,持续端这样的菜给读者,会使读者想到对方的取悦企图,而在马尔克斯的每句话下边,其实都隐藏着这种邀赏的企图。我始终不认为《百年孤独》与《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伟大作品,但我异常醉心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只有在短篇,马尔克斯才发挥了自己曾经是记者的长处,那就是简洁、规整、克制、不动声色、止步于当止步之时,作者本人不会跳来跳去。
徐:你对余华早期以后的作品也持如此评价。
阿:是的,我很喜欢余华,但有时他也不懂停止,某些作品的结尾不是太好。继续说马尔克斯。他的短篇《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我只是来这儿打个电话》等,甚至他写的关于首都降雨的新闻作品,都像闪光、不朽的钻石。但长篇时就释放了在写短篇时只是微瑕的部分,经营得不够细致。马尔克斯在中国的红火,可能得益于八十年代的盗版。人的红火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泡沫。时间会让马尔克斯沉下去一点,以让福克纳这样的圣贤升上来。
徐:你非常喜欢福克纳。
阿:非常喜欢。他懂得躲避自己的缺陷,同时也懂得不炫耀自己的长处。他停止时,别人无话可说。我感觉他的作品一概飘在空中,像一个伟大的城堡,它没有根,比山顶还高,你仰望着它,你就算做了个嫉妒的大炮,从各个角度去攻击它,它连一块石头都不会掉下来。
徐:我曾经说过:福克纳的长篇小说中,《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最好,《野棕榈》《去吧,摩西》可读。
阿:我正好读过这四个“最”。拾级而上的话,先《八月之光》,再《喧哗与骚动》,最后《押沙龙,押沙龙!》。如果临摹,《喧哗与骚动》这本书有着伟大的简单。真正孤寒的是《押沙龙,押沙龙!》,像是工匠打给自己的家具。福克纳的数部长篇,难以分级别,先易后难去读,于写作者是技法上的极大培训。很多作家一辈子调性一样,误人时间。
徐:你好像还很喜欢曹雪芹?
阿:曹雪芹这类的作家在人类历史上是绝对稀有的物种,它们对今天的读者有两层意义,其一是激励,虽然有时你会既绝望又嫉妒地幻想扛个大炮轰射它们,但无济于事,这便是第二层意义:镇压。所以我很少读当代小说也是这个原因。前者鼓励也好,镇压也罢,都是持续的、不曾中断的永恒。
徐:好的。今天我们聊得太久,耽误乙哥时间了。
阿:没关系,新的长篇已基本写好,现在主要是做一些修改。谢谢你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