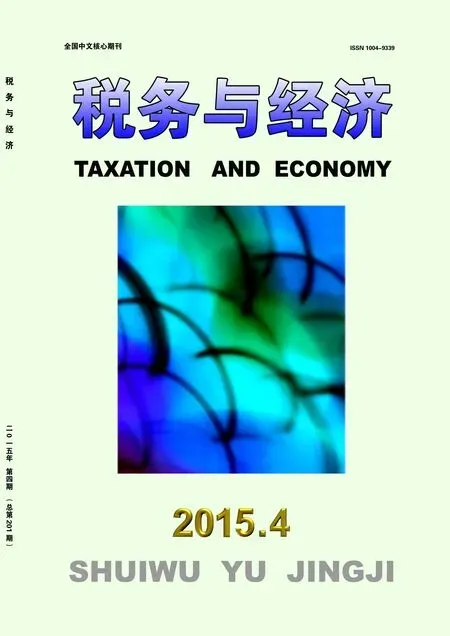中国与希腊外债使用效果对比分析
杨惠昶 , 孙 涵
(吉林大学 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和希腊同样是资本短缺的国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需求,适当举借外债是明智的选择。这是没有疑议的。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债务国如何合理利用外债,最大限度地发展本国经济,扩大出口,使外债这个外因转化成为发展本国经济的内在动力,而不是最终被其所累。
自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和相关研究机构都在探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经验、教训和启示。本文从外债是促进了GDP增长还是导致其萎缩、是推动了国际收支顺差还是导致其逆差、是促进了国民福利提高还是导致其下降、是增进了社会和谐还是加剧了社会矛盾这四个问题出发,深入分析中国和希腊外债使用的效果,并探究其成因。
一、外债是促进了GDP增长,还是导致其萎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希腊与中国相比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其在欧盟内部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和希腊两国的制造业都很落后,想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发展自己的经济,在本国财力不足的情况下,都需要向外国借债。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指出:“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翻两番,…… 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1]53-541989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基础工业,无非是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年到二十年,宁肯借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多大失误。……借点外债用在这方面,也叫改革开放。”[1]308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也堪称经济学大师,他深知,一旦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引进来,为我所用,中国的工业结构就会更新,中国的重工业、轻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都会发生革命,都会向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一旦中国能够通过合理地使用这些引进的外资,迅速形成自己完整的机械工业体系,中国的工业生产就如同获得了一种动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中国的企业借助先进机器的生产能力,就会以加倍的方式大量生产出成本更低、科技含量更高、更受本国和国际市场欢迎的产品,以这类产品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制造”是中国促进本国市场繁荣,夺取国际市场的强大武器,并为中国带来了异常丰厚的利润。
所谓引进外资,就是把外国资本引进本国。资本本身主要有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需要引进的实物形式的资本主要是先进的机械设备和国际领先的生产技术等;需要引进的货币资本其实就是把外汇借来用于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1978~198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182亿美元, 1978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8.2%、49.7%和23.9%;1989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101亿美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5.1%、42.8%和32.1%;1999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527亿美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5%、45.8%和37.8%;2009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918亿美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3%、46.2%和43.4%;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187亿美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43.9%和46.1%。这些数字说明,随着中国引进外资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稳定,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
表1历年中国引进外资额单位:亿美元

年 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979~1984182.00198548.001989101.001999527.002009918.0020131187.00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国家统计数据库。

表2 历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结构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国家统计数据库。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希腊却没有把从外国借来的债务有效地用于引进先进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进而发展本国的工业,而是直接用来增加公务员工资,提高社会福利,以国家信用作担保借来的债务并未有效地转化为资本,反而进一步成为了国家负担。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和贸易决定分配,决定福利,不生产和销售大量的商品和劳务,就无法形成强有力的GDP,那么福利也就无从得来。脱离了本国强劲的生产力和繁荣的贸易基础去搞福利,福利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靠借钱去谋福利,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也是必然的。
根据生产函数理论,一个国家总产量的增长是由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技术水平状况决定的。而技术水平状况只能物化在劳动和资本中,是由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效率表现的。从供给角度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由于中国卓有成效地大量引进外资,本国不但能够大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能够大量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不仅如此,从需求角度分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国际市场空间均得到极大的拓展,对中国生产的产品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众所周知,实物产品自身并不形成GDP,实物产品只有通过市场交换,转换成货币价值,才能形成GDP。由于中国有效地利用了外债,积极地推动了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强力拉动内需并促进出口,为自身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积累了巨大的潜力,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GDP都在以最高的速度增长。

表3 历年中国和希腊的外债与GDP规模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国家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4。
如表3所示,2007~2013年中国的GDP和外债规模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如此,债务与GDP的比率却一直保持稳定,没有提高,基本上维持在9%左右,合理的外债规模较好地促进了GDP增长的良性循环。与中国相反,2008~2013年,希腊的外债规模在大部分年份都保持了增长的势头(只有2012年是下降的),然而其GDP却一直保持了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希腊的外债未能对其本国经济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综上,对一个国家来说,举借外债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合理而有效地使用外债。中国把外债用于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促进了本国生产的发展,实现了GDP增长,有效地使用了外债,实现了良性循环。而希腊用外债来提高公务员工资,发放福利,外债未能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导致本国GDP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也就是说,希腊没能有效使用外债,步入了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
二、外债实现了国际收支顺差还是逆差?
信用是商品交换和货币借贷的基础,借债本身就是因为信用的存在才能发生。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其之所以愿意把货币借给债务人,就是因为其相信债务人能按时还本付息;从债务人角度分析,为实现顺利借债,保证自身声誉,其需要以个人信用为担保,向债权人保证会按期还本付息。“欠债还钱”是古今通则,无可厚非。邓小平同志在大胆提出向外国借债的同时,也敏锐地指出了外债的偿付能力问题。他说:“对借外债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有的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外债要适度,不要借的太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经验。”[1]193“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2]156“外资有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如果没有偿付能力,他们不会干的。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2]198-199作为债务国,如何才能增强自身偿付外债的能力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够取得更多的外汇用于偿还外币债务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增加出口,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出口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来赚取外汇。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外债和内债的性质完全不同,内债是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可以用本国货币归还。以中国为例,财政部通过向央行出售国库券,央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购买财政部的国库券,仅这一步就可以创造更多的本国货币;也就是说,财政部借内债原则上有无限的偿债能力,只要增加本国货币供给即可。然而,外债的情况截然不同,外债是用美元等外币表示的,只有将本国货币兑换为外币,或直接通过出口创收外币来偿还。以中国为例,本国的财政部和央行没有创造美元的能力,大量创造更多的本国货币只能导致本国货币贬值,无法换取所需的美元。因此,中国真正大量获得美元的途径只能靠出口。出口能力是检验债务国偿还债务能力的最重要的标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引进外资规模用于提高自身生产能力,中国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设备开始不断升级换代,已逐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出口的产品也逐步由初级产品转化为工业制成品,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质量也已逐步与欧美日的产品质量相媲美。一方面,中国出口的不断增加,实现了外汇收入的不断增加,偿债能力不断提高。不仅如此,中国出口的不断增加,也意味着外国市场对中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刺激中国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断增加,拉动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满足了外国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不断增加,刺激外资更多地流入中国,同时也刺激中国的进口不断增加,引进的先进生产设备不断增加,进而中国出口创汇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加。中国在适当借债、生产力提高、GDP规模扩大,出口增加、进口增加和按期还债各环节之间实现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表4 2007~2013年中国和希腊的国际收支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国家统计数据库;extracted on 05 Oct 2014 06:39 UTC (GMT) from OECD. Stat。
如表4所示,2007~2013年,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均不断增加,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这赋予了中国强大的偿债能力。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其中,中国出口排名世界第一,这也说明中国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改善做出的贡献位列世界第一,因为世界各国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提供的;中国进口排名世界第二,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就业和生产力的增加所做的贡献位列世界第二,正是由于中国的消费拉动,才刺激了世界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增加。
表5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单位:亿美元

年 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占比1997749.000.4120076954.000.57201210226.000.50201310437.000.47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国家统计数据库。
如表5所示,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扩大出口的贡献很大,功不可没。199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1%,2007年占57%。由此可见,外资的引进迅速加快了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2007年以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开始略有下降,这说明,经过之前10年的历练和发展,中国企业自身生产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出口创汇能力不断增强。由于中国不断引进外资,中国出口的规模不仅不断扩大,出口产品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80年,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正好各占50%;1997年,两者在总出口额中占比分别为13%和 87%;2013年,两者的比重分别为5%和95%。这足以说明,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发展生产力,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出口产品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各占半壁江山的状况,彻底扭转为以工业制品为主导的制造业大国的出口结构。中国通过合理借债和合理有效地使用债务,实现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到发达的工业制造业国的根本转变。
同样以表4中的数据为例,希腊的进出口状况正好与中国相反。2007~2013年,希腊的国际贸易一直是逆差,虽然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其贸易逆差不断减少,但仍旧是逆差,贸易逆差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希腊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赚取外汇,这也就注定希腊已经无力偿还外债了。表4的数据还告诉我们,希腊的贸易收支逆差之所以开始减少,并不是因其出口增加引起的,与2007年相比,希腊在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这4年的出口额均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即使2013年的出口额为53 013.94百万欧元,与之前年度相比有所增加,但也未达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的53 087.67百万欧元的水平。希腊贸易收支逆差减少,主要是进口减少造成的。2008年,希腊的进口额为90 052.10百万欧元,2013年大幅度跌降为57 815.38百万欧元。这是由于希腊政府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来说,进口是重要的,进口能直接提高本国民生,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由此可见,希腊通过紧缩经济政策,实现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的表象,本质却是以牺牲本国国民福利为代价的,这必将引起民众不满。这种政策和结果对希腊这个外债高筑的国家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由此可见,出口能力强弱,贸易收支能否实现顺差,是衡量一个国家能否按时对外债还本付息的基本考量标准。中国进出口逐年增加,贸易收支持续顺差,意味着中国有继续举借外债和顺利偿还外债的能力;希腊进出口均不断下滑,贸易收支持续逆差,说明希腊失去了继续举借外债和按时偿还外债的能力,也就必然导致希腊陷入外债危机之中。
三、外债使国民福利提高还是下降了?
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提出,中国引进外资的结果成功与否,“就看外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72

表6 2007~2013年中国、希腊消费储蓄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国家统计数据库;OECD,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如表6和表3中的数据所示,2007~2013年,中国外债规模逐步扩大,而中国的GDP由265 810亿元增加至568 845亿元,翻了一番还多;中国的人均GDP由20 169元增加到41 908元,也就是说GDP的质量也翻了一番;居民的消费支出由132 233亿元增加到292 166亿元,居民储蓄由137 403亿元增加到282 818亿元,这说明居民个人财富和个人消费水平也都翻了一番。以上的数据充分说明,中国人均GDP、消费和储蓄的成倍增长,与中国引进外资,举借外债用于提高本国生产力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这也足以证明中国的举借外债、引进外资的结果是成功的,举借的外债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福利。
然而,表3和表6中的数据也同时说明,与中国的情况相反,2007~2013年,希腊的GDP由3054亿美元减少到2417亿美元;希腊的人均GDP由27 361美元减少到21 910美元;居民消费支出由2125亿美元减少到1750亿美元;居民储蓄由384亿美元减少到251亿元。这些关键数据指标的下降都是希腊未能有效使用外债的恶果。希腊举借外债、引进外资,但未能有效加以利用,不但没有使希腊国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反而急剧下降了。也就是说,希腊举借外债、引进外资的结果是失败的。
为什么中国引进外资取得了成功,而希腊却失败了呢?简单地说,是中国的外债得到了有效利用,而希腊的外债未得到有效利用。对此,尚需进一步深入剖析。中国人常说,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内因和外因。外因是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发展变化的根本。中国的情况是把举借外债当作本国经济发展的外在借用力量,是外因,而成功地将政府、企业家、劳动者、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发挥其最大的综合效能,才是内因,而且是根本原因。中国GDP持续增长,外贸顺差持续扩大,人民的消费、储蓄不断提高,并非外债本身有神奇的魔力,是包治经济病患的灵丹妙药。举债只是工具和手段,如何用其撬动经济发展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政府层面的正确导向、企业家的科学管理、商人们卓越的市场营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劳动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报酬。中国经济这个大饼做大做强了,合理分配就不是问题了。工人得到了他们的劳动报酬——工资,企业家得到了他们管理企业的报酬——薪金,商人得到了他们市场营销的报酬——商业利润,政府得到了他们管理宏观经济的报酬——税收,外国债权人得到了他们的债权报酬——利息,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不断借入外债和不断归还本息,这就是资本在中国与债权国之间的流动,这就是中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信用。这种有用的和有成效的金融活动,赋予了货币、劳动、商品以生气和活力,推动中国和债权国的经济共同增长。
希腊的情况与中国相反。希腊没有把外债当作资本用到生产和贸易中去,反而把借到的外债当作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当作免费的午餐,用外债来消费和休闲,可谓不亦乐乎。如表7中的数据所示,希腊政府通过举借外债来满足政府逐年的财政支出,而其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并非其亟待发展的工业,而是每年将超过5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公务员薪酬和社会福利。2009年,公务员薪酬占希腊财政支出的24.87%,而社会福利支出占比高达39.27%,仅这两项占比合计就高达64.14%;而之后的几年,这个比例还在逐步攀升。由此可见,在希腊,外债主要被用于消费,而不是发展生产。其结果必然是GDP难有增加,外贸收支无法顺差。从本质上看,国民福利的增加意味着坐吃山空,待到外债还本付息期限迫在眉睫之时,就只好用最下策——勒紧裤腰带来还债了。然而即便如此,没有强大的生产力驱动和稳定的贸易顺差带来外汇收入,勒紧裤腰带只能减少挥霍,根本无法满足还债需要,结果就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表7希腊政府主要财政支出单位:百万欧元

项目年度199720022009201020112012财政支出总计4885270621124736114250108437103856公务员薪酬金额112661730831020277132570023948占比23.06%24.51%24.87%24.26%23.70%23.06%社会福利支付金额151432418448981475034718644314占比31.00%34.24%39.27%41.58%43.51%42.67%归还利息金额1011987411191813193150179705占比20.71%12.38%9.55%11.55%13.85%9.34%
EuroState: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Summary tables2/2013 Theme: Economy and finance ISSN 1725-9819。
四、外债带来了社会和谐还是对抗?
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可能发展成和谐关系,也有可能发展成对抗关系。因为债务关系的双方所追求的都是自我利益,都想利用对方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好处或者说利益,而这种各自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发生对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无论是在买卖关系中,还是在借贷关系中,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是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3]在债务关系中,只要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按合同办事,贷方按要求提供资金,借方按合同按期还本付息,双方似乎就能够实现互利互惠。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是不对等的,在债务关系中,债权人处在支配的地位,债务人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债权人以贷出的货币为资本,坐享利息;而债务人就没有债权人那样清闲自在了,他要利用借到的货币进行生产和贸易,赚取超过借款额以上的更大利润。如果债务人利用借得的货币进行生产和贸易所赚取的利润超过借款额,对债权人按期还本付息之后,自身还有剩余,双方就实现了互利互惠;然而如果债务人利用借得的货币进行生产和贸易却未能赚到利润,或者赚取的利润未能超过借款额,对债权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甚至破产还债,或者完全丧失还债能力,那么双方的关系就转化为对抗关系。
中国和希腊举借外债效果的鲜明对比,正好生动地诠释了债务关系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说,债权人和债务人两者既可能发展成和谐关系,也有可能发展成对抗关系。当今世界比较流行的外债风险指标是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制定的。主要包括4个指标:(1)偿债率。为当年中长期外债还本付息额加上短期外债付息额与当年货物和服务项下外汇收入之比,其国际标准安全线为20%。(2)债务率。为当年外债余额与当年货物和服务项下外汇收入之比,其国际标准安全线为100%。(3)负债率。为当年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国际标准安全线为20%。(4)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其国际标准安全线为100%。
表8 2007~2013年中国希腊外债风险指标单位:%

国家指标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希腊偿债率=付息/出口0.280.270.310.25负债率=债务/GDP1.071.121.291.471.701.771.90债务率=债务/出口4.514.666.716.656.816.526.53中国偿债率=付息/出口0.020.020.030.020.020.020.02负债率=债务/GDP0.110.090.090.090.100.090.09债务率=债务/出口0.290.250.320.290.330.330.36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国家统计数据库;希腊银行2014年年报。
注:表中未列出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原因是难以查到希腊的相关资料。
表8中的数据说明,2009~2012年,希腊的偿债率分别为28%、27%、31%和25%,超过国际标准安全线设定的20%,而中国则分别为3%、2%、2%和2%,完全符合临界点20%的要求。2007~2013年,希腊的负债率都超过国际标准安全线设定的100%,2013年竟高达190%,而中国在2007年最高才是11%,其他年份几乎都是9%,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安全线的的要求。希腊的债务率更是高于国际标准安全线要求的20%,即使在2007年的最低点,也高达惊人的451%,其余年份都在652%以上;中国的债务率虽然也略高于国际标准安全线要求的20%,但2013年的最高点也仅为36%。根据世界目前比较通行的外债风险指标测算,希腊所有指标都远远地超过了安全线,而中国除一项指标略高于安全线外,其他均完全符合安全线要求。也就是说,希腊的外债是不安全的,是高风险的,危机爆发是必然的;中国的外债是安全的,是低风险的。
由于中国的债务风险指标是安全的,外债的借用与归还进入了良性循环,中国经济社会保持了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的可喜形势。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GDP和人均GDP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储蓄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生产能力更加自信,对自己的出口能力更加自信,对自己举借外债、使用外债和偿还外债的能力更加自信,对自己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更加自信。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也赢得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信任。中国的自信和外国的信任结合在一起,中国举借外债最终收获的是和谐。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一方面引进外资,另一方面也对外投资。自2008年起,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逐年增加,到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达到6605亿美元。2015年1月16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表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95.6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对外投资额和自身吸收的外资额仅相差160多亿美元。可以预见,中国有可能很快会成为净对外投资国。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证券投资增长得更快,2007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4776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达到12 700亿美元,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最大债权国。
希腊的情况与中国正相反,由于未能有效使用外债, 2005年之后GDP和人均GDP不断下降。为了偿还外债,希腊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降低工资,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从2009年至今,希腊国内的消费支出和储蓄大幅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希腊政府和国民失去了举债和偿债的能力和信心,政府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不仅如此,希腊不能对外债还本付息,也失去了债权国的信任。自己失去了信心,对外又失去了信任,两种失信融合在一起,希腊举借外债最终面对的是内外两方面的尖锐对抗。作为债务国政府失信,不能及时履行对外债务偿付义务,引来希腊“国家破产”的危机。希腊也摆出了无力还债的姿态,确切地说,希腊确实到了无力还债的地步。这使希腊的债务国与债权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甚至到了对抗的地步。在债权国逼债的压力下,希腊国内某些党派主张退出欧元区,而法国和德国则回应说:希腊人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是否退出欧元区应由希腊人自己决定,但希腊新政府必须信守承诺,某些特定契约已经订立,必须完全得到尊重。公然向未来的希腊政府施压,不论其退出欧元区与否,都必须还钱。债务国与债权国的对抗完全公开化了。
把中国和希腊举借和利用外债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债务国若能有效地利用外债,提高本国生产力,发展本国经济,推动GDP增长,使国际收支实现顺差,债务国和债权国就会不断增强相互信任关系,实现互利互惠关系。否则,两者之间就会发展成对立关系。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