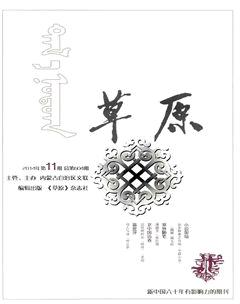昔日黄花
王琬莹
那年春天,我只是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第一天上班,在电梯口我的目光与另一个人的目光相遇。那双眼睛黑黑的,亮亮的,同时却又是迷茫的、忧郁的,很像深秋的海水,闪着并不温暖的光芒。我的心在不经意中抖了一下,感觉到自己的脸颊也在悄悄地发热,手里拿着的小包差点失落掉地。
人生也许不止一次地会有这样的“只如初见”,即使当时心灵抖了一下、脸颊热了一下, 那又怎么样?浮云而已。
春风吹来了夏日。那天落雨,我晚上加班后,又在公司门口碰到了他,他穿着暗红的格子衬衣,暗灰的休闲裤,但眼睛里却溢满了明亮的温柔。他向我走近来,我顿时感到了一阵眩晕。他手中的那把深蓝色的雨伞“啪”的一下开了,之后他极其自然地对我说:我们应该是同路的,我骑着摩托车捎你一程吧。我没有拒绝,于是,我坐在他的身后,嗅到了雨的——其实是他的、一种与女性截然不同的清新味道。
我知道了,他叫安长江。
那年的秋天好像被我忽略掉了,季节直接从雨的夏天跳到了雪的冬天。在元旦舞会上,他邀我跳舞,我躲闪着他的目光,在默默地寻找着记忆中的清新味道,我找到了,于是我抬起头来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仍然很像深秋的海水,但此时却闪出了温暖的光芒!我丢掉了一个女孩子应有的矜持,我迷恋着、深深地迷恋着那双眼睛,当时就想:我宁愿淹死在这片海水里永远都不要浮出水面,整整一辈子。
散场后,我就像失了魂一样尾随着来到他的宿舍里,在微弱的灯光下,他捧起我发烫的脸,轻轻地吻我,之后我在他的抚摸下浑身战栗……
很快,我在以往无数次想象中的、我在此时又急又怕等待中的那种痛楚,来了。我在他粗鲁的撞击下,好几次都想起身离去,但我没有,我看着那双深秋的海水般的眼睛,放弃了自己。
安长江,我什么都愿意,为你。
英国威廉王子与平民姑娘凯特·米德尔顿的婚礼,始终贯穿着的婚礼进行曲: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在他的缠绵中,在他的俯视下,我夜夜妖娆,一如初开绽放的玫瑰花。我的乳头和指甲,也都随着我的绽放而呈现出绯红的颜色,我明白了,这是爱的颜色。
都说热恋中女人的智商为零。我当时就像个傻傻的小孩那样追问他:
“告诉我,我是你的吗?”
“嗯,当然是,永远是我的。”
“我要你跟我生生死死。”
“好的,永不改变。”
“拉钩上吊,一万年不改变!”
我们十指交叉,竟是那么的吻合。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背着我在大街上奔跑,在路人的目光中,我们的笑声传到老远。我们一起去看烟花,从剧烈爆放的烟花里,我们看到了爱的光芒爱的释放、美丽甚至壮丽。
两情相悦的爱情真好,我在暗暗庆幸自己得到了真爱。
幸福的1994年,幸福溢满了我的生活,幸福流淌出异样的光彩。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我吃着馒头就着咸菜,心里在想:我怎么可以这么幸福?
早晨,我故意笨笨地穿着他的衬衣,笨笨地为他烧饭,我烫了手,他心疼地放在嘴里吸吮。
我们就是一对食人间烟火的情侣,幸福得找不到北了。
幸福的1994年并没有延续到年底,就在我的腹中开始有一个小生命在蠕动的时候,某天我突然在一个咖啡店里看到他竟拥抱着一个陌生的女孩!我的心当时就崩塌了,我要疯了,但我什么都没有做,一个人默默地回家了。我一整夜没合眼,他一整夜没回来。望着窗外的天空,我的心空了,我的神经即将崩溃。
吵架的日子开始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那是我们公司副总的女儿,安长江觉得自己靠近这个女孩,更有利于他的前途和事业。他那双如同深秋海水的眼睛后边,怎么会藏着如此一颗变幻莫测的心?
我不再像一个傻傻的小孩子了,我的智商在零的起点上开始攀升。情感颓废了,争吵升级了,爱情的玫瑰花开始枯萎了。
安长江也枯竭了,他眼里的海水日渐干涸,越来越多的是疲惫。
僵持和冷战维持不下去了,有一天争吵后,他终于离去。
就在那一瞬间,我被一种说不清是希望还是绝望的心情逼迫着、追出去大声质问他:你不是说永远爱我么,你不是已经和我拉过钩的一万年不变的么,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我是你心爱的琪琪啊,你就这样一走了之了?
他不答,他走了。
我一个人跑到医院,在冰冷的产床上打掉了他的孩子,我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泪流满面。
但是,当那个从自己的身体里剥离出来的、血糊糊的东西呈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
我明白了他不是真的爱我,我明白了他可以跟任何女孩子去倾诉同样的情话。我的爱情,原本并不是爱情。
我开始失眠,在失眠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抽烟、喝酒、跟各种男人周旋,只是不再言爱。我的爱已经麻木了,火红的烟灰掉在腿上,腿也麻木。
我度过了19年的生命,我的情感在1994年开始,也在1994年死去。从此以后,我不再是我。
灵魂死去了,身体还活着。身体在深夜里放纵,冰冷地放纵着。
但是在我一个人的夜里,深秋的海水依然能悄悄地流进我的梦,他的背影就在那片冰冷里,我拼命地追,但一直追不上直到最后消失。我望着远去的海水哭喊:长江你等等、你等等我!我在哭喊中醒来。
19岁,青葱葳蕤的19岁,我不知道镜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而我的心却似乎一步就跨进苍老的暮年了。
后来我辞去了工作,后来的后来,我迫于生计变换过很多活法,最后开了一家花店。某天我在街口遇到了他——一个为人夫、为人父的他。他胖了、老了。淡淡的几句对话,他问我:琪琪你现在……还是一个人么?我没有回答。
花店里,一千朵鲜花在清晨的阳光里,娇艳绽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