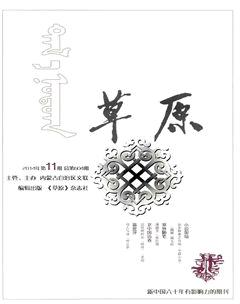打工的地方(短篇小说)
狄文亮
六月天,烈日炎炎。这三个女人在秦得义的麦田里拔草,她们是常霞、魏芳和乔海云。
常言说:三个女人就可以抵一台戏。其实,这里有乔海云一个人就足够红火了。这女人身高体壮,在她那黑黝黝的、非常瓷实的皮肤下面,仿佛蕴藏着无限的精力,老也使不完。她一边干活儿,一边不停地说。说夜里睡觉,她睡梦中把男人差点儿一脚蹬到床底下去;说她们家的那只大花猫,一肚下了六个崽;说今天出工时,在她家大门口看见两只小狗在打架……真是值得的也说,不值得的也说,中间还不时穿插一阵一阵爽朗的大笑;那笑声荡漾开来,和正在高空飞行的飞机的隆隆声搅和在一起,听起来是那样的响亮。
魏芳就开玩笑说:“好家伙儿!看人家这一路笑吧,把飞机的声音也盖住啦!”这不是明显地含着一些讥讽的味道?但是乔海云听不出来,只觉得这是在夸她,一仰脖子,便又爆发出一阵更加洪亮的笑声。
常霞看着魏芳,静静地笑了笑,又低头去拔草。不管乔海云这里有多么热闹,她总是闷声不响低头干活儿。只有魏芳时不时和乔海云接应两句,很显然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出于一种礼貌。
这乔海云除去上面这个性子外,还有一样非常不好的毛病,就是喜欢拿摸人家的一些小东西。如果追化肥,她总要在兜里往回装人家的一些化肥;如果掰玉米,她总要在怀里往回揣人家的几个棒子。她不怕女人们看见,有时一边拿摸一边还笑嘻嘻地对人们说:“怕什么?不拿白不拿,拿了还想拿。哈哈哈哈!”跟着就是一阵大笑。
“看见人家什么也爱,讨厌!”常霞经常悄悄地和魏芳嘀咕。
有一天,她看见乔海云撒完化肥后,把一个塑料袋藏在了草丛里,就眨着眼睛,静静地直看魏芳。过了两天,她们下工时路过秦得义的蔬菜地,乔海云弯倒腰正准备掏人家的蒜,常霞就慢言慢语开腔了:“怎?又想拿人家的蒜疙瘩哩?”乔海云正起身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尘土,走开了,一边说:“我拿他的干什么?我家里的还吃不完呢。”
这天一上工,常霞忽然对魏芳低声说:“芳姐,我告了她。”
魏芳一惊:“啊?你告了谁啦?”
“乔海云。”
“她怎啦?”
“她又拿了人家的塑料管儿啦。”
原来,昨天上午,常霞和乔海云到牛在山的小院里去喝水,出来时,看见大门口撂着一截二三米长的塑料管儿,那是牛在山浇蔬菜用的,撂在门口已经很长时间了,乔海云顺手就拿走了。把常霞弄得又急又怕,喉咙里短促地“啊”了一声,却说不出话来,脸当下就红成了公鸡冠子。乔海云肩挎塑料管儿,没事人似的,大摇大摆往前走。常霞一路快步,跟在后面跌跌绊绊紧着走,脖子直直的不敢左右扭动一下,仿佛身体两侧和后背上全都爬满了眼睛,眼睛。赶到了地里,她的额头上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
昨天魏芳没出工。为这事,常霞独自煎熬了一天,心里一个劲儿埋怨乔海云:“你老爱拿人家的东西,让我们跟着你受怀疑,长久这样下去,叫人家连个好赖人也分不清啦!讨厌!”赶到天黑,乔海云下工前头走,常霞就退在了后面,一转身溜进了牛在山的小院,把乔海云拿塑料管儿的情况说给了牛在山。
听了常霞的叙说,魏芳赶忙问:“牛在山说什么啦?”
常霞说:“他没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管他说不说哩,反正我是告诉给他啦,要不让他还怀疑我哩。”
魏芳默默地点了点头。
后来,一直也没听见牛在山过问塑料管儿的事。乔海云呢,照常说,照常笑,也照常拿摸人家的东西,真是活得洒脱自在。常霞就不时停下活儿来,静静地瞅魏芳几眼,那眼神里流露着一种困惑,也表现出一种询问。
麦田里拔完了草,她们接着又锄瓜。秦得义今年种了十多亩西瓜,那瓜秧一块一块长得非常旺盛,蔓子又粗又壮,顺着地皮往前疯窜,一黑夜就能长出二三寸长。足有小面盆大的叶子,花花的,肥肥的,呈现出一派灰绿灰绿的颜色。茎上开满了小黄花,花下结起了小瓜蛋,蝴蝶翩翩舞,蜜蜂嗡嗡飞。三个女人就在其间挥锄松土,锄头不时伸出土面,在太阳光下耀出道道白光。她们的头巾或蓝或黄,衣衫或白或黑,尽管汗渍斑斑,尽管粗陋不堪,但她们身上拥有的那些驳杂的颜色,足可以和银锄的颜色、瓜田的颜色交相辉映,成为这原野上一道靓丽的风景,而为画家所注目,为诗人所倾倒。
在一个太阳毒花花的下午,她们出的汗太多了,自己带的水也早已喝光了,人人渴得舌头转不动,嗓子往一起粘。于是魏芳就说:“走!到牛在山那里喝水去。”几个人相跟着,溜溜地走进了那座小院。她们攒在水缸边,每人“咕咕”喝了一气水,肚子里只觉得冰凉冰凉的了,这才解了渴,也镇了暑。
她们从屋里出来,魏芳说:“咱们歇一会儿凉再出去干吧。”几个人就蹲在屋檐下的阴凉地里了。那时候,牛在山吆着羊群出去了,小院里就只剩下乔海云的说笑声了。乔海云笑着说,说着笑,她讲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张老虎,(就是秦得义年年雇来浇地的一个汉子)有一天给我打电话,叫我到秦得义的葵花地里去,一听就知道他不安好心,我说,去也行,你给我准备下五百块钱,一句话就把他个孙子给撑住啦!再没敢作声!哈哈哈哈!”接着便爆发出一阵响鞭炮似的笑声。
魏芳被逗得“咕咕”直笑,看着乔海云开玩笑说:“那你就没骂他几句?你就说,你又想闻老娘的荤腥味儿,又舍不得你那几张烂纸片子,还是回家搂你妈去吧!”
“哈哈哈哈!”乔海云本来即将平息下去的笑声,马上又回升起来了,笑得牙颏打颤,笑得眼泪直淌。
这工夫,常霞却一直静静地坐在旁边,始终不为所动。那蓝色的头巾箍在头上,为了遮阳,两边朝前面抻出很长,把她的脸掩得只留下了一道窄缝。她的头微微地朝前伛着,看上去就像是瞅着地上。其实,她长时间看着的,是撂在那边墙角的一个生了锈的水泵。她嘴里嚼着一根小草棍,眼睛盯着那个水泵,脸上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endprint
她首先想到,那个水泵要是被乔海云发现了,又敢偷偷地拿走。她又想到,拿走也就拿走啦,这些地方,根本就不把东西当成个东西!……这样一路想来,她蓦地心动了一下,原本像个黑洞似的脑子里,这会儿忽然好像拉开了一道缝儿,透进了一线亮光——
她想到:她们家还有七八亩地,虽说早就没心思种地了,包出去也已经好几年了,但说不定哪天还会抽回来自己种呢。若要种地,就得浇水,若要浇水,不就用得着水泵啦?买一个新的,现在这价格,少说也得一二百块钱。可是……可是撂在墙角的那个水泵,虽然看上去旧了点儿,但是肯定能用,要是,……要是拿回家里去,到时候不是就能解决大问题啦?
想到这里,她不禁朝大门口睃了两眼,恰好听到牛在山在远处恶狠狠地吆喝羊,她便吓得浑身不由得瑟缩了一下。然而旁边乔海云那响亮爽朗的说笑,乔海云那表现的对什么都蛮不在乎的神态,就像一服特效的镇静剂,使她的情绪很快平静下来了。“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她默默念叨着这句话,三念叨两念叨,结果一个主意就打定了:“瞅个空子,我要往回拿那个水泵。”
就在当天傍晚,常霞注意到牛在山放羊还没回来,而她们下工的时间也到了,她就假装到那边渠壕里去方便,退在了后边。看着魏芳和乔海云两人骑着电动车“嘚儿嘚儿”地走远了,她就一转身朝牛在山的小院快步走去。她想,要拿就得趁这会儿拿,这会儿心里感到有一股勇敢的劲头!这得抓紧时间哩,要不然再过一会儿,也许主意就会动摇,一动摇,心里鼓起来的那股劲儿就会跑掉。这样想着,她便毫不犹豫地走进了牛在山的小院,毫不犹豫地走向墙角那个水泵,又毫不犹豫地把那个水泵一把抓起来,塞进了塑料袋里。在这段时间里,她的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她极力控制着,不让一丝一毫的思想钻进来。
直到回了家,把大门严严地关起来,把那个水泵卸下来藏在凉房里,常霞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她也才感觉到,脸颊热烘烘的,烧得就像要着火,两腿也哆哆嗦嗦地直想往下蹲。忽然身子一软,她就不由自主地靠着墙根溜在地上了。呀!心跳得原来也十分厉害,好像就要从嗓子里蹦出来了,怪难受的;她就蹙着眉头,拿手在脖子上用力抓挠。
这天晚上,常霞睡不着觉了,她老想这件事,心里七上八下实在不是个滋味:一会儿怨恨自己眼睛小,一会儿又嘲笑自己胆子小。她很想这时候身边能有个贴心的人,好诉说诉说此刻自己内心的感受,然后再能得到他的同情、理解和安慰,这样,一切也就能过去了。然而没有,丈夫进城打工去了,手机这会儿也老打不通;魏芳也肯定早睡下了,半夜三更怎好意思打扰人家?
苦熬苦挨到了天明,常霞真没勇气再到天天打工的那个地方去了。一旦要是让人家查出来,那可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哎呀,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不行!她得去找魏芳,魏芳和她是最贴心的朋友,她得让魏芳帮她排遣排遣心中的纠结。
到了魏芳家,一说这个情况,魏芳“呼哧”一声笑了。常霞心里一松,觉得芳姐就要对她说出一番宽心的话来了。谁知魏芳却只管对着镜子慢慢梳头,半晌没言语。常霞便只好愣愣地站在一边,但是,看魏芳脸上那一副平平静静的表情,她觉得,她的朋友肯定会认为这根本算不上一件什么事情!
然而,却见魏芳侧着脸,眼瞅着镜子,两手一面编辫子,一面笑着悠悠地说:“你个鬼!拿人家那个东西干什么呢?”
常霞一听,心里便立刻“咯噔”一下,掠过了一阵凉气,脸却热烘烘地烧起来了。她心扑通扑通跳着,难堪地笑了笑,叹了口气对魏芳说:“想的是,说不定哪时咱又把地抽回来,自己种,到时候,就用得上那么个东西啦。”
魏芳编好了辫子,回转身来,扑挲着落在身上的头发,看了看常霞说:“怎?你们还打算自己种地?”
“现在倒是没那心思,可是说不定吧……”
魏芳打断了她:“快不要动那些心思啦!以前自己没种过?为什么放下了?还不是觉得不行!现在这样就挺好嘛,你在地里打工,他在城里打工,一年不少挣吧?”
常霞点了点头。
魏芳在地上转悠着,一边做些零碎的事情,一边款款地说:“这点儿破事,那有什么呢!”
常霞心里顿时感到了一阵宽慰。
“不过,你要是心里头觉得有些不对劲,瞅个时间悄悄给他撂回去,不就行啦?”魏芳又说。
常霞的心一下子又搁了起来。
这天,常霞没去上工。她从魏芳家回来,心里更加难受了。如果说,昨天夜里,她的思想还在“这事应该还是不应该”这个问题上打圈子,那么今天听了魏芳的一番话,她觉得,这件事情她做得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水泵藏在凉房里,她简直不敢靠近一下,仿佛那里埋着一颗定时炸弹;打工的那个地方,她也不敢多去想了,那里的树木、庄稼、花草,还有那些飞来飞去的鸟雀,现在在脑子里一转出来,仿佛也全都对她抱着些敌意了。
又熬煎了一天,赶到傍晚,她打定了主意:“今天晚上,一定得把那个东西给人家送回去,要不然,我会病倒的!”
太阳落山的时候,从西边那片高高的杨树林子后面,涌起了一大片黑沉沉的乌云,闪电不时放出一道曲曲弯弯的红光,就像有人在甩着鞭子,狠狠地抽打着什么。
常霞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气,犹豫了一下,然后驮上那个水泵,骑着电动车出去了。
风刮起来了,在村街上卷起一阵阵黄尘,那些碎柴烂屑被风卷着,在空中不安地旋着圈子。四下里天色渐渐地黑了,西天的乌云漫卷过来,雷声躲在乌云后面,不时隆隆地响起,听起来让人觉得十分阴险,又十分可怕。风刮过以后,那些暂时静息下来的树木,显现着一片片黑黢黢的影子,一动不动,仿佛怀着惊恐的心情,在等待着恐怖的到来。
常霞骑着电动车,快速往前赶。在村口遇见一些人,迎头往村子里忙忙地走,看见她往出走,人们便都用奇怪的目光看她,有人大声问:“啊呀!眼看大雨就要来了,你还要到哪里去?”她含含糊糊答应一声,急急忙忙走过去了。endprint
突然,当头“咔嚓”响了一声硬雷,跟着打了一道闪,刺得人眼睛一时发花。雨点子噼里啪啦落下来了,在路面上激起一片片尘土。常霞头皮紧刷刷的,骑着电动车,身上却出了汗,眼里长久地留着刚才那道闪电刺下的影子,张大眼睛往前看,按下电门往前赶。
雨下了那么几点子,就忽地停住了,风又悠悠地刮起来,道路两边的庄稼叶子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声音,好像有许多人在轻声细语,有许多人在安慰着她:“这没什么!不要害怕!悄悄送给他不就行啦?”常霞心情放松了一些,摸黑赶到了牛在山的小院外面。
天阴得黑森森的,小院里那些房舍只能看见一个大概的轮廓,院子周围那些大树看见的也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而牛在山屋子里的那盏灯光,常霞却感到是贼亮贼亮的,亮得让人觉得刺眼。她的心又扑通扑通跳起来了。她警惕地朝左右看了看,感觉四周很安静,就把车子支在一个僻静处,把水泵从车上拿下来,放轻脚步朝大门口慢慢走去了。心跳得越来越厉害,“咚咚咚”的猛敲胸膛,常霞生怕她的心跳声让人听见,便用一只手紧紧地捂住了胸口。走到大门口,她又左右睃了睃,然后又猫腰往院子里瞅了瞅,灯光下,看见一只长着白胡子的老山羊正在院子里觅食,忽然发现了她,身子一震,蓦地抬头,跟着发出一声短促的鼻息,然后就瞪着眼睛,长时间地朝这边呆呆地瞅着。
常霞本打算把水泵放回原处去,可是进了院子,她的腿却软得怎么也迈不动了,“去他的!”她心里嘀咕了一声,便把水泵放在地上,转身快步走出来了。来到车子跟前,她蹲下身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精神也就跟着松爽了起来,从昨天以来,一直沉甸甸地压在她心口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她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活。
然而,当她站起来正准备走的时候,心里忽然又不自在起来了,一个劲地嘀咕:“哎呀不对!……不对不对!”她想,刚才那水泵放得可不是地方,倘或夜里被人发现,偷走了,那她身上的这个脏点子就永远也别想洗刷掉了!再说啦,让人家怀疑的也不只她一个人呀!成天从那院子里出出进进的,不是还有她们两个人吗?唉!——这时候,她的脑子里忽然又像裂开了一道缝儿,透进了一线光亮,让她看清了一些什么,于是,她把问题便又想到更加复杂、更加严重的方面去了。“难道让人家跟着我背黑锅?”常霞心里吃惊地想,跟着她就痛彻地感到:她在跟她心贴心的魏芳姐名下实在是犯下天大的罪过了,就连乔海云她也觉得很是有些对不起人家了!“哎呀!糊涂呀糊涂!你怎就办了这样一件臭事?让人家连个好赖人也分不清啦!”她连连拍打自己的脑袋,心里又气又急,眼里就扑簌簌地滚出了泪水。
“这该怎办呢?该怎办呢?”常霞心里又紧紧地挽起了一个疙瘩,勒得她连呼吸都感到有些困难了,她在心里这样反复地问着自己,在地上来回兜着圈子。
天上原本稀薄了的云层,这会儿又逐渐地变浓变厚了,四周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风越刮越大,周围那大片大片的庄稼的叶子“唰啦唰啦”响成了一片,仿佛有许多人在嘈杂地大声喧哗。雷又在云层后面恼怒似的震响起来了,闪电在远处近处哗哗地闪着,借着那一道道凛然的蓝光,常霞那瘦小的身影不时从旷野中闪现出来,她的脸色是苍白的,头发是凌乱的,在那对淡淡的眉毛下面,在那两只长着厚眼皮的细长的眼睛里面,此刻流露着的是焦灼而又痛苦的神情。
突然,一道强烈的灯光从那边射来,接着听见摩托车的“突突突”的声音响得越来越近了。常霞赶忙躲进旁边的庄稼地里。那个人一路骑来,嘴里还哼着山曲儿,车上驮着一把锹,随着摩托车的颠簸,不断地发出“哗啷啷”的声音。
常霞听出来了,那是张老虎,晚上给秦得义浇地来了。张老虎从常霞旁边掠过,径直朝牛在山的小院驰过去了。
常霞一个激灵,从庄稼地里倏地钻了出来。她忽然想起,张老虎可不是个好东西,看见人家的什么东西也爱,思思念念,非把那东西偷到手才歇心;村子里人们的羊,也被他偷去好几只杀的吃了。常霞紧张地想:他进了牛在山的院子,迎头还看不见那个水泵?看见了,还不顺手摸捞起来?这样想来,一霎间,事情就像真的发生在她的眼前了,画面竟是那样的鲜明而逼真。常霞着急得不行了,心里默念了一声:“不行!千万不能让他拿走!”撒开腿就往牛在山的院子里跑去。
恰在这时,头上“咔啦嚓嚓”滚过一阵巨雷,接着,冰凉冷硬的雨点子就像瓢浇似的倾泻下来了。常霞跑进院子,一眼看见那个水泵还撂在地上,就松了口气;她上前“噌”一下提起来,用手抹了一把糊住了眼睛的雨水,不顾一切地朝牛在山的小屋闯了进去。
她是带着一道蓝色的电光出现在门口的。屋里的三个人可真是被她吓坏了,他们是刚刚进来的张老虎,还有牛在山和秦得义,那两个正在喝酒,张老虎还没来得及入座。
常霞成了个落汤鸡,浑身上下雨水淋漓。她手里提着那个水泵,眼神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地看着那三个男人。眨眼的功夫,她周围的地上就滴滴答答淋湿了一圈。
秦得义和牛在山慌忙不迭地站起来了,差点儿把桌上的酒菜碰翻;张老虎正准备点一根烟,也一下子转过身来,纸烟支在嘴边,另一只手里的打火机,火苗子呼呼往上蹿,他却怔在那里。
定了定神,这三个男人才缓过气来,秦得义笑着问道:“哎呀!你这个常霞,黑天半夜的,又下着这么大的雨,你跑来这是干什么来啦?”
常霞眼睛一眨一眨的,却说不出话。
秦得义又问:“你提着个水泵,那是干什么哩?”
牛在山往前伸了伸脖子,仔细看了看那个水泵,说:“这不是我使用过的那个水泵吗?”
常霞轻咳了一下,哑着嗓子说:“是哩,这就是你那个水泵。”
牛在山笑了笑:“那你提着它干什么哩?”
“我……,我……”常霞那苍白的脸蓦地红了,她说不出话,头低下来了,身子簌簌地颤抖起来。
那三个男人互相看了看,然后又把困惑的目光一齐投向了常霞。
常霞忽然抬起头,用牙齿咬了咬嘴唇,紧紧地皱着眉头,好像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声音低沉地说:“我给你们送回来啦。”说完,就又赶忙低下了头。
秦得义看着牛在山,两人好像明白了什么,互相默默地点了点头。秦得义“呼哧”笑了,用一种非常大度的口气说:“嗨!你看你这个常霞!雨下得这么大嘛!跑什么呢!”
牛在山也笑了:“那是个坏的嘛!”
常霞又抬起了头,眼神亮亮地看着他们,声音不高,却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都应该给你送回来!收好吧!”说着把水泵轻轻放在地上,转身走出去了。
“咔啦嚓嚓!”天又爆出了一声惊雷,雨害怕似的,又加了一股猛劲,“哗哗哗”地泻得更紧了。
三个男人赶忙跑到门口,一齐向外面张望着,一声一声叫喊起来:“哎!常霞!——哎!快回来!”
常霞早已走得不见踪影了。
她跌跌滑滑,摸黑冒雨,喘息着回到电动车那里。她没有找个地方避一避,就那么直竖竖地站在雨地里,脸朝着天,闭着眼睛,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站了好久,好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