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去了哪? (中) 时光之河,溯洄从之
吕伟超
时间去了哪? (中) 时光之河,溯洄从之
吕伟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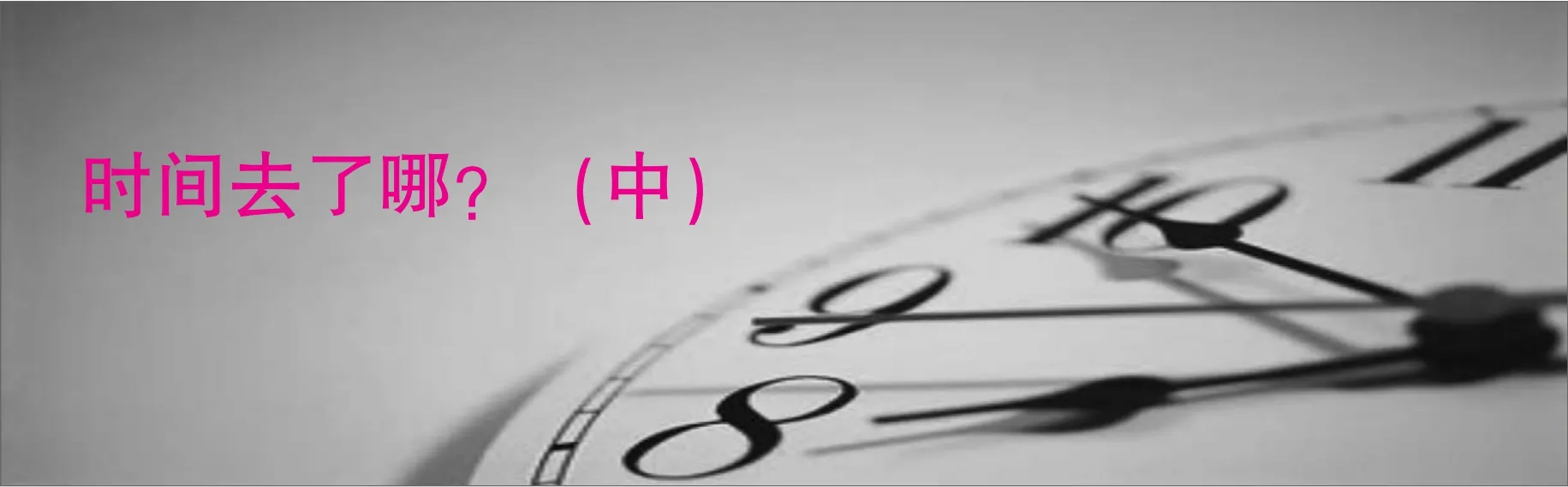
冬雪飞扬:绿肥红瘦,烟霞几瓣
冬夜,细雨无声,朔风凛凛,是要下雪了么?这样的夜,教儿子读古诗,莫若这首最好: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欢喜的,是炉火的红光,而你企盼的,是漫天的飞雪——在江南乡下,每年总会有一场,或是两场大雪,把时光“冻住”。 “冻住”时光,是在光阴之河里初游弋的少年,最笨拙也最纯真的想法。
我们谈谈雪吧。小时候,你和外婆在乡下,而我在两百里外另一座城的另一段时光里。周末,我跳上火车,在夜色里,向着你的时光穿行。金温道上的绿皮火车,古旧而舒缓,我哼着小夜曲,为远方的你催眠,这是一周里最静最慢的时光。遇到下雪天,车窗外,田畴山川,高山流水,在雪覆之下,无有声息,时光仿佛凝固在雪色里了。雪,是纯净的,它消解了尘世间的一切幻象;雪,是神秘的,一霰一天堂,它是沧海的旧时模样;雪,是温暖的,我在雪国里,驶向你甜美的梦乡。
在我小的时候,每到下雪天,母亲就会烧一道叫做 “酒糟鲫鱼”的菜。鲫鱼,是父亲从田里捉来的。在我的家乡,秋收后,要种冬小麦,油菜,但有些田里,种的却是紫云英,叫做 “绿肥田”。紫云英,可作青饲料,但主要用来 “肥田”。冬天,落了雨,绿肥田里积了水,便会冒出许多鲫鱼来。绿肥田里的鲫鱼,三指来宽,身形矫健,冰清玉洁,没有泥土味,却有花草香。父亲捉了鲫鱼,养在水缸里,等下了雪,便可以做酒糟鲫鱼了。为什么非要等到下雪天呢?现在想来,理由大概有这么几条。一是酒糟鲫鱼这道菜,做起来颇为细致,非有闲时不能为,只有在下雪天,农人们才有这份闲情。看,父亲把鱼去鳞,细细洗净,母亲从雪地里摘一把葱,拍进瘦猪肉里,再细细剁碎,填进鱼肚子里,再用新酿的红曲酒,腌上个把小时。这红曲酒,是吾乡的特产,用晚稻新米和红曲酿制,色泽红润如 “女儿”。吾乡有下雪天试新酒的习俗,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酒糟鲫鱼要等到下雪天才有的吃的另一个缘由吧。汲完新酒,鱼也腌得差不多了,母亲把铁锅烧热,淋入菜籽油,把鱼儿煎得两面微黄,再加入红曲酒酿同烧。菜籽油,这春光里收藏的金黄,等着与绿肥田里的鱼儿,在大雪天相遇,相遇在秋水酿就的 “女儿红”里,翻滚沸腾。大火使鱼汤里的酒气散尽,只剩酒香,而酒糟还保持着新米的模样,只是软糯了,胭红了黑白的鱼皮,仿佛烟霞瓣瓣。出锅前,还要加一把蒜叶,蒜叶要取肥厚者,这样才能与细长粒的酒糟,绿肥红瘦,相映成趣。云水烟霞白玉盘,窗外雪飞扬——雪花飞扬,思绪起落,我仿佛看见雪粒穿过瓦片,渗进灯火人家,在充盈满室的氤氲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唯留那绿肥红瘦的香气,在时光之河的悠远处,弥漫开来。
酒糟鲫鱼,也许只是母亲在某一个下雪天,就地取材的家常创作,然而孩子们都说好,于是,每年的下雪天,母亲便都重复着这道菜。绿肥红瘦,就这样成了雪天里,一个永远的仪式了——要问时间去哪儿了,谁知道呢,时光不能被冻住,也偷不了半日闲,时光无法重复,只值留恋徘徊了。
春梦凌乱:晴光翠暖,花压枝头

时光无法重复,天地却有轮回,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们的诗句,暂且不去管它。杜牧的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才是真真切切的江南春。如果说,雪国,适合于少年的村庄,那么春风,拂过的将是青春的城池。我的青春城池,地陷于金衢盆地的东南。那时,三五同学,最爱去城外河边,看飞花流水,仿佛自己就是一朵跳跃的浪花,满含地火的能量,要飞流直下,要一泻汪洋。要随飞花进入时空的隧道,到天尽头的某一条河边,某一座山巅,某一片云下,对着恒星,读永远的诗篇。那时的我们,躺在河边堤岸上,看堤柳如烟,芽黄鹅黄、鸭绿暗绿,浅深浓淡,撩人心意。看花满枝头,百媚淹然,游蜂浪蝶,春梦凌乱,却从来不曾注意,两岸的山石水土,竹林里,春笋拔节,延绵不绝。直至今日,青春已逝,方才明白,我们谁都不是奇花初胎,也追随不了飞花的脚步,我们不过是山中石,地上土,有的经了火,变成瓷,有的居华堂,有的贴地板,寻常也好、缭乱也罢,一齐在战栗里开放。只是当年,乱花迷人眼,五色令人盲,青春只管莺啼婉转,哪懂得一江春水,是如何温润了十里荷花、百口山塘、千亩竹林、和万顷稻田的?
年青时,时光在远方以远的任何地方,就是不在眼前。而今,故地重游,不为看烟柳,只在岸边竹林里,寻一根春笋,剥开来,烧一碗笋片雪菜片儿川。
夏日烈烈:太阳初出,只照山冈
讲到稻田,我的家乡,堪称江南边城,却是稻米之乡。春梦作罢,放了暑假,我们都要到稻田里参加 “双抢”。 “双抢”,使我第一次对时光的意义,有了真切的理解。稻谷金黄,原是从时光里抢来的,哪一年抢得多,那年就是黄金时代。

初夏的江南,梅雨隐藏了太阳的热度,稻田里一派烟雨迷蒙。等到一出了梅,太阳初出,只照山冈,可青青稻田,还是迅速地被染成金黄——镰刀 (我们称之为梳剪)已开亮,紧张的双抢开幕了。
双抢,先是抢收,割稻那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母亲已经煮好了粥,捞了饭,匆匆吃过后,趁着清晨的阴凉,赶到田里,借着晨曦的微光,挥舞 “梳剪”,七棵一行,两行一把,弯腰前行,埋头苦干。直到七八点钟,太阳渐高,露水消失后,开始打稻,打稻用稻匣,稻匣的三面要用地簟围起来,防止稻谷溅出。打稻时,放入稻匣梯,将“稻把”高高举过头顶,用力打击在稻匣梯上,如此反复多次,直到稻粒脱尽。打稻是极累的活,不一会儿,双臂就会又酸又痛。
抢收之后,紧接着是抢种,收割后的稻田里,放满水,先把一部分青稻稞用铡刀铡成三段,均匀地洒在田里,这样在拖拉机耕田时,稻稞就会被埋入泥里肥田。耕田时,大人要跟在拖拉机后面洒一遍碳铵,小孩呢,则在秧田里拔秧。这样,等到耘平了田,罩好田塍,就可以开始插秧了。插秧一般要等下午三四点钟后,太阳不那么猛烈时,才开始,这样插的秧不会 “煎叶”。插秧的区域,两边用 “种田绳”拉紧,边插边退,当然,种田高手也可以不用绳子,照样种得笔直。插秧要一直弯着腰,也是极累的,加之站在被晒得发烫的水田里,背上太阳晒,腹里热气熏,脚上蚂蝗咬,回想起来真是苦不堪言。
在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要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劳动强度之大,堪称最苦最累,但回忆起来,苦中亦有甜美——那田间地头弥漫的稻草的气味、新谷的清香、泥土和风、青草的气息,无不散发着旧时乡村之甜美。
双抢,是江南边城的子民,在浙中盆地的丘陵山水间,同时间争夺北纬29°的阳光的一场竞赛。农人把辛劳的汗水,融入到阳光的热度里,转化为碳水化合物的能量,贮藏在黄灿灿的稻谷里。
双抢,是农人们为获得更多粮食的一种笨办法。今天,人类的智巧,已使粮食变得更为易得,双抢也早已从乡村田野的天幕里淡出。割稻、插秧,那重复了无数次的弯腰方式,变成了瑜珈练习。双抢,究竟在抢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无论是先前笨笨的抢,还是今天不用再抢,也许在时光面前,一切皆无足观。
秋光澹澹:白露为霜,风轻云淡
再怎么抢,时光都将老去。白露为霜,河畔的梧桐树叶,如黄昏里的青衣,在天边云隙的流光里,婉转、留恋,最后,跌落在秋天浓重的影子里。在我的家乡,过了白露,就算是秋天了,这时候,埋藏在地下的作物,芋头、番薯都陆续成熟了。在农人眼里,这些埋在地下的食物,都是很 “补”的,他们终年劳累,很需要在秋天的时候,补上一补。他们进补的方式,自然不是服用什么膏方,只是取新芋头,持作羹,当作早饭而已。芋羹的做法很简单,头天晚上母亲先把毛竽、番薯去皮,第二天早上用一只大号的钢精锅煮粥,大火烧开,滚两三分钟后,用笊篱先把饭粒捞出来,盛进一只陶钵,埋在灶前灰膛里。而粥里只剩下少量饭粒,再把毛竽、番薯切块,青菜叶切碎,一起加进粥里,继续烧开,用文火煮透,一锅热气腾腾的竽羹就做成了。在秋天的早晨,盛起一碗竽羹,米的香味、番薯的甜味与毛竽的软糯绵滑,融和在一起,再加一勺辣椒酱,红白黄绿,五颜六色,百味柔和,一碗下肚,浑身暖洋洋,鼻尖冒细汗。
竽羹,不过是最寻常的食物,甚至有点 “瓜菜代”的嫌疑,要说怎样滋补,底气并不是很足。可我接下来要说的另一种食物,很多人相信是要赛过燕窝的,这就是我家乡的豆腐圆。
取一块老豆腐,加入细盐、味精,放在粗瓷海碗里捣烂,注意捣豆腐时要顺着一个方向,不能 “乱弹”。再取适量猪里脊肉、肥膘肉切片,用刀背捶茸,加入香茹、嫩笋尖、鲜姜切碎,混一点番薯粉,搅拌成茸泥,作馅。做豆腐圆时,把馅放在碎豆腐上,用筷子裹住,再取一只略浅的碗,加一些面粉,把包住馅料的碎豆腐放在面粉碗里,轻轻摇动。等摇成橄榄形、白白胖胖的圆子时,下到滚水里即可。豆腐圆入口腴润,柔而不腻,食后齿颊留香,暖肚暖心,说它赛过燕窝,想来并非虚言。
遥想,秋天的早晨,白露为霜,芋羹温润;秋天的黄昏,黄叶纷纷,豆腐圆腴润;秋天的天井,兰花伴着农家的烟火气息,散发着极淡极幽的香气;天上,大雁列队,越飞越远。
秋,那么高,又那么远。冷月如霜,时光明澈。
(作者单位:温州城市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