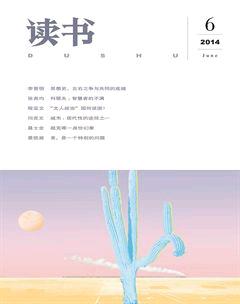新军国的旧基石
姚云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前夜,湖南人蔡锷即将就任清廷云南新军三十七协协统(旅长),在就职之前,他辑录了曾国藩、胡林翼论兵学语录数十条,分十二章,每章书写按语,分发将官,以代整训喊话之用。此时,这两位中兴名臣所缔造的湘军早已裁撤,其继承者淮军亦早已衰颓不堪,仿照西洋建制而组建的新式军队,既成为朝廷最后的精锐之师,又孕生着清廷的颠覆者们—武昌起义的始作俑者便是新军士兵,蔡锷本人亦倒向革命,成为云南革命的策划者。便是在这一时刻,蔡锷这个受训于西式军校、深受维新思潮影响的新军将领,却让手下将士重新温故“旧军队”的练兵要旨,这是何意呢?
蔡锷是这么说的:“窃意论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适于今。曾、胡二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象,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显然,蔡锷的目的就是针对当时军队的弊端,加以针砭,让新军将士领悟之后,效法古人,澡雪精神,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
这样一种返古开新的修辞在古今兵家之中并不独见,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兵法》便是其中一部代表之作。蔡锷读没读过《兵法》,现今已不可考。但是,《兵法》的开篇,便是述古,借着马基雅维里假托的主人公法部里乔的嘴巴,对古罗马的武功极尽赞美之事,并将古罗马的灭亡和当代意大利城邦的孱弱归咎于尚武精神的消退(马基雅维里:《兵法》,9页)。相对于马氏的开门见山,《曾胡治兵语录》的表述则隐晦得多,蔡锷将效法的“古人”分成“远古”和“近古”,“近古”所指明确,便是曾国藩和胡林翼两名湘军的缔造者,“远古”却语焉不详,我们不妨从蔡鹗本人的文字和他所景仰的两位先贤的抱负做派中窥见一二。
蔡锷早年写下最为掷地有声的文字,便是《军国民篇》。此文发表于一九零二年,分三期登载于梁启超所编的《新民丛报》之上。此时,清廷经历了甲午之败、庚子事变,国势微如累卵,深重的危机意识裹挟着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蔡锷将当时的中国看作病入膏肓,衰朽不堪的病人:“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而他治病的药方,便是“军国民主义”。
何为“军国民主义”?“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智识、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这也就是说,以军人的品质来引导国民的精神,以军人的标准来塑造国民的身体。可是,作为一种技术规范,军事规范有其普遍特征,但军人却来自特殊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们尽管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都必须具有勇敢果决的精神气质,但却为不同的价值理想而捉对厮杀。这种价值理想恰恰是军事规范转化为有效的文化理想和社会规范的必要中介。因此,蔡锷指出,军国民主义滥觞于西方斯巴达,十九世纪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中盛行,若要将这样一种舶来的观念引入国内,并倚仗此改塑国民本性,进而振兴故国,必须寻找到本国文化传统中与此观念相契合的那一部分。
在寻找这一契合点的时候,蔡锷遇到的困难可谓不小,从中他得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结论。他似乎认为,纵观国史,“民气最盛”,最接近其理想中“军国”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语有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僻处蛮方,文明程度远逊中原,尚终古不欲屈秦人,朔北之地,开化最先,且气候寒烈,民风之刚劲,高出南方之上,其绝不为强秦所奴隶鱼肉可知也”(《蔡锷集》,31页)。而自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军国民”气质则被渐渐磨砺殆尽,“自秦统一以后,车书混同,则国家之观念潜销已,自唐以后,乃专用募兵,民兵之义务愈薄已”。换句话说,“军国民”精神之沦落,与两大因素相关:首先,中国历史上长期维持的大一统局面,使民众淡漠了民族国家的观念,进而泯灭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意识;其次,唐朝中后期广泛采用的募兵制,使民众远离了军事生活,进一步瓦解了他们的“军国民”气质。
但是,无论是大一统的国家结构,还是募兵制,恰恰是晚清中国的客观形势和军队体制。与马基雅维里所处的时代形势不同,中国并不存在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盛行的雇佣兵制,即便是湘、淮两军和新式军队的兴起,也并未褫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因此,蔡锷并不需要提倡一种军制改革,他更希望通过对练兵思想和战术思想的改革,来塑造全新的军队气质,从而进一步熏染和改塑国家和民众的气质。
可是,战国邈远,当时民众尚武气质的获得方式已难以把握,因此,蔡锷最终找到了另一种训练民众、改造军队的手段,即中国历史上的“儒兵”传统。乍看起来,“儒”恰恰是主导数千年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观念,对泯灭先秦民众尚武锐气有着重要作用。但在蔡锷眼中,儒家传统恰恰又是中华民族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凝聚民心、组织民众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关键之处在于,在儒家传统中,找到有利于滋生“军国民”气质的涵养,而摒弃其糟粕。
对于儒家与军事的关系,《曾胡治兵语录》的一位作者—胡林翼,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读史兵略》这部文钞中,胡林翼辑录了荀子的《议兵》一篇,并写下了这样的按语:“此儒家谈兵之祖,故备录之。”(《胡林翼集》(三),118页)这一按语揭示了胡林翼的选择:寻找儒家治国之术和用兵之法的结合点,从而有效地管理和塑造一支可以戡乱救国,抵御外侮的“仁义之师”。而他所效法的前辈,不再是以行施“仁义”为第一要务的子思、孟子,亦不是后世专讲性理之学的朱熹和王阳明,而是生于战国烽火之际,以制礼作乐为强国手段的荀子。在《军国民篇》中,蔡锷虽然没有特别强调师法荀子,却也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甄别拣选,他指出,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与军国民理想不冲突的,被称为“孔派”,而与这一理想相冲突的,则是“老派”,但是,他话锋一转,立刻将“孔派”和儒家传统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夫刘、孔、韩、周、朱、程之徒,名为孔派之功臣,实为孔派之蟊贼。此种蟊贼,谓之老派可也。”(《蔡锷集》,23页)一个判断非常有趣,蔡锷一下子点了六个儒家传人的名字:刘向(刘歆)、孔颖达、韩非、周敦颐、朱熹和程颢(或程颐)。这意味着他对传承先秦儒学的两大传统,即清一代所谓的汉学和宋学,都持否定态度。由此推知,当时尚属年少气盛的蔡锷,服膺的恰恰是未被“老派”学说所混融玷污的“孔派”正宗—先秦儒家学说。当然,作为一个立志以军强国的年轻志士,儒家思想和军队建设的关系,是蔡锷首要的关切所在。endprint
那么,蔡锷和胡林翼从先秦儒家兵学中学到了什么?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议兵篇》的主旨,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荀子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孔门的军事观:“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换句话说,军事的胜利取决于民众的凝聚力,可是,若要获得民众的拥戴,军队就必须恪守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因此,荀子提出了一个军事原则:“反诈”。
这一点就与马基雅维里的《兵法》截然不同。在马基雅维里眼中,战争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因此,无论是练兵技术还是武器列阵,都是一种策略。因此,若用马基雅维里的话说,狡诈也是军事战争中的一种必要能力(virtu)。可是,荀子却认为,建设军队的核心能力并非狡诈,而是儒家伦理中的“仁”:“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显然,荀子区分了“诸侯之兵”和“王者之师”的区别,前者贪图胜利,以“权谋势利”之术为军事斗争的手段,最后导致军队中上下离心,凝聚力下降。后者以仁义为军事斗争的第一准则,虽然不一定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却取得了民众的支持,还能凝聚军队。
那么,这样一种儒家军事思想,是否仅仅是一种对军队建设的乌托邦信仰,或是一种儒者标榜的“意识形态”?从晚清两位儒学名将的军事实践来看,荀子的儒兵精神一直贯彻其中,具体到蔡锷所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中,这种精神已经转化为选材和练军的技术。
从蔡锷所选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我们发现,对于具体战略战术的选辑并不多,而对选材和练兵方法的选辑占去了十一章中的九章,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儒家道德直接成为军事纪律的来源和评价军事人才优劣的标准。
仅以前三章为例,第一章“将才”,谈的是选择统帅的标准,在本章的第一则语录中,曾国藩列举了为将者的四大标准,“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随后加以分析引申,可是到了最后,他指出,“忠义血性”是保障上述四条标准得以可能的核心选将标准:“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具至,无忠义血性者,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胡林翼则在本章的最后一则语录中,提出了将领所应具备的两种特质:“志”和“气”。显然,“忠义”是儒家认为君子应具备的两种道德品质,而“志”和“气”也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因此,曾、胡二人的选将原则显然是儒家的基本道德观。
蔡锷对这一章的按语更深入地揭示了这一标准:“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青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蔡锷集》,58页)曾胡二人的军事才能之所以被激发出来,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儒家道德修养,而不是他们天赋的军事才能。尽管在这段按语中,蔡锷以西方军事思想中的“天才论”来比拟中国儒家军事思想中的选将标准,但是,与其说曾、胡两位前辈选择的是军事上的“天才”,不如说他们选择了思想上的“圣人”—过人的道德修养加上一定的军事才能,必将使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军队统帅。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统帅,是因为蔡锷认为,曾国藩和胡林翼理想中的军队组织原则,就是儒家思想。曾国藩强调“诚”这样一种品质在军队组织中的作用,这不仅继承了荀子“反诈”的军事思想,还创造性地将一个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转化为一个军事管理的重要手段。曾国藩以《中庸》的“不诚无物”作为其立身治军的共同原则,蔡锷更是将这段语录看作《曾胡治兵语录》第四章“诚实”的开篇。值得注意之处在于,“诚实”一章并不仅仅空洞论述士大夫的修身道理,而是稍加修正,将这一道理拓展到军事管理实践之中。例如,曾国藩将虚华浮夸,言过其实之品行,称为“官气”,这恰恰是他所重视的“血性”之对立面,他指出:“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血性便少一分,军营宜用朴实少心窍之人 ,则风气易于纯正……”这也就是说,“诚”不仅是当时处于社会上层的士人君子的修养标准,还是全体士兵的精神气质。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尽管在“诚实”章的开端,蔡锷摘引了大量曾国藩对“诚”这一观念的哲学探讨,但他更多摘引的是具体军事实践中,曾国藩和胡林翼对“诚”这一观念的把握。显然,曾、胡二人把言行相符,不虚美隐恶看作军队管理中“诚”字的首要体现,例如,曾国藩说:“将领之浮华者……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搅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还指出:“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以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胡林翼更是将太平天国起义的蔓延归诸“诚”的缺少,导致下情无法上达。显然,对“浮词”的摒弃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要求,还不如说是一种军事管理要求,通过强调军事管理中的言行一致,军队领导者可以直接从下属的言辞反馈中,了解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势,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诚”是指挥官得以把握战争之真理的一种手段。其次,“诚”引申出“信”,凭借“信”,而不是“诈”,军队的秩序得以建立,胡林翼认为:“挟智术以驭人,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曾国藩更强调一种以“质直”为基础的官兵和上下级关系:“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谅其心……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诚”成为领导者组织军队,控御下级的重要手段。最后,“诚”还特指“质朴”,成为曾、胡心目中理想军队的气质标准,曾国藩认为:“军营宜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只有秉持这样的选材标准,才能获得一支作风勇猛、顽强坚韧的部队。
显然,曾、胡二人正是以“诚”这样一个高远的儒家修身理想,来锻造自己的湘军部队的。这显然和《兵法》这部对西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军事论著所倡导的治军思想有着深刻的分歧。《兵法》认为,组织军队最重要的手段并非某种修养和道德理想,而是善用策略的能力,无论是对敌人的削弱,还是对手下士兵的控制,将帅的策略和技术,也就是荀子所说的“诈”成为军队得以凝聚和建立的重要手段(马基雅维里:《兵法》,181页)。《兵法》的英译者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尼尔·伍德(Neal Wood)更建议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著作和《兵法》联系起来阅读。他指出,在《君主论》、《李维史论》这样一系列政治思想著作中,政治领袖所使用的统治策略和军事领导人的管理策略几乎无法分别。换句话说,用军事策略锻造一支军队和用政治技巧构造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回事。endprint
这由此启发了我们反观《曾胡治兵语录》的政治后果。如果说,按照尼尔·伍德的看法,马基雅维里将军事谋略施用于政治领域,我们不难发现,曾、胡两位晚清名臣在中国面临危机亟须转型的时刻,实际上将政治道德原则经由一定转化,成为一种军事组织和军事管理的手段,这不啻和少年蔡锷就试图奉行的军国理想有着不谋而合之处。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尽管马基雅维里在《兵法》中着力强调策略的作用,他所倾心的军事组织和政治共同体却和曾、胡二位晚清名臣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建立一个纪律共同体。
在西方思想史中,纪律(或称规训)作为现代西方理性社会诞生的先决条件似乎开启了一个不小的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自韦伯肇端,到福柯提出“规训社会”这一概念之后,成为人们理解现代西方的重要视角。而在《兵法》的导言中,尼尔·伍德亦提到了韦伯,在他眼里,马基雅维里对军事纪律的强调,正是现代西方社会开始纪律化的先声。相对于《兵法》与现代西方理性社会的关系,我更关心的地方在于,《曾胡治兵语录》既然同样强调纪律,对于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它有没有产生类似的“理性化”效果呢?
细读《曾胡治兵语录》,结果使人惊奇。尽管马基雅维里和中国晚清的两大名臣都强调严刑律、明赏罚,从而规范军事纪律,但马基雅维里的纪律得以保障的前提是技术。无论是将领控制下属的技术还是日常训练的技术,技术和军队管理者的修养和榜样力量无关,只和他的智能和对战争技术的掌握能力有关。尽管马基雅维里也强调军队领导者必须有勇敢、公平等道德素质,但是,这些道德素质已经完全被技术化了。例如,在马基雅维里眼中,军队领导者爱好财物无可厚非,只要不克扣军饷即可。但是,在《曾胡治兵语录》中,政治技术却被高度道德化了,在“仁爱”这一章中,曾国藩把将领与士兵的关系类比为父子关系:“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因使之扰民而坏品性,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这也就是说,军队领导者不仅有按照军事理性规范赏罚和改造士兵的义务,还有作为家长规范和引导普通士兵的德行修养,从而规范军纪的目的。按照罗尔纲的研究,这样一种军事技术的道德化,不仅有其理论倡导,更有其制度保障:湘军募兵的方式为一将募一地之兵,建制残缺之后,必须返回原地,重新募兵训练。这不仅能保证所募之兵长期跟随将领,兵将之间进而建立长期的连带关系,还能保障所募兵将的同乡、同族关系,这就自然将儒家的伦理关系移植到了军队之中。这种将道德引导关系转化为军队纪律保障的手段,与马基雅维里维持纪律的方式完全不同。前者依赖于领导者的榜样和所选择士兵的天然伦理关系,后者则凭借军事领袖的控制策略和严格的军事规范。
这种区别实际上彰显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西军事思想的差异:这种差异的背后彰显了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危机时刻,曾、胡两位晚清名臣及其后学蔡锷和马基雅维里的重要差异,后者强调技术和策略对人性无限的改造可能,前者则强调道德教养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组织纪律上的重大可能性。但是,即便是理学名臣曾国藩也看到,这种可能性并非无限,正是这一点使他看到了湘军的“暮气”,让他最终做出了裁撤湘军的决定(罗尔纲:《湘军兵志》,185—186页)。但是,曾国藩的后学们也许并没有他的审慎。蔡锷对“新军国”的展望最终落空,晚清新军迅速蜕化为各路军阀的私兵。可是,这部语录的影响却并未终结:蒋中正为这一语录补上了“治心”一章,试图以更高的道德训诫涵养自己的军队;而一九四三年《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在八路军内部的颁行,似乎暗示了蔡锷学生朱德和深受湘乡先人熏陶的毛泽东对于这部旧书的重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