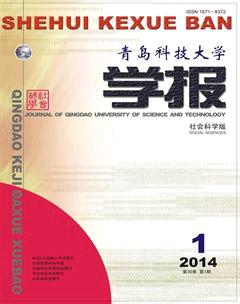乡土北京:《城南旧事》的老北京影像
张祖群 祖文静
[摘要]基于电影《城南旧事》和小说《城南旧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分析老北京影像。老北京的人情味和空院子、老巷子、旧房子、小园子等文化元素都是1920年代帝都北京的真实记录。林海音的怀乡文学以“女性”主义的视角书写,从儿童的眼睛观察成人世界,打开了一扇“真实”世界的窗口。《城南旧事》小中见大,书写“大时代”的“小人物”返乡故事,折射了中国大陆巨变时代的政治风云。作者以自身人生时空变迁对北京古城进行想象性的文学描摹和文化景观的地理投射,影视叙述文本被重构为一个遥远的可望不可即的“乡土梦”。
[关键词]《城南旧事》;老北京;文化元素;儿童的眼睛;怀乡文学
[中图分类号]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1-0088-06
一、电影和小说的同异
(一)电影和小说的相同点
第一,叙述视角相同。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城南旧事》均采用第_人称的叙述视角,始终以“我(即小英子)”的眼睛来看待、感受和理解这个世界。小说叙述中第一人称具有极深意味,这种叙述涉及个^经验的自我。第一人称叙述既可以作为叙述“自我”之后的重新认识与理解,也可以通过“自我”经验以更为有限的眼光叙述出来。电影《城南旧事》的观众首先回忆起的是那个浓眉大眼、清纯可爱的小英子。影片以小英子的眼睛为视角,以散文式的笔调勾勒1920年代老北京的人情世故与市井图像,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和无限想象,以儿童视角和女性视角体现“被女儿情结滋养”和“富有悲剧意蕴”的乡愁。电影从头到尾以主人公小英子的视角作为叙述视角,涉及英子的2/5主观镜头全部采用较低角度拍摄,从内容上基本做到凡是英子听不到、看不见的都不在银幕上出现。
第二,叙述结构相仿。小说的名字很有诗意,情节也富有诗意,改编的电影让人过目不忘。小说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没有花花绿绿的俊男靓女,却轻易地走进了观众内心,又轻易地留在了观众心里。全片以朴实的画面造型、精细的艺术构思、浓郁的地方特色,塑造了1920年代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为观众展开了一幅灵动的民国生活图景,朴实无华,寓于诗意,淡雅隽永,触碰心灵,回味无穷。影片如水墨画似的场景牵动着观众的心,何时离人断肠碎?透过主人公零散混乱的生活,剪不断理还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无论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在叙述结构与模式上都采用李显杰先生概括的“缀合式团块结构”。整体上,《城南旧事》并无统一连贯的中心情节,只是由几个相互间并无因果和直接联系的故事片段连缀串珠,穿线人就是小主人公小英子。看似零碎的故事片段都是“我”的所见所闻、生活体验和回忆。在电影中设置同样的叙述架构,没了承上启下,前后相连,时间分成一段一段,情节刻意淡化,反而使叙述显得更加诗意。
第三,叙事手法和抒情方式相同。小说版《城南旧事》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读者读文字如同观看电影,不自觉地沉浸其中,深受感染。小说中散文式的语言典雅柔美,散发着浓郁的乡愁气息,在平淡叙述中点滴呈现的场景描摹、人物刻画,都透着清新淡雅、诗词韵味、古老沧桑、逝水流年。不至于引人痛苦,却又禁不住要静静落泪,浸润“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电影版《城南旧事》从“建国十七年文学”窠臼中走出,用散文诗的笔法书写乡愁和人性,并发扬“中国诗电影”的传统,呈现海派艺术聚焦北京古都的独特艺术神韵。影视主题音乐充满表现力与张力,不仅丰富了影视的内在表达形式和内容,也借由影视内容展示出音乐的完美。影视主题音乐已然成为影视艺术语言的一种特殊载体。吴贻弓导演和原作者林海音一样,十分注重对情境的刻画和情绪的营造,于是在影片中便出现了大量的空镜头、长镜头和缓慢的摇移镜头,并配以带着伤感的《送别》音乐和略带沧桑的女生旁白,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和氛围。导演运笔侧纵,用白描的手法为观众娓娓道来。电影《城南旧事》将“留白”(空镜头+静默手法+散文化叙事结构)运用得淋漓尽致,体现了虚与实、静与动、情与景的对立统一。“留白”塑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与诗意风格,成就了整部影片的意境。
第四,都表现了成长主题。成长是人生的必然阶段,是一个个体在精神与心理层面上经过生活的历练日趋成熟的过程。任何关于成长的影像叙事都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城南旧事》关注女性成长,以温情的叙事手法通过对好的童年生活、友谊中成长、创伤里感受和女性自我成长等个人体验的真实描述展示了英子周边人物的遭遇图谱。不悲怆也不凄凉,充满了诗意的显著特征。《城南旧事》作为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代表作,描绘了小英子在爱与离别中,从懵懂纯真的儿童成长为早熟多思的少年的人生历程,让读者透过无可奈何的淡淡忧伤,感受到一种勇气与承担,《城南旧事》是一曲赞美成长的赞歌。
第五,都体现了相同的时空背景。小说《城南旧事》的背景是1923—1929年的北平,电影是根据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背景也设定在动荡、变革年代里的北京城。它的英文名更让人觉得与电影内容相符:My Memories of Old Beiiing,直译就是“我的老北京记忆”。这部在1982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的《城南旧事》营造了一种浓郁的京味气氛,影片里描述的北京城乡习俗、杂粮面食制作、民间谚语传说、土语方言、胡同街坊、趣闻轶事,是老北京的立体图像。小说《城南旧事》以自传体“回溯性”的叙述手法遣忆童年往事。电影《城南旧事》忠实于原著散文诗般的特点,继承原作中的儿童视角来叙述故事,用孩子的童瞳来观察和透视成人世界难以体察的生存状态。通过深邃、富有诗意的意境来表现艰难曲折的人生、多灾多难的命运和深深的离愁别恨,揭示出当时贫病的社会现实。两个版本的《城南旧事》都是将北京设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南,这一点不仅在小说或者是电影中都有明确表述,而且单从它们各自的景物、场景和人物描写中,也能很轻易地看出来。
(二)电影和小说的不同点
在小说和电影的比较视野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仍然存在差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是神来之笔。endprint
第一,情节的删减和人物设置的变化。小说《城南旧事》包括五个中短篇小说,分别为“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但电影在对其进行再创作时,完全删去了“兰姨娘”这一篇,同时将“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这一篇简化处理,作为了影片的结尾。这样,整部电影实际上只有原作的三篇故事,人物设置也就同样限定在了这三篇的范围之中。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加入了电影主创人员自身的理解,受电影时间长度、剪辑、篇幅的限制,自然不能完全将小说内容搬上银幕。
第二,电影中的人物性格更趋单一和理想化。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着复杂的性格和形象,比如爸爸曾在日本喝花酒、在北京的家中抽大烟、与兰姨娘眉来眼去。但是电影中删去了这些人物的立体型风格与复杂特性,人物性格更趋单一。比如,电影中的爸爸近乎完美的慈父形象,他不仅与妈妈十分恩爱,对英子十分疼爱,而且乐于助人,暗中帮助进步青年,最终不幸英年早逝。没了小说中旧式文人的行事和作风,更少了“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风流倜傥。正是因为这样,丑恶的一面被隐去或者冲淡,美好的东西被放大,整部电影才显得更加温情脉脉,引人无限怅惘。
1980年代以前,人们不能接受电影形象中正面人物有任何的“不好”,于是就有了1982年电影《城南旧事》的大规模删节小说情节,主要人物脸谱化,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泾渭分明。今天随着影视欣赏观念的变化,是忠实于原小说还是提取主线后再现核心人物、核心事件,观众和读者各有所钟(见表1)。笔者认为,只要是不偏离现实,以原定小说为主体进行限量删减或想象性增补,都是可取的。
第三,小说发生地与电影拍摄地的分异。《城南旧事》反映老北京故事。如果不知道这部影片背后的故事,一定还会以为拍摄地点理所当然是北京。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为了找到林海音笔下真实的老北京,吴贻弓攥着北京地图,带着一班人马穿梭于北京胡同小巷,从城南走到城北,从城东走到城西,没有找到“理想”的北京。虽有几处尚保留着老北京风貌的胡同,只可惜那黑黑的柏油马路、高高的电线杆将独有的历史静谧感给破坏了。他们带着无奈与失望回到上海“另起炉灶”,在上海寻找“老北京”。在上海郊区一个刚刚搭建的空旷机场,他们在屋檐上种上几撮随风摇曳的野草,将落寞院子里风吹雨打的树桩以假树桩代替,以假乱真,林海音笔下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才算是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上海。
二、电影中的老北京影像
(一)老北京的人情味
林海音在小说《冬阳·童年·骆驼队》里写到一个细节:“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铃声,童年重临于我心头。”电影开头出现了残旧的长城,骆驼队从卢沟桥上走过,驼铃声声。在温柔的、略带岁月痕迹的女声画外音的诉说中古老的城楼显现,《送别》音乐响起。
影片中古老的水井,古老的石质水槽,以及在胡同间安然穿过的骆驼队展现出了老北京气息。小孩子不用天天上课,可以像英子一样,在街上学着骆驼反刍,很自信地告诉爸爸说骆驼挂铃铛是为了给自己的漫漫长途解闷儿。影片中的老北京民居并不是象征性保护的四合院,而是很普通的院落,院子门口坐着两只石狮子或是石鼓一样的门墩;没有高大铺张的双开木门,门上早先刷的漆早已被岁月和风雨剥落,青灰的砖墙也已经斑驳,却有着一股别样的悠长韵味。
英子随着宋妈去买菜,在街上遇着一队拉着人去法场的队伍。被押着的汉子站在车上,一点儿也不怯懦,甚至让路边看热闹的百姓给他叫一声好。在一片应声而起的叫好声中,有人给汉子送上酒来,汉子一饮而尽。这样的豪迈,这样的陌生人之间的理解,透着浓浓的老北京的人文情怀。
有着东西跨院儿的老院落,圆圆的月亮门儿,满院子可见的树木花草,木窗和破碎的窗纸,木桶、木盆、木桌椅;指甲草和着白矾染成的红指甲,满地乱跑的小鸡,趴在门前吐着舌头的大黄狗,说着家长里短儿的大妈大娘;煤油灯摇曳的灯光中,飘动着的人情,应和着人物的悲惨命运。
从这些影像中不难看出,电影中满是老北京的文化元素,是现代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追忆:残旧的未经旅游开发的长城,像普通石桥一样供行人走过的卢沟桥,高大巍峨的城楼,普通两进的四合院,门前牌坊和石墩子,斑驳双开木门,悠长的胡同和青砖城墙,自自然然,落落大方,不加任何刻意的修饰和雕琢。一院子的花草树木,破旧的院子和蔓蔓野草,又或是胡同口汲水喂骆驼的生活景象,剃头挑子上的嗡嗡声,都是再难重现的老北京景物。邻里之间互相关心和帮助,小孩子之间友爱,这些自不必说,就连陌生人之间,例如那被押赴刑场的大汉和围观群众,也有一种似乎是生来就有的信任和默契,这就是久违的老北京的人情。尽管北京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却无法“消灭”空间,老北京的文化元素从实体空间跃迁到影视、媒体文化符号,乃至折射到受众心里,带来了人们对乡土北京文化的重新审思和文化自觉。
(二)老北京的文化元素
《城南旧事》作为一部成功的散文式电影,得到电影人和广大观众的普遍好评,体现了“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总基调,讲述三个故事片段,体现了主题、散文化风格、选景之美。整部片子始终沉浸在一种淡淡哀愁中。或许这就是一种怀旧哀愁吧,怀念那时的人,那时的事儿。当我们脱离电影情节,从那种感时伤人的情绪中慢慢抽离出来之后,那时的人和事儿,都值得今天细细思量,包括那些代表着老北京的京味儿元素的过去与现在。
第一,空院子。电影里表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还有荒芜的空园子留给孩子们踢球,那时这样的院子不少。而1982年拍电影时,偌大的北京城已经找不到荒芜的空院子留给剧组拍摄。
现在整个北京城大开发大发展大建设,一路高歌向世界城市迈进,别说那奢侈的空院子,就算古老普通、保存相对完好的有原住民的院落,也难得一见了0四合院在辽代已初具规模,经金、元至明、清,逐渐完善,成为了今天京味文化的符号。但是砖木结构的民居毕竟不能长久保存下来,现今的四合院,最远也不过是明清,大多建于民国。近百年来侵略、内乱、拆旧建新,我们推倒了一个旧世界,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例如“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大肆毁坏四合院堂屋内供奉的精美佛龛,削掉影壁上精致的砖雕,有些院子门前象征武力和权势的旗杆也被砍下来烧掉;1980年代的“建设性破坏”,拆掉许多老建筑来为新楼新院挪空间,对四合院造成了持续性且无法恢复的破坏。“当年的四合院外是‘凹形的穿廊虎抱,可现在为了拓展室内空间,早已将外面抹成了一个平面;昔日‘大宅门的恢弘气势在现代二层楼房的突兀中荡然无存;就连院子中央以养情的花坛鱼缸也被一排排的小房子取而代之。”熙熙攘攘,杂乱无章,原来的古色古香被一座座高楼大厦代替。endprint
多少个院落已经颓废,多少个院落已经风华不再,多少个院落曾经的流光溢彩掩蔽在由不同的年份、四下搭盖了的小房、厨房、接出的廊子后面。岁月不再,风华不再,但感情却怎能轻易流走。更何况,它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太久的岁月、太多割舍不了的情感。四合院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面目全非,甚至烟消云散,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纸上和图像里寻找《城南旧事》的文化符号。
第二,老巷子。影片中有一个地名出现了好几次,叫“齐化门儿”,就是现在的朝阳门。旧时的朝阳门曾是一个汇聚了山南海北的人的地方。在这儿“贴墙根儿”、玩蛐蛐儿、推铁环、逮“老琉璃”、窜房檐、放鸽子……每逢喜庆日子,“齐化门文场”就会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场面特别热闹,欢声笑语不断。只是小桂子被遗弃的“齐化门”,那个每个人都可以在城根下生活得活色生香的老朝阳门,现在早已不见踪迹。清代《乾隆京城全图》标有胡同1400多条,民国年间有街巷3200多条,1986年北京四个城区有街巷3665条。2007年曾有调查数据显示,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约50条的速度减少。从解放初的3200多条到1990年只剩下2200多条,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10余年间,又消失掉了800多条。北京胡同存量资源,已到危亡时刻。胡同是“老北京”的特色与灵魂,也是“新北京”的典型符号。没有了胡同,北京也就没有灵魂了。缺少了这种最有象征力、感染力的文化实体,缺少了这种最有亲民性的底层文化载体,也就缺少了“五都时代”以来北京铸就的文化内核。
第三,旧房子,小园子。除了空院子、老巷子,老北京的传统元素还有很多,比如旧房子、小园子,还有那些鲜有留存的古井、寺庙和老牌坊。这些传统的京味儿元素,如今不仅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光彩,甚至许多都已湮没无存了。所以这些电影景物的再现,不仅勾起旅居海外或者是滞留海峡另一岸游子的思乡之情和抹不去的乡愁,更勾起了那些对“老北京”有着深深记忆和永恒怀念的人们的浓浓哀愁。
三、无言的尾声
在英子病愈回家的路上,英子的爸爸对她说:“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慢慢就会忘记的。”在整部影片中,有许多人最后离开了小英子,有许多愉快的经历变为往事。秀贞和妞儿走了,偷儿被抓了,宋妈哭着回家了,到最后父亲的生命之花也凋谢了,可以说真正是“知交半零落,骨肉两分离”。随着这些人和事的离去,小英子的童年也逐渐逝去,天真不再,童心已泯。那个不得不离开、从小居住的城南再难回去了,一种感伤怀旧的情绪油然而生,在电影的画面之间弥漫开来。
1948年是多事之秋,轰鸣的飞机低徊于古城北平的上空作告别的盘旋,林英子随着亲人离别北京去了台湾。她幼小的心灵向千年古都投下了刻骨铭心的最后一瞥。她隐隐地懂得她年轻的生命里,有着一些什么像那逝去的流水一样永远地失落了。她所做的只有默默地怀想,而就在她阖上眼帘的一刹那,冬日暖阳下摇曳着铃声的骆驼队、小胡同里井窝旁嬉笑的玩伴、倚着门框招手的大辫子姑娘,还有那蹲在草丛里的小偷、斜着嘴笑的兰姨娘……一—重现。影片结尾是小英子和母亲、弟弟坐着洋车离去的身影,根据小说作者1948年离京赴台的经历,隐喻着他们一家人离开北京回到台湾。英子一家本来就是从台湾来到北京的,这次的离京赴台可以说是回到久违的家乡。但北京才是她骨子里从小认定的故乡,虽远在孤岛,却心在北京,形成她挥之不去的地方依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台湾女作家的怀乡文学以“女性”主义书写为特色。她们以“琐碎+真实”的故乡日常生活为题材,从国家宏大叙事走向女性视角的生存困境与婚姻悲剧,淡化“家国神话”,凸显个人自传色彩,书写另外一只眼睛里的台湾乡土世界。这种淡化“家国神话”与时代风云的文化构建,展现了大历史背景之下女性的小人物独特视角。以表2所举的三部作品为例分析,三者的相同点在于:1.童年视角。从儿童的眼睛观察成人世界,打开一扇真实世界的窗口。2.个人经历视角。作品都来自作者的真实经历和心路历程,具有女作家强烈的自传色彩,特别是聂华苓为《失去的金铃子》女主人公直接取名“苓子”,说明她在写作时实际上就是在写自己。在作品中可以找到作者的生命轨迹和影子。3.女性视角。要承认男人的眼光与女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三部作品中所有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细节都经过女性的心灵裁悟。
文学从来都是对现实的嘲讽和曲折反射,教会人在内心反省。如果一定要界定文学和旅行两个领域的关系,可以这么认为,文学是一场没有终点、没有疆域的“旅行”,作家是双足宛若鲜花的精神流浪者,“研究”文学的人是用爱与智慧去追踪流浪者足迹与精神流浪者同舞的人。而阅读文学的人则是一群同情、呐喊、哭泣、悲悯于精神流浪的观众,他们时常在“观看”中浮想联翩,迷失自己。文学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跌倒的人再次爬起,使受胯下凌辱之人找回做人的尊严,使悲伤忧郁之人得到心灵安慰,使沮丧沉沦之人恢复勇气和信心。诚然,“大时代”的“小人物”返乡故事,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在中美关系恶化或很不稳定的情况下,1954—1955年、1958年、1995—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三次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以应对与还击美国的政策,体现了追求国家最终统一的过程、行动与决心。无论是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还是两岸之间的攻守力量对比,“时间”的筹码都不在台湾一边,而在大陆这一边,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规律,任何人、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统一的潮流。海峡两岸分离60多年,文化鸿沟如何消除?
正如英子的爸爸所说,有些东西是需要被忘记的。但是那些关于老北京城的美好故事,那些在老北京城中的美好的人、事、物,是无论何时都不能被忘记的。北京在林海音的叙述文本中被构型为一个遥远的可望不可即的“乡土梦”,这是作者自己人生时空变迁对北京想象的投射。写到这里,笔者不免感叹,已经逝去的无法追回,已经毁坏的再难修复,衷心地希望现代的每个人都停下破坏古老的脚步,留住那些古老的文化元素,留住那些胡同、四合院、老房子和老院墙,留住那些寺庙、园子、牌坊和水井,留住那些弥足珍贵又不可复制的财富和美好。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还能再见到那个老庭院和旧街巷依旧鲜活,到处能听到儿歌和童谣的老北京。
责任编辑 王艳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