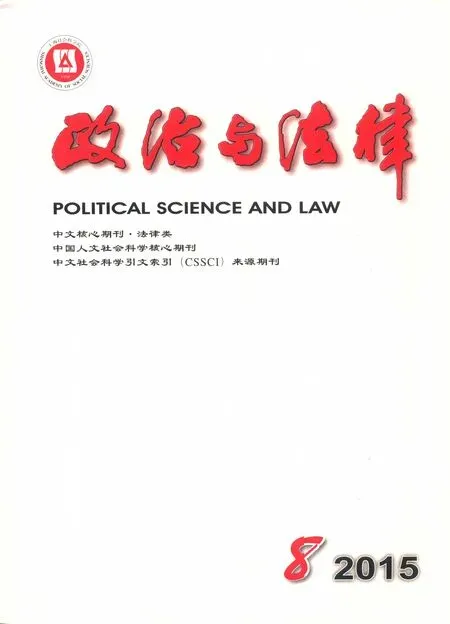论举轻以明重在行政处罚中的应用*
柳砚涛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论举轻以明重在行政处罚中的应用*
柳砚涛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举轻以明重意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依据“以小推大”的逻辑,对在违法性、社会危害性比法定当罚行为更重的待决行为进行处罚。其主要功能有二:一则弥补“开放的处罚漏洞”,防止某些更重的违法行为因法律文义狭窄而逃脱处罚;二则弥补“隐藏的处罚漏洞”,为当罚行为兜底条款的解释和延伸设定理性标准。尽管“法无明文”,但因属于同一违法类型内的类推、有默示规范为依据、结论具有可预测性等,其并不违背处罚法定原则;尽管“结果不利”,但因具有优先适用性和法意保护功能,其并不违背“有利归于个人”原则。为确保行政处罚理论的先进性与规范的包容性,须将举轻以明重融入当罚性评判标准,并遵循对象同质性、梯度明显性、立法目的符合性和说明理由等规则。
举轻以明重;处罚法定;有利归于个人;类推;弥补处罚漏洞;裁量基准
一、问题的提出
事例一: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2条和第67条等条文已把“酒驾”、“醉驾”和“毒驾”纳入处罚范围,但对“药驾”的处罚仍属法律空白。①这里所说的“药”指的是感冒药、止疼药等非受国家管制的常用药,非《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所规定的“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者实质上属于“毒驾”的范围。
传统理论认为,处罚法定寓意“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据此,在立法机关对“药驾”的当罚性作出明文规定之前,不能施以处罚。但从药理学角度看,有些药物服用后会导致视力、听力减退、注意力分散,甚至不能正确分辨交通标志,极易导致判断失误、酿成惨剧,因而“药驾”对交通秩序及公共安全的危险性、危害性甚于“酒驾”和“毒驾”,更应受到法律制裁。那么,能否引入举轻以明重原理,依据“酒驾”、“醉驾”、“毒驾”的处罚规定对“药驾”进行处罚呢?
事例二:2006年1月至11月间,周某明利用在短时间内“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的手段操纵“大同煤业”等15只股票价格,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2007年12月17日,中国证监会以《证券法》第77条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为依据,对其进行处罚。②参见“周建明操纵市场案”,http://www.cs.com.cn/rx/03/200903/t20090311_1785801.htm,2015年3月24日访问。
因“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不在《证券法》第77条明文列举的“联合买卖”或“连续买卖”、“相对委托”以及“洗售”三类当罚行为之列,按当下通说,若证监会仅依据笼统的兜底条款作出处罚,会违背处罚法定原则之明确性要求。但是,该行为不需投入任何真金白银,弹指之间就能操纵股票价格,时间短、风险小、收益大,对证券市场秩序及股民财产安全的危害性甚于“示例性列举”的当罚行为。那么,在缺少针对兜底条款的立法解释的情况下,执法人员能否应用举轻以明重原理直接依据兜底条款作出处罚呢?
上述两个事例共同指向一个命题:执法机关能否在缺乏针对性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情况下,应用举轻以明重原理判断行为的当罚性。该命题的研究价值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治时代是一个讲究理性与逻辑、重视法律方法的时代,“从法哲学、法学理论和法社会学发展一般的注释理论从而为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提供方法”,③[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2页。已经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同时,随着实质法治理念不断拓展,以“理念法”为代表的不成文法源在行政法领域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将兼具法律方法与“理念法”性质的举轻以明重作为处罚法定原则的必要补充,在实践层面便于确保当罚标准的适度开放性和包容性,在理论层面有利于以法律方法来“激活”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第二,行政实践中确有不少与前述事例相类似的理论问题急需学界解答:受制于处罚法定原则,面对违法性、危害性更重,但法无明文规定当罚的行为,执法人员是否只能感叹行为人的“幸运”和“条文法”的无奈而无所作为?法律解释机关“延展”当罚行为的兜底条款应遵循何种理性标准?如何确保兜底条款的“延展”行为与“示例性列举”相一致?针对新型案件,执法人员可否直接“举轻以明重”,而无需等待立法或法律解释?
第三,举轻以明重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中已有相应角色定位,④民法中的主要论述可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357页;王泽鉴:《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梁慧星:《论法律解释方法》,《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刑法中的主要论述可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中的当然解释》,《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6页;欧阳竹筠、杨方泉:《刑法当然解释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3期。行政法理论对此尚无只言片语,实践层面也少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个案,面对其在行政处分、处罚、救助、奖励等广泛的适用空间,我们不能不感叹当下行政法学者理论与制度体系的滞后。
据此,笔者试图将举轻以明重原理引入行政处罚,旨在解决法无明文及兜底条款情况下违法行为的当罚性问题。
二、必要性及应用场合分析
举轻以明重意指在法无明文规定但待决行为比法定当罚行为的违法性、危害性更重时,依据“以小推大”的逻辑对待决行为进行处罚。该原理最初作为刑法“入罪”的条件,早在虞舜时代就有记载,《尚书·舜点》载明:“宥过无大,刑故无小。”⑤该句话的含义是“不罚取法重的明文,处罚取法轻的明文”。参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及至唐代,该原理得以发扬光大,《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刑部郎中》规定:“若正条不见者,其可出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可入者,则举轻以明重。”⑥《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刑部郎中》总第107条。在《唐律疏议》中也有多处记载,如《名例律·断罪无正条》总第50条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⑦《唐律疏义》卷六《名例律·断罪无正条》总第50条。该条疏议对“已杀”、“已伤”期亲尊长等是否当斩问题规定:“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⑧《唐律疏义》卷六《名例律·断罪无正条》总第50条疏议。《名例律·十恶》总第6条疏议对子孙“厌魅”父祖是否属十恶之罪的问题规定:“厌、诅虽复同文,理乃诅轻厌重。”“然祝诅是轻,尚入‘不孝’;明知厌魅是重,理入此条。”⑨《唐律疏议》卷二《名例律·十恶》总第6条疏议。
举轻以明重的价值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泯灭,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该原理对于处理“法无明文”的疑难案件和兜底规定的阐释仍具重要的法律价值。⑩在民事审判中适用最多,如在“董明平、张光清与朱纯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中,法院明确指出,根据举轻以明重,法律规定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以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出质”的行为无效,则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转让”其出资份额的行为更无效。参见安徽省宣城市中级法院(2014)宣中民二终字第00051号判决书。
(一)顺应“条文法”向“理念法”转变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人民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定和维护法律规定的严肃性,确保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统一性和连续性”,又要“避免刻板僵化的理解和适用法律条文”。无论执法抑或司法,均不能机械地执行法律条文,而应透过条文的字里行间探寻和执行法的精神、理念、价值、目的,使机械的法律条文在法律方法的冲击与调和下真正演变成“活的法”,使法的“明文”不仅视为“法”,更应成为“法源”。相应地,执法、司法人员亦不再是“一个把既定的法律条文安放在一定的案件事实上的机械工具”,⑪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页。而是变成一个以全面法律知识和良好法律素养为基础的法的精神、理念与理性的领悟者和实践者。以曾一度引起社会轰动的“闯黄灯被罚”案为例,法院根据“黄灯亮时,车辆已经通过停车线的可以继续通行”的法律规定,应用法律目的、反向推论、利益衡量等“理念法”,得出“黄灯亮时,车辆还没越过停车线的不能继续通行”的结论,使闯黄灯这种危险驾驶行为得以处罚,并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⑫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嘉行终字第15号判决书。
将举轻以明重原理引入行政处罚,是“盘活”机械、有限的“条文法”,应对“理念法”转向的必要举措,这主要体现在举轻以明重的两种存在样态上。
第一,从静态上看,举轻以明重是一种共识性的法理,符合事物本质或普遍的正义观念,具有“理念法”的普适性、客观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当属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将其以法源的形式引入行政处罚,能在“条文法”之外为执法或司法提供一种可资利用的规范依据,以增强处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诚如学者所言:“当正式渊源完全不能为案件的解决提供审判规则时,依赖非正式渊源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一种强制性的途径。”⑬[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页。
第二,从动态上看,举轻以明重是在规范与事实之间找寻实质契合性的法律适用方法,从立法本意或实质精神方面来解读法律规范,运用“合法性”而非“合法律性”的思维来审视待决事实,⑭这里的“合法性”强调公权力的行使要受具有普遍共识的法治精神、原则、理念和要求的约束,是一种经验主义倾向;“合法律性”强调公权力的行使要符合既定的法律规范本身,是一种规范主义倾向。参见韩春晖:《论法治思维》,《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笔者认为,作为“合法性”基准的还应包括法的价值、目的、原理、方法、规则等。以“轻重相举”的当然之理在待决事实与规范条文之间架起桥梁,最终求得处罚结果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这完全符合“理念法”的规制方式和价值目标。
(二)推动立法性解释向具体适用解释转变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进行理解、阐释和适用的能动整合过程,必须遵循亲临性原则,只有将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的处理相结合,才能保证过程的有序性和结论的正当性。我国当下行政法解释是一种立法性解释,无论是行政解释还是司法解释,主要由有解释权的机关发布统一的解释文件或政策,执法人员或法官无权具体解释法律。这种“适用者不解释,解释者不适用”的模式无法保证解释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及时性,进而使法律对实践的指导、监督或矫正功能大打折扣。
举轻以明重是打破行政法解释“立法性垄断”的依据和方法。在“法无明文”时,只要待决事项与法定事项呈现轻重相举关系,具体执法人员就有权依据举轻以明重直接实施处罚而无需等待有权机关的立法解释。这实质上是对具体执法人员法律解释权的承认,使行政法适用权与解释权有效对接,增加执法过程的能动性和灵活性。
(三)弥补“开放的处罚漏洞”,提高处罚应对性
“条文法”的有限性和僵化性弊端以及对处罚法定的机械性、偏执性理解会导致“开放的处罚漏洞”,致使一些违法性、危害性更严重的行为因“法无明文”而逃脱处罚。
“运用法律的价值推导工具,可以在法律对具体案件未规定或无明文规定,以及实在法明确规定或规则不能涵盖具体案件,存在法律‘缺乏’或‘漏洞’时,消除其‘缺乏’或‘漏洞’,为具体案件建立起裁判大前提。”⑮王洪:《司法判决与法律推理》,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作为一种价值推导工具,举轻以明重能弥补法律缺位,克服“处罚不能”的现实困境。如在英国有这样一则案例:根据英国1920年《官方秘密法》第三节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军事“禁区附近”从事阻碍公务人员维护国家安全的活动。在阿德勒诉乔治案中,乔治因在“禁区内”(皇家空军基地)参加抗议活动阻碍哨兵值勤,而被治安法官依据上述规定认定其应被罚。⑯Adler v.George,[1964]2 Q.B.7.“禁区附近”的字面含义仅指“禁区外围”,不包括“禁区内”,但“禁区内”较之于“禁区附近”的活动在危害性、违法性等方面更重,更能阻碍国家公务,如不对其处罚,会影响法律的平等性、权威性和正义维系功能。
我国当下行政处罚实践急需引入举轻以明重来解决类似问题,有案为证:2006年证监会以未及时披露公司的诉讼和仲裁事项为由,根据2004年修正的《证券法》第177条对深圳和光商务公司作出处罚,但这里的未披露事项属于“上市公司”应披露的“持续信息”,非本条规定的“发行人”应披露的“发行信息”,⑰对于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公司而言,因在证券发行阶段,公司还未正式成立,更未上市,故“发行人”不能包含“上市公司”。正基于此,2005年修订的我国《证券法》第193条对该罚则条款进行修改,在“发行人”后单独增加了“上市公司”,但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只能适用修订前的我国《证券法》。按处罚法定原则,证监会不能援引本法条对“上市公司”进行处罚。⑱参见刘井玉:《隐性法律规范冲突的解决》,《人民司法》2009年第10期。举轻以明重有助于摆脱该案中处罚“对象不能”的窘境,因有资格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的影响力远大于还处于募集设立阶段的“发行人”,前者不遵守披露义务对证券市场秩序造成的破坏甚于后者。加之,“持续信息”较之于“发行信息”,直接关乎股东的利益,更需要被披露和监督,既然第177条规定证券“发行人”当罚,则“上市公司”更应受罚。
(四)弥补“隐藏的处罚漏洞”,克服处罚随意性
为确保处罚条款的周延性和灵活性,法律常以“等”或“其他”等词语来“延展”、“衍生”当罚行为,但这些词语在词义上的概括性和模糊性会使一些立法原意并不涵盖的行为被纳入当罚范围,如果没有理性标准加以约束,执法人员就会藉此扩张处罚权,导致“隐藏的处罚漏洞”。例如,已废止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2款笼统地将“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交由“省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国家法规和政策认定”,这就等于给解释机关一个“空白授权”,难以确保由兜底条款“延展”、“衍生”的行为与“示例性列举”行为在当罚标准上保持一致,公民也会因兜底条款解释的随意性而时刻面临“动辄受罚”的风险。
举轻以明重可为兜底条款的“延展”范围“立界”,其以示例性列举之“轻”,明兜底内容之“重”,“当且仅当”待决行为重于“示例性列举”行为时,执法人员才有权直接依据兜底条款施以处罚,进而防范行政机关巧借字义的宽泛性滥施处罚。例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第4条第2款的规定,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应一次记二分。如果驾驶员在驱车过程中“利用手持电话玩游戏”,这更能分散驾驶员精力和妨碍安全驾驶,交管部门完全可以依据举轻以明重将该行为“装入”“等”字兜底条款内进行处罚。
(五)迎合多种行政处罚实践场合的需求
除作为当罚性判定标准外,举轻以明重在行政处罚的其他场合也有应用价值。
第一,在处罚适用规则层面,当待决行为是否属于法定从重情节缺乏明文规定时,可依据“‘轻行为’尚属从重、‘重行为’更当从重”的逻辑,对待决的重行为从重处罚。这一点对我国《行政处罚法》显得尤为必要,因为该法只规定了“不予处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刑折抵”等适用规则,缺少“从重处罚”规定,当下执法实践中对“从重”的理解或者基于一般法理或者基于行政机关的自律规则。对此,举轻以明重可以“补缺”和“助成”:凡是其他具体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从重情形的,重于该情形的违法行为均应受到从重处罚。
第二,在程序选择方面,当处罚是否必须履行某个特定程序缺乏明文规定时,须依据“‘低强度’的处罚尚须履行该程序,‘高强度’的处罚自不待言”的逻辑,将“高强度”处罚纳入该程序的适用范围。以听证为例,《行政处罚法》第42条将“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列为应听证的处罚范围,根据举轻以明重,具有“加甚性”的“撤销”处罚更有听证必要,执法机关在作出撤销之前,应当告知相对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否则即构成程序违法。如此可以将传统观念中的某些“任意程序”变成隐性“强制性程序”,不仅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和保障权利,而且有利于提高实体处理的正确性。
第三,在“规定权”的范围界定方面,《行政处罚法》第10条至第13条将处罚“规定权”限定为“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范围内”。何为“范围内”?法律未明文限定。笔者认为,为防止有权机关借“规定权”之名行“设定权”之实,须将举轻以明重作为界定“范围内”的标准,“规定权”所衍生的当罚行为在违法性、危害性等方面必须甚于上位法所列的当罚行为或所隐含的当罚标准,否则即属于“超范围”规定。
三、可行性之论证
举轻以明重以待决事项与法定事项之间存在的种属关系或递进关系为逻辑基础,当用以弥补“隐藏的处罚漏洞”时,其所依据的是种属关系,并把种概念的范围加以具体化、明确化。尽管当前对该情形下举轻以明重的性质存在争议,⑲有学者认为该种情况下属于文义解释而不是当然解释。参见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但因至少在形式上符合法条的字面含义,且能起到限制处罚权的实际效果,因而并不违背处罚法定原则。当用以弥补“开放的处罚漏洞”时,其所依据的是递进关系,因在形式上超越了法条的字面含义,且有“扩张”处罚范围或“加重”处罚程度等不利结果,故学界对其自身的正当性及其与处罚法定原则之间的符合性存有异议。
因此,欲建立人们对举轻以明重的可行性确信,至少需要回应两点疑问:第一,举轻以明重以“法无明文”为前提,这是否违背处罚“法定”?第二,举轻以明重得出的是“当罚或重罚”等不利于相对人的结论,这是否影响其正当性、是否违背“有利归于个人”原则?
(一)不违背处罚法定原则
尽管举轻以明重的“法无明文”、类推处罚、价值判断等特点与处罚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法定性和限权性等要求有视觉冲突,但二者在本质上并不抵触。
1.处罚法定并不禁止同一违法类型内的类推
“类推处罚之禁止”是处罚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这不容质疑。举轻以明重在性质上属于类推,这已是国内外学界的通说,⑳如拉伦茨指出“举重明轻的推论”之正当理由与“类推适用”相同,均存在于基于“相似之事物应为相似之处理”之正义要求。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6页。笔者亦无意加以否定。但是,举轻以明重并不违背处罚法定,原因在于两种语境下的类推不是同一概念。处罚法定所禁止的是不同违法类型之间的类推,举轻以明重是同一违法类型项下不同违法行为之间的类推,同一违法类型内的类推不但不会被处罚法定所禁止,而且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和必要性。因为处罚条文的作用并不在于固定或指向具体的违法行为,而在于表明法律所欲规范的违法类型,这一违法类型可包含多种没有体现在文字上的违法行为,其内涵与外延需要借助同一违法类型内的类推来“找寻”和具体框定。
处罚法定禁止类推的实质是禁止比照已规定的违法类型创设新的违法类型,并不禁止在同一违法类型内部进行具体违法行为之间的类推。如法律规定对使用“畜力车”盗窃林木的行为必须加重处罚,则加重处罚用“汽车”盗窃林木的行为自不待言,㉑此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盗窃林木案件中的判决,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两者属于同一类型,只是行为表现和种类上有差别。“法律有时给行政划了一个圆,只要行政机关不越出边界,在这个圆内基于行政任务而创造性地从事行政活动,也是符合依法行政原理的。”㉒章剑生:《依法行政原理之解释》,《法治研究》2011年第6期。这个内在于行政处罚中的“圆”的边界就是已明定于法律文本中的“违法类型”。
举轻以明重是同一违法类型内类推的典范,其所对比的轻重两事物只是处于同一种类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如“禁止以网捕鱼”较之于“禁止垂钓”,前者只是在后者基础之上的发展和递进,并没有突破法律规定而额外创造新的违法类型。与处罚法定所禁止的类推相比,举轻以明重是一种“微弱意义上的自由裁量”,㉓德沃金将自由裁量区分为“微弱意义上自由裁量”和“强烈意义上的自由裁量”两种样态,前者意指遵守现有法律规则,但必须有判断而不能机械地使用;后者意指抛开法律规则约束,完全诉诸于价值判断的法外裁判。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3-55页。其建立在“超过的相似性”的基础之上,㉔杜宇:《刑法上之“类推禁止”如何可能?一个方法论上的悬疑》,《中外法学》2006年4期。实质上是“有类进推”的“法的发现”而非“无类而推”的“法的创造”,其“不是对预设的法进行创造性地具体化,而是去认识预设的法”,㉕[德]乌尔弗里德·诺依曼:《法律教义学在德国法文化中意义》,郑永流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5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是对法定处罚范围的“还原”而非“扩大”。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在表1中可直观体现。

表1 处罚法定禁止的类推与举轻以明重的不同
2.处罚法定之“法”包括默示规范
从规范层面看,举轻以明重与处罚法定并不抵触的原因还在于,处罚法定中的“法”不仅指明示规范,还包括默示规范。对在默示规范“射程”范围内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并不违反处罚法定,这主要源于默示规范的内涵与价值。
默示规范㉖也有学者称为“隐形规定”,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凡是被法律文本的字面所记载的,就可以说是法律有显形规定。凡是法律文本的字面所未能载明,但被其逻辑所包含的,就可以说是法律有隐形规定。无论是显形规定还是隐形规定,都是法律的明文规定,这是没有疑问的。”见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的逻辑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3期。与默示推理㉗法律推理中存在“默示推理”,意指有一些不言自明的既存事实,不需要特别声明即可认定。当前合同法中的“默示废止”以及证据规则中的“事实推定”(笔者注)就是该原理的体现。参见刘平、史莉莉:《法理在行政执法中应用的研究》,《政府法制研究》2007年第5期。相对应,意指一些不言自明的当然性规范,不需要法律明文就可被推知。正如学者所言:“制度中不仅有明示规范,也有默示规范;默示规范是不言自明的;……在行政执法中我们应当学会运用默示的规则,依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㉘同上注,刘平、史莉莉文。默示规范只是法律形式之“默”而非法律内容之“无”,其作为一种法的现实存在状态,理应充当权力行使的依据。有限的处罚明示规范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为防止仅以法律明文为依据造成“以辞害意”的后果,必须将默示规范纳入处罚法定之“法”的范围。
默示规范通过举轻以明重得以延展和具体化,举轻以明重则以“以小推大”的逻辑“挖掘”或“示明”潜在的默示规范,并以此为依据对“大”事件作出处罚。在此,立法者采取的是“以小定大”或“见微知著”的逻辑,对存在“大小覆盖”关系之“小”事件的当罚性作出明示规定,以此表明“大”事件当罚的态度。换言之,“大”事件的当罚性已包含在条文法的语义之中,所谓的“法无明文”实则立法态度处于一种“隐而不显”的状态,这与耶塞克、魏根特所称之“被隐藏的构成处罚的行为情况”具有相通之处。㉙[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罚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70页。此言针对的是刑罚中主客观不统一或不对应的情况,而本文针对的是行政处罚中事实与规范不统一或不对应的情况,但二者在道理上具有共通性。
3.举轻以明重与处罚法定具有目的重合性
处罚法定并不苛求处罚设定与法律文字一一对应,而是意在确保处罚的可预测性和可控性。举轻以明重所含价值理念的普适性和推理过程的客观性决定了“推导”结论的可预测和可控,并以此与处罚法定的实质目的相一致。
其一,举轻以明重不是一个或几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整个社会共同体所持有的牢固的正义观念,是一种社会通行的行为标准。其所蕴含的理性在实际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并能被任何有正常智力和理性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预测。
其二,与一般类推相比,举轻以明重的推理过程具有相对客观性。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从推理标准上看,一般类推遵循的是横向的“相似”标准,在类比点的选择以及相似性的判断上具有较多的主观裁量因素,处罚结果因此变得捉摸不定。相反,举轻以明重遵循的是纵向的“加甚”标准,其以行为的危害性为对比点,以轻重程度为判断标准,比较点的特定性和判断标准的客观性决定了其推理过程具有法律可控性。例如,我国《刑法》(1997年修订)第201条曾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按照举轻以明重原理,“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三次(或三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更应该处以上述刑罚,这里的“二次”与“三次(或三次以上)”的数理计算关系更加鲜明。据此,《刑法修正案(七)》特将该条修改为“二次以上”的做法实属多余之举,只要借助举轻以明重就完全可达致相同的目的,而不必通过修法在法条文字上动“外科手术”。第二,从推理方式上看,举轻以明重运用的是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大前提是法条F明文规定A1当罚,小前提是A2与A1属于同一类型且比A1“重”,结论是“A2当罚”是F的隐含规定,应依据F对A2施以处罚。可见,其推理过程仍遵循事实之于规范的“涵摄”思维,本质上是对既有法律规范的发现和适用。而一般的类推运用的是类比推理方式,仅由两个事实在某些属性上的相似性即推出法律应对其作相同评价的结论。例如,通奸与重婚相类似,且重婚当罚,则通奸行为同样当罚。这一推理过程既不包含对现有法律规范的解释和分析,亦无“默示规范”的推出,本质上是从应然层面所作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大。
(二)不违背“有利归于个人”原则
“有利归于个人”作为行政法乃至公法解释之特有原则,与刑法理论中的“存疑时有利于被告”或允许“有利类推”等秉持相同的人权理念,意指在一项利益不能确定应当属于个人、国家或公共团体时,一般应作有利于个人之解释。㉚参见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88页。按此逻辑,当行为是否可罚存在法律上的疑问时,是否必然要作出“不罚或不重罚”的解释,进而否定举轻以明重?答案是否定的。举轻以明重在结果上的不利性并不影响自身的正当性,其与“有利归于个人”原则并行不悖。
首先,举轻以明重是法律解释方法,“有利归于个人”是法律解释政策,前者具有优先适用性。
法律解释方法是发现法律真意的“技术”,其以文义、体系、历史等为考量要素,以实现立法意图为目标,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内”;法律解释政策直接指向裁判者欲达致的实际效果,其既不探究法律的真实含义,亦不分析事实与规范的对应关系,而是直接从结论角度为法律解释设定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外”。因法律适用必须以其自身的含义为基本前提,故“方法”应优于“政策”。据此,当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导致适用上的疑问时,应当首先借助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去探究立法含义,并依此得出法律结论。只有当穷尽一切法律解释方法仍无法得出唯一确定的法律结论时,法律解释政策才具有适用的空间。
举轻以明重是一种具体的法律解释方法,“有利归于个人”是一种具有公法价值倾向的法律解释政策或立场。当某法条只明文规定轻行为可罚,重行为是否可罚不得而知时,应首先适用举轻以明重去发现或补充法律的真实含义,而不能直接根据“有利归于个人”得出“不罚或不重罚”的结果。正如有法国学者所言,当法律存在疑问时,“法院并不能因此而免于适用法律,法院也无义务一定要采取‘最利于犯罪人的限制性解释’……法官应当首先借助于一般的解释方法,从中找到法的真正意义
……如果疑问仍然存在,法官则应当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㉛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这虽是对刑法“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阐释,但道理同样适用于本文立场。
其次,举轻以明重指向法益保护机能,“有利归于个人”指向人权保障机能,两者应协调统一。
处罚法定的价值不仅在于监督处罚权行使和保障人权,更在于惩治违法、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无论是处罚的设定与实施,还是对处罚法的解释与适用,都应兼顾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的双重机能。尽管囿于国家处罚权的天然强大,现代行政法需要对人权保障投入更多的制度设计,法益保护机能更容易实现,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后者具有优先性或排他性。据此,因“有利归于个人”指向人权保障机能,“当罚或重罚”意义上的举轻以明重则指向法益保护机能,二者应具有平等性和协调统一性,任何以结果不利性来否定举轻以明重的观点都是对二者关系的误读。
四、应用规则
举轻以明重必须在处罚法定原则的框架内运行,而严守这一界限的关键在于遵守相关的应用规则。因举轻以明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依据主要来自形式逻辑、事理逻辑和立法目的,其应用规则的设置也须围绕这三方面展开,并适当融入程序正义理念。
(一)同质性规则
欲使举轻以明重具有形式逻辑上的当然性,必须满足“待解释事项包含在法条规范含义之中,也即在法律规范之中存在待解释事项的落脚点”,㉜李翔:《论我国刑法中的当然解释及其限度》,《法学》2014年第5期。而“落脚点”有无的判断需要依靠同质性规则,即只有待决的“重行为”与法定的“轻行为”属于同一类型,且“重行为”是由“轻行为”和“加甚因素”发展而成时,才能将其纳入当前规范的规制范围并施以处罚。
目前对于“同一性”的判断标准存在不同观点,㉝如“构成要件类似说”、“实质一致说”、“同一思想基础说”,转引自刘士国:《类型化与民法解释》,《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再如“共同意义说”,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笔者认为,“构成要件相似+共同意义”的综合判断标准能兼顾客观形式与实质价值两个方面,因而更科学更全面。首先,就相似的构成要件而言,关键在于判断哪些特征在法律考量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惟有法定行为与待决行为在这些关键点上具有同一性时,才可作同类认定。如前述案例一中,“醉驾”、“药驾”和“毒驾”都是服用了影响驾驶安全的物品,这是对案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共同构成要件,至于其他具体物品种类上的差别并不影响案件同一性的认定。其次,共同意义是指轻重两行为损害的客体必须相同。“毒驾”和“醉驾”、“药驾”都是对正常的交通秩序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一客体的侵害,符合共同意义的要求。
(二)梯度性规则
梯度性规则要求待决行为必须比法定当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重,且这一轻重差距足以达到一般人都能识别和认知的程度。唯此,才能保证其在事理逻辑上的当然性,才有所谓“更有适用的理由”可言。如“禁止折枝”与“连根拔起”之间就存在轻重程度上的明显差距,法律规定前者当罚,则后者更当罚,这是任何有正常智力和理性的社会公众都能认同的。
实践中,“轻”与“重”该如何判断?王泽鉴先生主张将“要件”和“效果”作为轻重程度比较的对象,“所谓‘重’者,指其法律要件较宽或者法律效果较广,而所谓‘轻’者,指其法律要件较严或法律效果较狭”;“何者为重,何者为轻,应就法律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关联为法律上衡量的判断”。㉞王泽鉴:《举轻明重、衡平原则与类推适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8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重”者系法律未规定的行为,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法律要件和效果,所谓要件的“宽”与“严”和效果的“广”与“狭”,以及二者“关联”的轻重衡量根本无从谈起。
相比之下,张明楷教授提出的从“违法”和“责任”两方面来比较“轻”“重”的主张更具有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可操作性。㉟关于“违法”和“责任”标准的内容,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中的当然解释》,《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无论违法抑或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都是由行为构成要素决定的,待决行为与法定行为的轻重比较自然要从其自身的构成要素入手,即“危害程度的轻重是法律评价上的轻重,而其判断还需借助于法定案型与现实案型的行为构成比较而进行”,㊱余文唐:《简论罪行法定下的举轻明重》,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FullText.aspx?ArticleId=89251,2015年3月19日访问。“违法”与“责任”标准恰好符合此要求。“违法”是指法益侵害的轻重,涉及行为的客观构成要素;“责任”是指主观恶性的大小,涉及行为的主观构成要素。从具体内容上看,前者包括行为的手段、对象、后果、时间、场合、次数、数额等要素;后者包括行为人的动机、目的、故意、过失等要素,执法、司法人员必须在考察多种要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
(三)立法目的符合性规则
立法目的要素的引入,不仅能提高法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更是避免法律适用恣意、维护法律权威的关键,“恰恰在一种以规则为中心的法律秩序中,为了减少对条文解释的恣意,或者制止官员越权行事——即超出授权范围行事,推论必须经常要求离开规则而求助于目的”。㊲[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举轻以明重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方法,必须受立法目的制约。执法人员应首先根据目的性条款、立法背景资料中关于立法目的的说明或是借助体系、历史、比较等解释方法,确定法律明文背后的目的;然后将举轻以明重的结论与立法目的相比较,只有两者相符合时,待决行为才能被当前法条所吸收。例如,由“禁止游泳者着装不当、修补不当、衣料透明”的法律明文,可确定“规范游泳者着装行为,维护海滩文明秩序”的立法目的,据此处罚“一丝不挂”行为当然属于立法目的的应有之义。㊳参见刘星:《西窗法雨》,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四)说明理由制度
为避免“法无明文”状态下的处罚给人以突兀和妄为之感,必须提高举轻以明重应用过程的说理性。为此,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关于处罚告知制度中的“依据”,不应只限于当下执法实践中大都采用的法条罗列,还必须对选择该法条作为处罚依据的理由作出说明。可喜的是,已有个别地方或部门通过规范性文件对此提出了要求,如杭州市2010年《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操作规范》第8条中规定,“办案人员应当结合个案事实对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更详尽的法理阐述,以充分的说理来论证采用特定的法条作为处罚依据的理由”。第10条“说明法理”项下则规定“运用法理对案件的定性、情节、处罚等问题做透彻的分析说明”。这些规定为举轻以明重融入“法理”预留了空间。
从内容上看,举轻以明重的说理应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结合个案事实,从目的、精神等方面对法条进行全面剖析;二是在具体分析法定事实与待决事实之“轻重”关系的基础上,对选择举轻以明重的正当性进行严密论证;三是对应用举轻以明重,由前提导出结论的过程作出详细说明,增强处罚结果的说服力。
五、应用现状及不足
当下行政处罚实践中,举轻以明重的法律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尤其在“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权利生成法则和“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权力生成法则之下,执法、司法人员大多对其“敬而远之”。笔者通过检索最高法院公报、审判指导案例丛书、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查得应用举轻以明重的案例寥寥无几,有限的案例也大多出现于其他部门法领域,且存在若干不足。
(一)应用方式隐晦
因受制于传统观念或迫于舆论压力,执法、司法人员对举轻以明重“讳莫如深”,即使实际运用其弥补“法无明文”的缺陷或解决实践中“先法”未预料的问题,也很少在相关法律文书中明确提及“举轻以明重”的字眼。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举轻以明重”和“举轻明重”为关键词,以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28日为区间,检索出的122条裁判记录中,只有1例行政案件,且其针对的是行政确认而非行政处罚。㊴该案中,法官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关于工伤认定情形的规定是立法者采用了举轻以明重的立法原则。根据“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标准,本人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的不应认定为工伤,相比主要责任更为严重的全部责任,则更不应该认定为工伤。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行终字第00130号判决书。
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应用方式,在“吴俊铭、郑清诈骗罪再审案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㊵因相关行政裁判案件数量有限,只能借用刑法裁判实例来说明,但问题具有共通性。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闽刑事终字第1号判决书。检察院在抗诉理由中提出:“《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七条已将在犯罪中所起作用及社会危害性均相对较小的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等帮助行为明确规定为诈骗罪共犯,根据举轻以明重,对于在诈骗中起重要作用的转移赃款行为更应该以诈骗共犯论处。”法院判决肯定了上述结论,但仅以“根据《解释》第七条之精神,郑清应以诈骗共犯论处”作结论,举轻以明重被笼统的“精神”掩盖。这种回避或隐晦的应用态度,既不利于判决的说理,亦不利于举轻以明重作为法理或法律方法的完善和推广。
(二)标准不统一
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则,实践中对举轻以明重的判断标准宽严不一,与行政一贯性、司法统一性的要求相差甚远,其主要表现有二。第一,曲解举轻以明重的含义。以一公司对职工的处罚案件为例,麦格纳动力总成(常州)有限公司以员工张瑞年在厂区公共区域小便,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为由将其解雇。该公司认为,《渐进惩处管理规定》已明确规定:“因过失对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应给予“书面警告”,举轻以明重,该员工故意破坏环境的行为应当给予更严厉的处罚(即解雇)。㊶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民终字第430号判决书。可见,此公司管理者把举轻以明重在量罚中的含义理解为“情节比法律明文重的,可适用比法定量罚类型更重的处罚”,这曲解了该原理的本意。因为举轻以明重只能在“是否从重”层面上判断从重条件,不能在“怎样从重”层面上创设从重结果。易言之,处罚决定的作出只能依据法条明文规定的量罚幅度直至最高量罚标准,而不能以举轻以明重为由在法外创设更重的处罚幅度或种类。第二,颠倒举轻以明重的逻辑顺序。举轻以明重作为“入罚”标准,必须遵循以“轻”行为之规定处罚“重”行为的逻辑,而实践中这一“入罚”口径被扩大,出现以“重”行为之规定处罚“轻”行为的案例。如某市地方性装修管理法规明文禁止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成”卫生间或厨房间,某房主在自家装修时,将原来的卫生间向卧室“扩大”了1.96米,并铺设排水管道。该市房管局以违反上述地方法律规定为由对其作出处罚。㊷参见最高院行政审判庭:《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7页。这实际是以“整体改成”之禁止的法律规定来处罚“局部扩大”的待决行为,错用举轻以明重的推理逻辑,导致处罚范围的扩张。
(三)论证不充分
当下举轻以明重的个案应用均缺乏将内心裁量形之于外的推理论证过程,以致人们无法检验执法、司法人员在同质性、合目的性、轻重梯度等问题上判断的正确性,既增加了举轻以明重被滥用的风险,亦不利于增强结果的说服力和相对人的认同感。如在“胡志良与天安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法官对应用举轻以明重作了以下描述:“在上述三种情况下,保险人不承担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其垫付的抢救费用。举轻以明重,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受害人后仍有权向致害人追偿。”㊸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温民终字第291号判决书。法官适用举轻以明重,试图从可追偿“抢救费”的法律明文,推出“一般赔偿费”也可追偿的结论,但“抢救费”和“一般赔偿费”是否具有同质性?判断后者可追偿是否内隐于立法目的?从何角度比较两者的轻重?其轻重梯度是否符合明显性的要求?对于上述问题判决书中均缺乏明确论证,以致人们无从了解判决理由,自然会对判决结论的正确性心生疑虑。
六、融入当下行政处罚理论与制度及关联机制的路径
欲克服举轻以明重在实践与技术层面的不足,确保行政处罚理论的先进性以及制度的应对性和可预测性,需将举轻以明重由一种潜在的逻辑思想转变为一种现实的处罚规则和当罚性评判标准。其基本方法有二:一是将其融入我国当下的行政处罚理论与制度机制;二是融入行政处罚关联机制。
(一)融入行政处罚理论与制度体系的路径
第一,统一行政处罚概念。当下行政法学理论关于行政处罚的概念有“规范说”与“秩序说”两种观点,前者将处罚前提设计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后者则设计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除非“规范说”中的“规范”涵盖“默示规范”,进而融入举轻以明重原理,否则,笔者建议一律采“秩序说”,一则避免因将“规范”狭隘理解为“条文法”或“明文”所带来的对于举轻以明重的排斥;二则“秩序说”便于融入举轻以明重,以危害社会秩序的轻重梯度为标准,对社会危害性“甚于”或“重于”“明文”当罚行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第二,并入《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的处罚公正原则之中。处罚公正原则包括“处罚平等”和“过罚相当”两方面的内容,二者均与举轻以明重的“法理”相通:一方面,举轻以明重项下的轻重两行为具有同质性,对重者施以处罚是“处罚平等”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只有对重者施以处罚才能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保持基本均衡,进而符合“过罚相当”或“合比例”的要求。
第三,将来修改《行政处罚法》时,将举轻以明重作为处罚适用规则纳入第四章“行政处罚的适用”当中,与不予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行刑并科与折抵等共同组成行政处罚适用规则体系,使举轻以明重由“原理”上升到“法律规则”层面。
第四,构建一种“行为可罚性推定”制度,将举轻以明重作为推定依据融入其中。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规定了推定制度,法官可依据某些“不证自明”的道理直接推定事实存在而无需证据证明。其实质上是一种“事实存在性推定”。与此相呼应,有必要构建一种“行为可罚性推定”制度,意指在某行为实质上具有当罚性但缺乏明文的法律依据时,法官可依据某些“不证自明”的道理直接推定该行为当罚。
举轻以明重具有合理性、客观性和公认性的特点,符合“不证自明”的要求,将其作为推定依据并纳入“行为可罚性推定”制度的具体方式有二:一是借助“法律推定”模式,将其作为明确的推定规则写入立法;二是借助“事实推定”或“司法认知”模式,将其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
(二)融入行政处罚关联机制的路径
第一,融入行政法律方法体系。法国学者Barreau指出,“离开方法的科学就不能称之为科学”,㊹转引自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法律方法能有效提升理论对实践的回应能力,对提高学科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完整性具有重要作用。举轻以明重作为一种对行政法学相对陌生的法律适用方法,理应融入当下行政法理论体系。
按照传统法律方法理论,行政法律方法体系应包括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不同内容,㊺参见陈金钊:《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据此,举轻以明重融入其中的方式亦有多种:在法律发现层面,其是在制定法出现模糊或空缺时寻找裁判大前提的方法;在法律推理层面,其作为连接法律规范与待证事实的实质推理方式;在法律解释层面,其属于论理解释或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内容;在利益衡量层面,其是在法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社会公共秩序维护与公民权利自由保障之间进行价值权衡和利益取舍的依据;在漏洞补充层面,其作为弥补开放漏洞和隐藏漏洞的工具,在“禁止裁量”与“绝对裁量”之间达致“有序裁量”和“合目的裁量”的目标。
第二,扩张行政裁量的范围,承认要件裁量。要件裁量与和结果裁量相对应,㊻关于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的界分,请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3页。前者是指行政主体对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享有判断余地,后者是指行政主体对行为的法律后果享有选择空间。当下行政法理论对行政裁量的理解主要停留在结果裁量层面,对要件裁量尚缺乏必要的探讨。举轻以明重是在法律适用条件规定不明时,解释法律并将事实带入法律之中的依据,在性质上属于一种要件裁量基准。若将要件裁量纳入行政裁量的范畴,举轻以明重的融入便可顺理成章。
第三,纳入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涵范畴。合理性原则所关涉的“客观规律”、“立法目的”、“道德观念”等要素与举轻以明重所遵奉的“事物本质”、“当然之理”等要素具有相通性和契合性,这就决定了合理性是举轻以明重的实现目标,举轻以明重是合理性原则的具体化或实现途径,将举轻以明重归入到合理性文义范畴应无障碍。
第四,作为行政审判依据,当前有三种具体实现途径:一是完善以修改后《行政诉讼法》第63条为载体的行政审判依据体系,改变条文法“一统天下”的现状,将举轻以明重等“理念法”纳入其中;二是将“理念法”融入修改后《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合法性”审查标准的“法”当中;三是修改后《行政诉讼法》第77条将“变更判决”的条件设定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举轻以明重可以作为“明显不当”的判断依据。
七、结语
徐国栋教授有言,“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因而“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㊼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法律不可能包罗万象,不可能预见未来的所有法现象,但秩序、福祉等价值要求法律必须时刻“跟进”甚至“领先”社会生活,因之法律方法对于当下日新月异、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而言就显得尤其必要,唯有如此才能使法律规范条文真正成为“活的法”。面对“条文法”无法涵盖和预测的违法行为,“举轻以明重”可以起到“理念法”、法律方法和法律精神“传送带”的作用,能够在不违反处罚法定的前提下“延续”行政处罚设定中“示例性列举”和“兜底条款”的生命力,使法律在社会实践面前不至于陷于被动落后的窘境,也能以法律方法和不成文法源“激活”当下几近静寂、不能与时偕行的行政法学理论、制度与规范体系,避免出现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曾经描述的那种景象:“各种法律规范,无论是表现为法律,还是表现为判例,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凝固的东西,并落后于生活。”㊽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法学流派与法学家》,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责任编辑:姚魏)
D F3
A
1005-9512(2015)08-0062-13
柳砚涛,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生导师,法学博士。
*本文系山东省2013年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具体行政行为跨程序拘束规则研究”(项目编号:13BFX J02)的阶段性成果。山东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海霞对本文形成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