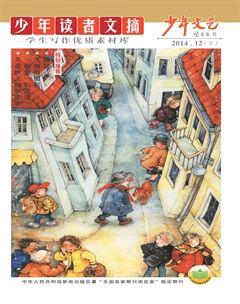锦瑟
李秋沅
一
课外阅读,我为孩子们选读了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在孩子们的诵读声中,我仿佛又看见她了。
她侧转身,回过头,笑吟吟地看着我说:“记住这首诗,也就记住姨婆了。薇薇,你会永远记住姨婆吗?”
“会的,姨婆。”幼年的我脆生生地答,不假思索。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朗朗的诵读声中,我沉下心来细细地回忆她的容颜,竟惶然发现,她终究还是远行了。我心深处,她的身影徘徊依旧,却轮廓模糊。时光不断地在亡人日渐模糊的面容上添枝加叶,我终于还是忘记了她的确切容颜。
她的名字,就叫锦瑟。
母亲从来都只叫她“柳姨”。而我,唤她“柳姨婆”。
二
外祖父去世后,尚在乡下的父母,先设法让五岁的我回到城里的老家。偌大的房子,就我和她两人住。
刚回老屋,我不习惯独眠。夜晚熄灯时分,令人绝望的黑暗便突然涌进卧室。层层的黑,连我的呼吸都仿佛陷入了黑暗之中。我在黑暗之中,宛若将被黑暗所融化。我揪紧被子,用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抵抗着黑暗。
除了黑暗,老屋夜晚的寂静也令我胆战心惊。有时我在梦中突然被从内耳发出的耳鸣声惊醒。轰隆隆尖锐的耳鸣像锋利的刀刃,将我的意识分割得细碎。最后,声响从耳到心,像一道霹雳,轰然将我劈作两半,于是我便在痛苦中惊醒。
“婆婆……”
我光着脚,穿过廊道,呜咽着往姨婆的卧室跑。我爬上姨婆的大床,一双温暖的手立刻从黑暗中伸了过来,搂住我的腰,一把将我拽进散发着沉沉暖香的被褥里。喜欢用香木珠熏衣物的姨婆身上有一股幽幽的木香,我枕着姨婆的手臂,听着她连绵悠长的鼾声,黑暗的恐惧在她鲜活的鼾声中消失殆尽。层层黑暗忽然变了颜面,温柔敦厚地催我入梦。
晨起,我最喜欢看姨婆梳头。姨婆的头发长长的,一直垂到腰际,稀疏灰白。牛骨梳缓缓地滑过她的长发,牵扯下丝丝灰白。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将缠在梳齿上的落发根根卸下,在手上缠成一团。她将落发放在一方黑色的脱胎木首饰盒里:“以后,等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可以填在发髻里。”
她一边梳头,一边教我背古诗,最常叫背的,就是《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姨婆的嗓音轻柔。
“一弦一柱思华年……”我一边把玩她的落发,一边应对着她的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我背全了诗,姨婆的头发也就梳好了。
“薇薇,这是婆的名字——锦瑟,记住了没?”
“记住了,我的名字有诗么?”
“有,《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婆,你念,你再念一遍。婆,你也要记我的名字,我的诗。”我扬起头,一本正经。
“婆记得的,憨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后如果你长大离开婆了,婆一念这句诗,你就跑回来看婆好么?”
“好!你要大声念。倘若离得太远了,我怕听不到。”我蹙眉。
姨婆笑着把满面愁容的我搂进怀里。
遇到天晴时,姨婆就将阁楼里的几个大箱子打开,让箱里的东西见见天光。大多数箱子装的是古籍书。其中有个小巧点的,装的是衣物:金线绣的凤凰牡丹织锦缎面、水绿的生丝旗袍、银色软缎披肩……漂亮的丝织物件,沾着箱子沉沉的樟木香,隐约还嗅得被时光藏起来的冷清的皂香。我一件件展开衣物,喜滋滋地往身上套。
“憨女,一手的汗,别弄脏了!”姨婆骂是骂,眼里却含着笑,“喏,这件,绿旗袍,是我做姑娘时最喜欢的。”
我看着她展开绿丝旗袍,往身上一比划,匆匆收起。我嘎嘎地笑着:姨婆几时从绿丝旗袍里走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
“姨婆,我要。”我拿起旗袍套在身上,长长的丝袍拖到了地上。
“哎哟!”姨婆作势要打,一把拎起旗袍下摆,顺势将它从我身上剥了去。
几年后,父母也返城,搬回老屋住。我看着突然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父母,却生分了。我紧紧地拉着姨婆的手,手心汗津津的,死也不松手。
母亲回来,将老屋整理修葺一新。除了姨婆的那几个樟木箱,阁楼里的杂物统统地被搬到了储物间。
“柳姨,有些东西,扔箱里几十年没用,占地方,最后也得处理掉……”母亲有意无意地和姨婆提了几次。
终于,樟木箱从阁楼被挪到了客房,最后又被挪到了放杂物的储藏间。
“理理吧,那木箱……”姨婆犹豫了一下,“该扔的就扔了吧。”
母亲叫了工人过来收拾,扛箱子出去。姨婆突然起身,打开其中的一个木箱,摸索着,抽出那件水绿色的生丝旗袍。
母亲说我长大了,夜里,不许再去打扰姨婆。“以后,晚上别老去姨婆那里睡。自己睡!”母亲冷着脸,黑色眼瞳里出现了我看不清的星星,隔开了映在她眼瞳中的我。
夜里,我将头蒙进被里。被窝里,黑暗漫无边际。我的呼吸沉重,闷闷地压在我心上。我紧紧地揪住被角,睁大眼,严严实实地将自己与被子外面的黑暗隔离开,可黑暗的恐惧如水,无缝不入。
“婆婆……”我呜呜咽咽地掀开被,跳下床,光着脚想往姨婆的卧房跑,却又不敢。我团坐在床上,在黑暗中哭着。除了哭,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哭什么?”母亲生气地从她的卧房走出来问。
“我怕。”
姨婆也被惊醒了,走了过来。
“来,过来和姨婆睡。”
我看着她,只是哭。黑暗中,模糊不清的一团影子,缓缓地走近我。我嗅得见她身上清爽的木香味。这味道令我心安。我向她伸出手去。
“自己睡!这么大的人了!柳姨,别惯着她。”
一声叹息,那团温暖的影子离去了。黑暗中,清冷的木香久久地踯躅。
三
柳姨,母亲总这么叫她。
我知道,亲外婆早已扁成了一张薄薄的相片,就在母亲的卧房抽屉里。我曾无数次凝望着相片上那身着碎花旗袍的女子,看着她凝固在时光之外的笑颜,看着她与姨婆有几分相似的眼眸。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有和姨婆一样沉沉的木香。
母亲与姨婆相敬如宾。我能感觉得出她们之间的隔阂。她们间的淡漠,是母亲将姨婆整理过的书架,一言不发地重新擦拭一番;是母亲独自熬了白粥,而不吃姨婆做的面食;是姨婆笑着指出母亲的南洋口音,而母亲则厌烦地打断姨婆教我背的古诗……
我困惑地行走于母亲与姨婆之间,渐渐习惯于独自沉思。我长久地趴在院里的水井边,低着头看井。井水平静,隐隐约约看得见自己的一双眼睛,从黑魆魆的井里往外瞅着。阳光仅在暑天午后的某个时刻直射水井,向井底投下绿莹莹的一道光柱。在绿莹莹的光柱下,我可以窥见隐藏在平静水面下崎岖不平的井壁、凹凸起伏的井底。光柱转瞬即逝,井面下的世界倏地隐没,水面平静如镜。大人的世界于我而言,神秘若那井面下的世界,若即若离。
四
上学识得几个字后,我便时常躲进姨婆屋里看书。母亲不喜欢孩子一副老气横秋的读书相,见我成天不吭声,捧着书看就皱眉头。而我也怕招惹她,唯有走进姨婆房里,嗅着淡淡的书墨香看书,心里才觉得踏实。姨婆从不责备我,她的房里有数不尽的书,一本本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姨婆把带有插画的书全摆在最下层,我够得着的地方。
“这憨女,以后估计是书呆。”家人这么说。
“多出去跑跑啊,别老呆在婆婆房里,和别的小朋友玩去啊。”母亲听罢,皱着眉,拿开我手里的书,“出去,出去玩去。”她挥挥手,像赶一只不听话的蝇虫般。我站着不动,盯着她手里的图书。
“出去玩,听见了没?”她大声训我。
我泪汪汪地看着她,不知所措。
“薇薇爱看书也不是坏事,你就由着她看吧……”姨婆笑着劝。
“不行!出去玩!”母亲突然发怒了。
姨婆一下子噤声。我朝姨婆扑过去,紧紧地抱着姨婆不放手。“这孩子,去……去啊,听妈妈的话。”她抚摸着我的背,柔声说。
我一动也不动,就是死死地抱住她。
“唉,这孩子若天性好静爱看书,就让她看书吧,是好事啊。”姨婆轻声说。
母亲看了看死死缠住姨婆不放的我,冷冷地剜了姨婆一眼:“为人做事哪能总由着性子来?”
必有一些事,是我所不了解的。它们藏在时光中,藏在母亲的眼眸中,藏在被丢弃的姨婆的樟木箱里。
十岁那年,断了十几年音信、远在南洋的姨妈和表姊辗转回来了。分离几十载重又与母亲相逢,姨妈泪汪汪地拉着母亲不松手,而对一旁的姨婆,只淡淡地寒暄,话里带着冰。
住了几天,表姊惊异于我对姨婆的依恋。“她是假外婆啊。我们的亲外婆早就不在了……憨女,你知道她是假外婆了还和她亲?”
我看着大表姊的眼,怔怔的。
夜里,表姊与我同榻,用与母亲相同的、柔柔的南洋口音絮絮地对我说:“外公被她迷了心哪,否则我们白家也不至于这么凄惨。亲外婆是南洋的阿祖为外公娶的,外公不合意,兀自娶了她做二太太。阿祖去世后,外公索性不回了,把亲外婆和我阿母、阿姨孤零零抛在南洋。她几年没有生育,外公又想把两个女儿要回内地。亲外婆不舍得,留了一个在南洋。要不是她,阿母不至于和阿姨姊妹分离几十年。亲外婆也不至于成天躲着人抹眼泪,早早得了肺病死了。倘若外公好好地留在南洋经营祖业,后来哪里会受那么多苦,还连累了你阿母……”
“外公不回南洋,真的不管你阿母和亲外婆啦?”
“唉,开始时还往南洋写写信的……后来,这边时局变了,音信全无,彼此都不知道是死是活……”
“话说回来,她也真够胆大啊,一个女学生,居然在那时敢抗着父母嫁一个商人做二太太。”表姊冷不丁又补了一句。
“那……她是坏人?”我的心思全乱了。
我屏住气,等着表姊往下说,可她打了一个呵欠便止住了。不一会儿,我的枕边传来她沉沉的呼吸声。我抬眼看窗,白日里的溽热已消散,夜风习习探进屋来,掀起窗纱。于是,窗外幽蓝的天幕便在窗纱轻舞飞扬时分,倏忽隐现。我躺在床上,提着心一次次地等待着,等待着窗纱扬起。
姨母和表姊走后,我问姨婆:“婆,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说呢?”她不看我,闭上了眼。
我不停地问,执著地要知道答案。
……
五
我离姨婆慢慢地远了。姨婆的故事,在姨母与表姊出现后,再次流传在父母亲戚邻居的言谈中,故事的主人公是抽象的音节,寄生在他们的唇齿间。我惶恐地发现她在我的心中变了轮廓,却无能为力。
我沉默着,静静地躲进姨婆的书里。我翻遍了姨婆房里所有带插画的书,连那些不带插画的书,也生吞活剥地读了许多。在姨婆的书里,我不再惶恐,那里有我熟悉的油墨香,有令我屏息难弃的故事,还有我烂熟于心的诗歌。
端午到了。姨婆母亲一同置粽叶、糯米、肉馅、虾仁包粽子。粽子做好后,母亲警告我:“小孩子,不能多吃!只能吃一个,吃多了不消食!”
我吃完一个粽子,抬眼看着姨婆:“婆婆……”我闷闷不乐地盯着眼前诱人的粽子,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了下来。她软下心来,慌忙朝我眨眨眼,待母亲一离开餐厅,立刻偷偷把几颗大粽子塞我手里。我快乐地吃着,一个接着一个。
“别吃了,够了,够了!”姨婆急急地拦我。
我甩开她的手,蒙头吃。我果真吃伤了胃,躺在床上起不来。在母亲的质问下,我一下子把姨婆供了出来:“是婆婆……婆婆让我吃的……”
母亲沉下了脸。
“明知道薇薇胃肠弱,姨,你……”
姨婆难堪地搓着手,看着我,求助。
“我不想吃的,是你给我的。你给我的,给了几个。”我怯怯地说,偷偷瞥了她一眼,我看见她的眼倏地暗淡了。
她起身离去。
“你个憨女,她……难道她让你吃屎你也吃啊?”母亲见她离开,轻声责怪。
我点点头,讨好地说:“她是假外婆,心肠坏……”话音未落,我发现母亲看着我的身后,脸色陡地变了。
姨婆手里拿着从院子里摘来的消食草药,不知何时已悄然进屋。她一言不发地看了我一眼,缓缓地退出屋。她的眼神若一道寒流,从我的心上滑向指尖,我的手指倏地凉了。
夜晚,我躺在卧房的床上,胃疼得厉害。铺天盖地是疼痛的牙齿,啃啮着我的胃我的神经。隐隐约约,我听见了姨婆的抽泣声,在夜间,如茧丝,层层叠叠,将她的哀伤裹在黑暗之中。最后,一切归于宁静,抽泣声、叹息声,全部消逝得无踪无影。我的意识,也渐渐地坠入漫无边际的夜的寂静之中。
第二天醒来后,我看见姨婆已盘好头,和父母一起端坐在餐桌前。隔宿的哀伤是凝固的冰,藏在她的眼眸里。我的胃依旧疼着。
六
姨婆离我愈来愈远了。她身上沉沉的木香偶尔还会飘进我的梦里,但隔帘望月般不真切。她养了一只猫。落日时分,她长时间地抱着猫独坐在露台的躺椅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夕阳的方向,看着太阳一点点失去热度。
偶尔,我还去她的屋里寻书看,可拿了书就走。
一天,我在垃圾桶里看见了那方掉了漆的脱胎首饰盒,掀开的盒盖微微露出丝丝灰白的头发。
“姨婆,你的头发。”
“不要了,”她淡淡地说,“老了,手抖得厉害,头也梳不好了。”姨婆把头发剪了。
“那,盒子给我吧。”我想拿盒子装我的塑料珠链。我拾起首饰盒,拭去上面的污渍,犹豫了一下,把灰发从中捡出,团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里。
我最后一次和姨婆在露台上纳凉,已是仲夏。她躺在摇椅上,一边啪嗒啪嗒地为我摇着蒲扇,一边吟诗:“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我趴在长竹椅上,一边听着她吟诗,一边看着天上的月,悄然由初升时丰淳和温柔的黄色变为凄清冷寂的银色。
“姨婆,你剪了发,我认不得你了。你是从前的姨婆吗?”我冷不丁地说。
月光映照在她的脸上,她叹了一口气:“不是了。薇薇,你也不是从前的薇薇了。薇薇长大了。”
她的目光又从我的身上收了回去,重又抬起脸看头顶的月。许久许久,她突然幽幽问我:“薇薇,你长大后,还会记得小时候婆婆教你读诗么?”
我慌忙点头。
“薇薇,我想回家去了。”
“家?这不是你的家?”
“姨婆的家在很远很远的江宁。”
“嗯,那你干吗到这儿来?”我突然心一硬,挑衅地看着她。
她愣住了,低头看着我的眼。我紧盯着黑暗中她逆着月光的眼,那里面有我看不清的雾。良久,她移开目光,仰首望月,轻若耳语道:“薇薇,人还是得听从自己的心愿做事——身体委屈点不要紧,别委屈自己的心。”她的眼瞳中,映着清冷的月,兀自在舞蹈。
“你后悔么?”我突然问了这句话,连自己都觉得吃惊。从大人们的言谈中,我隐隐约约地知道,姨婆的娘家在江宁也算旺族,祖上出过翰林。嫁做白家二太太后,她就再没脸回娘家。她的老母亲知道她没有生育,为她在江宁收养了几个养子,早早为她安排了日后的归宿。老母亲临终前,还苦苦地等她回去。
“不,心正所愿,我不后悔。”她笑了,“薇薇,我走了你会想姨婆吗?”她拿眼睛愣愣地看着我。
“不想不想。”我嬉笑着,看着她。
“真的?”她蹙了蹙眉,用手抚我的头。
我也蹙着眉。我说的,一半是实话。姨婆早已不是那个从前的姨婆了,她已从我记忆中那个温暖的、令我万分依恋的影子中走出,如同曾经的她,从绿丝旗袍里走出,便再也回不去了。我突然难过起来,低下头:“会,会有一点点想的。”
月光如水般滑过她的摇椅,铺向我的竹椅,在我的光脚丫上印上苍苍的一片白迹后,忽然消失,不知隐没在何方。我看着头顶的月,眼皮越来越沉。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远,渐渐地离了我的心……
七
姨婆执意要回老家。她和母亲彻夜长谈。她们的话语,在黑暗中游走,丝丝缕缕,忽而飘进我耳中,忽而隐匿无踪。
“我回去……把你妈和你爸合葬了吧,你妈等得够苦的了,入土为安……我知道,上次你姊来,带你妈的骨灰回来了……我……以后陪我老母亲去……”
随后几天,姨婆开始收拾东西。
“这件,薇薇你小时候要的。薇薇,现在还要么?”她拿出了那件水绿色的丝织旗袍。
“嗯。”我接过旗袍,往身上一挂。旗袍下摆搭在我的脚踝上,凉丝丝地痒。
“薇薇,你大了……”她看着我,眼眸深处,晶晶亮的星星晃动。“薇薇再过几年,该是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呢。婆婆怕看不到了……”她轻声笑了笑,可笑声尚在唇齿间,便戛然而止。
姨婆走了。
姨婆养的猫咪小白哭了几天,蹲在姨婆常坐的椅子上,睁着美人眼看着我。“傻猫,婆婆不会回来了。”我欲上前抱它,可它一个转身,跳下了椅子。它号叫着往前走,走了不远,又重新蹲下,睁大眼睛看着我。
八
亲外婆的相片已从母亲的卧房抽屉挪出,被母亲显眼地挂在书房里。相片中的女子身着一袭素雅的小碎花旗袍,身姿婀娜,细长的眉下一双美目凝视着前方。
我拿出姨婆的那方黑色的脱胎木首饰盒,黑漆漆的盒面上隐隐约约映着我的眼睛。我后悔,我不该将姨婆的头发扔了。
姨婆回去不久,就生病了。她的养子照顾她。母亲每个月定期给她汇钱。我同母亲一起给姨婆去汇钱。我看见薄薄的几张钞票刷啦啦滑过银行小姐的指尖,姨婆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慢慢地薄成一张张钞票。
“又写信过来了,说这个月血压又高起来了……又得寄钱过去,那边怎么照顾的……”
“那……让婆婆回来吧……”我怯怯地说。
母亲沉默良久。
我咽了一口口水。低头。
新年将近。母亲买了一堆的贺卡。我兴奋地在一旁,从中挑最美的,依次递给母亲写贺词。剩下最后一张,俗艳的深红底,热闹的红色团花,红得逼人的眼。母亲蹙着眉,再也想不起该寄给谁了。
“这张……给婆婆寄去吧。”我轻声问母亲。
“嗯,你写吧。”母亲叹了口气。
我工工整整地在贺卡上写了“节日快乐!”就再想不出该写什么好了。我的手心全是汗,濡湿了贺卡的衬纸。
“薇薇”,我在落款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九
姨婆回信了,歪歪斜斜的几个字,尴尬地趴在纸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我宛若收到了烫手的烙铁,把信塞进抽屉里。没过多久,信就知趣地消失了。
姨婆养的猫咪小白下猫仔了。满月后,父亲把猫仔扔了。
猫咪小白天天睁着美人眼,对我哭着要猫仔。后来,它不哭了,鬼鬼祟祟地躲着我。不久我发现它的肚子又鼓了起来,我莫名地慌张。后来,它的肚子瘪了,我却不见猫仔。不到一个星期,它死了。据说是误吃了药老鼠的东西,死在沟里。夜里,我隐隐约约听见猫仔在邻家荒废的院子里哭泣。
“猫仔在邻居家。”我对父亲说,却没看父亲的眼。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无济于事,大人不可能为救猫仔打开邻家早已锁闭多日的院门。
夜里,我提着心寻着猫仔的哭声。它们哭了几晚后,就再没声音了。
收到姨婆的回信不久,母亲就接到姨婆去世的电话。母亲挂上电话,怔怔地,许久不说话。那年的春节,天特别阴冷。我躲在家里,藏进被窝里看书,我的脚冰凉,许久许久暖不过来。窗外劈里啪啦的爆竹声连绵不绝,我起身将鼻子贴在冰凉的玻璃窗上,呼出的热气模糊了窗,阻隔了我的视线。我用食指在窗玻璃上划字:锦瑟锦瑟锦瑟……
被上摊开的书,写着我早已熟悉的诗《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诗页上画着彩图,拙劣的笔触,俗艳的色彩,生生扎疼了我的眼睛。
后来,我开始做梦:我走进了邻家荒废的院子里寻找猫仔。我打开邻居家枝藤蔓生的后院门,闯进了尘土飞扬黑魆魆的楼里。猫仔的哭泣声微弱若悬丝,若隐若现。可我始终寻不到猫咪。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和着猫咪的哭泣声,一下下地响着,惶恐而又无助。
我无数次闯入这个梦境。
悠长的梦,在六年后,我十八岁那年,才有了结局:邻居家的大门开了,出来一个陌生的女子,她告诉我,猫咪死了,不用再找了。
我长吁了一口气,仿佛是早已得知的答案。我明白,有些事,是再无法改变的。时光前行,过往、现在,在我们身后,在我们的足下,寸寸凝固。
忘了吧。
十
填报高考志愿时,长辈们坚持让我读商科,但我还是执意报考了我所喜欢的中文专业。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你读中文,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一辈子清贫,以后会后悔的。”长辈们对我说。
“心正所愿,我不会后悔的。”空灵处,我听见她的声音。
那年清明,我去了一趟姨婆的老家。我带去了一大捧她最喜欢的白茶花。
“喏,那就是妈的墓。妈总说你和她最亲。妈临走,还念叨着你的名字。”她的养子陪着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找着话茬。
“妈说,你肯定会过来看她的。”他蹲下身,随手将墓座边的荒草拔了去。连根拔起的草掀起土,弥漫起淡淡的土腥味。我怔怔地看着他翕动的嘴,声音从他的嘴里吐出,却只滑过我的耳膜,落不到心上。
我抚摸着墓石碑上冰冷的字符:柳锦瑟。恍惚间,我看见许多许多年以前,那个穿着水绿色生丝旗袍的女子,眼眸深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一柄断了的戟,狠狠地刺进了我的心里。时光中的女子,忽地隐去。满捧的白茶花从我的手中滑落。落花飞扬,记忆的碎片如烟消散……
(摘自作者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