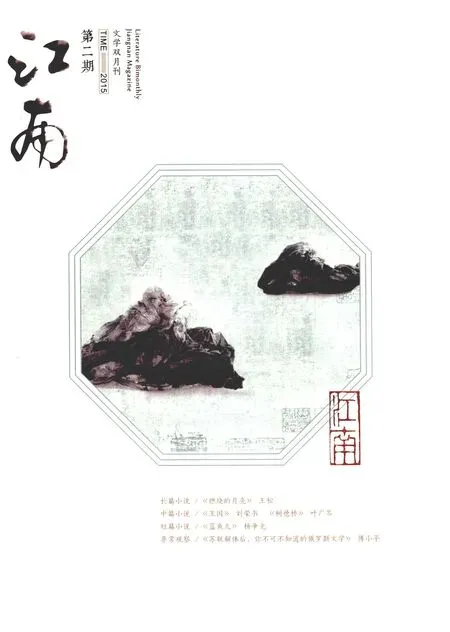刀笔乡
□郑骁锋
刀笔乡
□郑骁锋




这条名号不明的乡间河道,因为师爷而连接着整个中国的水系。数百年来,无数如娄心田那样的安昌子弟,被封藏严密的乌篷船,顺着河水源源不断地送往天南海北的“夫子院”。要过很多年以后,他们才能趁着夜色返航。当船帘被颤抖着掀起,阳光当头射下,重新出现在故乡的游子,原来已是白发佝偻。
就在这一往一返间,乌篷船不动声色地载回了帝国某块版图数十年内所有的秘密。
安昌多桥。短短三里许的沿河古街上,就有十多座,号称“彩虹跨河十七桥”。
安康桥﹑普兰桥﹑三板桥﹑弘治桥﹑横桥﹑安普桥,桥旁有桥,桥外有桥,形状各异,年代不一,从元明清直到当代皆有。
查阅资料方知,这些石桥中,大部分皆为返乡归老的师爷所捐建,即乡人俗称的“师爷桥”。桥之外,“师爷亭”﹑“师爷路”在安昌也是随处可见。
落叶归根,修桥铺路造福乡梓,本是人之常情。只是,因为那位用一生积蓄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的祥林嫂,这类义举在安昌,却不免给我以某种心灵救赎的意味。
无须讳言,“师爷”名号并不能算是褒称,而带有洗刷不去的负面﹑阴性的感情色彩。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就说过,“境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一般概念中,师爷往往被归类为刁钻奸猾﹑贪婪狠毒﹑睚眦必报的小人;即使绍兴本地,乡野闲谈时也常对师爷加以嘲讽奚落。
如此推论也在情理当中:一辈子躲在黑房间捣鬼,伤阴骘的勾当想来少干不了。清人笔记确实曾提到有师爷做了亏心事而夜夜噩梦,最终惊吓而死。周作人也指出,鲁迅《狂人日记》的原型,就是他们的一个表兄弟,在西北游幕时得了“迫害症”而精神失常。
这种印象,固然有失偏颇,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人心良莠不齐,害群之马暂且不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的被师爷奉为圭臬的四句口诀,倒也能让外人对这个行当的性质有所了解。
“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所谓救生不救死,指的是处理杀人案件时,反正被害者已死,还是尽可能不要处死罪犯,避免再闹出一条人命的好。救旧不救新,指官员交接,如有罪责,尽量推给后任,毕竟他有时间去填补。这两句虽有和稀泥之弊,但出发点倒也不失仁厚。至于另外两句,则毫不隐讳地表明了师爷的立场:如果需要做出抉择,他们一概以保全官员,而且是级别高的官员为准则,曲直是非百姓冤屈只能放在一边。
有一个现象值得思索。师爷晚年,多有著书立说者。清代三大尺牍经典之一的《秋水轩尺牍》,作者许思湄便是一个安昌籍的师爷。传世的师爷著述,比如《刑幕要略》﹑《幕学举要》﹑《居官资治录》﹑《审看拟式》,为数不少。几乎每一部,作者都会极力强调幕僚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如“立心要正”﹑“尽心尽言”﹑“勤事慎事”﹑“不合即去”等等。
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幕学著作传授的,却有很多是这一类经验:比如上报案情时必须“晓得剪裁”,根据需要对情节﹑供词﹑人证﹑物证﹑书证,甚至伤痕﹑尸检结果,都可大刀阔斧地加以删削;如此铸成铁案,非但犯人无从翻异,又能左右逢源,回旋有路,就是同为老手的上级幕友也难以识破。
我怀疑这些还是经过了删减的节本。
安昌的文史工作者曾收集到一套包括律例﹑成案﹑公文﹑书信﹑告示以及钱谷账册在内,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清代幕业档案。两百余万字都是安昌师爷孙云章一手抄录,用以训课子孙:师爷一行,多为子承父业亲友提携,每家每户各有心得秘本,绝不对外显露。这也是绍兴师爷为别处不可及之处。
棺材匠与郎中,两者的职业能做出道德上的评判吗——对于安昌人来说,师爷也只不过是一门熟能生巧的手艺,所谓的“吏学”或“幕道”,与打铁﹑烧窑﹑酿酒﹑制酱一样,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通过满足雇主的需要而获得报酬。
善恶都在雇主一念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也归恺撒。
师爷的要价相当高。
每座官衙其实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因为不入朝廷编制,师爷只能由官员以私人身份自行雇用;每个师爷一年薪酬少则数百﹑多则要上千两白银——而一位官阶七品的知县,每年俸禄却只有可怜兮兮的四十五两。
常言道千里做官只为财,背负如此悬殊的亏空,官员们也是没奈何。《官场现形记》云:“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一定要吓得慌作一团。”
几乎所有官员都经历过这种惶恐。三更灯火五更鸡,好不容易修成个官身,不料甫一坐堂,却惊惧地发现,自己苦读半生,到头来却是百无一用。
他们往往连书写一张合格的文书也难以胜任。八股的起承转合,倒也得心应手,可日常公文却截然是另外一套路数。详﹑验﹑禀﹑札﹑议﹑关,一格有一格的禁忌。何况判牍行文只是政务基础,其他如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林林总总乱七八糟,同样一笔在手,昔日纵横捭阖,如今却重如千斤。
并不能责怪他们无能。明清以来,官员事务已经形成一套规范,所有行政措施都得严格依律办理,否则便是“违例”,罪责不小。乾隆年间《大清律例》已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而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愈增愈多,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而这项知识却被严格地隔绝在科举之外,清律三令五申,生员读书期间绝对不准过问地方政治。
因此做了官的文人便必须承受这种所学非所用的错位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原来,入了官场,弦歌而治竟是一个南辕北辙的笑话;若想坐稳公堂,需要的并不是浪漫与激情,而是他们最欠缺的务实与琐碎。
师爷们兜售的就是这样一门手艺。
不过,如果说官员聘请师爷的目的仅在于此,却还仍未勘破那上千两白银的真正意义。我在娄心田故居所见的一则轶事,或可启人深思:雍正初年,本地有位徐姓师爷,精通幕业;某日,忽有使者邀幕,幕金优厚,只是不肯说出主人名字;入馆之后,使者关照,饮食自有人服侍,但绝不能出馆一步;待案卷送来一看,竟都是各省的重案;徐某满腹狐疑,多方打听,但房里服侍的下人却都含糊其词;如此过了两年,来人送他回家,再三嘱咐此处事宜切不可泄露半字;多年以后,他才知道,这位神秘的雇主居然就是雍正皇帝。
此事同样没有注明出处,但雍正对幕业的重视的确屡屡见诸清人笔记。据《春冰室野乘》记载,他甚至还曾在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奏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这位邬先生,便是田所聘用的绍兴名幕邬思道。
邬师爷的事迹近乎传奇:他问田文镜想不想做个有名的督抚,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打包票说这事他能搞定,但有一个条件,他要以河南巡抚的名义上封奏折,不过内容田文镜一个字也不能看;田文镜咬牙赌了一把,结果一炮而红,大获雍正恩宠。只是当他事后终于读到署着自己姓名的奏折时,却吓出了一身冷汗,那竟是封言辞凌厉的参本,参的居然是雍正的母舅,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权贵隆科多!
原来,隆科多跋扈日盛,雍正极想翦除,却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自己又不好出面;如此憋闷之际,田文镜猛然参中痒处,其心畅快可想而知。
抄写应酬,协助长官例行公事,不过只是粗浅功夫;一位高层次师爷的真正价值,正在于此。
顺带提一句,后来田邬二人因事龃龉,邬甩手而去;之后田便事事不顺,屡遭雍正斥责,无奈之下只得再请邬师爷回来;结果邬师爷大摆架子,要求每天在他桌上放一个五十两重的银锭才肯捏笔,田也只能依他。
田文镜脾气很坏,待同僚下属都极其傲慢,但对邬师爷,却一直毕恭毕敬。
为何读懂帝王无法言说的心事的,不是本该倚为肱股的大臣,反倒是邬师爷这群素未谋面﹑游走于灰暗地带的绍兴平民呢?
我居然又想起了入赘并终老于此的禹。
幕学名著《佐治药言》曾用一句话概括过幕道精髓:“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所谓避律,指绕开或者化解各种障碍,以安然抵达目的地。
一定意义上,当年大禹治水,进行的也是同样性质的工程。他的伟大,正是从父亲的失败中,知晓疏比堵更能有效地打开一条活路。
重重淤阻,禹凿开的是高山巨石;师爷们避开的,究竟是什么?
雍正对师爷的特殊眷顾或可对此做出解释。功过另说,雍正的勤勉与务实,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而其主政有一种力图挣脱传统束缚的倾向,如撇开内阁六部,设置军机处直接操盘。此等举措,固然可归结于其权力掌控欲之强,但也未尝不可理解为他在尝试着启动另一套操作系统。
以雍正之清醒,应该能看穿,帝国发展到他的时代,几千年烂熟下来,无论是乾清宫的“正大光明”,还是州府县衙的“明镜高悬”,所有堂皇的冠冕,其实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但就像一口酱缸,必须定时翻捣才不会变质,雍正必须为它的王朝寻找一个新的运行模式。他将视线投射到了缸底的淤泥深处。
在帝国的阴影里,雍正惊喜地发现了这群来自会稽山的手艺人。秉承了治水真传,又经过多年训练,绍兴人已经成为经验最丰富的舵手,探明了帝国所有潜行于地底的隐秘河道,熟知河道里的每一处暗礁﹑旋涡﹑泥淖。水流的每一道细微褶皱他们都了然于胸,足以胜任任何轨迹的航行,只要交给他们两个点,无论之间阻隔着什么,绍兴人都能将其顺利贯通。阳光无法照及之处,帝王与禹的弟子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包括紫禁城,再也没有一座公堂能够离开乌篷船的导航。这支地下舰队最终成为了王朝运转的最直接动力。仅就清代统计,1358个县﹑124个州﹑245个府,全国的师爷总数,已经是一个不亚于正式官员数量的庞大群体。
关于绍兴人独特的口味,外人曾有调侃,说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酱来吃。那三四百年间,整个中国,实际上也被绍兴人酱了一酱。当霉斑与皱纹被酱色遮掩,一种注定的死亡也由表入里,暂时隐匿。
突然想到,成千上万艘乌篷船中,假如某天有那么一艘两艘,猛然掉转方向,会是怎样——
终于该说到那位无法绕过的绍兴人了。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连为一体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什么进去,都变成漆黑。”
“假如有一间铁房子,是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
只要进入绍兴,再迟钝的游客也会感觉到,就像空气,鲁迅的笔力无所不在。
故居,三味书屋,咸亨酒店,固是当行本色,连远离老城区的安昌也不例外。
河街上的“宝麟酒家”很有些名气。掌柜沈宝麟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蓄着半尺全白了的山羊胡,大概喜欢喝几口,鼻头与两颧透着酒糟的颜色。宝麟表情丰富,开朗健谈,常年戴顶乌毡帽,长袍短褂轮替,模仿阿Q或者孔乙己,兴致来了还唱几段莲花落,有趣得很,被公推为安昌的形象代言人。
不过严格说起来,鲁迅大抵对安昌不会有太多好感。他的这段话众所周知:“我总不肯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总不肯”三个字斩钉截铁地表明了他对幕业的厌恶。周作人在谈《彷徨》时也提到:“鲁迅对他的故乡一向没有表示过深的怀念,这不但在小说上,就是在《朝花夕拾》上也是如此。大抵对于乡下的人士最有反感。除了一般封建的士大夫之外,特殊的是师爷和钱店伙计,气味都有点恶劣。”
然而,伴随了鲁迅大半生的笔战中,他却屡屡被对手詈骂为绍兴师爷,而且是手段最毒辣﹑专门用深文周纳陷人于死地的刑名师爷。
当年的是非按下不提。鲁迅对师爷的排斥,我却认为只是当局者迷。肚腹里的反噬才是最致命的,黑暗真正的天敌,只能来自最黑暗处。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
被窒息在同一口酱缸中,当有人终于无法忍受靠着越来越艰难的翻捣才能喘几口气,而是渴望着破壁而出时,只一个决绝的转身,那艘叛逆的乌篷船上就昂然站起了一位鲁迅。
不过这位从“黑暗与虚无”之处走来的绝望战士,其斗争策略,依然还是袭用着师爷的思维: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两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酱缸深处,那支如刀的笔,一丝一丝剜剔着堆积了数千年的冻土,为自己日渐陷入昏迷的族人开辟一条新的航道。
“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我再一次想起了上古那次发生于此处的邂逅。
“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鲁迅·《理水》)
沉重的脚步声中,大禹与鲁迅,两个中华民族应该永远铭记的背影,在师爷的故乡合而为一。
蒸腊肠,茴香豆,臭豆腐,花雕酒。
在只有四五张方桌的宝麟酒家,我叫了几个最绍兴的酒菜,来结束这次安昌之行。宝麟的“老太婆”主厨,他本人则腰系围裙,只管跑堂收钱,得了闲不忘撮起锡壶咂口老酒,再哼上几句小曲耍宝。
学界一般认为,幕僚制度终结于张之洞。张任湖广总督时,废聘幕友,委任在册官员成立“刑名总文案处”,作为督府的正式机关。“各省效之,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若依此来算,中国的最后一代师爷,应该正是宝麟的祖父那辈安昌人——是巧合吗,“仁昌酱园”的创办,也差不多在那个年代。
微醺之际,忽有隔桌食客吃得过瘾,要买几斤霉干菜带走;拎过一杆乌亮的老秤,这位师爷的后人笑嘻嘻地开始了另外一种计算。
呢哝着看秤花时,他不知从哪里摸出一副眼镜戴上。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圆形镜片后面,有道狡黠的光一闪而过。
【责任编辑 谢鲁渤】
- 江南的其它文章
- 南宗孔府记
- 祭典:实非神灵,乃是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