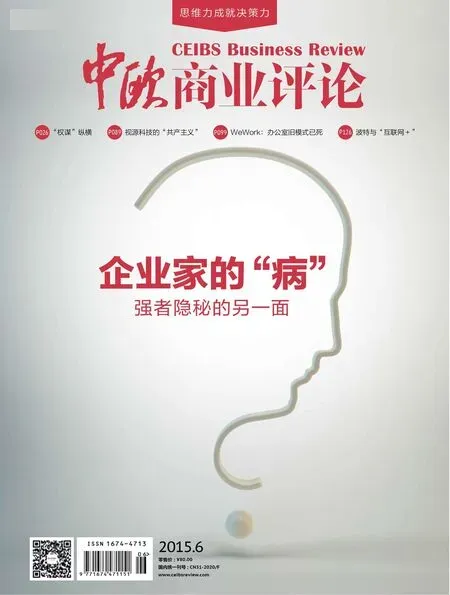一位创业者的抑郁
文/汪洋
一位创业者的抑郁
文/汪洋
“创业者总在试图改变别人的生活,试图在帮助他人实现价值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痛苦是很正常的。”
2014年底的北京,坐拥愁城的周海斌正计划着以一次远行来摆脱内心的束缚,这个26岁青年的心情如同冬天窗外漫无边际的霾,那时,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门了,吃饭靠叫外卖解决。“就是打怵,连出去一趟都打怵”,周海斌说。
在他的印象中,似乎总有一面镜子摆在面前,如影相随,不得不去面对镜中的自己。“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选择了,最好和最坏的选择就是去旅行。”他网购了与旅行相关的书和装备,也做了旅行攻略,总之,他想“走出去”。
创业失败导致的抑郁状态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在周海斌看来,“像放电影一样来回顾自己这段创业中的点滴,包括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电影”已经结束了,人仍沉浸在内心的剧情中,内心的自己坐在空荡荡的“影院”里发呆,屏幕上一遍遍地放着过去的事儿。
岁月中的闪光点
当然对于周海斌而言,过去并非总是那么灰暗,如此年轻,他已经有过好几次创业的经历,前几次都算是做成了,岁月中的闪光点反而让他更难以接受现实。
大学是在广西念的,大二时,他发现同学们会把一些闲置的物品放在校园的BBS上卖,有点无序,于是他做了一个校内物品的交易网,“算是电商”,他说,“一边是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另一边是我们在学校周边找一些餐饮店、特产店以及各类商家,当然还有卖东西的学生,这是一个平台,既是B2C的,也是C2C的。”
大四的时候,他一边准备雅思,一边和同学在一个综合楼的露台开了一家餐厅,他说:“布置得像是空中花园。”同时,他们还办了一个驾校,一边招揽学生,去自己租赁的场地学车,一边在其他驾校购买名额,送学员去考驾照。那个时候他是快乐的,既满足了同学们的需求,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也赚到了些钱。
2011年夏天,事业随着大学毕业而终止,他面临着去英国念书还是就业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一场矿难使得前者变得遥不可及。用周海斌的话说:“ 父母是农民,在辽宁老家承包了一个煤矿,不幸受邻矿的矿难波及,被整顿了,欠了很多债,尽管他们给我预留了留学的钱,但我心里难安。”
他来到北京,因为北京的机会更多,先是进了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他一边在信息可视化实验室里工作,一边为它的产业公司服务,2012年,周海斌被派往鄂尔多斯,那里有一个与当地政府合作的产业化的项目正在落地。
“一个突然崛起的煤炭城市,有很多挥金如土的土豪”,这是鄂尔多斯给他扑面而来的第一印象,他认识了一些同龄小伙伴,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他意识到:“如果每年都在这里生活的话,我就废掉了,这里的生活节奏非常慢,人们关心的只是晚上去哪儿玩,去喝酒。”这在中国很多中型城市中,其实是人们生活的常态。
“我希望这里有一个带点文化的交流场所,于是便在豆瓣网上发帖,众筹了一家咖啡馆,叫做‘很多人的咖啡馆’。”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周海斌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会反复说起“我是个外地人”。
由于没有开咖啡馆的经验,他聘请了咖啡师,不过,咖啡师拿走了一笔不菲的服务费,却没有提供任何服务,反而换了地址和联系方式,跑到呼和浩特复制他们的模式。他和另一个股东追到呼市,但这属于“民事纠纷”,警方只能调解,起诉又不划算,只得不了了之,他因此有点抑郁,但不算严重。而当地的某个酒吧老板以入股为名,在股东大会上突然向他发难,要夺取咖啡馆的领导权,也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但最终绝大多数股东选择信任这个外地毛头小伙,他觉得自己在压力下,还是可以做成点事的。
“我的合伙人先抑郁了”
2013年4月,他回到北京开始了另一场创业,这次创业让他发现创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创业是暴动,是一个‘我’推翻另一个‘我’的暴烈的行动”,把大人物的话山寨一下,似乎也说得通。
他和自动化所的一位老大哥合伙创办了一家青少年创客空间,用自主研发智能玩具的方式教小朋友做机器人,会教一些编程,把编程和搭建结合在一起,简易的智能机器就诞生了。在起初的设想中,“未来是智能社会,相对来言,人也会跟着升级。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从小培养智能社会的居民,虽然目前没有这样体系,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体系,我们将来可以很伟大”。而现实却很骨感,“尤其是当时的环境里,我们做得有点早,北京第一家,市场有点冷,然后就会怀疑自己。我的合伙人陷入了这样的纠结,他抑郁了”。
“我的合伙人的心理落差比较大,他以前创过业,拿到过上千万的投资,公司也成功地卖掉了”,他在周海斌眼里,不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看事很长远的人,每一步都规划得井井有条,当现实和想象发生偏差时,他就会很难接受,“他在科研领域非常厉害,虽然做过企业,过去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实际的执行力差一点”。
合伙人的抑郁越来越严重,慢慢地淡出了公司的运营,他不缺钱,但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他想用这次创业来证明自己,而现实又和理想重叠度太低,“都过去一年多了,他现在还在家猫着呢,黑夜白天颠倒着过。”
“人很容易走进一个中间状态,往理想方向走,现实未必能被调整,往现实方向走,就要去调整理想。如果一个人走不出这个中间状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很可怕了”,周海斌的眼里有一种和他年龄不相称的沧桑。
退出了公司运营,让周海斌感到像堤坝塌方了一片,“有时候少了一个人,不仅仅是团队缺一条腿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们挺互补的,像拉链缺了另外一半,这一半无力地挂着,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面对了,工作变得越来越辛苦,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这件事本身也潜伏着一个隐患,他们在创业的时候,使用的是某科研机构的专利,用周海斌的话说,“起初大家是默许的,当公司正在谈天使轮融资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公事公办了,科研机构不同意以入股的方式分享利益,坚持要我每年向他们缴纳专利使用费。”而价格又是周海斌难以承受的。
公司黄了,周海斌也陷入了抑郁,“我会反复回忆起,我开除一个员工的场景,觉得很难受,认为自己相当虚伪”。他下意识地会去分析自己,把自己的缺点一一放大,“每找到自己不好的一点,我都会为它找一个理由,每天都在逼自己,给自己剥皮,剥到哭”。于是镜子出现了,他不得不直面内心,非常痛苦,“我会发现我是虚假的人,会戴着善意的面具去欺骗人,其实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为了商业上的成功,又去做了一些事,既自欺,又软弱,没担当”。
那时,他偶尔闪过一念,离开这个世界会轻松很多,但又觉得荒唐,毕竟还有父母,自己还没有结婚,以后还要承担家庭责任。“想想也就过去了,就在家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迈不开腿了,张不开嘴了。”
如果一个人走不出这个中间状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很可怕了。
周海斌有一个小香插,在最纠结的时候,便点一支香,抄写《心经》,“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我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平静了一会,又纠结了,我越想让自己平静,内心反而越不平静”。
“我会想起与我接触过的每一个人,我都在和别人分享我的生命,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这是一个剧情。另外一个剧情是,我本来应该干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但是事没有干成,别人会认为我无能。还有一个剧情是,已经这样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把成功与否看得太重要了”
周海斌的想象里,他的同学、朋友、股东、原单位的同事,都觉得他做事情就应该是成功的,自己也觉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不成功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我这个人有什么别的问题?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能力很差劲?会不会认为我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会把自己去和生活不好的人做比较,这个好与不好只是心理状态,不能说吃大餐就好,我凉水泡饭就是不好。于是越纠结,就越想结束纠结,就越陷入纠结,总会拿自己和比自己牛的人比较,心理就处在那种奇怪的状态上。”
后来在网上,周海斌看到一个创业团队在招募合伙人,他们在做一个旅游度假地产的众筹平台,一边是众股东,另一边是那些在风景区经营客栈的项目。“我就和他们聊了一聊,觉得这件事有意思,又是自己擅长的领域——互联网平台和众筹,就加入了。那时候也很纠结,因为我已经决定了要去旅行了。”
最终,他放弃了旅行。他会觉得,如果面前有四扇门,就会下意识纠结,现在他学会了关掉三扇门,而不是非要从四扇门里面选一扇,以前会觉得每个选择会关系人的前途或公司生死,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他说。
他也慢慢意识到,人生中没有事情是不变化的,而且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成功或不成功的。“所有的事都是小事,对我这个小人物来说,更没有什么是轰轰烈烈的,创业更像个生活方式,”周海斌说,“当然,创业和做买卖不同,做买卖也许会活得不错,但创业不仅仅是开一家公司,还得让它运营下去,有的人说不定在创造一个行业,创业者总在试图改变别人的生活,试图在帮助他人实现价值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痛苦是很正常的。”
在雾霾充塞的心情中,周海斌曾经想过去找工作,但又觉得,企业需要的是专才,是在流程里工作的人,自己似乎什么都懂一些,什么也不精,这条路被自己堵死了。
现在他在厦门读一个体制外的商学院,学习与创业有关的课程,也发现“抑郁过”不是他独有的,“有的人是被投资人伤害过,和投资人想法不一致,是选择服从还是坚持自我,难免纠结”。
周海斌说话慢条斯理,少了同龄人的意气风发,眼神有点显老,他说他已经走出来了, “我觉得我有点变态,在抑郁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享受那个状态的,有点像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