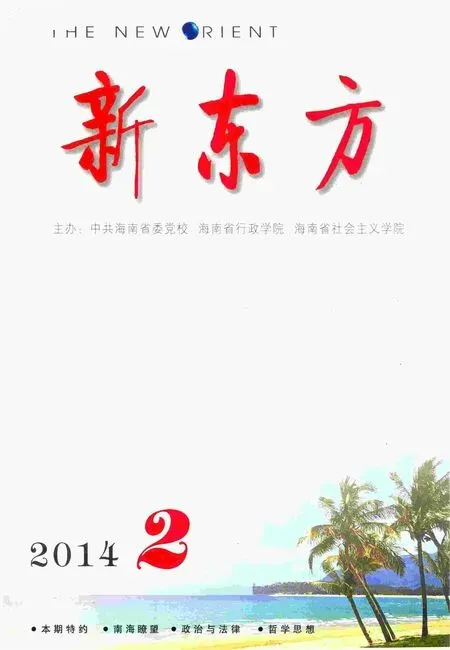浅析国际媒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胡文秀 郝瑞霞
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观念要得以传播,总要经由一定的媒介进行。按照传播学的概念,媒介是指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结构[1]。这种公共机构,就是所谓的媒体。在当代,媒体主要包括三大类:(1)印刷媒体,包括报纸、图书、杂志等;(2)电子媒介,包括广播、电影、电视等;(3)数字媒体,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主要体现。
由于行为体进行互动离不开观念的互动,而观念的互动又离不开媒体,因此媒体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体系中,国际媒体也是有复杂的体系的。这种媒体的体系不但对每一国家具有影响,而且对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互动的整体进程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一、媒体与政治的关系
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媒体不仅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而且还有能力通过事实和信息的选择,影响公众在重大问题上的言论和立场。不过,媒体所传播的信息无论如何包装和加工,归根结底是来源于行为体。行为体需要媒体发布特定的信息,需要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这个角度来讲,媒体是具有工具性的。作为工具,媒体要为各种不同的行为体服务,要传播不同行为体的声音,但媒体从来不是纯粹的机器。尽管媒体传播信息离不开物质技术与设备,但传播过程毕竟是由人进行的,媒体工作者在传播信息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己的认知、情感和立场的影响。这一点决定了媒体本身也是具有政治文化的行为体。它们有自己的意识与意志,有自己的判断,在文化互动中常常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政治属性。由于媒体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为行为体互动服务的工具,本身又是独立的行为体,因此媒体在国际政治文化的互动中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观察媒体的实际运作,可以看到,在任何国家中,媒体都不能免于国家的影响。虽然媒体常常强调自己是中立的,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独立于政治,宣称自己的报道能够完全客观地反映现实,但事实上,它们都需要遵守国家制定的相关行为规范,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其倾向都不得不接受国家权力的限制。
由于媒体在为行为体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会受到政府和行为体的制约,会受到自身的政治倾向与态度的影响,因此它们在谋求完全的“客观”“公正”的时候,充其量只能做到在党派斗争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曾提出,媒体应该永远为进步与改革而斗争,决不向不公或腐败妥协;永远与所有党派的哗众取宠斗争,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与特权阶层和压迫阶级作对,决不失去对贫困者的同情;永远为大众福利而奉献;永远旗帜鲜明而独立,决不因怯懦而不敢攻击错误,无论这些错误是因为权势还是因为贫困[2]。然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媒体在本质上乃是政治行为体,不可能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也不可能高居于政治斗争之上。
作为信息载体,媒体始终是政治互动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媒体能够通过形成社会舆论来影响行为体(即政府)的政治倾向。在现代社会,公众所了解的有关国内和国际问题的信息,主要来自媒体。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众能够得到什么信息。由于媒体在传播过程中都要对事实和信息进行筛选,并且可能通过自己的解释左右公众的情感和对事情的分析与判断,因此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众在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在没有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公众不得不根据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思考,并且很容易先入为主地接受媒体所宣传的观点。一旦媒体宣传的观点变成公众舆论,就会在特定问题上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所曝光的虐囚丑闻,就导致了小布什政府的支持率的下跌,并且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与支持度。从这个角度讲,媒体能够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这也是媒体被称为继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后的“第四权力”的原因。例如,2007年美国媒体曝光沃尔福威茨安排女友的工作的丑闻,沃尔福威茨在各方指责下被迫辞去了世行行长的职务。
从另一个角度讲,政府也可以利用媒体宣传自己的观点,通过改变舆论倾向,调动公众情绪,来营造有利的决策氛围。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利用媒体把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建构成美国的敌人,宣称伊拉克所拥有的大杀伤性武器是对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由于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不起作用,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发动战争。在当时,美国的媒体大量进行这样的宣传,使得美国公众在攻打伊拉克问题上同仇敌忾,形成了对小布什政府错误决策的一致支持。
在美国,政府领导人利用媒体动员公众是进行重大决策的常见做法。在历史上,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就是一种引人注目的与民众沟通的方式。罗斯福在12年的总统任期之内,共进行了30次炉边谈话。每当美国面临重要抉择时,总统就用这种方式对公众进行动员。
由于媒体可以通过引导舆论对政治互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任何国家都不会听任媒体完全不受控制,都会对媒体的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与约束。尽管媒体希望扮演独立的政治角色,但不可能免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当传播与国际问题和国家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时,媒体都需要有一定的“自律性”和“责任性”,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如果涉及机密,那就更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了。所以,任何媒体与政府都存在相互依赖关系。
在媒体与政府的相互关系中,尽管媒体会受到国家行为体的一定的管制与利用,但并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属性。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政治倾向不同的媒体,不同媒体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可能有不同的立场与声音。这一点表明,媒体是具一定的政治独立性的行为体。它们能够独立地参与国际互动,能够对国际互动发挥独立的影响。
二、国际媒体与跨国传播网络的形成
在国际关系中,媒体传播信息与行为体的国际互动是对应的。说得确切些,有国际互动,就有传播国际互动信息的需求。从信息传播的逻辑看,基本的表现就是范围的不断扩散。在这样的过程中,信息传播范围在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机构也在不断扩大。正是这样的过程,推动了国际媒体网络的形成。
这里所说的国际媒体,主要是指那些从事国际信息传播活动的机构与网络。这样的机构,有国营的,也有私营的(目前是以私营为主);有独立机构,也有媒体集团(如贝塔斯曼);有的是以新闻传播为主(如报纸、电视、通讯社等),也有的是以娱乐性业务为主(如影视媒体集团)。与国际政治相关的媒体,主要是指以新闻传播为主的媒体。
当代国际媒体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19世纪中叶哈瓦斯、路透社、沃尔夫等国际通讯社的诞生,开启了国际媒体的信息传播时代。
哈瓦斯通讯社(Agence Havas)是全球第一家通讯社。1825年,哈瓦斯(Charles Havas,1783-1858年)在巴黎创办了一家新闻社,其业务就是从外国报刊上选出法国人感兴趣的报道,然后译成法文,卖给巴黎各家报纸。1835年,哈瓦斯兼并几家新闻社后,正式亮出“哈瓦斯通讯社”的招牌,哈瓦斯也因此成为了通讯社的鼻祖。一战结束以后,哈瓦斯社已控制了法国80%的报业广告,成为法国最大的广告垄断组织。1940年,德军占领了法国,哈瓦斯社瓦解。
路透通讯社(Reuters)是由英国人保罗·路透(Paul Reuter,1816-1899年)1850年在德国亚琛创办的,次年迁往英国伦敦。1865年路透社在欧洲率先报导了林肯被刺杀的新闻,之后声名大振,并于1923年开创了使用无线电在国际间传播新闻的先例。
沃尔夫通讯社(Wolffs Telegraphisches Bureau)是由德国人贝纳德·沃尔夫(Bernard Wolff,1811-1879年)在1829年创办的,它与哈瓦斯社和路透社并称为19世纪的三大通讯社。与后两者的独立自主不同,沃尔夫社从创办之初就与普鲁士王国有密切的关系,表现出官方的性质。该通讯社1933年停办。
在世界新闻发展史上,通讯社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通讯社以精良的设备,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通讯网和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向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机构提供各种消息,使得国际互动中所发生的事能够广为人知。通讯社既是新闻信息的生产者,亦是信息的传播者。
从20世纪20年代起,以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VOA)的相继出现为代表,国际媒体进入了广播时代。英国广播公司成立于1922年,由几个大财团共同出资,公司成立最初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广播传输网络。1932年,BBC第一次向英国本土以外地区进行广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BBC一直垄断着英国的电视、电台。时至今日,BBC已经成为在全球拥有高知名度的媒体。美国之音(VOA)于1942年2月由战时情报组组建,向德国占领的欧洲和北非地区提供盟国的新闻节目。目前它以46种语言通过无线电和电视以及因特网向世界各地进行信息传播。
媒体传播手段的不断发展,使得新闻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传播范围不断扩大,这些都进一步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现在,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际广播,广播一方面有传播新闻和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了政治宣传的功能。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出现的一些著名的电视媒体如CNN等为标志,国际媒体进入了电视时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980年创办于亚特兰大,是全球第一家全天24小时直播新闻的电视媒体,任何突发新闻,CNN都会作现场报道。1981年,CNN率先通过电视报道里根被刺事件而引起轰动。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1年的“9·11”事件,CNN的报道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CNN直播新闻的出现,改变了新闻是已经发生之事的传统观念,让世界各国观众都成为了新闻的目击者,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国际巨型媒体集团的出现,比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等,国际媒体出现了跨国发展的趋势,使得信息的传播与文化的交流成为了国际互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国际媒体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在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世界主要媒体,虽然总部是设在某一个国家,但其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支机构或者记者站,专门负责采集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并进行国际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其信息传播活动穿越了所在的国界,在国外也有较多的受众群体。例如,美国的CNN,总部在美国,而实际上却覆盖了六大洲,每天将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传递给全球一亿多观众。
由于媒体在随时报道世界各地的信息,其传播活动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是以全球民众为传播对象,因此其影响也就具有了跨国性质。国际媒体的跨国传播活动与影响,导致了国际传播网络的形成,在各国新闻发布会现场所聚集的各国媒体就是这种互动网络存在的生动体现。无论这些媒体是发出一致的报道,还是就同一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它们的传播活动都会相互影响,这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文化互动的组成部分。这种媒体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是各媒体互动的产物,反过来,也影响着各个媒体的传播活动。共同的受众与对共同问题的报道,导致世界各种媒体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既是精神性的,也是物质性的。前者是指各媒体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形成的对国际问题的共有认识,后者是指媒体在传播信息过程中通过自身扩张和机构之间的联系而形成的国际媒体网络。
在当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媒体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观念上相互依赖程度都在不断加深。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把全球公众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公众也日益参与到了媒体的传播活动之中。如果说传统的国际信息的传播有传播者与受众之分,那么在网络时代,这种区分已日益模糊。在互联网上,公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与传播者。这样一种变化,其影响是深远的。由于广大公众都在随时随地参与国际信息的传播,因此围绕信息传播而形成的体系进一步扩大了。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在线”的人都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既在物质上(通过计算机)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观念上(共享知识)也联系在一起。伴随着上网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体系也在日益扩大。
由于媒体能够使公众“在线”,因此公众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国际互动,并进而对相关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例如,2008年法国政府对华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就是通过中国民众和媒体互动来实现的。2008年4月北京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遭到了“藏独”的干扰,几天之后巴黎市长表示将要求议会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的称号。这两起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在网络媒体的宣传之下,全国范围内以抵制家乐福为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巴黎政府行为的活动。法国政府被迫采取危机公关,一周之内,法国参议院议长克里斯蒂安·蓬斯莱、法国前总理、人民运动联盟副主席让-皮埃尔·拉法兰和萨科齐的首席外交顾问让-大卫·列维特相继访华。爱丽舍宫随后也传来消息“:萨科齐同意双方要继续深化关系。”[3]
可以说,媒体的发展使得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舞台不同了,演员不同了,上演的戏目也不同了。不但参与互动的行为体在改变,行为体互动的方式也在改变。
三、国际媒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多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媒体通过传播信息,可以造成某种国际舆论,从而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国际舆论是指一种观念,即国际互动中众多行为体在一定问题上所形成的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国际舆论环境一旦形成,就会构成一种规范的压力,倡导某些行为并制止另一些行为。这样的一种“主体间结构”,是行为体从事国际互动的文化环境。
国际舆论作为互动的一种环境因素,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战略决策和具体政策的执行。对行为体来说,如果推行的对外政策与国际舆论一致,就能够得到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取得合法性。如果与国际舆论相反,则会面对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比如,“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形成了反对恐怖主义的舆论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哪个国家敢公开声称支持恐怖主义。在维护人权的问题上,国际舆论环境也有相同的作用。在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人权规范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行为被认为侵犯了人权,就会受到谴责甚至干涉。由于国际舆论总是与一定的规范相联系,因此能够对行为体发挥强有力的建构(社会化)作用,使行为体不得不改变立场与态度,并进而发生观念的变化。
由于国际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行为体的政策乃至对问题的认知,因此进行舆论战就构成了国际政治互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实施对外政策的过程中,行为体为达到改变他者行为的目的,经常会利用媒体工具,试图在观念上战胜对手,瓦解其意志,“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针对古巴政权的马蒂广播电台,针对亚洲的亚洲广播电台,针对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自由欧洲电台等,都是宣传其价值观和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媒体工具。冷战结束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中,西方国家也利用媒体优势,为反对派实现政权变更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在国际政治中,传播媒体所发挥的作用,与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国家形象是指各国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的好坏,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别国对该国的态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使一国有较多朋友,在争议问题上得到较多的支持,遇到困难会得到较多的帮助。一个国家有怎样的形象,决定于人们得到了怎样的信息,并且特别决定于媒体长期报道的积累。如果一个国家常常得到负面的报道,那么该国就会给世人一个不好的形象。有学者对《时代》周刊2003年5月5日至11月24日有关伊斯兰世界的140篇报道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这些报道中,恐怖主义是第一主题,报道中所涉及的恐怖分子全部来自伊斯兰世界。按照这些报道,多数穆斯林是生活在“血腥的日子”里,从伊拉克到沙特、伊朗、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很多人受到非人的虐待[4]。这些新闻报道在经过其他媒体的转载之后,就会在广大的读者群中形成有关伊斯兰世界的负面形象。
由于在国际政治中国际舆论有重要作用,而国际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媒体的话语权,因此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就表现为对国际媒体的主导地位的争夺。谁掌握了主流的国际媒体,谁就掌握了国际舆论导向;谁掌握了国际媒体的舆论导向,谁就掌握了话语权。正如冯·戴伊克所言,话语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各种话语无不体现着社会权势的意志,无不对应着特定的权力结构[5]。行为体掌握话语权,可以突出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屏蔽于己不利的信息,可以对事实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从而造就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倾向。
国际行为体对话语权的争夺,首先表现为对传播媒介的竞争,即谁在物质条件上居优。在当代,传播媒介包括语言媒介、印刷媒介、影视媒介和网络媒介等多种形式。谁拥有最便捷的传播媒介,能最及时地传播信息,谁就可以取得传播的优势。在这方面,行为体的物质实力是基础。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国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直在国际媒体和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按照有关的数字统计,目前占世界总人口不足1/5的西方国家,占有世界信息流量的80%,占有世界图书出口量的3/4,以及音乐市场的绝大部分。在全球无线电频率分配方面,西方国家占据了全球90%以上的资源[6]。在因特网的全部网址中,78%为英文网址,96%的电子商务网址是英文网址,有70%的网址出自美国。在网上的信息,约90%是英语,法语占5%,西班牙语系为2%。网上信息有80%是美国提供的[7]。
在新闻媒体方面,据统计,美国等西方媒体垄断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信息传播。美联社目前的国内媒体用户有5700家,国外媒体用户有8500家。路透社的财经新闻和国际新闻拥有55.8万家的国际订户。法新社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用户。西方三大通讯社的日发稿量相当于由84个国家新闻单位组成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提供新闻量的1000 倍[8]。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在传媒资源的占有上享有超强的地位。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来自美国的占60%—80%[9]。据联合国一项调查显示,全球每周约有25万小时的电视节目播出时段,美国在其中占据了9万多小时,几乎占40%。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75%来自美国。全球联网信息约3/4来自于美国[6]。据统计,世界最大的300家跨国传媒公司,美国占据了将近一半。这种情况导致美国历史学家爱西奥多·怀特将美国传媒比作“世界上最大的传声筒和洗脑系统”[10]。
在信息传播的竞争中,如果说物质因素是媒体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内容质量则是媒体发展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要掌握国际舆论,不但要有现代媒体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有能够说服人的传播内容。就新闻传播而言,尽管所报道的对象都是发生的事,作为媒体应当坚持客观、中立的原则,但由于新闻本身乃是人主观加工的产物,因此与客观真实并不能划等号。在实际运作中,媒体所传播的内容,总是有选择的。现实世界的信息无穷无尽,媒体在发布信息之前,必须进行过滤和筛选,这样加工出来的信息都会体现出传播者的视角与意图。经过加工处理,新闻媒体给受众创造的是一个“虚拟环境”。在这样的“虚拟环境”中,主要的国际媒体通过设置新闻议题,然后对该议题先入为主地发出海量报道,从而不知不觉地影响人们的思维。例如,中国在美国媒体国际报道中的出现频率是较高的,但报道议题却十分集中,主要是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对华贸易问题、汇率问题等。
国际媒体的传播竞争,从时效来讲,主要表现为争夺重大信息传播的首发权或首播权。新闻是有时效性的,谁先掌握了首播权,谁就掌握了先机。比如,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声名鹊起,就是因为在许多事件上取得了首播权。在“9·11”事件中,半岛电视台几乎与美国CNN同步播放了美国遭受袭击的整个过程。在随后美英联合打击阿富汗后,半岛电视台成为唯一获准进入塔利班控制区的电视台。在美国军方到处搜集本·拉登情报而不能如愿时,半岛电视台却频频播放本·拉登的讲话录像。可以说,这些首播的重要信息使得半岛电视台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半岛电视台致力于打造阿拉伯地区新闻自由的努力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
在传播媒体的竞争中,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应当是一个基本原则,但虚假的报道却不时出现。比如,在伊拉克战争刚刚打响之时,美国媒体就报道伊拉克第51步兵师的师长和副师长率8000名士兵在伊南部地区投降,这则消息被多国的媒体转载。但是仅隔一天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伊拉克战争的副总指挥斯坦利·麦克克里斯托少将就表示,这支部队并没有投降[11]。这条新闻被证明是虚假的。这类虚假新闻的出现可能与媒体的不当竞争有关,但也可能有国家或者集团利益的驱动。
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行为体是故意——或者是为抹黑对手,或者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而传播和散布虚假信息。利用媒体作虚假宣传,是有人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就讲过,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为了获得国内公众的支持,就不断释放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息。这些事先精心制作的信息,经过大量的报道之后,成功地左右了公众的情绪与态度,使得美国取得了攻打伊拉克的国内合法性。直至战争结束,美国也没能找到大杀伤性武器,这则新闻也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假信息。美国利用媒体传播虚假消息谋求战争的合法性,尽管最终酿成恶果,使自己陷于泥潭,但新闻媒体的影响与作用却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正是由于媒体对国际关系存在特殊作用和影响,因而世界各国在国际互动中都非常重视媒体的作用。各国外交部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是要通过传播信息谋求国际互动的话语权。发言人总是希望媒体能够把自己精心准备的东西发布出去,影响国际舆论和别国政策,但媒体的传播是有自己的解读与选择的。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发言人的阐释是重要因素,而国家形象则是更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想要影响国际媒体,使之接受自己的话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于媒体在国家外交中有重要作用,因此“媒体外交”也应运而生。媒体外交是新闻媒介积极参与并发挥影响的外交方式。媒体外交最初是指新闻记者和外交官之间的各种活动,现在主要指一国政府通过大众传媒与另一国民众交流,通过媒体向他国民众释放信息,宣传本国的政策,塑造本国的形象,获取他国民众的信任,从而推进本国利益的活动。尤耳·科海恩(Yoel Cohen)在其著作《媒介外交》(Media Diplomacy)中指出:“媒介外交是指新闻媒体与现代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和民众对国际事务兴趣的增长已对外交产生了冲击,反之,政策制订者也利用大众传媒为己服务,同时也对它进行必要的控制”[12]。以他国民众为对象进行媒体宣传,这实际上构成了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的国际文化互动中,媒体提供了物质的平台。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使得行为体之间的文化联系成为了一种便捷、快速、普遍的互动结构。在这种互动中,信息的传播都是经由人实现的,因此各种媒体既是传播工具,又是具有主体性的行为体。它们能通过信息的传播引导国际舆论,并且能够把全球公众都联系在这个体系中。由于媒体对国际政治有巨大影响,因此通过媒体进行舆论战就成了国际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61.
[2]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3.
[3]重压之下法密集公关,一周三政要访华[N].东方早报,2008-04-22.
[4]宋庚一.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建构:以《时代》周刊个案为例[J].阿拉伯世界,2004(2).
[5]庄晓东.传播与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62.
[6]林立民.国际“话语权”:21世纪战略竞争制高点[N].中国国防报,2008-07-29.
[7]苑立强.网络对社会道德的双重影响[N].科技日报,2000-06-30.
[8]韩松,李佩,刘雅鸣,黄燕.浅谈全球化时代我国对外宣传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J].对外宣传参考,2003(3).
[9]徐耀魁.世界传媒概览[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693.
[10]王纬.镜头里的“第四势力”:美国电视新闻节目[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1999:1.
[11]五角大楼的武器: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的媒体及报道 [EB/OL].(2003-06-10).http://news.xinhuanet.com.
[12]Yoel Cohen, Media Diplonwcy:The Foreign Office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 Age,London:Frank Ca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