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金
刘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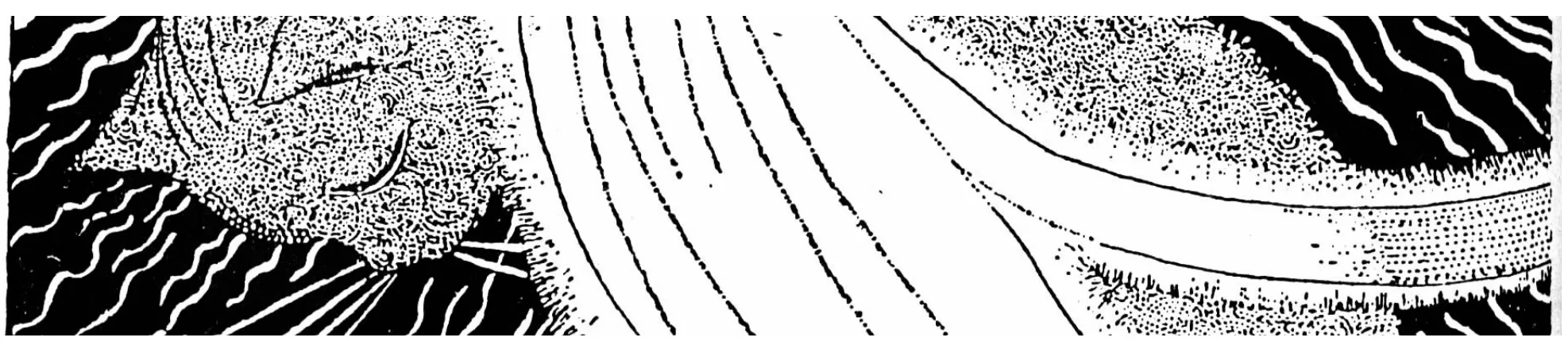
——只是一场恶作剧,当猫从鱼缸中捞出那只金鱼时,故事开始了。你结束了我的孤独,我带你来到这个残酷而美丽的世界。
1
秋天从第一片阳光变成叶子的时候开始,以及一声猫叫。
那是一只挂在我脖子上的黄毛杂种猫,金色和蔚蓝色的双色眼眸,毛茸茸的肉球缠着我的脖子,将自己如挂件般固定在我身上。阳光顺着它的毛流进了我的衣裳。
猫的名叫“肖邦”,与我白藏是“买一送一”的关系。
“北边(偏)东45度,一只接近喵!”它叫道。我立刻会意,看也不看,便将手中的妖刀挥向它所指的坐标,果然有一只“阿肖”。利刃划着优雅的弧线砍下了“阿肖”的脑袋,黑色的血液从“阿肖”的脖子喷出,洒在了阳光颜色的叶子上。
“阿肖”就像老鼠一样无处不在,杀之不尽;我白藏正如此自言自语着,如猫捉老鼠般讨伐着“阿肖”。反正不论身为武神的我,还是“阿肖”,普通人都看不见——不被看见的我们,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构建着独特的世界:
包括我手中的妖刀,脖子上的猫;
以及被我砍断了脑袋,流血身亡的一只“阿肖”。
“阿肖”并不做恶,我也不做恶。我和“阿肖”的关系是樵夫和树,或是猫与老鼠的那种,和谐而相铺相成——我负责杀,“阿肖”负责被杀,我们的世界就可以运作。
仅因为这样的理由被追杀的“阿肖”很无辜,但反正当今的小学生们也总是为了一种自我安慰,不断做算术题,抄写汉字;那些被解开的算术题,被无数次抄写的汉字也很无辜。
而我之所以追杀“阿肖”,或许是因为我太闲了,闲得需要自我安慰。
清晨上课前的停车场,我结束了今天的工作——“阿肖”讨伐数一只,近一个月来的最低纪录,同时也是最高纪录。藏起妖刀,“肖邦”趴在我肩膀上眯起了眼睛。
我躺在一棵挂满阳光的梧桐树上,数着穿蓝色衣服的学生;昨天我数着穿黑色衣服的。“黎城工业大学”,简称“黎工大”的校园无关我与“阿肖”的厮杀,岁月静好如昨日。
而当我数到第三十三人,踩着上课铃走进教学楼的一批人中,我找到了她的身影——
仅一个人晚于人群缓慢踱步,戴着耳机,两手捧着包子细嚼慢咽的模样,显得与周围格格不入。当她经过梧桐树下的时候,有些恍惚的苍白但很漂亮的脸似乎朝我看了一眼。
琉金,是她的名字。经济学院大二年级,有些低血压的女孩;但她看得见我,一个颓废然躺在梧桐树上的可疑男人。
“……猫男!”
只见她色白的嘴唇嘟囔道,就好像在我和“肖邦”的关系中,我才是“买一送一”的附赠品一样。但不顾我朝她扮的鬼脸,她留下一个神秘的微笑,消失在了教学楼的大门里。
如果说在我千篇一律的日常中有任何突破性进展的话,那就是她的出现。
2
能看得见我的琉金,不可能是普通的人类。
一切开始于我的恶作剧——当两年前,我借“肖邦”的手,从女生寝室的鱼缸中捞出金鱼的瞬间,“它”变成了“她”。
名叫“琉金”的金鱼女——不,金鱼公主于同年的秋天入学,除了看得见我之外,过着普通的大学生活,被朋友簇拥,偶尔坐在教室的后排,听着教授的长篇大论,或一整个下午恍惚地浮在泳池的水面上,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有时候,她在明媚的天气敞开窗户,挂着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伸着懒腰。温煦的阳光浓妆艳抹地停滞在她轻轻吹拂的头发上,她有些恍惚的眼睛微微眯起,轻轻地哼起了歌;午后的窗外好像清澈的水潭,升起了一团泡泡。
这样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
她朝本该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呼唤:“猫男——”
“干什么啊?”我从梧桐树冠里探出了脑袋,故作不耐烦地问道,“要是找‘肖邦’的话,现在不在这里哦,它在抓老鼠呢。”
“今天找你呢——话说你不去抓‘阿肖’没问题吗?你又在偷懒。”
我真喜欢这种总是关心我“工作”进展的女孩。
“没问题,没问题——”我悠然飘到了她的窗口,“天下太平,让它们去好了。那么你找我又有什么事?”
“给我讲讲阿神呗——我又有点想不起来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
阿神是她的同班男生,今天早上约她出去一起玩。但究竟是什么时候去,去哪里,为了什么目的,而她是怎么回答的,她丝毫也想不起来了。
她的记忆好像流水,似乎总是在遗忘上一瞬间发生的事情,不论那些是多么平常,多么普通的事;亦或是多么美好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情形——我扶着她的窗沿,叹着气,本周以来第三遍跟她重复:“阿神一定是喜欢你的啦,以前也总是约你出去——你都忘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催促我继续说下去。
“至于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自己猜去吧。”我坏笑着说。
我诚然不喜欢阿神,但我不会干涉她的生活——就算她是因我的恶作剧而生的生命,唯一能看得见我的人类,既然她有可以说话的朋友,可以触及的东西,那么她注定与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所以,有时候像现在这样,扶在她的窗沿上,千千万万遍重复着她所遗忘了的记忆,仿佛给睡前的孩子讲着故事,而她听得不厌其烦,每次都仿佛第一次听说似的,闪烁着眼睛。
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猫”与金鱼之间的小小秘密。
我会在心里什么地方想着,这样的生活能一直持续下去该多好。而若她脸上的阳光能一成不变地延续到明天,那或许对我而言,明天也会是与今天不同的一天。
3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好像在海滩上寻宝的孩子,捡拾着她所丢下的贝壳,一点一点地还给她。但其实,她所丢下的并不只是贝壳——虽然她早已遗忘,而我也没告诉她,但她绝非她自己所想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女孩。
比如她曾在社团遭到排挤,才只能在一个人的时候进入泳池;比如那些簇拥的好朋友们,其实在背后对她议论纷纷;比如那曾在讲台上高台阔论的教授已经被逮捕;又比如她所在意的阿神,是很帅但没有良心的好色之徒,总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但就算她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反正她迟早会忘掉的。
虽然有悖于我不干涉她生活的原则,但这是我唯一的任性——因她的真实生活而伤心,受伤的只有我一人就够了,她不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起那些残酷的真相,揭开好不容易愈合的伤疤;就好像那些普通的人们,也不需要知道阳光的叶子上其实沾满了“阿肖”的黑色血液。
谁让我太喜欢她脸上的阳光呢?
一边给她讲着故事,我心里这么想着。
4
当天晚上,“肖邦”的叫声异常。它竟使劲挠着我的巴掌,把我从酣睡中惊醒。明明已关了它的自动索敌系统,它却有如此反应的,只有一种情况。
“莫非是琉金出事了?”我战战兢兢地问道。
“肖邦”猛一跃跳上了我的后背,肉球紧紧勒住了我的脖子,仿佛在不耐烦地说:“还能有什么可能喵?”严格意义上,赋予琉金生命的是“肖邦”,我相信它的心灵感应。
随即,我感到心底发凉——琉金最终应了阿神的邀请,和其他几名同学去了校外的KTV,但时间已经过了门禁的11点,他们早该回寝了才对。
我原本该跟过去的——但作为“猫”,对一条金鱼死缠烂打算什么?更何况我在琉金面前晃来晃去,而其他人又看不见我,只会让她感到别扭。
事到如今,一切解释都成了马后炮。
若因为我的清高和自作多情,让她遇到任何危险的话……
“你由我来保护。”
——虽然她早已不记得了,而正因为她不记得,我曾偷偷对她说过。
关键时候却不在场的我,连一条金鱼都保护不了的话,算什么。我疯狂地转遍了他们的寝室,但果然大部分人已经回来了,唯独没有琉金和阿神的身影。
琉金喝醉了,所以阿神留下来陪她。隔着墙壁,只听女生们在如此讨论道,但原本一个劲向琉金灌酒的罪魁祸首就是阿神。阿神是有预谋的。
“或许琉金真的会被阿神乘醉下手哦,活该……”
她那些所谓的好朋友们愉快地窃窃私语着。
怎么想都是我的错,若我当时好好提醒她阿神的不良用心,若我不在乎无聊的尊严,跟着她们一起去的话……随即我脑子一片空白,仿佛在云上行走一般。
明明在全速奔跑,却怎么也前进不了。熟悉的校园景象极缓慢地向后推移,空旷无人的马路上,皎洁的月光像一个巨大的水缸,让我溺水般窒息。
冲出校门——险些被一辆急速驰过的丰田撞倒。当终于踢开那家KTV的大门时,只见大厅里一片肃杀:两个早熟的不良学生模样在角落的沙发上缠绵在一起;洒满爆米花的地板上躺着一个潦倒的流浪汉……
“肖邦”从我后背跳了下来,猛撞向了一个大门旁的立地广告牌。
虽然没人看得见我和“肖邦”的身影,但广告牌发出了巨大的声音。服务台后的工作人员惊讶地走过来扶起广告牌,以为是风的缘故。我便乘机翻过了服务台,看到在包厢预定名单的最上面,用潦草的字体写着一个情侣包厢的午夜场——而开始的时间,正好是大伙离开KTV的时候。
303室。
5
各个包厢都在发出噪音——人们对自己的走音总是不知觉,303室却异常安静,鸦雀无声。我冲进房间,瞬间看见了那番地狱——灯光被关闭到了极限,机器也没有运作,大屏幕上的画面定格在“欢迎来到XXKTV”的浮动文字。
还有无处不在的“阿肖”们,到处都是黑乎乎的黑影。
并不大的房间角落,阿神慌张地抬起了脑袋,面色土黄地盯着突然打开的门。他正骑在琉金身上,已经脱下了她的外衣,一只手刚解开了她衬衫的扣子,只见她丰满的胸部和紫色的内衣外露,随着她痛苦的喘息上下起伏。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冷静地观察这一切的。但下一瞬间,不顾混乱的脑海里交错的信号,身体已经踩着娴熟的步伐冲了上去。我听见了自己的怒吼——歇斯底里得仿佛不曾有过这种悲伤和愤怒,而我手里不知何时握着妖刀,毫不犹豫地向阿神的脑袋砍去。
我清楚地感到,那分明是杀人的冲动,几欲把阿神的身体剁成千丝万段的念头占据着我的脑海。
然而,妖刀挥了下去,却如空气般穿过了他的脑袋——取而代之地砍中了一只“阿肖”的胸膛。整个身体被切成两半的“阿肖”喷出了滂沱的黑色鲜血,洒在阿神的脸和令人恶心的时髦发型上。
我撞上了阿神,他仿佛被一个看不见的力量所击中,凭空飞了出去,脑袋撞在墙壁上失去了意识。我半骑在他的身上,反手握紧妖刀,疯狂地大叫着,一遍又一遍地刺向他的胸膛,而妖刀却偏偏一遍又一遍地穿过他的身体。我所恨之入骨的男生只是感到有寒气进入自己的身体,但没有流血,不会受伤。
直到“肖邦”发出尖锐的叫声,我仍没有停手。我踢着可恨男人的肚子爬了起来,如泄恨般一刀砍断了“阿肖”的手臂,切开它的肚子,紧接着是脑袋。
“……我们回去吧。”
如死了一般的声音,从我嘴里缓慢吐出。
6
从很久之前——或许自从两年前,我就一直在心底藏着恐惧,为的是当初因为孤独,如恶作剧般从鱼缸中捞出的金鱼究竟是否幸福。
世界是残酷的,仿佛一摊污浊的水;
仅拥有七秒钟记忆的金鱼,原本就不可能生存。
她脸上的微笑,或许只是自我安慰的产物。而在她心中,或许一直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困惑和痛苦。她该恨着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我。
那些短暂停留在她脸上的和煦阳光,终究是短暂的美好,虚无的时光。像今晚这样的事,其实是迟早会发生的悲剧。
是结束的时候了,我搀着她回到学校的时候,心里这么想着。她身上披着我的外套,微凉的夜晚空气寂寥然拂过她的头发。
当宣告一切魔法落幕的深夜12点,我们站在了女生寝室前——并不是她的住所,而是两年前我潜入的那一栋,所有故事开始的地方。
她醒来的时候,看着我的脸发出了惊讶的叫声:“猫男,你在干什么?”
我沉着脸,向她诉说了今晚的一切——仅这一次,一段完整的残忍故事以及即将发生的事情。她重新变成一条金鱼,我再一次变成孤独一人,和“肖邦”一起讨伐“阿肖”。
可她的脸色显得很忧伤,当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时,我心里猛一颤栗。有什么地方不对,有什么事情——或许是很根本的事情,我想错了吗?她的眼神是这么告诉我的。
“今晚我是真喝醉了,”月光照在她的脸上,苍白而忧伤,“阿神并没有想侵犯我,是我感到胸闷,让他解开衣服的……”
我不想听。
“但还是谢谢你,白藏——你想着来救我,我会很感动的。”
这不是平时的琉金。她从来不会叫我“白藏”,因为她根本不记得我的名字。
“但或许如你所说,是该结束的时候了——”她的口气显得平静,仿佛忍着什么,“我一直以来没有对你说实话,让你这么痛苦……”
她不会用“一直”这种词汇,她的表情总是充满了阳光,不懂思考昨天的事情。随着她的示意,我抬头清楚地看清了那栋寝室楼的面貌——残破不堪的废楼。
这栋寝室楼,在十年前的校园重新规划中,就成为废楼了。而若这是真实的话,我两年前从鱼缸里捞出金鱼的事件就不可能成立——我的记忆存在着严重的破绽。
如此想来,真相原来如此简单——我怎么从来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琉金并不是我的幻想创造出的人类,恰恰相反,我才是她的幻想产物——不被任何人看见,只被她一个人看见的我,原来一直活在她的心里。
“这个世界本身,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鱼缸。”她惨淡地笑着说。
原来,她从来没有失去记忆——不论是那些朋友们的窃窃私语,还是社团对她的排挤,还有其他很多事情,她其实记得很清楚,仿佛扎在心头的针芒。
对她而言,世界就是一个鱼缸,一个逃不出去的牢笼,所以才假装忘却,变成了一条金鱼——碰壁的瞬间就往回游,下一瞬间就已遗忘了自己活在鱼缸里的事实。
千篇一律的故事仿佛第一次遇见一样;痛苦的回忆,也仿佛第一次碰上一样。每一天都充满了阳光。而我——白藏,还有“肖邦”,是在她自我保护的幻想中产生的因素;一只将她从鱼缸带到这世界上来的“猫”,和一个为她讲美好故事的武神。
若可以的话,她一直都不想揭穿。
但当幻想遇见现实的时候,也即是幻想该结束的时候了。
不知怎的,我的眼角没有眼泪——“你由我来保护”,即便我是她幻想的产物,这句话曾是我的真心,我所存在过的痕迹。
金鱼会很快忘记我吧,仿佛埋藏于枕头深处的一场梦。
我由衷地祝福道。
秋天从第一片阳光变成叶子的时候开始,以及一声猫叫。次日清晨,当人们走过梧桐树的时候,只见阳光在和煦的风绪里纷纷而落,满地打滚。
随着猫叫声不知向什么地方远去,仿佛一缕阳光碰着明亮的鱼缸。涟漪不知何时收敛了,世界变得一片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