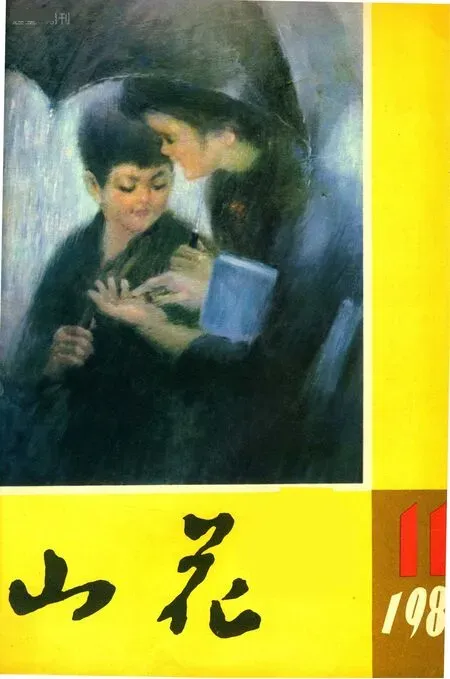潜水史和预防针(组诗)
潜水史
从影子的浩瀚中
居然挤出了这么多水。
如果你想下潜到最深处,
它足以把宇宙的孤独淹没两次。
第一次,你可以辩白你准备不足。
第二次,你可以推说你不想把生活想得太坏。
绝望的美妙,如果以前它过于模糊,
那么现在,它就是刚刚浮出来的一块礁石。
错觉研究
我很不政治。我希望
我的颜色没误会过道德。
我开的花很黄,但绿色
是我的本色。灰色的地带,
有人在小区的院墙外
辟出了一小片天地,
将我种下。从此,我的生死
就不再是一个谜。假如我没能成活,
那不是任何人的责任;
那甚至也不能归结于
命运的疏忽。那最多只是
我的顽强没能在你的口信中
得到及时的总结。我应该感谢你吗?
假如我是否还活着,
已不再牵扯到另一个谜。
一天的时间里,我敏感于
四种不同的声音:早上的鸟鸣,
傍晚时突然密集起来的雨声,
以及仿佛来自一只绵羊的
犹如齿轮一般的咀嚼的声音,
最后的声音集中于收废品的女人
用浓重的方言,喊着这只羊的小名。
一个人同时走在两条路上是可能的
夜色像撒上了黑芝麻。
月光掸去前尘,当着丛林法则的面,
继续打着迷人的死结。
这么安静,甚至连颜色的偏激
也可以是放进嘴里的一枚野浆果。
并无借助鬼魂,或信念,
一个人同时走在两条路上,是可能的。
走在这路上的你,用怀疑的眼光
打量走在另一个路上的你。
会塑造出偏僻的品尝。滋味即责任。
这之后,精神是精神的一个现象,
牵连到我们。或者仅仅牵扯到你。
即便是伟大的死者,也会褪色。
但绝对的自我,仿佛因绝对保持了
一种清醒;对于尘世,它不实用,
不像是一个礼物。说到底,
微波产热是以生物体本身作为热源,进行内部加热,产生电磁辐射的一种治疗方法。微波产热不易扩散到外部,辐射场中的组织受热均匀,热效应好。这种治疗方法不会使患处产生伤口,且微波凝固具有定位准确、治疗时间短、对正常组织损伤小、伤口无需缝合、安全,无副作用、无后遗症以及费用低廉等优点。
没分裂过的人,并非不可能,而是不可信。
往返于早市
从早市上返回的人
基本上是老人和妇女。
有的手里只拎了一小捆茴香。
所以,去那里应该有比买菜更重要的事。
所有的接触都很短,在摊位间移动
似乎不需要特别的眼力,但天灾
和人祸,也都被一一探听到了。
随着太阳的升起,返回的老人和妇女更多了。
哪一种眼光更接近强烈的阳光呢。
他们看上去像是从游泳池锻炼回来。
传神太重要的了,但更重要的是
你得学会捕捉面目背后的东西。
比如,新鲜的青菜,就像生活中的波浪,
浮力巨大,在他们和我们之间
其实毫无差别。而你太年轻,
假如早市像晚年的一个挂钩,
你几乎没时间看清
钩子上,都挂了些什么。
火山下
它的真实是缓慢的。
不同于回忆录里的阶级密谋。
通向它的旅途,被生活碾得如同一根细绳。
轻轻一拽,唯有风铃的低语
还没被爱的记忆收买过。
它从不参与历史或真理。
它理解恋爱中的男人和女人
对风景的依赖。作为一种安慰,
也为了配合我们矛盾于绝望,
它看上去也很依赖风景。
它推敲过人心,有敬畏的,
或没有敬畏的,但它不急于裁断
我们的错误是否已无可挽回。
看待它的角度,有可能是完美的。
它端正自己如一个祭坛。
在附近,激情之门寂静得可怕。
大地的雄辩和宇宙的沉默
统一于它的清晰的隆起,
决定性的参照,哪怕神圣的喜剧中
男女主角轮换的次数已数不过来。
更改了尺寸,甚至底线也被惊动了,
它不断向后推迟有关的悬念;
它仁慈就好像在艰难的世事里
我们有时的确能配得上这样的静物。
预防针
没有人叫你刺猬,如同没有人
叫你鲸鱼。你躺在床上
和掉到漩涡里,没什么区别。
所以你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问
我最后见过的人,是不是狐狸?
表面上,我们有相同的命运,
却从未面对过同样的悲哀。
在我们的秘密中,凭个人机缘战胜死亡
并没有那么难,但我并不想战胜死亡;
所以请理解,最后的话,真的又那么重要吗?
初 夏
这么早。以至于早晨还没出现。
这么早,以至于尖锐地醒来
和美妙地睡去,不像是
你的身体里,独有的一个落差。
已经醒来的东西,不需要新的争论,
已经睡死的东西,不需要新的安慰。
世界的秘密取决于诗,
这样的想法也许有点早。
但是没关系,一个小时后
由纯粹的光织成的地毯仍会准时开铺。
鸟鸣会掀开厚厚的铁板。还算幸运,
并非每一件礼物都取决于你已清醒到什么程度。

荀贵品-《山林漫步》 200×300cm 布面丙烯 2012
它们的目光
幸好,这不是他们的目光。
幸好,这也不是她们的目光。
幸好,还有这样的角落。
即使你看错了眼前的一切,
它们也不会误解春天。
它们不会像你那样过于介意
去年的春天和今年的春天
其实没什么差别。它们也不会申辩
今年的春天和去年的春天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油绿
像一种药:且当着你的面,
挑明了生活是生活的偏方。
它们抬起的头,像小小的彩旗;
它们盯着你看,样子就像从楼下
经过的小贩突然被叫住后,
伸着脖子,寻找海棠树上的声源。
它们的眉目介于瓜苗和树芽之间,
就好像你猜到了它们是谁,
也就猜中了你自己。
真实的选择
曾经有过的体面是
你,可以在体面地面对高山
或体面地面对漩涡之间
做出一个真实的选择。每一座高山
都是一个纪念碑,半真半假地
在纪念它自己的孤独的间歇,
偶尔也纪念一下你的孤独。
它的孤独中,和胜利有关的那一面
仿佛是,它因它自身的高度
而战胜过我们的软弱,以及
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脆弱之间
种种文明的区别。和失败有关的那一面,
可以确定是,它因无法降低
它自身的高度,而失去了你的耐心。
一念之间,它也曾想通过控制它的高度
来亲近你。相比之下,你的失败
要坦率一些。在没有做出选择之前,
你,不可能知道你的耐心,
就是那个可让世界消失两小时的漩涡。
没错。有时,两小时的陌生,
足以让你神秘地体面一回。
墓志铭
原始的恐惧中,我
是一个新的裂缝
也是旋即将它填满的
一块石头。没有人能重新认出
从这裂缝中飞走的
那只蝴蝶。至于石头
它只是不断增加一种记忆的重量
将我吞没的,似乎不是
黑暗本身,而是你
并不在你的黑暗之中
和我们听力有关的魔术
演奏的过程中,灯光
一直像剃刀一样
刮着我的胡须。真相和悬念
叫着劲,暗中争夺着
诸如此类的细节。耳朵里
有一个伟大的舌头,
我们会被舔成什么形状?
就好像我只需再坚持一秒钟,
这旧物,便能把满街的棉花
钢化成广场上的金字塔。
原谅我。一开始,我没想到
你,会需要这样的变化。
也没想到,你会用声音判断
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像我。
碎 片
在海上,漂浮了这么久,
它似乎获得了它自身的命运。
它渐渐从波浪中独立出来,
开始将孤独作为它永久的利息。
同样的漂浮中,我们依然会犯错,
而它却不再有错误需要弥补。
对我们来说,将它复原到
它曾服务过的那个整体上,
就好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里
又添了一朵奇葩。如果你的运气不错,
它近乎于一个完美的迹象,
一个准生物体,和梦中见过的东西
相似到了极点。它的眼睛里,
已成为碎片的东西,无法再碎裂一次。
而它的耳朵里,没什么东西
是没碎过一百次以上的。
它的鼻子里,充满了碎片的气息。
它的背影中,就好像与鲨鱼搏斗过的
那个人,去年还深吻过你。
如果你站的地方合适,
远远看去,它更像一个浮标。
浸泡了这么久,还没褪掉的颜色仿佛在暗示
我们一直在鲸鱼的腹中做爱。
所以说,这样的碎片,是没法翻译的。

陶 发-《田山·阳光》 200×300cm 布面油画 2012
对我们如何观察生命之舞的一个建议
空气的钉子旋转在
我们的内部。每个起伏
都会碰上一个钉子。但即便如此,
你的肺,依然是你的舞蹈。
而我们之所以也会有和你一样的疑惑,
是因为现在,骑在墙上的感觉
实在太像骑在天鹅上了。
你的肺,一直瞒着你在跳舞。
没错,我们差点也被瞒过了。
而空气的钉子,从进入那一刻起
一直就想把这内部的舞蹈
固定在一个隐隐的痛感中。
在你打电话给诗歌之前,
救护车已往返过多次;他们
甚至还从笼子中放出了七八只孔雀,
试图分散你的注意力。
表面上完好的翅膀下
几根骨头已被剪断,我们好像
真的有点走神了:因为我们的偏见
看上去很像这些完好的羽毛。
但假如仔细看,这些孔雀中仿佛有一只,
正跳着你从未见过的舞蹈——
一会儿像替身,一会儿像化身;
甚至对替身和化身的挣脱,也会偶尔闪现一下。
莎士比亚纪念日
因为你,我的渺小不同于
鲸鱼没见过蚂蚁。有两个完全
不同的世界存在,其实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方便。
像你一样,我的渺小
是我的方便。但也有可能,
我的渺小,就如同我走出邮局时
有人贴过来,向我兜售
晃动的长矛。摆脱纠缠后,
我记起,我确实参加过
一些没有硝烟的战斗。
壕沟挖得比坟墓还深。
因为深,苍蝇的奏鸣曲润滑着
血的荣誉。野蛮也没料到
渺小和伟大都出卖过我们。
壕沟中,我读我的渺小
如同你的那些生动的角色
并未能将我穷尽。
一旦走神,我读我的伟大更如同
你的死并未在我这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