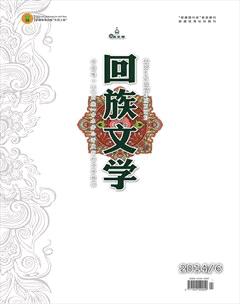悲越天山
打 猎
在东干人主要的聚居区,我几乎都居住过,实际体会了东干人的生活。其实,我的考察也就像探亲访友一样,我已完全融入了东干人的生活之中,因为我们都是陕甘的回族子民,好客的东干人早把我视作他们的一位亲人,让我感动不已。
记得我第一次拜访东干人时,在哈萨克斯坦的新渠农庄村公所里,东干人给我举行了一个小型而又隆重的接待会。会后,我接受了被东干人请来的当地报纸《江布尔州报》的记者的采访,那位女记者是住在哈萨克斯坦的韩国籍人。记得结束采访后,我几句回答的话在报纸上刊登了,在东干人中影响很大。记者问:“你是做什么来的?”我回答:“我是专程看望东干人来的。”她又问:“是不是里面有你的亲戚?”我回答:“是的,他们全部是我的亲戚。”
后来,我和东干人在闲扯中,也开了几句玩笑话,我说:“咱们的祖辈都是陕西人,你们的祖先本事大,腿长,跑到苏联这地方来了。我的祖先腿短,跑了一点路,跑到陕甘交界处就住下了。”惹得他们大笑。
在和东干人的交往中,我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比较惬意。几乎所有东干人聚居的大农庄,如新渠、营盘、骚葫芦等,都有他们的音乐团和歌唱家。平时,在农庄的俱乐部,他们还有打台球的。在新渠还有足球场,虽然简略一些,但土地广大,可以尽情尽意地踢球,况且足球场地并不需什么复杂设施。他们把踢足球称为“踢毛蛋”,这是地道的陕西农村话,我小时也是这么讲的,在这里听起来就很舒服。我住宿的地方,邻居的东干小娃娃也喜欢踢足球,一位叫苏来曼的小男孩还给我童言无忌地讲道:“你看,我会踢毛蛋,一下子把毛蛋踢到阿斯麻尼(天空)上去了。”
东干人也很喜欢钓鱼。若去靠近东干农庄的秋河,可以看到东干人悠闲地在钓鱼。在比什凯克到托克马克公路旁的东干人的田地里,还可以看到一座清真寺,原来是钓鱼的东干人专门在鱼塘边修建的,以便礼拜用。有些东干人还驾车到深山的小湖里钓鱼,说可以钓到远到的西伯利亚的鱼种。这儿地广人稀,钓鱼并不需交任何费用,纯粹是一种消遣。我曾经应邀到秋河小分流中去钓鱼,但我在城市的快节奏中生活惯了,钓鱼总是希望一下钩就能钓到鱼,这种心理使得我并不热心于钓鱼。还好,东干人代我做的鱼竿上有两只鱼钩,结果,一下去就钓到两条鱼上来。东干人高兴地叫道:你我命大,财气旺。
到了炎热的夏季,东干人喜欢到天山里面的风景区去避暑,在这时可以看到从天山上消融下来的雪水在山沟里跌宕起伏,也有去伊塞克湖游玩的。我曾去过天山的避暑胜地,看到许多游客是戴着白帽子的东干人,心里想,东干人很会生活。
我不能忘却的是跟东干人一起打猎的事。我幼小时,做梦也想打猎。记得有一次在集市上买到一只被猎人打下来的野鸡,味道绝美。和东干人闲聊中,说到打猎的事,我便要求一起去打猎。记得当时是5月份,东干人给我讲:“现在的时节不能打猎,因为野兔、野鸡和其他野生动物都正‘抱儿子(野生动物的怀生期)着呢。到了秋冬,才可以打。”
富有的东干人都有猎枪。2002年9月,我算有机会领略了一次打猎的经过。我的东干老朋友侯赛因·安和几位经常爱打猎的老猎手,带着我一起上路了。车上专门载了两条猎狗,其中一条是刚上阵的,一条是经验丰富的老猎狗。东干人对狗也十分偏爱,老猎狗上了车,在车里的后座,看起来待遇很高。我吃惊地看到,那猎狗也散漫惯了,竟然垂着舌头,头一直向前座伸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旅程,秋河河谷的一个广阔的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在雨雾中若隐若现,闪闪发光,令人神往。洼地正前面是一片硕大的湖,四周生长着高过人的芦苇和茂密的灌木丛。虽然已是秋季,但洼地河谷里宛如一座秀丽的花园,一切都是清新的,绿油油的。
我跟着三个猎人,静悄悄进入一条小路,两边是稠密的芦苇洼地,两条猎狗已窜入了周围的芦苇中。不久,正当我失望时,只听见“叭、叭……”的声音,我往上面望去,只见半空中的一只野鸡飞着,鸡毛散落下来,紧接着野鸡坠入水塘中。后来,我们又来到一大块蔬菜地里,侯赛因·安眼疾手快,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举枪打去,两只野鸡已应声坠落在菜地里。真是:
书生随友打猎行,
西域芦香处处闻。
枪起鸡落看不见,
恰似当年东干人。
我们又去芦苇丛中,那条老猎狗窜来窜去,东干人一直喊着“马拉贴子,马拉贴子”(俄语,“好样的,好小子”)。在老猎狗窜入芦苇丛中不久,野鸡又扑棱扑棱地飞出来,枪声过后,打中的野鸡落入湖水中。东干人吆喝猎狗,那猎狗浮入水中,把打落的野鸡叼上来。而那只新猎狗可能嫌路途太远,早已溜之夭夭了,害得狗的主人找了半天。后来回去时,那新猎狗早已等在停车处。
一会儿,这里大风凛冽,阴云遮盖着天空,群山的轮廓消失在茫茫的雾霭中,我们便动身返回。而那只老猎狗仍然不尽兴,一直向远处的芦苇丛驰去。我不时回头看着那远处芦苇丛中飞起的野鸡,扑棱棱地飞走了。这次打猎,我才明白,打猎除了老练、敏锐的好猎手外,优秀的猎狗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闻知及惊起猎物,又可以循迹找到打下来的猎物。若没有猎狗,打猎只能是像打赌一样,仅凭运气了。即使侥幸打了一只猎物,也不知它掉落在哪里。后来,侯赛因·安又给我讲,那猎狗一旦嗅到了猎物,它会潜伏在猎物旁,一只爪子抬起来,等待,听见主人的脚步声就在附近时,它会用爪子去惊动猎物。这次,一共打了七只野鸡,我用双手提着,沿着湖边走回停车处。晚上,东干女人们给我们做了顿野鸡美肴。
在这次打猎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头脑里不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那几位东干老猎手持猎枪、寻猎物的神态,就恰似当年他们的前辈们奋击战场的英姿。同时,我也由衷高兴的是,现在的东干人在异域过上了十分舒适的太平生活。
“石头城”的东干朋友
2005年9月初,当我结束了对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和哈萨克斯坦南部秋河两岸的东干人的访问之后,便乘机前往塔什干,想拜望一下那里的东干人,也想去探望一下几年前认识的居住在塔什干的东干朋友哈肯目·林家,与其叙叙旧。塔什干的东干人在地理位置上讲,应该是距离中国西部边界最远的。
从比什凯克的玛拉斯机场起飞,飞机朝西飞去。从飞机上鸟瞰,秋天的秋河草原,绿油油的田畴,高耸的白杨树,绿树丛中的户户住家和围绕在比什凯克平原田野上蜿蜒曲折的河流,尽收眼底。从机舱口还可以领略到南部雄伟壮丽的天山雄姿。
然而,从飞机上往下看,最美丽的、难以忘怀的景象是几条长长的蜿蜒曲折的河流,似一条条飞舞的银龙,又似那晶莹的珍珠镶嵌在翠绿的吉尔吉斯斯坦大草原上,缓缓地流淌着,田野显得那么宁静与祥和。
当飞机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后,眼下是一片深暗色的沙丘和沙碛地带,没有人烟,没有树木,也没有水源,这种情形直到飞机飞到塔什干(即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附近才有了改观。
塔什干,在乌兹别克语中意为“石头城”,中国古代也把这里称为“石国”。它位于奇尔奇克河流域,城内有几条运河,如萨拉尔运河等。塔什干是一个美丽的充满绿色的城市。
在塔什干城内居住着五十多户(不到一千人)东干人,他们多数从事买卖生意,也有的从事文化教育和政府公务员工作,如塔什干大学的几名教授是东干人,塔什干机场海关负责人也是东干人。接待我的是哈肯目·林一家,哈肯目·林的双亲都是虔诚的穆斯林,讲一口标准的新疆式东干话。从这点上,又难以轻易判断他们是从哪里搬迁来的回民。早在2000年,当我第一次访问东干人时,也是哈肯目·林接待的。东欧剧变,本来在塔什干国家电力公司做电工的哈肯目·林已经辞职,在他家附近的萨拉尔运河旁养起了几头牛和一群羊。据他说,上班工资太少了,一月不到五十美金,不如放牛养羊好。哈肯目·林的父母给我讲,他们的祖先是十九世纪从新疆搬迁来的,现在新疆乌鲁木齐还有亲戚。在与哈肯目·林的闲聊中,四十多岁的他骄傲地说:“我的爷爷从新疆来到塔什干后,开了一家东干餐馆,他会做甜馍,会做豆腐,还会唱中国戏,我的叔父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会讲中国话。”他还拿出其叔叔签过名的著作,是教授学中文内容的,有些内容和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有关,看来他的叔父是有名的人物,中文造诣很深,但署名是用俄文写的,便不知道其中文的名字。哈肯目·林的父母退休在家,哈肯目·林的三个兄弟在塔什干商场做烧饼生意,听说生意不错。在萨拉尔运河河畔,当地居民在一片森林中开垦了果园和菜园。我参观了哈肯目·林的牛羊圈,他养着四五头牛,二十多只羊,还有鸡鸭,牛羊圈有三条狼狗看护着。据哈肯目·林讲,每条狗都有位置,拴在院中的大狗是内卫,门口的是看大门的,而在牛羊圈外四处走动的是外卫,是看外面的情况的。他养的狗见了主人后尾巴一直在摆动着,非常听话。在我的赞美声中,他还自豪地做了实验,在五十米外的回家的桥上,他用手扣住嘴,“嘘——嘘——嘘”地发出长长的口哨声。守大门的狗惊闻哨声后,一会儿便飞驰到主人面前。虽然一直吹口哨,门外面的狗反应却缓慢。他说,那条外面的狗逛野了,不听话了。
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有两万多,大多数居住在靠近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城市附近的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那里是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的主要聚居区,那边的东干人多数已经不会讲东干话了,讲的是乌兹别克语的“东干话”,只是在身份证和护照“民族”一栏里,仍写着“东干人”。
我到了塔什干后,前两次由于时间所限,没有去成中亚名城——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西瓦古城,但和哈肯目·林一起走访了塔什干市郊东南边的东干人农庄——卡拉松农庄(过去曾叫卡尔·马克思农庄)。2007年,我专程去了中亚文明古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应该说,撒马尔罕的清真寺和房屋的精美雕刻技术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新疆的许多优美的清真寺雕刻和设计应该是受到了这里的影响。
我们访问的卡拉松农庄是清一色的东干人农庄,有一百五十多户、三千多人,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最靠近首都的东干人农庄。朋友提前打电话约了当地的东干朋友尔沙,他曾是苏联驻外国大使馆的外交官,现退居在家,讲一口地道的“陕西话”。他说他现在闲了,和朋友做些生意。他用他的小客车载着我们前往卡拉松农庄。在路上,他又叫了几位他的老朋友,说要陪我这个远方来的客人。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尔沙说:“我的父母是陕西人,祖先来到中亚后,先住在营盘。1935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发生‘饿年(饥荒)时,父母带着我们一家人搬到塔什干住下了,因为当时塔什干是中亚的大城。”
小客车向东南方向行驶着,一会儿尔沙指着矗立在路边的一个大土坎说,这是元代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留下的土坎,名字用东干语说不上,俄罗斯语我也听不懂。他指指远处,说在塔什干郊外,相隔十公里就有类似的土坎。我下午仔细察看,郊外原野上的这种大土坎,原来是古时留下的烽火台,很有规模,在野外的平原上引人注目。几位东干人说,若有敌情,土坎上的蒙古兵就会点燃狼粪,狼烟会一直升上高空,即使有大风,也不会被吹散。在车上闲聊中,那位叫尔德的东干人问:“有这么多的狼粪吗?”同车的东干人说,以前肯定狼多。
一路上,我注视着一座座矗立在野外遥相呼应的元代烽火台,想起在十四世纪崛起的成吉思汗,怀着对上天的敬仰,一路跪拜祈祷着,一路又驰骋沙场,同时又在策划着去联合远方的中亚民族,共同战金击宋。不料中亚残暴的花剌子模国王,谋财害命,把几百名蒙古商人杀掉,抢走了财物,于是惹怒了铁木真,他率领强悍的蒙古兵策马西去,一路上踏平了中亚诸国。七百多年过去了,烽火台依然显示着当年的历史面目,就像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日没贺延碛作》一诗中所写:
沙上见日出,
沙上见日没。
悔向万里来,
功名是何物。
约莫一小时,我们赶到了东干人的村庄。从卡拉松东干农庄到去塔什干南郊的大路,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使人感觉卡拉松农庄远离尘嚣,非常清静。庄头是一所中学,读书的多是东干子弟。听说中国曾派来一名老师教授过一段时间的中文,但后来这里的东干学生们因为不大习惯说中文,学习的人并不多,老师最后也走了。
在农庄前有一条长长的溪水,溪水两旁是青翠的树木。在尔沙的带领下,我见到了我一直寻访的一位张家川老乡毛素福。毛素福的名字是我从陕西政协副秘书长冯均平处听到的。冯先生曾说过:“塔什干的卡尔·马克思农庄有位张家川的老乡,叫毛素福,和我们陕西前民委主任毛文祥是亲戚,毛主任见面就责问他,‘你离开了几十年,为什么不给母亲写信,母亲每天叫你的名字,把眼睛都哭瞎了。”冯先生接着说:“毛素福见到了我们,尤其是见到了他的本家毛文祥时,当场就失声痛哭,并且说,只是当时环境所限,写信不方便。”
秋高气爽,我们来到毛素福家的院子里坐下,他的家有左右两排房,北边有水井,还有花园、茶园,风景优美。毛素福和我细说了约两个小时,我才知道他是1962年从霍城县离开中国的,当时他才十八岁。同行的五个人,除了他一人外,其余全都是汉民,他们来自北京、广州、江西和上海。他说,他文化不高,加上是回民,便在当地成了家,一住就是四十多年。文化高的,早就去了法国、美国等国家。来自上海的青年,后来回了中国,因为他家里过去曾是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中国改革开放后给他家平了反,他父母就上门来找,把儿子叫回去了。至于当时来到苏联的原因,他说,当时中国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为生活所迫,他十六岁就到新疆打工,1962年那年,边界开放了,他就跑了过来。
毛素福主要种棉花,问他为何不种菜时,才知道乌兹别克斯坦的改革仍不彻底,田地仍归政府,私人只允许保留小部分自留地,所以种植何种植物和粮食,仍由当地政府说了算。
他的中文还没忘,我手里拿的中文书,他马上说出了书名。给他看了,他也会朗读,也知道意思。他说好多年了,看不到中文书,我顺势送了他几本中文书和杂志。他的生活也挺不错,家园也比较大。
随着尔沙,我又访问了另一家东干人。他姓张,青海湟中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来的,讲一口青海话,也从事农业,是农庄清真寺的老乡。他的院子收拾得美丽无比,各种花卉鲜艳夺目,像城里精心装饰的花圃一样。
姓张的乡老又带我们一行去参观了清真寺。听乡老讲,这是东干人自己捐建的清真寺,边捐边修,所以还没修好。在苏联时期,教门长期得不到发展,现在虽然开放了,但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并不好,1995年这里的人均产值才三百七十五美金。
在清真寺门口,我碰到一位在那里乘凉的东干老人,名叫依布拉热海木,讲一口陕西话。在聊天中知道,他是从哈萨克斯坦东干根据地——营盘过来的,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迁到这里已经二十多年了。后来才明白,这里的东干人多数是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迁徙过来的,其余一小部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从中国移民过来的。这使得塔什干附近的东干人都保留了东干话和回民的生活习惯。一是他们聚居在一起;二是这里的东干人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以及中国新疆的回民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大多数卡拉松农庄的东干人都从事农业,种植棉花和小麦等。居住在首都塔什干和市郊的东干人总数约有四千人,他们也都会说东干话。现在南部的东干人属于真正的老东干人,但和几个主要的东干人居住区隔得太远,而被同化了。
2005年9月4日晚上,我回到塔什干,采访了等候我很久的乌兹别克斯坦东干协会主席麻耐。麻耐现在是塔什干一家农业公司的经理。由于卡拉松和哈萨克斯坦两地东干朋友的电话误传,使他对我到达机场的时间不确定,他说跟儿子去了两趟机场,还用机场的喇叭在找我。
麻耐也是一位东干知识分子,我见到他以前,就见过他用俄文写的《东干人饮食文化》一书。麻耐和我夜谈了很久,使我感到吃惊的有两点:一是麻耐本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程度很高,东干话讲得很地道,他的夫人和小孩的东干文水平也很高;二是我发现麻耐家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文物。通过了解,我得知麻耐是中亚三国东干人中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一个。他家里有中国古画、瓷器、陶器,有明代有名的铜器、宣德香炉等。瓷盘则有宋、元、明、清各朝代的,有的非常大。他用雍正年间的小瓷碗给我泡茶。我说:“我是第一次用三百多年前的瓷碗喝茶,很稀罕啊,打破了赔不起。”他说:“打破了没关系,招待远客就要用古器。”他收藏的中国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属上乘。
麻耐说,他收藏的文物曾放在楼下的停车库,前段时间,他的私人车库进了贼,由于不识货,瓷器都没有动,只偷走了些铜铁之类不值钱的东西。后来他觉得车库不保险,就把大部分精品搬到了家里。据他介绍,这些瓷器都是颐和园里的,很可能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俄军抢掠来的,后来遗留在了中亚一带,有些蓝色的大瓶像是庆贺慈禧大寿的。
当我问起为何收藏中国文物时,他说,从他祖父开始,就喜欢收藏,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知识分子,一直喜欢收藏中国文物。他本人在前苏联塔什干大学搞研究工作时,有机会去撒马尔罕、阿什哈巴德等地考察,闲余时间,就去当地的市场转转,看到有中国图案的文物就收藏下来。有些精美文物非常珍贵,他们是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小儿子从网上下载了香港有关中国文物的介绍,他们就按图案索骥,虽不懂中文,但把收藏的文物和网址介绍的图案一一对照,也可以大致猜测出文物的年代和价值。
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属于古丝绸之路,是中外客商的主道,应该遗留了不少稀品文物。2005年在文莱,我在由马来西亚丁加努州的文物商人举办的伊斯兰文化展览上,亲眼看到了几件珍品。一件是唐三彩,一件是镶有阿拉伯文的中国宝剑。据介绍,这是唐朝政府送给中亚穆斯林的礼品。还有一件瓷器,很珍贵,在国内也没有机会看得到。我想这些都是古丝绸之路上中外关系的历史见证吧!而据熟悉马来西亚文物的商人给我讲,乌兹别克斯坦应该还有类似的许多中国古代珍品。
天色已晚,陪我在麻耐家的哈肯目·林看样子很焦虑,不时在看手表。我问他原因,他说陪了我一整天,他养的牛羊还没吃草,想必是饿慌了。我便开玩笑道:“让牛羊也封上一天斋吧。”他竟当真了,惊奇地问:“牛羊也可以封斋吗?”我回答:“老回回的牛羊也应该封斋吧。”后来,他明白了意思,便和朋友们大笑不已,也就静下心来。
从麻耐家里收藏的这些遗落在中亚各地的文物来看,中亚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据古书记载,早在公元前138年,汉使张骞奉旨出使西域的大宛、大月氏、乌孙等地,虽然没有和大月氏结盟,但大大加强了和中亚的关系,把他们的葡萄、苜蓿、胡蒜、胡桃、胡琴带到了中国。石榴原来也是塔什干的产品。公元前129年,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另外,公元前一世纪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了讨夺汗血马,也曾征伐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西域震惧”。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这里也曾经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唐将高仙芝进攻石国。但在第二年,唐军在怛逻斯兵败,留在撒马尔罕的唐军被俘虏后,在此定居,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欧洲。明代,公元1404年乌兹别克斯坦统帅帖木耳曾率军进攻中国,但在半路上,帖木耳去世,入侵计划因此宣告失败。
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较慢,但生活在这里的东干人因继承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美德,收入普遍不差,倒也其乐融融,过着幸福的生活。
居塔什干数日,时短事急,聚短离长,与热情好客的东干同胞只好长亭一别,不由怅然若失。“今日难得有相见,重逢不知是何年?”
中亚现状观感
中亚,一般是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西域”。
中亚是在十九世纪末并入俄国的。
在十九世纪俄国并吞中亚时,中亚仍处于落后的封建时代。当时,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一直批评沙皇的对外扩张政策。但在这里,连托尔斯泰也承认:俄国占领中亚,给这些愚昧落后的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即使在苏联时代,有些俄罗斯人也批评俄国占领中亚并未占到任何便宜,相反,俄罗斯成了中亚诸国的“一头大奶牛”,中亚各国依靠俄国这个大奶牛的乳汁,发展了现代工业、铁路和教育。
在并入俄国一百多年后的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统治而宣布独立。1991年,中亚等国以乌兹别克斯坦为首,也跟着宣布脱离苏联而成为独立国家,苏联自此解体,改名为俄罗斯联邦。
虽然这样,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仍千丝万缕,俄语仍是中亚通行的语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所有的课本也使用俄语,一些中亚国家的边界还是由俄军驻守。
东干人主要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其中哈、吉两国分别和中国接壤。
我第一次碰到东干人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塔什干”的原意是“石头城”,它是中亚最大的都会,也是中亚农业和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在乌兹别克斯坦居住的东干人共有两万人,在首都塔什干约有一千人,多数是从新疆迁移过来的。在塔什干的郊区有一个东干人的大农庄,叫卡尔·马克思农庄,是营盘和新渠的陕西人迁移过去的,其余的东干人则主要聚集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上的安集延市。
我在塔什干拜访的第一家东干人,是从新疆伊犁迁来的,姓马,有三个儿子,都会讲新疆式的甘肃话。他的第二个儿子带我逛了大半个塔什干城,参观了塔什干有名的清真寺,清真寺里带有阿拉伯文的建筑壁画非常精美;还参观了一座不知名的古老的清真寺,那里有一个古代乌兹别克老学者的地下修行室,又黑又深,转了好多层木梯,才到底层一块圆状的空地。在塔什干并没有东干人的学校,东干人住的地方虽然零散,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东干人都有亲戚关系。
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部城市撒马尔罕是一座古城,也是中国青海省撒拉族人祖先的故乡。据说,几百年前,撒拉族人的一个部落为了躲避迫害,牵着骆驼,带上部落人马,茫茫东去,一直来到东方的中国青海。据说骆驼停下不走的地方,便是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最后,骆驼走到青海循化的黄河岸旁不走了。这就是青海循化撒拉族来源的传说。有趣的是,一百多年前东干人又从陕西往西迁移到了中亚。
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仍保留苏联时期修成的建筑和铁路。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一度提出“哈萨克斯坦是哈萨克人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是属于吉尔吉斯人的国家”的口号。哈萨克斯坦曾有人口一千七百万,国家独立后不久,大约两百万俄罗斯人搬迁到了俄罗斯,使其总人口减少到一千五百多万。虽然俄罗斯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主要政府部门是由哈萨克族人组成。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情形也是一样。
住在这三国的东干人占极少数,但中国人在那里主要侧重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一般不会有激烈性的参与。
在目前的东干人社会中,主要问题是文化教育条件的弱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前苏联时代,东干人的整体教育素质高,因为当时没有民族主义色彩,而且上大学都是政府鼓励并提供费用,这样就使得东干人上大学的人数多。但自从国家独立后,政府不再负担上大学的费用,因此,东干人中上大学的人数便明显减少了。以前,东干人种植农作物和蔬菜,收入很高,生活比较富裕。而独立后,失掉了俄罗斯这头“大奶牛”,种植的农作物和蔬菜价格低,许多卖不出去,经济一蹶不振,生活已受到严重影响。
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以前,在政府、大学等部门有许多东干人工作。独立后,好多大学毕业的东干人被迫去种菜、做生意了。尤其在吉尔吉斯斯坦情况更加糟糕,大学的教授,在2002年,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五美金;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有名的东干研究所,研究员的工资每月只有十五美金左右,有些人一周只好上一两次班,其余时间在街上做生意,当小贩。
我在比什凯克碰到一家东干人,男的叫尔利,以前在前苏联时期的东干人报纸《东方火星报》工作,其夫人上大学时是学建筑设计的,曾在国家设计院工作。苏联解体后,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他们说“再没人管了”,只好在比什凯克一个小商业市场摆卖小百货。看他穿戴的样子,已经不是从前做过报馆工作的专业人士了,而变成了彻底的论斤算两、赚取微利的小贩了。他们很辛苦,市场是开放式的,早晨一大早去摆摊,晚上十点后清货。回家后他说:“累得只想到睡觉,连数钱的时间都没有。”这和我在纳戎碰到的阿不都拉·白彦虎夫妇一样,以前他们是专业人士,现在则开饭馆了。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
东干人的报纸和学校课本,在前苏联时期都由政府负责,现在则没人管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学校从小学到中学的东干文课本,用的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干企业家尤努斯洛夫赞助下出版的。东干文报纸在苏联解体后,一夜之间报馆也解散了。东干人的报纸目前只有吉尔吉斯斯坦的《回民报》和哈萨克斯坦的《回族报》,都是由东干人协会出版发行,有时出有时停,哈萨克斯坦的《回族报》则变成三个月一期。
在中亚诸国,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实力算是最好。哈萨克斯坦国土面积二百七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万,每月平均工资约八十美金,造成吉尔吉斯斯坦的好多大学老师到哈萨克斯坦来任教。其实,哈、吉两国东干人乐意聚居,他们以秋河为界,仅隔一条河,工资待遇则是两个天地。
后来,我也吃惊地意识到,东干人几乎不去银行存钱,多是现金交易。东干人的储蓄是最原始的,他们把挣到的本地钱或哈萨克斯坦的 “腾给”或吉尔吉斯斯坦的“索姆”,都换成美金,存放在家里的柜子里。我一打听,原来他们在前苏联时期在银行存了好多钱,苏联解体时,一夜之间,好多东干人存的货币变成了纸。即使现在,他们把钱存在银行也 “不放心,存得多了,那银行里的就把钱偷(贪污)完了”。所以,在东干人聚居区几乎看不到银行的影子,银行的信用在中亚很差。
东干人的农庄基本建设设施差,尤其公路质量差。公路多是苏联时期修建的,破烂不堪。最可怕的是营盘,这个东干人的根据地至今还没有供水设施,仍从水渠里挑水来使用。
东干人活动的中心——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以前曾是工业城市,前苏联解体后,这里也变得萧条不堪,工厂几乎都停了。我在托克马克旁边的城镇米秋里,看到以前的一个大型水泥厂,据说当时工人达三千多人,设备很好,而现在冷冷清清,被当地东干人租下来,但只利用里面的车间在做三合板。
中亚各国现在正是一个历史的过渡时期。明显地,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帮派制、任人唯亲、不讲信用和贪污现象十分普遍,投资的风险很大。
居住在东干农庄的东干人,多数是农民,对于时间的概念没有城市人那样守时。一次,东干人请我去参加一个农庄大型集会,通知说是早上十一点。我依约十一时准时到了农庄大礼堂,结果一个人都没有,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人才陆续前来。后来,根据经验,请客参加大会在约好的时间一小时后行动,那才比较准确。因为农庄大,东干人活得也潇洒。2001年,我在新渠农庄碰到从陕西来投资的两批人,第一批是由陕西来的回民在新渠农庄西边修建旅馆和文化中心,当时房子正在修建,我刚来这里,情形并不了解。而第二批人是从陕西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准备投资筹建番茄加工厂,因为东干人种的西红柿大,品种又好。这时,我已对东干人的生活作息特点以及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有了了解,觉得投资不太现实。由于我来这里是以采访为主,对于其他事持不参与态度,所以对此事闭上了嘴巴。2002年,我又去新渠时,看到那西安回民修的旅馆院里长满蒿草,而那家房地产开发商投资近八万美金的番茄加工厂,也已孤零零地矗立在田地里。不过,另一位西安来的人合资建的养鸡场还较成功。这里属于农村地区,又地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交界地带,海关管理混乱,手续繁多,投资环境比较散乱。所以,在这里投资,应该经过详细的考察才可进行。如果来观光旅游,这里则是一个自然景观非常优美的地方。
中亚国家的宗教信仰,除了乌兹别克斯坦比较正统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前苏联七十多年的影响下,就像俄罗斯的《独立报》1993年1月13日所报道的那样:“吉尔吉斯民族从来就不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道德沦丧,在吉尔吉斯斯坦全国五百多万人口中,就有五千多人是艾滋病患者。
我在和东干人的交往中发现,东干人对俄罗斯人的印象普遍较好。他们认为“毛子” (指俄罗斯人,有些人也习惯称之为“猴”)讲公道,文明高。是的,最早是俄罗斯人保护了东干人,又帮助东干人创造了东干文字。俄罗斯人也对东干人的勤劳、朴实很欣赏。后来,在前苏联期间,东干人有较高的生活水准,上大学的人也多,文化水准相应也高。
我在中亚,通过和东干人的交流,也亲自和俄罗斯人见面,有了交往,使我改变了过去对俄罗斯人的看法,同时也增加了对俄罗斯的好感。我欣赏俄罗斯是个伟大的民族,有正义感,文明高,心胸宽广,也热爱自然,培养出了伟大的天才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还有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和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等。
可贵的是,东干人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伊斯兰文化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成为一个文明、勤劳和成功的民族。
中亚的局势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期。
(本文选自刘宝军长篇纪实散文《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题字:李兰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