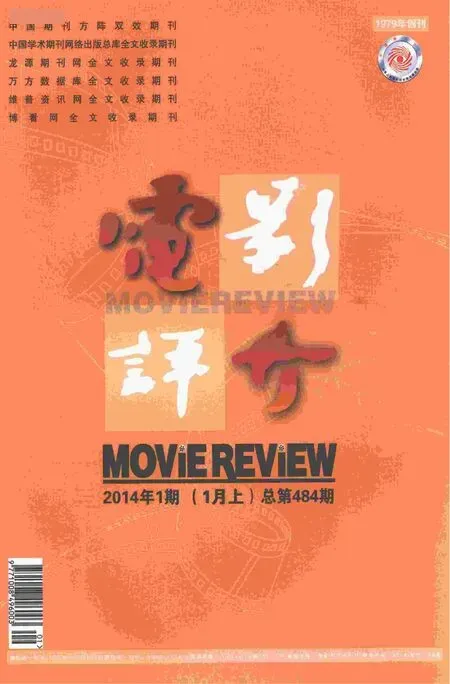漂流的精神世界——解码李安电影中的隐喻
□文/吴福泰,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剧照
李安的3D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除了剪辑方面有些瑕疵之外无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它的精彩不仅在于真实生动的3D 场景和形象设计,还在于该片是可供多种解读的文本,这也是其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李安电影自身建构起一个独特的文本阐释场域,在这一场域中‘马赛克主义’的各种理论话语都可获得其阐释空间,对于李安电影文本展开某种程式的解码。”[1]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根据一部同名小说改编的。说的是印度少年派跟随动物园园长的爸爸和妈妈及哥哥一家人准备迁往加拿大。途中不幸在海上遇到大风暴,派全家不幸遇难,只有他自己侥幸地上了一个小船,却意外地遇上了逃命爬上来的老虎,猩猩,猎狗和一只摔断了腿的斑马。经过动物之间的厮杀,最后只剩下老虎。于是派与老虎在小船上的斗智斗勇又相互依存中开始了一段奇幻的漂流之旅。如果故事到派最终被救上岸之后结束,那么影片不过是《鲁滨逊漂流记》的翻版,充其量不过是表现人的生命意志的坚强、果敢与大自然斗争的无畏精神。李安用故事套故事的方式将上述情节大大复杂化了。当影片结尾派对日本记者道出第二个故事之后,影片的分量骤然加重,观众的思维霎时间仿佛穿过了小小的地球进入太空,人们开始咀嚼品味着片中所深涵的寓意。因为影片给人思考的空间太大,内涵实在太厚重了,观众大多是带着疑问或者思考走出影院的。诚如片中派对两个日本记者说的,“这个故事是你的了,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句话也是对每一位观众说:“这个故事是你的了,你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毋容置疑,导演李安通过影片向我们展开了一扇“罗生门。”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海报
网上影评普遍认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有隐喻的,但具体隐喻什么却众说纷纭。我认为靠谱一点的是人性与兽性的结合与分离。显然,影片中的派与老虎是结合体“人”的两个方面,即人性和兽性。如果细细品味影片,我们不难发现,片中的两个故事,其实相比之下后一个故事更符合历史真实。换句话说,派能够漂流那么多天活下来,是靠食人肉活下来的。根据派的描述,具体细节是厨子杀害了水兵并吃了他的肉,接着杀死了派的母亲,派愤怒之下杀死厨子并吃了他的肉得以最终存活。这里显然暴露了人作为动物的兽性一面,是自然而真实的。与此相对,影片第一个故事人在与大自然搏斗中展现的人的坚强和无畏精神,表现了人的人性一面。片中很大篇幅表现了派与老虎的搏斗,其实质是表现人的兽性与人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最后老虎决然而去时,代表着人最终从兽性中分离,人依靠了上帝依靠了信仰,意味着人终究靠人的理性生活。
然而,“对于同一个李安电影文本,两种本质对立的理论话语可以同样取得阐释的胜利。”[2]在笔者看来,对《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大大拓展开去。相信李安选择此剧本拍摄,肯定会添加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进去,要参透里面的思想和精神,还得从李安影片的一贯思路说起。
从台湾电影父亲三部曲《推手》、《饮食男女》和《喜宴》开始,李安就开始了用电影表达自我的精神信仰之路。从这三部影片看得出,一方面,李安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是被“西化”了的人。另一方面,作为黄皮肤黑头发的李安,骨子里流淌着东方人的血,这个事实和基因是改变不了的。更何况东方文化如影片中的中国书画、武术和饮食文化等等在李安眼里是那么的富有底蕴和魅力。这种东西方文化血统的矛盾促成了李安电影人物心理总是常常表现出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于是李安借这三部电影试图调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李安并没有在这种文化冲突中充当和平的公证人。应该说李安内心的精神信仰是有倾向性的,并且表现出一定的发展轨迹。如果说在《饮食男女》影片结尾处吴倩莲主演的具有西方文化教育背景的二女儿最终回归家庭传承了父亲的老屋和厨艺(象征中国文化)昭示着作者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有所偏向东方文化的话,那么到《喜宴》里,作者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向西方文化转向了。此片结尾代表中国传统的父亲最终向儿子屈服,同意儿子组成了包含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三人家庭。2000 年《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奖,在笔者看来,《卧虎藏龙》影片中的三角关系,周润发扮演的李慕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杨紫琼扮演的俞秀莲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已久和长大成人的子民,而章子怡扮演的玉蛟龙则是渴望自由渴望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弄潮儿。2007 年李安的《色·戒》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中争议的焦点是王佳芝竟然爱上了汉奸。可在我看来此片的政治隐喻并不在汉奸,而在于作者明显的追求精神自由的政治隐喻。
21 世纪以来,台湾电影追求自由独立的本土意识大大加强。2008 年魏德圣的《海角七号》轰动台湾影坛,整部影片都在表达台湾土著居民被外族文化侵占后的压抑和焦虑以及本土意识中对自由独立的渴望。“在《海角七号》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相互渗透的关系构成了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经由这个‘模棱两可的,伪装的,模拟的第三空间’,主体的参照维度开始模糊,台湾与大陆、日本的关系也变得暧昧不清。”[3]《海角七号》凸显了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以及台湾对日本的“他者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文化的植入,“成为台湾电影最危险的他者认同。”[4]
事实上这种隐含的政治诉求在台湾电影人心中并非个案。无独有偶,去年钮承泽导演的《赛德克·巴莱》就是一部用暴力反抗外族入侵政治隐喻非常明显的台湾电影。影片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本土独立。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该片表现了日本外族入侵,但影片一大部分表现的却是土著两个部落之间的内斗,与此同时,作者花了不少情节表现日本阵营里的友好人士。由此可见,“地理景观不是一种个体特征,它们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或者说一种文化的——信仰、实践与技术。”[5]台湾电影兴起本土意识热潮并非偶然,这是当前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结果。与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几乎所有的影片都反映了香港人的压抑、彷徨和苦闷一样。台湾人其本土意识身份认同的诉求也在台湾电影中得到展现。
回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如果根据上面的思路来分析此片,不难发现,李安在影片中继续了他一贯的政治隐喻。如果思维仅仅局限在老虎是人的兽性的象征,那么我们会遇到理解上的困境。首先整部影片,老虎在与派的斗争中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强烈的兽性,相反倒给我们某种人性的感觉。比如老虎接受并感激派为他抓鱼吃的行动,听从派的呼唤一起逃离食人岛等等,获得自由后进山之前也并没有把昏迷中的派吃掉更是有力的证明。由此可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真正隐喻并不一定是指人的兽性和人性的结合与分离。
在我看来,李安此片中隐喻用自由文明和野蛮传统的分离更为贴切。影片末尾,派凄惨地看着老虎决然地走向森林,与《卧虎藏龙》里李穆白看着玉蛟龙绝然而去有异曲同工之妙。当老虎头也不回地走向大山深处的时候,意味着李安完成了他的精神信仰已经从家长制的传统东方文明向民主自由的西方文明漂流而去。
[1][2]吴迎君.“马赛克主义”的面孔——文化研究视域中李安电影的总体特征[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2):110,109.
[3]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0.
[4]洪帆,张巍.隔岸观火——台湾电影的“后独立时代”到了?[J].电影艺术,2009(3):56.
[5](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