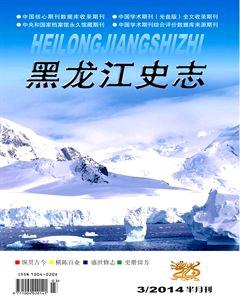日本当局与上海南市安全区成立关系初
探于宁
[摘 要]抗战初期,法国神父饶家驹(Jacquinot)等人在上海南市建立的安全区拯救了大量中国平民。然而与南京安全区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南市安全区的研究相对薄弱。虽然安全区存在期间屡经磨难,但是由于上海南市的特殊区域位置和饶家驹的个人声望,日本当局对南市安全区(Nantao Safety Area)的存在基本持默认肯定态度。
[关键词]抗战;难民;日本;南市安全区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战火燃烧到富庶的“东方明珠”——上海。当时上海每天因战争不断产生大量的难民,如何妥善收容、安置他们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沪的各慈善团体纷纷成立收容所等临时机构,为难民提供食、宿等基本生活保障。上海南市安全区即是由法国神父饶家驹(Jacquinot)等人筹划建立,并一直运作至1940年6月30日。在此期间南市安全区在方圆三公里的区域内,收容了总计约30余万难民。[1]饶家驹等人筹建上海南市安全区拯救难民的事迹经报纸的宣传赢得了广泛的世界赞誉。八一三抗战之后南京沦陷后,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等人受饶家驹(Jacquinot)鼓舞在南京筹建南京国际安全区。
一、难民问题的产生
1937年淞沪会战的爆发,不仅导致中国人民的巨大伤亡和财产破坏,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10月初,上海附近的难民已经不下一百三十万人。[2]大量难民涌入当时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寻求庇护,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3]当时两个租界所能控制的区域所辖人口仅近一百万,但租界当局不愿也无力承担救助如此多难民的重任。因此为防范难民冲击,战争爆发后不久,公共租界当局布设铁丝网、设置路障并派出军队在边界巡逻,严加戒备。8月15日,法租界公董局更是宣布戒严,关闭租界与外界的铁门阻止难民涌入。战争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不得不露宿街头饱受饥寒之苦,还不得不忍受着来自日军炸弹、炮火等袭击,生存处境极其艰难。
二、南市安全区的建立
为使难民免遭不幸,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复旦大学操场、徐家汇等地设立6所难民收容所,其他一些慈善团体、同乡会等组织也纷纷尽力为难民提供一些帮助。此时担任震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的饶家驹神父鉴于法租界周围聚集了大量难民,希望在附近划出特定区域设立安全区以安置众多的难民,为此他四处奔走,很快便得到了受难民问题困扰的租界当局支持。但建立安全区的关键是必须要得到中日双方的首肯。9月21日,饶家驹在与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的一次谈话中,尝试提出了建立安全区的想法,日方却没有给出切实肯定的答复。[4]11月初,随着战事的紧迫,战局对中方已明显不利,安置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刻不容缓。中方出于对设立的安全区主权归属问题的不确定,唯恐其成为变相的租界,故对此一直未明确表态。然而上海市政府当局迫于形势,在饶家驹的积极斡旋和保证治安权归中方管辖的情况下逐渐打消顾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认为饶家驹的安全区的建议“纯系友邦人士热心人道之举动,颇甚钦佩,故已予考虑”[5]。最终上海市同意在战火破坏较轻,仍保留不少闲置房屋和许多公共场所的南市划出一块区域作为难民的避难所。
在中方态度明朗化后,饶家驹向日本驻沪领事冈本季正报告了协议,冈本表示欣赏饶家驹公正的立场,赞成合作设立安全区,并表示将通知日本地方驻军和海军的司令官们。冈本本人也对饶家驹与中国当局-无论是民政当局还是军政当局的商讨都十分满意,因为这有助于防止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6]11月3日,日本媒体也证实日本当局将支持饶家驹的计划。[7]
11月5日下午,饶家驹再谒中日双方,获知已正式批准,于是公开宣布划南市北部为难民区之建议已获中日双方之同意。[8]南市难民区的边界在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的三分之一面积,方浜路以北,民国路(今人民路)以南,方浜桥以东,小东门以西。南市难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宣言称“难民区不受任何形式的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根据于11月9日下午5时正式接纳难民。[9]安全区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监督下,由上海国际救济会负责,并成立了以饶家驹任主席的南市监督委员会共同管理,而中方仍保有主权。[10]中国方面则派出警察负责维持治安。
之后不久,随着日军在南市开展军事行动,南市安全区面临着危机。南市城厢多是老旧的木结构建筑,在日军的攻击下燃起熊熊大火,时刻有蔓延至临近的安全区的可能。[11]但日军名义上还是尊重安全区的存在,没有针对安全区进行大规模的炮击和轰炸,这稍微缓解了南市安全区面临的战火危机。
淞沪会战后期,随着战事的恶化中国军队陆续撤离上海,安全区治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日军时常搜查安全区。11月12日随着日军完全占领上海,最后一批中国警察也被迫撤离安全区。[12]安全区不得不与日军协商派出宪兵巡逻以维持治安。11月12日,因一名日军士兵在临近安全区的边界上遭到枪击,日军派出部队对安全区进行逐户搜查。凡通入南市之各街巷,皆有持刺刀来福枪之日兵把守。[13]日方发言人也开始质疑安全区是否有存在的必要。[14]12月11日,日军又对安全区进行了搜查。12月16日,在进行搜查中的日军又一次遭到袭击。这一系列事件的接连发生引起了日方的强烈不满。面对主宰上海的日本占领军,南市安全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饶家驹不得不出面与日军进行谈判。饶家驹再一次展现了他出色的外交能力,在达成的声明中日方称“继续遵守它们与安全区达成的协议诸条件”。[15]此后,经过多次谈判,安全区与日方达成新的协议,安全区继续由难民委员会管理,日方只是在治安方面给予协助与合作。[16]
南市安全区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赢得了日方的尊重。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封信中也承认“南市安全区的成立,从而让大约10万名和平无辜的中国居民免遭厄运”。甚至日方领导人出于某些目的为安全区进行了部分资金捐助,如日本驻华中方面军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捐助难民委员会1万日元。[17]
虽然如此,但安全区与日方当局和伪上海市政府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1938年12月3日,日本驻军曾将南市安全区的与租界间的电话线切断,后经饶家驹的据理力争才得以恢复。总体说来,日本当局囿于上海的国际影响,不敢贸然破坏南市安全区的中立性。因此,南市安全区得以顺利的保留至1940年。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南市安全区的工作运转卓越成效,仅从成立到1938年4月,共收容难民38393人。[18]1938年之后一方面随着上海周边环境逐渐趋于稳定,许多难民开始重返家园;另一方面欧洲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德国入侵并迫使法国投降。诸多因素导致南市安全区存在的价值逐渐降低,最终于1940年6月30日正式关闭,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南市安全区作为抗战时期成立较早的难民区,其成功经验被其他地区纷纷仿效,如杭州、汉口、广州等地,特别是著名的南京安全区。
三、结语
日本当局之所以支持上海南市难民区的设立,并基本未与其发生大的冲突。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上海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上海是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心,境内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居住着大量的外侨,可谓是“中西交汇、华洋杂陈”,蒋介石称为“中外观瞻之所系”。当时,上海还有诸如《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大陆报》等英文报纸,每天新闻报道充斥着上海的各种消息。南市难民区临近法租界,担任难民区管理人员的外侨很多是工部局的董事,[19]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鉴于此,日方既要顾及采取的行动产生的国际影响,又要树立日军的良好形象。所以日本占领军当局在安全区不危害日方的统治的情况下,对其一般活动基本不会横加干涉。
其次,安全区给难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建立基本秩序以减少对平民和城区的破坏的活动也是对日本占领军的统治是有利的。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拥有大量的工厂企业和人口。日方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也不希望城区遭到严重破坏。战争产生了大量的难民,需要为其提供食物和居住地。在日方看来这在无形中增加自己的负担,而此时安全区当局愿意提供食物和场所解决难民问题,资金除部分来自国民政府的拨款外,很大程度来自慈善机构举行的募捐,加之上海南市难民区保有较好的市政设施和法租界自来水厂的饮水供应系统,这一切客观上等于帮助了日方。此外,安全区内承诺绝不允许保有军事设施和驻扎军队,[20]客观上也有利于日方军事行动的开展。
最后,饶家驹神父的崇高声望和杰出的活动能力。提到上海南市安全区就不能不提他的发起人及主要领导者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饶家驹1913年受教会指派来华传教,先后在上海虹口教区担任神父,并担任震旦大学教授等职。饶家驹在上海积极投身社会慈善事业,声望昭著。1931年,长江水灾时他曾协助宋子文组建国际水灾救济委员会,并担任饥荒救济委员会负责人。[21]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他和上海万国商团的贝泐(F.Hayley Bell)少校拜见日本海军司令野村吉三郎达成了停火四个小时的协议,并在协议时间营救250名平民。[22]长期的社会工作使饶家驹神父赢得了上海社会各界的信任、尊重,1924年中国政府授予他勋章。[23]此外,饶家驹还担任公共租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饶家驹本人具有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流利的日语和高超的谈判策略,使他易于与日本当局的沟通,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日方高层也被其个人魅力所深深折服。与他谈判的冈本领事、日本外相纷纷对他义举表示钦佩。这一切为南市安全区的建立和日常运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参考文献:
[1]张化:《饶家驹与南市难民区》,文汇网 http://culture.whb.cn/article/view/21075.
[2]《立报》:1937年10月1日,载罗义俊:《南市难民区述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编委会编:《抗日风云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3]《立报》:1937年8月31日,载罗义俊:《南市难民区述略》,《抗日风云录》(下),第172页。
[4]《饶神父救护难民热忱》,《申报》:1937年9月23日,第5版。
[5]罗义俊:《南市难民区述略》,《抗日风云录》(下),第175页。
[6][美]阮玛霞著,白华山译:《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第71页。
[7]《朝日新闻》:1937年11月3日,载[美]阮玛霞著,白华山译:《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第71页。
[8]《密勒氏评论报》发行《中国的抗战》第一集第94页,载罗义俊:《南市难民区述略》,《抗日风云录》(下),第175页。
[9]《南市难民区实现 昨日开始收容》, 《申报》:1937年11月10日第5版。
[10]《Safety Zone Declared Open To Residents》, 《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37年11月10日第1版。
[11]《南市火焰仍炽》,《申报》:1937年11月22日第五版。
[12]《南市警察 最后一批退出》,《申报》:1937年11月15日第5版。
[13]《日兵开始搜查》,《申报》:1937年11月12日第5版。
[14]《Japanese Soldiers Again in Zone》,《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937年11月12日第7版。
[15]《南市难民区用水问题解决》,《申报》:1937年12月14日第5版。
[16][美]阮玛霞著,白华山译:《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第82页。
[17][美]阮玛霞著,白华山译:《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第84页。
[18]《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视察组报告书:民国二十七年七月至十月 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监察委员会监视组报告书:民国二十七年十月至廿八年四月》,1939年版6月版,第47页。
[19]南市监督委员会:麦克诺登准将担任副主席,来自上海工部局和英商公会;普兰德是美商公会会长、上海工部局董事等。
[20]《Safety Zone Declared Open To Residents》, 《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37年11月10日第1版。
[21]张化:《饶家驹与南市难民区》,文汇网 http://culture.whb.cn/article/view/21075.
[22]《字林西报》:1932年2月11日,载[美]阮玛霞著,白华山译:《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第46页。
[23]耶稣会档案馆(Archives des Jésuites,Vanves,France)“饶家驹”,第1页,载[美]阮玛霞著,白华山译:《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