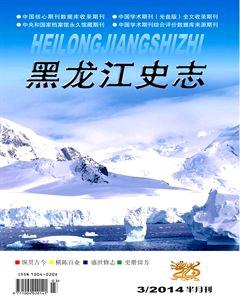晚清法界人士的民法观
石璠
[摘 要]在晚清变法修律的过程中,处于变法修律最前沿的法界人士对民法为规定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这一属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民法的重要性也已引起了法界人士的注意,他们也已经认识到民法与民事诉讼法是主法与助法的关系,主法宜在助法之先制定。制定中国自己的民法典一定要进行民事习惯调查也是法界人士的共识。此外,在民法的立法宗旨与立法模式上法界人士也已经有较成熟的看法。
[关键词]晚清;法界;民法观
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法界人士,在晚清的变法修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处于变法修律的最前沿,他们更容易接触到西方以及日本的最新民法知识和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民法观念,建立在这些民法观念之上的立法建议和主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清廷民法修订活动的展开和民法的样态。沈家本、张仁黼、俞廉三作为晚清修律部门以及法律实务部门的主持者,他们对民法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晚清法界人士对民法的认识状态。
一、沈家本的民法观
作为修律大臣的沈家本“是深了解中国法律而且明白欧美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1),他对西方的民法知识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并以较为中国化的方式在人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进步主张(2)。在主持修律的过程中,沈家本以“会通中西”的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具体的修订民法的建议。
对于民法的性质,沈家本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开馆日期并拟办事章程折”中说:“民商各法意在区别凡人之权利义务,而尽纳于轨物之中,本末洪纤,条理至密,非如昔之言立法者仅设禁以防民,其事尚简也。”(3)他认为,民商法是用来规定普通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而这类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涉及面广,且其理论博大精深,与以往仅用来防范人民犯罪的刑法是不同的,它比刑法要复杂得多。
有鉴于此,沈家本对民法的制定非常慎重,尤其是对民事习惯的调查非常重视。他在上述同一奏折中主张“广罗英彦,明定职司,以专责成而免旷误。……拟设二科,分任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之调查起草”(4),并在其后的奏折中指出:“中国现定民商各律,应以调查为修律之根柢,此事极有关系。”(5)然而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风俗习惯差异较大,民事习惯的调查也非易事,对此沈家本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上奏的“法律馆咨议调查章程折”中称:
臣等自开馆以来,督同提调各员昕夕考求,悉心体察。凡关于东西各国法制,先以翻译最新书籍为取证之资,事虽繁重,尚有端绪可寻。惟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纤悉周知,恐创定民商各法,见诸实行必有窒碍。与其成书之后多所推求,曷若削简之初加意慎重。臣等公同商酌,谨拟咨议调查章程,分缮清单,恭呈御览。……其调查员即由臣等随时遴派,期收广集众思之益。(6)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沈家本又与俞廉三以及各军机大臣商议民商各法的修订宗旨,仍强调了习惯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各地习惯多不相同,又由于国家交通不发达,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相对较少,在短时间内各地习惯难于统一,在修订法律之时先将部分局部习惯予以吸收,等到国家发达、新的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再注意对一般习惯的吸收。《东方杂志》第六卷第七期对此记载如下:
人类通行之习惯各因其地,苟反而行之,则必为人所摈弃而不相容。故各地方之习惯亦有强制力含其中者,是以国家法律承认之,或采之为成文法。然所谓习惯者,有一般习惯与局地习惯之不同。一般习惯可行于国内之一般,局地习惯只行于国内之一部。国家当交通机关未发达时代,往往局地习惯多于一般习惯。我国现时修订法律,似宜承认局地的,采为成文法,庶得因应而便实行。俟各省一律交通,法律逐渐改良,然后注意一般习惯,于修订法律甚为便利。(7)
宣统二年(1910年),在总结商事习惯调查的基础上,民事习惯的调查正式开始。此年正月沈家本上奏:
窃维民商各律,意在区别凡人之权利义务而尽纳于轨物之中,条理至繁,关系至要。中国幅员广远,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洞澈无遗,恐创定法规必多窒碍。……而民事习惯视商事尤为繁杂,立法事钜,何敢稍涉粗疏。臣等公同商酌,拟选派馆员分往各省,将关系民律事宜详查具报。并分咨各省督抚饬司暨新设计之调查局,造具表册,随时报馆,庶资考证。(8)
随后修订法律馆制定了《调查民事习惯章程十条》,重申了民事习惯调查的重要和复杂,提出了具体的调查方法。(9)可见,沈家本不仅认识到民事习惯调查对民法制定的重要,制定了具体的民事习惯调查的方法和步骤,而且对于中国民事习惯调查的困难以及立法对习惯采纳的困难已经了有较理性的认识。
在具体的民事立法技术上,尤其是民法典应采取“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沈家本也有自己的主张。在此问题上,翰林院内阁学士朱福铣奏请采纳日本民法学家梅谦次郎的学说,将民法和商法合一编纂,并延聘其来华主持修纂。沈家本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对此作出了回应:
臣等伏查欧洲法学统系,约分德、英、法为三派,日本初尚法派,近则模仿德派,心慕力追,原奏所陈确有见地,臣等自当择善而从,酌量编订。总之无论采用何国学说,均应节短取长,慎防流失。原奏又称日本修正民法时梅谦次郎曾提议合编,以改约期近,急欲颁行而不果,中国编纂法典之期后于各国,而采主义学说不妨集各国之大成,为民商法之合编等语。查自法国于民法外特编商法法典,各国从而效之,均别商法与民法,各自为编。诚以民法系关于私法之原则,一切人民均可适用,商法系关于商事之特例,惟商人始能适用。民法所不列者如公司、保险、汇票、运送、海商等类,则特于商法之中规定之,即民法所有而对商人有须特别施行者,如商事保证、契约利息等类,亦于商法中另行规定,凡所以保护商人之信用而补助商业之发达,皆非民法之所能从同。合编之说似未可行。10
也就是说,沈家本认为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从法国创立开始,得到欧洲各国的仿效,其原因在于民法是私法一般法,适用于所有的普通民众,而商法是私法特别法,只适用于商人,商法中的一系列特殊规定不是民法所能代替的,因此,反对民商合一的模式,而采民商分立的模式。
二、张仁黼的民法观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向清廷上奏了一封关于修订法律办法的长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民法观念。其奏折云:
一明订法律宗旨也。国之所与立者惟民,一国之民必各有其特性,立法者未有拂人之性者也。西国法学家,亦多主性法之说,故一国之法律,必合乎一国之民情风俗,如日本……民法五编,除物权、债权、财产三编,采用西国私法之规定外,其亲族、相继二编,皆从本国旧俗。……特闻立法者,必以保全国粹为重,而后参以各国之法,补其不足。此则以中国法系为主,而辅之以罗马、日耳曼诸法系之宗旨也。
一讲明法律性质也。中国法律,惟刑法一种,而户婚、田土事项,亦列入刑法之中,是法律既不完备,而刑法与民法不分,尤为外人所指摘。故修订法律,必以研究法律性质之区别为第一义,而区别之要有四:一、国内法与国际法之别,二、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别,三、公法与私法之别,四、主法与助法之别。盖此四者不外乎国与国,国与人,人与人三种关系。……人与人之关系,则属乎私法。……私法如民法、商法是,……而修订法律之要者,则在主法与助法之别,盖主法为体,助法为用,如刑法及民法为主法,而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为助法是也。有主法而无助法,则徒法固不足自行,主法虽精,而助法未臻完善,其行之也犹不能无弊。且也主法不可纷更,而助法则可以屡变,盖主法一有改移,则于人民权利之得失多少,罪罚之轻重出入,即相悬殊,屡事纷更,是使民无所措手足也。……
一编纂法律成典也。……近者修律大臣等所订之民刑诉讼法,本甚简略,而窒碍难行者,已复不少。且民事诉讼法,当以民法为依据,今既未修订民法,则民事诉讼法将何所适从,未免先后倒置。至民法为刑措之原,小民争端多起于轻微细故,于此而其平,则争端可息,不致酿为刑事。现今各国皆注重民法,谓民法之范围愈大,则刑法之范围愈小,良有以也。……凡民法商法修订之始,皆当广为调查各省民情风俗所习为故常,而于法律不相违背,且为法律所许者,即前条所谓不成文法,用为根据,加以制裁,而后能便民。此则编纂法典之要义也。(11)
从此折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在民法制定与民情风俗的关系上,张仁黼认为立法应合乎一国之民情风俗,并举日本民法亲属、继承二编的编纂为例加以说明,主张中国注重礼教道德的传统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法系的特色之一,立法应当以保全此国粹为重。第二,在民法的性质问题上,张仁黼认识到中国民法不发达,民刑不分的缺陷,提出要根据不同法律的性质分别立法。他认为刑法是公法,规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民法为私法,规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法律的主从或者说体用关系,认为民法、刑法等实体法是主法,规定人民之权利多少、罪罚之轻重,因此,不宜多变而宜稳定;诉讼法等程序法是从法,规定办事程序,应随时随事予以改进,因此,变动可以较频繁。第三,在立法顺序问题上,张仁黼认为立法应遵循一定的次第,如果无民法则民事诉讼法即无存在和推行的依据,因此,应先有民法而后有民事诉讼法,清廷先定民事诉讼法而后定民法是先后倒置。第四,在民法的社会作用问题上,张仁黼认为“民法为刑措之原”,民法的调整和适用范围愈广,刑法的调整和适用范围就愈窄,如果小的纠纷能够以民法来解决就不会酿成刑事纠纷而带来刑杀。最后,对于不成文的民事习惯,张仁黼肯定了其作为裁判依据的效力,提出,只要是与法律不相违悖,且为法律所允许的民事习惯可以作为不成文法,用于裁判,这样做可以方便民众。
三、俞廉三的民法观
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民律前三编告成,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上折呈请皇帝御览,在此折中修律大臣对于民法之性质、民法典内部之体系以及民法典编订之宗旨做出了论述。其内容大略如下:
窃维民律之设,乃权利义务区判之准绳,凡居恒交际往还,无日不受其范围。探厥旨要,尤在存诚去伪,阜物通财,促使国民日臻上治,功用之宏,既较刑事等律为綦切,撰述之法,实较刑事等律为更难。况我国幅员寥廓,迈越前朝,南朔东西,自为风气,若不注重斠一,诚恐将来颁布,难获推暨之功。臣馆曾经延聘法律学堂教习·日本大审院判事·法学士松岗义正协同调查,并遴派馆员分赴各省采访民俗习惯,……依据调查之资料,参照各国之成例,并斟酌各省报告之表册……初称完备,呈由臣等复核。
夷考吾国民法,虽古无专书,然其概要备祥,……至今未替,此为中国固有民法之明证。各国民法……其编纂配置,有主张人事法与财产法前后之别者,如拉丁派与日耳曼派所争之主意是。有主张物权、债权前后之别者,如日耳曼派中所争之主意是。而法族之异同复分拉丁系、日耳曼系、折衷系、俄罗斯系四种。……折衷者如日本民法以财产法为先,瑞士民法以人事法为先,而物权先于债权,则为二国之所同。各系以形式论,皆依罗马,不过大同小异,以实质论,各按己国之民族,不无彼此之殊。凡此皆中外民法源流之大较也。此次编辑之旨,约分四端:
一、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瀛海交通于今为盛,凡都邑、钜埠,无一非商战之场,而华侨之流寓南洋者,生齿日益繁庶,按国际私法,向据其人之本国法办理。如一遇相互之诉讼,彼执大同之成规,我守拘墟之旧习,利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是编为拯斯弊,凡能力之差异,买卖之规定,以及利率时效等项,悉采用普通之制,以均彼我而保公平。
二、原本后出最精之法理。……各国法律愈后出者,最为世人注目,义取规随,自殊剽窃,良以学问乃世界所公,并非一国所独也。是编关于法人及土地债务诸规定,采用各国新制,既原于精确之法理,自无凿枘之虞。
三、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立宪国政治几无不同,而民情风俗,一则由于种族之观念,一则由于宗教之支流,则不能强令一致,在泰西大陆尚如此区分,矧其为欧、亚礼教之殊,人事法缘于民情风俗而生,自不能强行规橅,致贻削足就屦之诮。是编凡亲属、婚姻、继承等事,除与立宪相背酌量变通外,或取诸现行法制,或本诸经义,或参诸道德,务期整饬风纪,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敝。
四、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匡时就弊,贵在转移,拘古牵文,无裨治理,中国法制历史……以私法而论,验之社交非无事例,征之条教反失定衡,改进无从,遑谋统一。是编有鉴于斯,特设债权、物权详细之区别,庶几循序渐进,冀收一道同风之益。……(12)
此折发出的时候已是清朝覆亡的前夕,从清廷宣布变法修律到此时,已历近十年的时间,西方以及日本的民法知识已经在晚清人士中间传播开来,尤其处于变法修律活动中心的法界精英们,对于民法也已有了较为系统和科学的认识。在此折中,俞廉三等首先对民法的性质和目的进行了界定,认为民法乃是区别权利义务的准绳,它规范人民的日常生活,制定民法的目的在于“存诚去伪”、改善民风、促进经济的发展。接着,阐明了民法制定过程中需要对民俗习惯加以调查和吸收,否则难于适用的观点。随后,他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虽无民法专典,但是有关婚姻、债负等民法规范是有的,只是散见于各种典章当中。此外,对于民法典的内部体系结构,俞廉三在考察了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瑞士等国后认为,人法与物法、债权法与物权法的先后次序根源于本民族的传统,没有也无须整齐划一,中国可根据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安排法典的体系结构。最后,俞廉三等给出此次民法编纂的四项宗旨,分别是“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即是为保证国人在对外交易的过程中能获得公平利益,在制定民法典时,有关行为能力、买卖、利率以及时效等问题的规定,要与世界通行的法律规则相一致;“原本后出最精之法理”,即是法律学说并非一国所私,中国制定民法典在有关问题上可以采用本于最新法理的各国新制,这样就不会与之格格不入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即是由于中国民情风俗不同于他国,在人事法即亲属、婚姻、继承等问题上除了与立宪根本相背的需进行一定的变通之外,主要内容仍应本于道德经义,以维持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即是法律的制定不可拘泥于既有的规范,而应以有利于治理为目的进行改进,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四、总结
总结来看,晚清法律变革过程中,这些与变法修律有着密切关系的法界人士对源自西方的民法已经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首先,在民法的性质问题上,法界人士普遍认识到民法乃是规范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准则,是私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规范国家与个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公法,正因为其所规范的关系是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以所面临之问题的复杂程度是禁令性质的刑事法律所无法比拟的。其次,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也为法界人士所肯定,他们认为民法应该属于国家基本法律,它与传统上最重要的刑法是并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刑法更重要。同时,民法与辅助民法实施的民事诉讼法是“体”和“用”的关系,是主法和助法的关系,先有“体”,然后才有“用”,先有主法,助法才有制定和实施的准则。因此,在法律制定的次第上,应该先制定民法,后制定民事诉讼法。再次,注重民法制定过程中对中国的民俗习惯的吸收是晚清法界人士的共识,他们认为为了更好地掌握中国的民情风俗,进行民事习惯调查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不成文的民事习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应当可以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最后,在民事立法宗旨和具体的立法技术上,晚清的法界人士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观点,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和世界民法发展的趋势确立了“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之法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等四项民事立法宗旨,并在此宗旨之下采用了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这些宗旨和立法模式的选择表明,随着清末修律活动的展开,法界人士对源于西方和日本的民法知识已有了较成熟和理性的认识。
注释:
(1)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
(2)参看李贵连、俞江:《论沈家本的人格平等观》,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3期。
(3)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4)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5)“修订法律大臣奏馆事繁重恳照请经费数目拨给折”,载《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第六十一号。转引自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6)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7)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8)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261页。
(9)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10)“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议复《朱福铣奏慎重私法编别选聘起草客员折》”,载《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第三七三号。转引自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
(1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奏修订法律请派大臣会订折》,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4~836页。
(1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奏编辑民律前三编草案告成缮册呈览折》,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1~9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