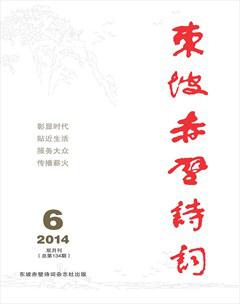我的乡村 我的乡亲
刘能英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生活很是清苦,虽说是天天生活在田园之中,可对田园生活实在是熟视无睹。再加上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所以一直到离开农村前,我都不曾写过诗词,更谈不上田园诗词。当然读过、背过的田园诗词不少,有古代先贤的,也有当代名家的。
那个时候感觉田园生活并没有诗人笔下描写的那样好,或者说是我对诗人笔下的描写不屑一顾。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篱菊有啥好采的,能当饭吃吗?南山见了又如何,还不天天是那样。我羡慕的自然是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所以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我一直把跳农门当作唯一的梦想。也许是老天格外眷顾我,让我有了两次跳出农门的机会。第一次是高考,让我从农村到县城。第二次是签约,从县城到北京。
在县城的时候因为离老家很近,每逢双休或是节假日,还得回家帮父母收割小麦或稻子,不能算是完全地跳出农村。所以对田园还是热爱不起来。随着回家次数的减少,以及劳動强度的减弱,还有就是温饱不再是头等大事,渐渐地再回来倒多了几分亲切感。及至结婚后回家,父母就基本上不让我插手农活了。这个时候的我才有一点点闲情逸致,采采东篱的黄菊花,看看天边的大别山。或是逛逛旧街的庙会,走走宋渡的浮桥。于是雏鸡试步地写了几首诗词。其中一首《鹧鸪天·春景》还获了黄鹤楼诗词大赛玉笛奖。这给了我极大的肯定与鼓舞。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失去了创作的兴趣。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作品总是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思想。尽管我努力了很多年,依然得不到改善。以致我在后来的写作中,就有意或无意地避开了乡村,避开了乡亲。
去年,接到来北京的通知,一看地址是草桥,便倒吸一口凉气。不是让我来京城吗?怎么还是农村啊。来了之后才知道,草桥其实就是个地名,跟田园和乡村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也许很久以前是有过关系的,这个我也懒得去考证。到北京后,真正地享受了一番大都市的热闹与繁华。然而开心过后,便是“地铁公交走走停,晓霾吹尽晚霾生。”“想见那长安夜阑珊,却恨这交通,堵生无奈。”“酸肩痛臂,拎着油和米。难得此时人不挤,地铁换乘公汽。”每当我被雾霾包围,每当我堵在途中,就特别想念家乡“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想念“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想念“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想念“东风吹淡野梅香,春树长池塘”;还有那“竹篱上演缤纷,黄昏虚掩柴门。偶尔一声犬吠,忽然生动乡村”诗意般的生活。
也许只在这个时候,我才深刻地体会到,我所生活过的乡村,是那样的恬淡宁谧,是那样的诗意洋溢。我所接触过的乡亲,是那样的勤劳善良,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我才知道,为什么古代的士大夫喜欢隐居在乡野之间。
春天来的时候,我似乎看到我的乡亲翻土犁田,各自忙碌的身影。我似乎听到柴门开合,鸡鸣犬应,人试镰刀的声音。
夏雨过后,绿杨已经摇曳生姿,连翘半熟,棉花开始封行,草莓大面积挂果。我似乎看到我的乡亲脸上的黑汗在流淌。似乎能感觉到他们咚咚的心跳以及深深的忧虑。不知道这一季的西瓜能不能换来好的收成。
秋风乍起,篱菊孕意正浓,笑待花开。潺潺流水,不管不顾地奔向远方。芰荷立残照,村树晚归鸦。我仿佛看到我的乡亲牵着牛从容地穿过梅园。似乎闻到乡亲身上弥漫的花香与果香。
晚来天欲雪,月隐云藏。我似乎听到远处的汽笛声,忽然打破山村静寂。似乎看到我的乡亲开门后的惊讶,以及来了贵客后的欣喜。然后以借鸡蛋的名义,将这种喜悦分享给山村的每一位乡亲。
每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想回家的冲动。原来我一直是深爱着我的乡村,深爱着我的乡亲的。带着这些爱与思念,我又开始了我的田园诗词创作。这回不用刻意地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那些朴实的场景,朴实的语言,朴实的形象,自然而然就流到我的笔下。还有他们的勤劳与朴实,他们的纯洁与善良,他们的苦与累,他们的期与盼,他们的忧与虑,他们的隐与忍等等,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活色生香了。我是怀着对乡村的爱与对乡亲的敬,完成了我的田园诗词创作。也可以说是我对乡村的爱与对乡亲的敬,成就了我的田园诗词,使得我的田园诗词较之前相比,有了思想,有了灵魂。
真想此刻就抛弃一切,于东篱把酒,度诗意人生。春赏百花秋赏月,诗咏凉风词咏雪。放牧山歌,垂钓乡野。对牛弹琴,听花解语。三杯淡酒,一壶清茶,半卷朱帘,看炊烟袅袅升起,夕阳慢慢西斜。与乡村同醉,与乡亲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