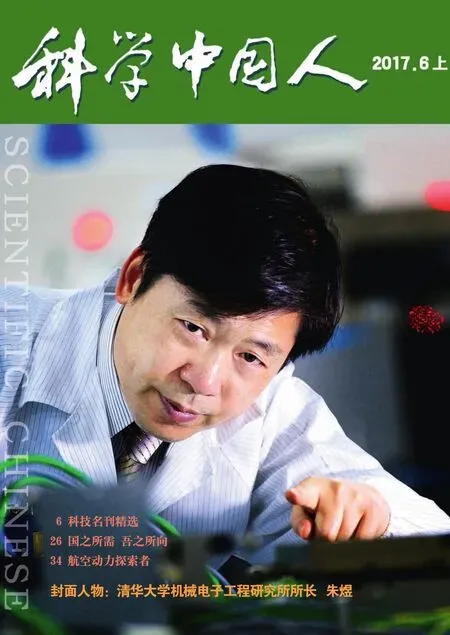年轻的梦是最美的星光——记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华中农业大学傅振芳教授
本刊记者 李晓文
那时,傅振芳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背着简易的药箱行走于乡间,见多了狂犬病带来的痛苦,却没有见惯。从这个少年赤脚医生的心里,生出对狂犬病的种种情绪:不忍、不解……这些纠结,最终成为他朦胧的愿望——消灭狂犬病。
兜兜转转几十年,他在专业上偏离过,那个愿望却慢慢站稳了脚跟,成为他此生的事业。而今,当世界知名狂犬病专家傅振芳回首往事,记忆里那个少年暗自的坚持,便是他此生所追寻的最美的星光。
一颗星,指引理想的方向
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去做一件事。
傅振芳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消灭狂犬病。
1976年,傅振芳高中毕业。因为曾经学习过卫生知识,十七岁的他成了乡间的赤脚医生。一年多的时间,他遇到很多被狗咬的病人。“我们知道,被狗咬了不一定会患上狂犬病,但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打疫苗。”说到这里,傅振芳脸上又浮起无奈的神色,“那时候的狂犬疫苗副作用非常大,甚至可能会引发与狂犬病患者相似的症状。这种状况难免令人恐慌,而我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跟病人解释。”
少年傅振芳第一次有了无能为力的感觉。如果能够消除疫苗的副作用,为狂犬病患者带来生存的保障该有多好。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狂犬病该有多好。他心里隐隐生出这些念头,蛰伏着,伺机而动。
恢复高考后,傅振芳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在那里,他开始接触微生物细菌病毒研究,希望能将之与狂犬病治疗结合起来。连老师们都记住了这个对狂犬病充满热情的学生。就在他以为要在狂犬病上展开深入探索时,却在毕业后阴差阳错地到了没有狂犬病的新西兰。
兽医学硕士、病毒学博士,他在对疱疹病毒和轮状病毒的研究中获得了学位,却从没忘记过对狂犬病的追求。“每次回国休假时,我都会到湖北省防疫站去调查国家对狂犬病的管理,以及每年的病例等情况。所以,拿到博士学位后就想一定要去世界上最好的狂犬病实验室做研究。”他相信,新西兰近六年的时光并没有虚度,在那个没有狂犬病的国度中,他收获了独立科研的方法和理念,也将以更成熟的姿态去面对最初的梦想。1988年12月,美国费城WISTAR研究所接受了傅振芳的申请。一扇新的大门向他敞开了。
自此,他在狂犬病研究领域发表期刊论文128篇,其中在PNAS和国际主流病毒学术期刊包括J. Virology,Virology, J. Gen. Virology, J. Med.Virology, Virus Research, Vaccine等发表SCI期刊论文100多篇;主编学术专著1部;在学术专著和会议论文集上发表27个章节。到目前为止,共被引用2459次,最高单篇被引用364次,此外,还有100多篇短文及摘要被相关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录用。而他的身影也出现在加拿大、法国、泰国、韩国、日本、蒙古、中国香港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场上,先后做了158场特邀学术报告,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重视。
“从上大学到博士毕业,我在专业上与狂犬病出现了几乎十年的断层。终于回到这个领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或许正是因为中间的断层,傅振芳愈发看清了自己的心意,也愈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转折,全身心投入到曾梦寐以求的研究中。二十余年,他辗转于WISTAR研究所、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乔治亚大学,像不知疲倦的海绵,不断吸收着养分。在知识体系和科研实力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他本人也逐渐从研究助理、助理教授,慢慢成长为副教授、教授,在世界狂犬病研究舞台上取得了一席之地。而脱开世界著名狂犬病专家的光环,他的心还惦念着梦想升起的地方。
一颗星,照亮奋斗的路程
真的开始狂犬病研究后,傅振芳很是振奋。然而,要从何处做起呢?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着手开展狂犬病毒RNA转录与复制调控的研究,其研究重点在于探讨病毒核蛋白与磷酸蛋白,核蛋白与RNA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又通过建立反向遗传体系,构建了以固定毒(L16和HEP)为框架的一系列重组病毒。他的工作,证实了狂犬病毒N蛋白磷酸化对狂犬病毒转录与复制的影响,一旦N蛋白去掉磷酸化位点,病毒转录与复制能力就会大大减弱。
几乎与此同步,他对狂犬病疫苗的研究也没有落下。从蛋白亚单位疫苗,重组(痘病毒,腺病毒,细菌等)疫苗等开始,他的目标逐渐向减毒甚至无毒活疫苗方向发展。当然,在研发过程中,他认识到,要有新的疫苗,首先要从狂犬病发病机理上产生新的发现。
“狂犬病固定毒能引起感染的细胞凋亡而街毒不引起细胞凋亡”,“狂犬病固定毒能刺激机体中枢神经系统非特异性免疫反应,包括干扰素和趋化因子的表达而街毒逃逸非特异性免疫反应”,“狂犬病街毒感染影响离子通道ATP酶和参与膜融合蛋白的表达”。
在经过反复实验后,傅振芳和他的团队以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的方法比较了感染不同狂犬病毒的宿主做出的应答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新的学说。其中,弱毒株狂犬病病毒能刺激机体先天性免疫反应就是病毒减毒的机理之一。据此,他们利用反转遗传学的技术终于首选出新的重组病毒。这种病毒就算是用大脑直接注射的方式,都不会使小鼠致病,同时又能刺激产生高滴度的中和抗体,一次免疫就能100%保护动物用大剂量街毒攻毒。除了作为疫苗预防动物和人的狂犬病,还有可能用来治疗人的狂犬病,将为治疗临床上的狂犬病提供了基础。
年复一年,傅振芳在世界各地走访调查,在实验室里一丝不苟地研究,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他安于现状。或者说,在追求理想的路上,他的思考从未停歇过。
严格来说,狂犬病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可能感染。全世界每年因狂犬病死亡的人数达7万多人,其中大多数病例发生在亚洲。印度是狂犬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平均每年因狂犬病死亡2万多人;中国的狂犬病例数仅次于印度,每年有3千多人死于狂犬病,狗的狂犬病更是泛滥成灾。
傅振芳忘不了自己因何投身于狂犬病研究,也希望能够将自己多年的经验用于祖国的“灭狂”事业。
且不说在新西兰期间就已经多次回母校进行学术交流,到了1997年和2004年,他更是分别与武汉病毒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展开了正式合作。而他在母校的工作比重也在慢慢加大:1999年,客座教授;2008年,楚天学者讲座教授;2010年,“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身份的转变,让他的责任心更加强烈,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更多的事情。这些年,他带领团队与华中农业大学、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进行了大量的狂犬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分离收集了大量毒株,并对其致病性、基因组进行分析,借此总结出国内60年来狂犬病流行规律。他们发现,中国狂犬病毒具有多样性,其中一部分与东南亚国家流行的病毒相似,而与全世界其他的病毒形式有所区分。目前他们已经完成了国内街毒安徽株的全长序列测序,为建立国内第一株街毒传染性克隆提供了物资基础;研制出的动物狂犬病灭活疫苗已经拿到新药证书,投放市场;为流浪狗特制的无毒活疫苗也正在实验当中。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传递出一个概念——健康犬是不带毒的。这也意味着我国对狂犬病的防治将从战略上走向由人到犬的转变,出现新的转机。
一道光,传递出灭狂新概念
有数据显示,多年来,我国狂犬病疫苗的接种量保持在1000万人份以上。有人开玩笑地说,“全世界超过80%的狂犬病疫苗都被中国人打了”。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狂犬病泛滥的情况。
“通常的做法是人被咬之后去打疫苗。”傅振芳认为,这种无法无异于亡羊补牢,看上去为时未晚,但如果从最初就做好预防,显然才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我们已经证明,健康犬是不带毒的。不妨就换一下思路,将狗的狂犬病控制住。”这个念头,就像是一道光,拨开了他心头的疑云。
“用于人和狗的狂犬疫苗,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工艺上不同。同样的疫苗,人的需要把病毒放在细胞里培养,经过纯化、浓缩、灭活、检验等一系列过程,要保证不能有任何活的病菌存在。由于要求相对较低,狗的疫苗工艺要粗糙得多,培养出来之后,灭活、包装,就告成了。”
工艺链的长短直接导致疫苗产出的成本,“如果说人的疫苗要50亿能做下来,狗的可能10亿就行了。再说,一个人得了狂犬病,会对一家人的经济和心理等都造成影响。一旦从作为源头的狗身上将狂犬病控制住,不仅可以使那么多人免于死亡,还能为国家节约很多资源。”他一一列举着这样做的好处。
话虽如此,由于国内多年来的惯性,国内的疫苗生产还是集中在人的疫苗上。既然没有人做,那就自己做!傅振芳想的很简单。为了更好地推进成果转化,傅振芳从2006年起,就开始计划成立同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他自己出任技术总监。“从2007年开始成立,2011年底拿到新药证书,2012年拿到生产批号,我们用了五年时间才开始正式生产。”
细心查阅的话,可以发现,现在生产动物狂犬疫苗的并非只有他们一家。面对竞争形势,傅振芳倒是蛮大气,“我们本来也可能不是第一个,只是做了这么多年,有些重要的积累。这其实是件好事,大家都在做了,总算是我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用于动物的灭活苗。”
相比之下,他只愿意在研究上花心思。
狂犬病毒为什么难治?傅振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它就像是小偷,可以绕过人体免疫系统,偷偷摸摸地沿着神经纤维径直朝大脑爬行,而疫苗注射后形成抗体需要数天的反应期,狂犬病毒可用不着等这么久。话说回来,即使血液中产生了抗体也没办法进入神经系统。“在血液和大脑之间,有一道屏障,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容易进出,抗体这种大物质就进不去。这就是血脑屏障。”
明白了这个道理,傅振芳也开始想办法,在刺激免疫反应并使其穿透血脑屏障上去寻找突破口。“血脑屏障是一道门,它可以将有害物质拒之门外。现在,我们要打开它,可能会招惹很多不该进来的东西进门。所以说,这扇门要开多大,开多久,都是个问题。”
不怕有问题,就怕不作为。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傅振芳就是在不断为自己找问题。“很多事情都需要深入去想。比如说,为什么狗感染狂犬病毒后会发疯,总会有个机制在里面。再比如,即使不疯,人和动物在感染病毒后,也都会有个亢奋阶段,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症状,又为什么会造成死亡。”想得多了,他就注意到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狂犬病诊断程序,没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狂犬病参考实验室。回国以来,他专注于将国外的基础研究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建立一套完整的狂犬病诊断系统,研究趋化因子在狂犬病发病及减毒过程中的作用,为控制国内的狂犬病治疗打下良好的基础。
有了抗原检测系统,可以筛选出一系列抗N蛋白抗体,利用荧光抗体,酶标抗体技术检测狂犬病病毒抗原,用来快速检测动物狂犬病;有了RT-PCR系统检测病毒核酸,可以用来确诊动物和人的狂犬病并进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而建立中和抗体检测系统,就能用来检测狂犬病流行状况,评估疫苗效价。一套完整的狂犬病诊断体系,是促进国内狂犬病诊断标准化、产业化、快速化的重要手段,也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成立世界卫生组织狂犬病参考实验室。
同样的,只有研究趋化因子在狂犬病发病及减毒过程中的作用,才有希望构建重组病毒,研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其实,我们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嗜神经病毒学研究中心,以狂犬病为模型研究嗜神经病毒病的发病机理。并带动其他嗜神经病毒发病机理的研究。”
“这些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完的,需要团队的力量。”在乔治亚大学实验室,傅振芳拥有一个10人团队,只是回到国内,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开始难免举步维艰,在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焕春院士的合作帮助下,他逐渐搭起实验基础,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由原来的两位教授,十几个学生发展到现在5位教授、3个科研助理、4个博士后和60多个学生。
“病原与神经系统的相互关系是我们以后的研究重点。因为会涉及神经免疫学、神经病毒学、细菌学、神经生物学等方向,我们在团队的人才构架上也会注重多学科协同发展,用团队的智慧来完成我们的目标。”傅振芳说。
一道光,从个人兴趣走向国家事业
“把爱好做成事业,就不会觉得累。”傅振芳总是这样说。但一路至今,又怎么会如此云淡风轻。
早在回国前,傅振芳就开始频繁与国内展开合作。这段经历中,他最为头疼的就是对狂犬病的定位问题。“狂犬病是一种传染病,应该去找卫生部吧,但是它是由动物引起的,似乎又该归农业部。狂犬病里有野毒,野生动物该划到林业部,可是如果再算上警犬,公安部好像也脱不了干系。”
他认为,要真正实现对狂犬病的监管,应该创造一个平台,让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谈。2007年,在他的参与下,全国狂犬病防控策略高层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而为了进一步推动狂犬病研究的多学科交流,促进狂犬病防控跨部门合作,随后,他又开始奔走斡旋,提出创办中国狂犬病年会的倡议。在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等单位主办下,首届狂犬病年会终于在2012年成功举办。目前为止,该年会已召开两次,会议聚集了国内外相关专家,对狂犬病的研究进展、防控实践、监测和狂犬病的疫苗方面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对促进我国狂犬病防控工作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倡议组织学术交流会议、开办讲座、为国家建言献策,傅振芳用所有他能想到的方式靠近“灭狂”的理想。在他看来,这已经不仅是个人要追求的事业,还是国家发展的大计。正是有了一批像他一样的有识之士,国家才会对由动物引起的狂犬病加倍重视,并将之列入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力争到“十四五”期间完成“灭狂”的目标。“我国的经济、教育等都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再加上政府在卫生防疫上下了不少功夫,对狂犬病研究者而言,正是恰逢其时。”
“当然问题也存在,比如乡下养狗还是容易到处乱走,城市里也常有流浪犬等。我想要研究一种针对狗的口服疫苗,但是狗服东西通常是先吞到胃里再反过来咀嚼,如果是疫苗的话,胃酸就先做了灭活,再回来也不会引起免疫反应。我们要做的就是克服这种毛病,使狗的防疫更加方便。”
在世界各地行走多年,傅振芳亲眼目睹过没有狂犬病的地区。他所梦想的,就是将中国也变成无狂犬区。他也相信,只要多管齐下,那些发达国家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一样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