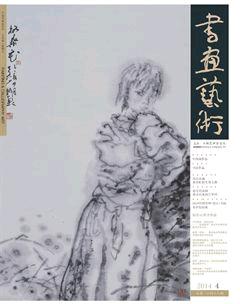论五代宋初南北山水之异同
盛诗澜
上:时代之美与五代宋初山水的品评标准
五代宋初是中国山水画的成熟期,出现了荆、关、董、巨、李、范等一大批里程碑式的人物,无一不是百代标程的典范。提到中国山水画,很多史论家会自然地提及南北分野。唐人山水尚处于探索阶段,体貌多变,因此,稳定成熟的南北分野实际上正形成于五代宋初。已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是,北方山水画派以荆浩、关仝、李成、范宽为代表,审美趣味具阳刚之气;南方山水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审美气象有阴柔之美。
南北山水分野主要存在于五代及北宋,这取决于南北两地迥然有异的地理环境。当时画家对于山水画的理解是“贵似得真”,以描写真山真水、“度物象而取其真”为审美追求,故地域实景的客观差异直接导致了南北山水绘画风格上的差别。郭熙通过细致的观察,总结出“西北之山多浑厚”、“东南之山多奇秀”的特点。这些客观性特点表现到艺术作品中;便形成了或阳刚或阴柔的审美差异。尽管如此,南北山水概念仍然是地域分野,而非审美分野。因为审美E口象毕竟是笼统而模糊的,且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如果以此作为衡量作品分野的标准,容易造成偏差。而到了北宋中后期,文入画思想日益兴起,如苏轼大力倡导传神,不拘形似,米芾更提出“意似便已”,讲求笔墨趣味。由是中国山水画的风格日趋复杂和多样,若再强以南、北二派相别,则难免捉觏肘了。
在厘清了南北山水概念的内涵之后,不妨先来确定一下五代宋初南北统一的时代标准。长期以来,一说到五代宋初山水,美术史论者往往只强调南北分野、南北差异,而忽视南北共性。对于南方山水中董、巨的传世作品,至今未能形成意见统一的标准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缘于此前研究中对于时代特征的忽视。事实上,五代宋初时的山水作品无疑都带有10-11世纪鲜明的时代之美。而时代特征无关地域、不拘南北。通过梳理南北之同,建立起五代宋初山水的时代标准。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依据确定无疑的传世真迹,可以发现五代宋初的山水作品一般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作品构图以全景式山水为主流。马鸿增在《北方山水画派》一书中分析说;“在”山水之象,气势相生的审美观念指导下,北方派画家在艺术创作中总是首先着眼于北方高山大岭的整体气势……以表现天地之无限,造化之壮观为目的……”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山水画作品的构图特征,即大山、大水的全景式构图,而形成这一构图模式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画家“山水之象,气势相生”的基本审美观。不过,将大山、大水的全景式构图视为北方山水所独有的特征,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南方山水中,被一致公认为经典范本的南唐卫贤《高士图》(故宫博物院藏),就是非常典型的全景式山水构图。画幅中群山气势宏伟,近、中、远景层次分明,石体浑厚,深远壮观。杨仁恺《中国书画》称:“这一件作品反映出来的独特风格,是以北方山水人物画为基础……”实际上,与其说身为南唐画院内供奉的卫贤刻意去学习北方山水的风格,倒不妨直接承认这恰恰正是当时南北统一的时代特点。再如南方山水画派之祖董源,后人一度以《潇湘》、《夏山》、《夏景山口待渡》三卷为其画风标准器,得出其构图平远、一片江南之结论,认为南、北画风差异巨大。其实《宣和画谱》明确指出:“大抵元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根据这样的描述,董源作品构图同样以全景式山水为主,这应该无可置疑。因之,与《潇湘》三卷风格迥异之《溪岸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尽管被以高居翰为首的一些境外专家认为是张大干的伪作,确无疑更接近董源向本来面目。至于巨然的作品,以争议相对较小的《秋山问道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来看,同样采用了高山大川的基本构图。当然,全景式山水构图在当时虽属主流,也不可一概而论。在北方山水中,也有李成表现寒林、荒野的平远之景,而南唐赵斡《江行初雪图》绘一派江南渔村冬景,亦是五代南方山水作品中最可征信的作品之一。”
第二,人物与山水并重。高居翰曾指责董源《溪岸图》中“众多的人物与早期山水画的典型图式不符”,这是完全有悖历史事实的。从传世的五代宋初山水作品来看,人物与山水并重是早期山水画的普遍特征。纵观中国绘画史,人物画成熟较早,山水画则起步相对较晚。故唐代山水画家大多兼工人物,吴道子自不必说,二李青绿山水中都有大量人物形象,王维也尚有人物作品《伏生授经图》(传,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传世。北方山水画派之祖荆浩直接继承了唐代传统,兼善人物。在其公认最为可靠的传世作品《匡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绘有船夫、骑士、童仆等诸多人物形象。范宽是北宋时期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其比较可信的真迹《溪山行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近景绘商旅车队自右向左前行,中景树丛后并绘有一名赶路僧人,人物虽小,却刻画精微,于整件作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另外,北方山水画派中的李成在当时享誉画坛,而唯一公认可代表其典型画风的《读碑窠石图》(今在日本)同样是一件山水人物并重的作品,近景主体绘一骑士驻足观碑,身旁并立有一位牵马的仆人。碑侧款署“王晓人物,李成树石”,说明这是一件合作作品。这种合作的现象在当时还比较常见。据文献记载,荆浩的弟子关仝不善人物,故其山水作品一般请同时的名家胡翼补绘人物。后周的山水画家郭忠恕“于人物不深留意”,故“假(王)士元写人物于中,以成全美”。这足可说明,在五代宋初,人物是山水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不擅人物者往往需假人合作。人物与山水并重的现象,在南方山水画派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前述董源《溪岸图》“众多的人物形象”,可算是典型的一例。卫贤《高士图》(故宫博物馆藏)详绘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的场景,在张光福《中国美术史》中被干脆列于人物画类评述。而赵斡《江行初雪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江岸行旅及渔人捕鱼的生活场景,人物所占比重足与山水相抗衡,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徐建融指出:“在宋人山水画中,点景人物起到‘点睛的作用,在元人山水画中,点景人物仅起到‘点缀的作用。”这样的总结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三,忠实于自然的具象表现手法。一方面,以“贵似得真”为审美追求的五代、宋初画家普遍具有忠实再现自然的意愿和要求,另一方面,在较好地继承和总结了唐人山水实践的基础上,五代、宋初画家已逐渐积累起丰富的技法经验,具备了忠实再现自然的能力。因此,繁复细致的具象表现手法,成为彼时山水画的又一突出特征。以画山石为例,往往层层晕染,反复皴擦,力求真实表现石面质感与明暗凹凸的立体感。五代宋初时山水的主要成就正表现在皴法的丰富与成熟,如荆浩有类似小斧劈皴的短条子皴,李成有卷云皴,范宽有雨点皴,各成一体,自成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皴法是一种结合了用笔与用墨的技法,相当复杂而多变,与元人简单且略带程式化的点皴、线皴截然不同。事实上,五代宋初山水往往并不突出用笔的痕迹,画面最终所形成的皴法效果绝非仅用一两笔绘就。以范宽的雨点皴为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称其“抢笔俱均”,实际上是一种变化比较丰富的笔法,绝非简单的虱点。在《溪山行旅图》中,山体的皴法密如雨点,但可明显看出是经画家反复皴染后积墨成面,因此,点的形态各异,变化复杂,并不给人以程式化的感觉。石体由此自然呈现浑厚、质朴、坚凝的质感,雄强的气势顿出。这种不突出线条笔触的山石皴法,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是一种普遍存在,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辽墓出土的佚名《深山会棋图》、南唐卫贤的《高士图》等等,画中山体的画法率多如此。在西蜀入宋的著名花鸟画家黄居案的《山鹧棘雀图》中,其坡石画法亦明显由积墨而成,可为佐证。再看树法,同样都以忠实于自然为基本准则,不仅详尽再现枝干盘屈的形态,于树干的明暗变化乃至干上的每一瘿结,也都作细致的描绘。枝干分叉则四面出枝,绘叶也是用笔多变,根据不同树种叶片的客观实际,以夹叶为主,点叶为辅,刻画精细。水法则延续隋展子虔《游春图》中网巾水之画法,当然这主要存在于南方山水画中,毕竟江南多水。在卫贤《高土图》、赵斡《江行初雪图》、董源《溪岸图》中都可见网巾水的精彩表现,在《溪岸图》中,瀑布跌落的动荡、风吹浪动的起伏、水击岸石的回旋无一不描摩得精细入微,令人叹为观止。五代宋初山水画具象的表现手法体现在作品的方方面面,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展开。
在对五代宋初山水作品的时代特征有了上述的大致把握之后,再去衡量那些备受争议的作品时便可有一个大致的评判标准。如被高居翰全盘否定的董源《溪岸图》,其全景式的构图“使人观而壮之”;山石、树木、人物、水纹刻画精细繁复,真实自然;皴法几本看不出线的痕迹,水墨渲淡,渍墨成阴,气息高古,应该说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并可被视为南方山水中的标准件之一。
下:地域文化与五代宋初南北山水的审美分歧
在具备鲜明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五代宋初的北方山水与南方山水之间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风格差异。正如很多美术史论家已经意识到的,五代宋初南北山水的风格差异与审美分歧,往往与南北两地不同的地理实景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
提到南北差异,一个接踵而来的重要问题是,绝大部分史论家都以董源的《潇湘图》(故宫博物院藏)、《夏景山口待渡图》(辽宁省博物馆藏)、《龙袖骄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夏山图》(上海博物馆藏)诸卷作为南方山水画中的“标准件”,以此与北方山水进行风格对比。但董源作品的复杂性在于,鉴于前文所提到的《溪岸图》与《潇湘》诸卷存在着明显的画风差距,一旦《溪岸图》被确定是带有鲜明五代特征的董源真迹,那么,《潇湘》诸卷本已入史的牢固地位就岌岌可危。张大干、陈佩秋就曾先后明确表示出对《潇湘》诸卷的怀疑态度,谢稚柳在晚年也对他们的看法表示认同;徐建融在怀疑诸卷的同时,认为尽管《溪岸图》是五代的画迹无疑,但也并非董源的真笔;丁羲元则认为,《溪岸图》、《夏景山口待渡图》为董源真迹,《潇湘》、《夏山》为后入仿伪。事实上,针对巨然的作品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如曾被视为巨然真迹的《层崖丛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及被王翚、王季迁、张大干、张珩等^定为真迹无疑的《秋山问道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也都有论者提出并不符合宋人风尚。
本文无意就董、巨作品的真伪问题进行深入辨析,这毕竞属于另外一个议题。但既然对于南方山水派之祖董源与巨然的作品尚存在众多模糊和纷争,我们在分析五代宋初南北山水作品的差异时,若再以它们作为标准件来与北方山水进行对比,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在接下来的比较分析中,本文将尽量回避董、巨那些被认为已具元人特征的经典作品,而尽可能选取那些更符合五代宋初典型时代气息的南方山水作品。当然,《溪岸图》是个例外,因为根据目前国内公认的观点,无论它是不是董源的真迹,其确属五代宋初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其绘画风格隶属南方山水一派也是毋庸置疑的。
即使摒弃了董源那些“平淡天真”、“一片江南”的存疑的经典作品,五代宋初南北山水之间仍然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差别。
首先,从作品立意来看,南北山水画家在山水观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郭熙《林泉高致集·山水训》称:“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据相对可靠的传世作品,北方山水多为可行、可望、可游者,南方山水则往往为可居者,而这正充分体现出南北山水画家对于山水价值的不同理解。面对山水美景,北方画家似乎普遍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表达对于大自然的崇敬心态。如荆浩隐居于太行山中,“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北方山水之祖荆浩为自然美景所折服,遂反复观察,刻苦临摹,力求通过建立完备的山水技法,取山水之真。此后的关仝、李成、范宽三家与荆浩在绘画思想上一脉相承,都致力于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细致观察,刻画和描绘真实的自然景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察往往以一种旁观者仰视与叹赏的视角进行。为了更好地突出造化美景的雄壮气韵,画家们通常还会对画面构图进行细致严谨的安排,以尽可能在客观再现自然全景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自然之壮美。因此,北方山水画面的主体往往是雄伟的高山巨石,皴法用笔坚挺,充满力量感;其间树石繁密,力求形象真实丰满;整个画境显得浩瀚壮大。面对这样的客观自然,人类显得非常渺小,只能叹赏仰视。而观者从北方山水画家的作品中,则能够清晰体会到这种建立都在详尽观察与严谨安排之上的秩序感,山石雄伟壮美,四时之景各不相同,自成体系。南方山水画则与此截然不同,南方画家腼的山水往往是人们可以日常居住其中的山水,人与山水浑为一体、和谐共存。因此,即便是“下笔雄伟”,令人“观而壮之”的全景山水,南方山水也自有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沈括《梦溪笔谈》称董源绘画“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这固然与南北两地不同的山石质感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体现出画家对待山水的亲近态度;绝非崇敬的旁观仰视,而是自然的天入合一。假如比较一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卫贤的、《高士图》就可明显看出,前者将整座国嶝蝴画幅主体的大胆构图,以—种震人心魄的视觉效果。突出了山体的雄伟气象,其关注的焦点在山;而在后者中,高旷雄厚的群山尽管同样具有崔嵬之势,但仅是作为背景出现,画面主体突出的是居住山中的梁鸿与孟光夫妇,画家关注的焦点在人。当然,南方山水更关注于表现的是人与自然互相亲近的客观状态,它描绘的仍然是“无我之境”,但无疑地,比起北方山水,南方山水画的这一山水观更接近也更容易申发至文入画的“有我之境”,米芾对董源的发掘与力捧显然也正基于这一认识。
其次,南北山水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南北山水题材上的较大差异。大致来说,北方山水多行旅题材,南方山水多隐居题材。北方山水着力于描绘出游所见、行旅所览的自然景观,相应的,画中人物往往只起到一个点景的作用,很少带有叙述性的生活情节。最典型的如范宽《溪山行旅图》,无论是近景步履蹒跚的驮队,还是中景行色匆匆的僧人,都只是雄阔山水中的过路人。入与山水似乎正代表着尘俗凡世与宇宙天道,前者渺小,后者巨大,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也由此充满了张力,动人心魄。而李成的《读碑窠石图》是北方山水中少有的人物占有较大比重的作品,但骑士鲜明的过客身份,使本该作为人物背景的寒林荒漠得以凸显。残碑与枯树、原野浑为一体,画境苍凉萧疏,而读碑的路人不过是作为这大自然的景仰者与观赏者出现。当然,北方山水也并非完全不涉隐居题材,如荆浩的《匡庐图》就表现了高士隐居的主题。但画面构图中对于人物与山水关系的安排设计,与南方山水中的处理方式是迥然不同的。在《匡庐图》中,“鸟瞰式”的全景构图占据画面主体,画家精心构筑了群峰叠嶂的万千气象,人物与屋舍的存在更突现了山水造化之壮观。因此,观者看画,首先看到的是山水。而在董源的《溪岸图》中,尽管就人物与山水的比例而言,前者同样是渺小的,但任何一位观者都能够毫无疑义地聚焦于画面的主角:端坐于山脚水轩内,眺望江面的文士。这种构图上的巧妙差异,体现出画家在题材表现上的主要差别:北方山水以行旅的视角表现自然,突出的是景观;南方山水以隐居的视角表现自然,突出的是人。在南方山水作品中,隐士的家居生活被得以充分展现。《溪岸图》中文土的身后,有夫人和怀抱的幼子,有陪伴的仆从;文士坐于一张官帽椅上,斜倚凭几,身后地板垂帘,草书屏风,陈设古雅。水榭夕h篱落曲折,水井、钓台一应俱全,并见晚炊的妇人、肩荷木犁的农夫、骑牛的牧童。一派江南生活实景。这种对家居实景的细致描绘,使人与自然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卫贤《高土图》亦是如此,人物被置于画幅中部,是画家突出的中心。梁鸿端坐于榻,竹制矮几上卷轴横展;孟光跪于榻前,目光下敛,举案齐眉。画面描写的是带有故事性的生活场景,尽管屋外也是峰峦重叠,山石奇绝,气势雄壮,但山水仍然只能作为人物的背景出现。赵斡《江行初雪图》更将南方山水题材的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俨然就是一卷江岸渔村的生活风情画。尽管画中真切再现了江南初雪时的景致,树石水波刻画精细,弹粉作雪,意境萧寒,但随着江岸风景一起展开的,还有近30位渔人和旅人真实的生活记录。他们或摇橹撑船,或收网捕鱼,或生火炊煮,或瑟瑟赶路,与周围的景致浑为一体。如果说,北方山水是一片独立于凡尘俗世之外的体系严整的宏观山水,那么,南方山水则无疑是一片可以优游其间的、天人合一的人间天堂。南北山水都是具象而真实的写实作品,又都超越了客观自然的真正实景,体现出南北画家不同的审美理想和追求。
最后,南北山水因所绘实景的差异,形成了绘画技法上的鲜明差别。五代宋初山水画家所体现出来的不同艺术风格,往往来自于实景对象的不同特点。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评李、关、范三家的不同特色:“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状雄强……范氏之作也。”三家中,关、范描绘的都是中原黄河流域的山水风光,石体干燥、峻厚,因此二人画风都有雄强气势,而李成所描绘的是山东齐鲁一带的平原山水,擅长表现“烟林平远水妙”,虽同属北方山水,但意趣迥然。就绘画师承而言,李成学荆、关,但“师荆浩未见一笔相似,师关仝则叶树相似”。同样的,范宽学李成,艺术风格上也有鲜明不同。这都是外师造化的结果,不同的艺术特点取决于不同的地域特色,在这种情况下,“齐鲁之士唯摹营丘,关陕之士唯摹范宽”。江南山水与北方山水气格不同,因此南方山水作品又是另外一种艺术面目。《宣和画谱》称董源“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干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又“巨然山水于峰峦岭窦之外,下至林麓之间,犹作卵石、松柏、疏筠、蔓草之类,相与映发,而幽溪细路,屈曲萦带,竹篱茅舍,断桥危栈,真若山间景趣也”。“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幽溪细路,屈曲萦带,竹篱茅舍,断桥危栈”,这些都是江南山水的独特气韵,南方山水由此具有了别样的风情。看惯了北方山水作品,入或谓南方山水作品“气质柔弱”,其实不然,因为这恰恰证明南方山水画家在表现实景方面同样具有不俗的功力。具体到笔墨技法上,尽管南北两派都兼具用笔及用墨的高超技法,但北方山水普遍笔性刚硬,南方山水则笔性阴柔,差别一目了然。为更好地表现北方多石少土、石质坚凝的质感,北方山水一般用墨线清晰勾勒山石外形轮廓,皴法则多用钉头皴、斧劈皴、雨点皴,硬勾密斫,反复皴擦,淡墨烘染,最终形成刮铁、质实的视觉效果。即使是北方山水中以文质彬彬、“秀媚”而著称的李成,其卷云皴用笔清瘦劲挺,仍具刚硬尚骨的气质。树法上,北方山水画家善绘枯木寒林,树形挺拔枯瘦,分枝劲健锐利,或如
“蟹爪”(李成),或如“扫帚”(范宽)。而南方山体多土少石,且云雾显晦,故画家往往通过笔触不明显的墨韵变化,表现石面的光影变幻,画面效果朦胧模糊。沈括《梦溪笔谈》称:“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像,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溪岸图》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其石体之间并无清楚明晰的轮廓线作为分割,“近视无功”,但皴笔紧密融浑,远视则“杳然深远”,南方林木葱郁,故树叶多以浓墨勾写,枝干以淡墨渲染,滋润蓊郁。又南方多水,故南方山水于水势开合、波浪翻卷之景,刻画最是精彩。而北方山水画家对于水的表现力无疑要单薄得多,往往仅作一线狭窄的瀑布。
在北宋人眼里。北方山水才是当时的主流画风。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立“论三家山水”一章,明确指出:“画山水惟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于董源、巨然则评价一般,称董源“善画山水,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巨。然“工画山水,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但林木非其所长”,寥寥数语带过。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中列李成、范宽为神品,《五代名画补遗》中列荆浩、关仝为神品,均不提董、巨。《宣和画谱》则明显更推重李成的作品。这或许与南唐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不无关系,但也正如前文提到的,宋人以为南方山水偏“柔弱”,他们在审美趣味上确实更接受北方山水的气势雄强。直至米芾《画史》贬荆、关,推董源山水“近世神品,格高无比”,南方山水的地位才开始提高。到元代汤重《画鉴》中,一改李、关、范三家之说,提出“董源得山水之神气,李成得体貌,范宽得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而为百代师法”,南北山水对峙之格局由此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