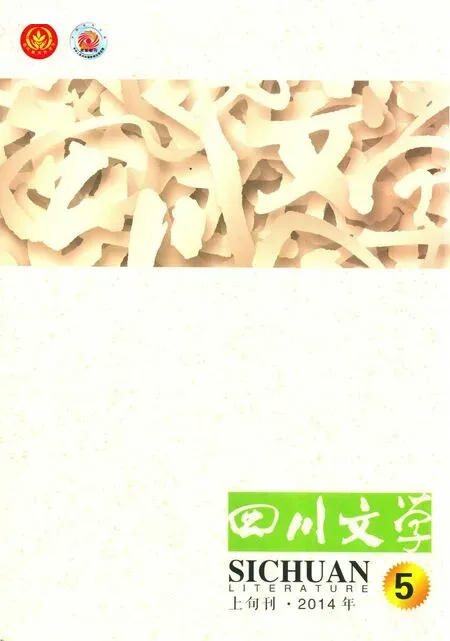小小说三题
/吴永胜(四川)
皮 狗
从韭菜地里一抬头,皮狗就看见村主任皮旦从地那头摇摇摆摆走过来。皮旦脸红红的,像戏里的关公。斜叼着半截烟。看见皮狗,嚅动着嘴招呼,那纸烟便一上一下晃动。皮狗呀,韭菜长得好。
皮狗停下锄,嘿嘿笑了。主任,要不要捎点回去?
皮旦呸地吐了烟,亮出两排牙齿,很响亮地笑说,球呢。韭菜壮阳的,我头上都冒白烟了,还吃得?
皮狗说,那是,那是。
皮旦走了,从皮狗身边走过,打了个嗝,一股浓郁的酒味留下来。
皮狗又开始锄草,可眼老花锄也不听使唤了,一锄下去,几片嫩绿的韭菜叶断了。直起腰来,往手心里狠狠吐泡口水,两手相互搓揉,直到手心都润了滑了,一锄再下去,几片韭菜叶又断了。撞鬼。皮狗沮丧地嘟囔:真是撞鬼了。再也没心思锄草,皮狗平放了锄头,坐到锄杆上。皮狗看见皮旦一路晃一路哼,已经晃着哼着进了院子。皮狗跳起来,抓起块土疙瘩,狠狠往院子的方向掷出去。狗日的皮旦,我日你先人!皮狗涨红了脸,张大了嘴,却没骂出来,土疙瘩也像垂头丧气样,在三五丈远的地方,歪歪斜斜落到菜地里。
皮狗看看四周,没一个人影。皮狗就咬牙切齿骂出了声,皮旦,我要日你先人!停了停,又骂,皮旦,我要日你女人!骂几句,皮狗有些丧气了。这时候皮狗看见锄杆上,一只黑蚂蚁正爬上来。皮狗捡起块土疙瘩,狠狠拍下去。皮旦,老子打你皮旦!土疙瘩碎了,黑蚂蚁烂成了一团,糊在锄杆上。皮狗感到有些快活。皮旦,你是黑蚂蚁,我打你个黑蚂蚁!皮狗重新拾了块土疙瘩,在地里搜寻黑蚂蚁。皮狗勾着头偻着腰,在地里寻着拍着。黑蚂蚁像躲着皮狗,皮狗拍过了七只黑蚂蚁后,一时间就找不到黑蚂蚁的影踪了。拍过七只黑蚂蚁的皮狗直起腰,说狗日的皮旦呢,你不是人!你是黑蚂蚁!说过了就朝院子的方向走。
皮狗进了院子,站住了。他听见里屋掩门的声音,女人似乎在说,主任要不得呢。皮旦很急促地笑,笑过了说,狗日,我想你了呢,看你多白……
皮狗脸腾地就红了,皮狗一步蹿进屋里,屋里桌上,皮旦的黑呢子大衣很随便地放着。一支钢笔现出锃亮的帽子,晃着皮狗的眼。皮旦在里屋问,谁呀?皮狗有些怔愣了,有些不知所措了。皮狗干着嗓子说,我,是我咧。
里屋的门开了,皮旦懒洋洋出来,我说皮狗呢,你好好锄你韭菜吧,回来干啥?
皮狗拿眼朝向里屋张了张,女人正坐在床沿上,长辫子散了,一绺绺铺着。女人勾着头,只把一个乌亮的头顶朝着皮狗。皮狗咽了口口水,说主任,我回来喝水呢。
皮旦横皮狗一眼,说,皮狗,你哪根脚趾动我也知道呢,不就是睡睡你女人么?
皮狗脸有些灰白,皮狗低声说,我、我真口渴呢。
皮旦嘿嘿冷笑,从桌上黑呢子大衣里掏出根烟,叼到嘴上,然后点上,吸一口喷一道烟雾。烟雾在屋里兜好大一圈了,才说,皮狗哇,有种你擂我两拳,我回身就走,往后再不来了。
皮狗想笑笑,嘴角扯几下也没能笑出来。哪能呢我……
皮旦大马金刀坐到凳上,说皮狗,你擂吧,我不还手的。你擂了我就走,你擂吧。
皮狗向后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说,哪能呢我……
皮旦眯缝着眼,紧紧地盯着皮狗。你擂呀,擂一下吧,擂了我就走,往后再不来了。
皮狗再退时,脚跟在门槛上一磕,向后便倒了。皮狗重重摔在院子里,皮狗爬起来时,脸已经白得像纸。皮狗慌张地向院外走,皮旦在身后问,你不渴了?
皮狗说,我,不渴了。
皮狗重新走到地里,重新在锄杆上坐下来,坐下了,从地上抓一块土疙瘩,叭地在锄杆上拍碎,说一声皮狗,你是黑蚂蚁。又抓一块土疙瘩,叭地在锄杆上拍碎了,说一声皮狗,你是黑蚂蚁……
皮大喊了三声爹后皮狗才回过神。皮大放学了,挎着个大书包,站在地角看他。皮狗说,娃,你过来。
皮大说,我饿了,我要回去叫娘做饭。
皮狗朝院子那边望了望,没有动静,没有皮旦的影子。皮狗说,娃,你忍忍吧,你娘忙事去了呃。
皮大说,我饿了呢。
皮狗说,我给你钱,去小卖部买饼干。
皮大欢喜了,跑过来伸手接钱。
皮狗从怀里掏出几张小票,却不急着给皮大。娃,你说,长大后干什么?
皮大说,你说了,要我当村主任呢。
皮狗点点头,又问,为啥要当村主任?
皮大眼巴巴望着小票,说我知道呢,你要我将来干皮旦家儿媳妇。
皮狗笑了,好!记住了,可不能给皮旦家那小狗日的知道。
皮大说,知道的。皮狗将小票递到皮大手里,脸色也好看得多了。
皮大拿了钱欢天喜地就走,走了几步又折回来,说,爹,皮旦家娃儿说,他长大要当乡长,比村主任官还大呢。
皮狗一屁股跌坐到菜地里……
镟 磨
入冬后,地里的活少了,趁着空闲,李香素想把屋檐下那副磨镞一镟。想想,得找何少保。
李桐沟很有些石匠,但大多只有砌砌基石、垒垒堡坎的手艺。能干镟磨这细活的,现在,就剩何少保了。
石磨是有福打下的,选的是上好磨子石,用了十多天工夫才打出来。新磨在檐下一放,惹得沟里的人都眼热。磨墙上,阳刻四幅喜鹊闹梅图案; “呼呼”推动磨子,图案跟着旋动,那些喜鹊就雀跃着活了。下面磨承的沿,雕了两条龙:磨下的粉末或者浆水,从龙口会合处,“扑扑”、“哗哗”地出来,很有气势。磨道阴阳凹凸,最难处理。有福有那本事——两扇磨一合,那缝,规整得只细细一线。磨经常推动,有磨损,隔一两年,便得把磨道镟一镟;有福镟了十来回,到如今,再镟不动了。
要不是有福想吃汤圆,李香素是不会去找何少保的。何少保和有福都是李桐沟名字响当当的石匠。到现在,她都不知道当年自己到底是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当然,她也一直没去想过这个问题。自从爹妈做主把她嫁给有福后,她总觉得对何少保欠下了什么,每次碰到他,都很不好意思。有福瘫痪后,她更不敢见到何少保,怕别人说三道四的。
何少保端碗南瓜饭,蹴在门槛上,正吃,见了李香素,咧开嘴就笑。
“咋的,想我了?”
“老都老了,还没个正经!”
“老了好呀!好比这南瓜,嫩的只甜不面;老的又甜又面,多好。”说笑过了,才问,“有啥事?”
“我想把磨子镟镟。”
“谁还用磨子?机器多好,省事又快。”
“有福喜欢吃汤圆。机器磨出的米粉有股铁腥味。”
何少保嬉笑的脸,一下板了起来。
“有福有福,他龟孙真有福呢!”叹了口气,说,“镟子、凿子啥的,好多年没用了,得煎煎火淬一淬。明天来。”
回家后,李香素称出十斤糯米、四斤饭米,拌和匀称了,再倒进桶里,舀三瓢清水漂上;把躺椅支在檐下,从灶膛里扒出炭头,装了半烘笼,拿毡子捂盖严实了,放到躺椅下;然后给有福洗脸、喂饭,再背他出来,放在躺椅上;安顿好有福,从井上提来桶水,拿洗衣服的刷子蘸了水清洗磨子。算一算,磨子快十年没用了。
她一边洗,一边和有福说话:“你喜欢吃汤圆,把磨道镟镟,磨好粉子给你做。”
有福眨巴着眼,“唔”地应了一声。
“你镟不动磨了,找了何少保。”
有福眨巴着眼睛,没有回应。
洗到龙口处,李香素停了下来。她伸出手,拿指肚子轻轻刮摸水泥修补过的龙头,叹了口气:“立秋那短命鬼!那一榔头呀,没伤到你,却把你的手艺给毁了。也不晓得他们过得好不好?”
有福在躺椅上挣了几下,努力要说话,脸都涨红了,却说不出来,只嘴里“嗯嗯哧哧”响。李香素赶紧过去,拿手在有福背脖处揉,“你急啥呀?你别急!我就和你说说闲话,不然闷得慌。”待有福平静些了,伸出手掌,摊在有福嘴前,问:“有痰没有?”见有福转动眼珠,没有要吐痰的意思,才又回到磨前,叹了口气,说:“往后任我说啥,你都莫急。”
何少保来的时候,眼睛上挂一副老花镜。他左手提个竹篮子,里面装着镟子、凿子、碥子、锤子;右手拎着棕叶绳,绳上捆着两只腊猪脚。一入院子,不等李香素说话,打几个哈哈,先开了口:“一个人吃饭,火都烧不旺、煨不 。这个腊脚脚硬哈!你得拿火慢慢煨,煨 和了才安逸。”
李香素眼眶子有些红。
“他叔……”
何少保将猪脚往李香素面前一放,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啥他叔?我就是你哥嘛!以前你喊一声 ‘哥’,我锤子都捏不稳,‘哐当’一声就砸脚上;现而今喊 ‘他叔’,要划清界限哈?”
李香素脸就有些红了,赶紧从屋里拿出酒瓶,说:“我给你舀酒去。帮我照看着有福。”
“酒当然要舀。帮工不喝酒,干活手打抖。看有福做啥?我恨不得踢他两脚哩!”何少保嘴上说着,还是去跟有福打了个招呼;然后脱下大袄,换上褂子,拆下磨扇,放到地上,排开工具,拿张小凳子坐下,一边 “叮当叮当”清磨道,一边和有福说话。
“你说你龙精虎猛一个人,咋就瘫了?”
有福喉咙里 “唔”一声。
“香素那么好块地,让你给荒废了!你是有福还是没福哟?”
有福 “唔唔”两声。
“香素跟着你,辛辛苦苦的,好不容易把娃些都拉扯大、都出息了,眼瞅好日子来了,你龟儿却瘫了。早知道,老子当年就不该把她让给你!真想踢你几脚!”
有福涨红了脸,涨红了眼,一个劲“唔唔唔唔唔”。
何少保停下手里的活,伸个指头,把眼镜往上推了下,偏过头,看着有福。
“你个龟儿子!我就是说闲话嘛!你‘唔唔唔’个啥?”
有福就真不 “唔”了,定了眼珠子,看何少保。
“有福有福,你到底有福呢,还是没福?”何少保回过头来,又忙上手里的活计了,隔好一阵,才补上一句,“你还是有福的,我觉得。”
爸妈过年回家
听奶奶说过,爸妈过年要回来?五月就努力地在脑袋里的角角落落,搜来刨去。有多长时间没看到过爸妈呢?奶奶说,有三年了。五月掰着指头算,左手五个指头,加右手一个指头,是自己的年龄。扳下去三个指头。五月就算明白了,爸妈是五月三岁时走的。
五月把算来的结果告诉奶奶。奶奶正坐在街沿下,就着暖暖的太阳,纳鞋底儿。奶奶鼻梁上架着个大镜子,听到五月的话,就抬起头来。眼镜一下子滑下去,滑到鼻头子上,像那副眼镜子,专门戴给鼻蛋子的。鼻蛋子想看什么呢。这么一想,五月就嘻嘻笑了。奶奶说傻女子,你笑啥呢。你爸妈走时,你是三岁。又指指在一旁忙得满头大汗的八月,说八月才一岁。
八月正将所有的玩具,挨着个在院里排开。有恐龙,有装着警灯的汽车,有炮筒断了一截的装甲车,有铁甲超人,还有飞机。八月不停地将它们调换位置,嘴里不停地呱啦呱啦,指挥它们战斗。五月上一年级了,已经是大人了,才不玩小孩子游戏呢。五月拍拍八月的脑袋,说弟弟,爸妈过年要回来呢。八月抬头看了眼五月,一甩脑袋,便将五月的手挣开了。八月的脸红红的,有层薄汗,粘着泥灰,整个脸蛋儿,弄得像戏里唱花脸的。他不理会五月的话,继续呱呱啦啦,指挥他的无敌战队。
见八月没有兴趣,五月只好重新坐回奶奶身边,努力去回想爸妈的样子。五月已经不太清楚爹妈的样子了。好几次,爸妈的样子似乎都快看得清了,可就像水田里的鱼秧子,刚才明明还在那儿呢,可指头才在水面一碰,鱼秧子一甩尾巴,就不见了。
坐了一会儿,五月坐不住了。她觉得八月和自己,都是爸妈的娃。都是爸妈的娃,怎么能对爸妈要回家的事,不欢喜呢?不理会呢?她觉得八月太不懂事,太不应该。她本来想去扰乱八月的战队,但那样八月肯定会哭鼻子,奶奶也会骂自己。她突然想到了个好主意。她把两个小手交叉着放在背后,慢腾腾走到八月面前,说,八月,你想不想要闪灯鞋呀?
八月抬起头,抬手在额头上抹一把,额头上立刻添了几个道子。要。
要不要机关枪呢?
八月终于站了起来。要,我要可以打子弹的。
五月骄傲地一昂头,说爸妈过年就要回来,到时都给你买!
八月似乎有些狐疑,他不太相信五月的话。颠颠地跑到奶奶跟前,扑进奶奶怀里,说奶奶,爸妈要买闪灯鞋?
奶奶慌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抬手在八月屁股蛋子上拍了下,说先人板板,惊风火扯的,针差点扎着你了。又说,当然要给你买哦。
我要有多少灯的。到底有多少呢?八月犯了难,想了想,说有天那么多的。五月嘻嘻又笑。天哪有好多嘛,天只是大,大得没有边界,大得眼睛都看累了,也看不到边。八月的脚板才比鸭掌掌大多少?给他双天那么大的鞋子,他才穿不得呢。
是不是要给我买枪呢?奶奶拾起围裙,擦去八月脸蛋上的汗污,说,当然要买呀。八月可乖了,从来都不淘气。五月就撇嘴,八月怎么不淘气呢。天天追鸡撵狗,打烂过奶奶的镜子,扯坏过自己的本子,还老尿床。晌午那会儿,八月把鸡笼里下蛋的鸡,拿棍子掏出来,惹得奶奶扬起个桑条子,满院子追,骂他是淘气货。奶奶也真是,记性太差了。八月才不知羞哦,还得意洋洋的,真以为自己多乖。我还要甩炮。买。我还要坦克。买。我要把把糖,还要坨坨糖!一口气说了许多,还要买什么,八月想不上来了,瞅瞅五月,又说,我还要买书包,比姐姐的大。奶奶全答应下来,说都买都买。
八月那个得意哦,好像那些东西已经拿在手里了,欢欢喜喜,又蹲在了那堆玩具面前,开始当他的战队司令去了。
五月也有很多东西想要。比如,小梅姐那种绣着金线子的鞋,比如李小文那种上面画着猫和老鼠,里面分几个格子的文具盒,或者,一双暖暖和和,写字一点都不碍事,露半截指头的手套。但心里想呀想呀,却不跟奶奶说。五月上一年级了,读书了,有文化了,可不像八月啥都想要。五月开始盘算,距离爸妈回来还有多久呢?
奶奶说,现在才冬月头上,到过年,还有一个多月。一个多月是多少天呢,五月扳着指头数一数,数来数去,把自己都数糊涂了,还是数不出到底有多少天。但数不清楚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爸妈过年就要回来了。
奶奶说过,爸妈打工的那地方,往南方走哇走,要走几天几夜。那地方,冬天里不用盖被子,穿件单衣就把冬天打发了。不像王家沟,冷得人索索抖。奶奶说过,爸妈打工的地方,在五月眼睛看不到的天边边下面。五月心里想,说不定爸妈已经提着买好的东西,坐上了回家的火车。这么想着,五月心里像揣了窝兔子,全都蹦跳开了。
奶奶重新拾起活计,嘴里叽叽咕咕的,说每年都说要回来,到年关上了,不是坐不上火车,就是赶上挣双份工资。回来不回来,到家才作数。
奶奶说的话,一句也没进五月的耳朵,五月心里,装着列哐啷哐啷响的火车,正朝王家沟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