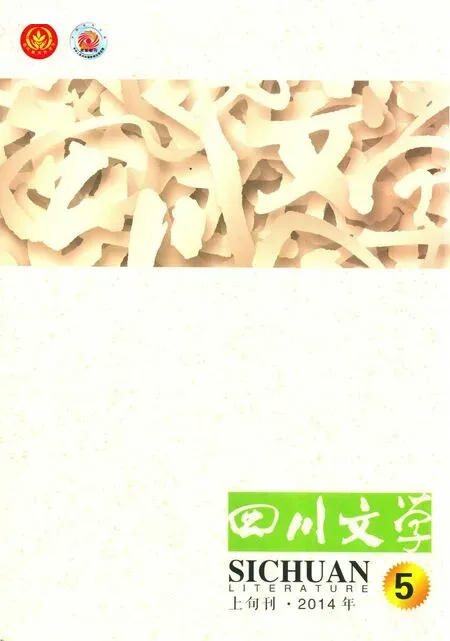他就是一头牛
/蒋寒(北京)
狗日的抓进看守所没几天,通知家属去领骨灰盒了。万大胆死了!雪村乡亲沸腾了,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狗日的哪有家属?打小手脚不干净,谁敢嫁给他,四十好几仍光棍一条;几个哥姐不堪乡邻戳脊梁骨,外出打工了;家里只剩下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老牛贩子万自清了。
尽管万大胆叫万自清爸,但是万自清却不认他这个野种。
都知道万大胆是万自清的女人偷人生的,从相貌、皮肤到秉性,与几个哥姐大相径庭。
人们着实不解,精明的牛贩子万自清明知万大胆不是他的骨肉,还甘心缴了罚款,认了。
都骂他,脑子被牛踢坏了。
万自清精明一时,糊涂一世。他为生产队乃至大队的耕牛买进卖出,走南闯北,乡亲们高看他一眼。偏偏他女人后院起火,他不仅不灭,还扇旺火焰,这就怪不得别人骂了。
那些年,万自清常常一出去就几月,有时半年,有时一年。回不回家,逢年过节总给妻儿捎回些东西,为此他家常常出没些陌生男人,说是他的同行。他家门朝大院开的,一只苍蝇也难逃大院人的眼睛。或许为避嫌,那年他回来,翻修新房,改了朝向。他家再来人,只能从他娃崽的脸上判断了。小脸蛋红扑扑的,不用问,准来人了。那年,他娃崽的脸蛋红了一冬,他女人就挺起了大肚子……
万自清回来,女人就像犯错的孩子,等他责罚。女人不是第一次犯错,每次都被打得直奔大院老井,死去活来。这回,他不责罚,反而交了罚款,让女人战战兢兢生下野种。随着又黑又丑的怪物一天天长大,在雪村颇有几分风韵的女人彻底变了,抬不起头,少言寡语,服服帖帖了。
再看万自清眼里闪出的丝丝狡黠,大家愕然了,原来他用这种方式降服女人?这未免代价也太大了吧。真是一头蠢牛!
或许降服,已经成了牛贩子的本能。每次从几百公里外的山上买回的牛,都要经过他的亲手调教,才能老老实实耕地……
女人的老实并没有结束他的降服。后来那野种长大了,听到村里的孩子叫野种,没上几天学就不去了,开始到处打架,惹是生非,从此捡回了 “万大胆”这个绰号。告状的天天上门来,女人管不了,只哭。万自清也不管。女人哭诉,是万自清在换着法子收拾她。大院人劝万自清,同情同情女人,管管大胆吧,好歹他也叫你一声爸。万自清理直气壮,说,你们看看我万自清的几个孩子,哪一个像他?他要是我万自清的孩子,我早将他打个半死!从那以后,万大胆一犯错,女人就往死里打,打得万大胆双脚跳。女人一边打,一边骂,还一边哭,我作孽啊!女人终被孽子气得一病不起,直到咽气……
万自清并没有为女人的离去而伤心,甚至为女人的解脱而平静。
女人下葬时,那个跟万大胆长得一个模子、一个色儿的男人露了一面,也正是那个男人的露面,让万大胆从此无地自容。
万大胆从此成天成天地飘荡在外,万大胆从此更加疯狂地报复挖苦他的乡亲,万大胆从此让每个家庭鸡犬不宁……
人们纷纷向万自清投诉。万自清说,他不是我儿子,他就是一头牛,你们杀了他,炖了他,吃了他吧!
这不,死了。仿佛眨眼的事儿,狗日的死得蹊跷,抓进去还活蹦乱跳的,就变成骨灰了。毕竟是条命啊,都以为万自清会翻天,没料他从早上接到通知,到下午还在村小卖部喝寡酒,喝得晕晕乎乎,嘴巴不时念叨,他不是我儿子,他就是一头牛!
都以为万自清伤心过度,说胡话了。
万大胆是一头牛不假。上年纪的人都清楚一笔账,他女人生万大胆时,罚款足够买一头牛了。那年头,牛可比人金贵。
乡亲们真正纳闷儿了,万自清既然不喜欢万大胆,又怎舍得花一头牛钱,要了万大胆呢?单凭惩罚他女人,也说不过去啊?
那年头,一个生产队的公有财产,也不过几头值钱的牛了……万自清口口声声说万大胆是一头牛,他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呢?
万大胆的骨灰最终没人去领。万自清不去领,他在外打工的儿女也不回来领,许是怕那野种的骨灰,脏了村里的土地。
乡亲们同情已年过七旬的万自清,背越来越弯曲了,早已没了他当年走南闯北买卖耕牛那般威风,如今只能在村里给儿女看看家,跟老头儿在村小卖部下下象棋,喝点小酒……
这天,万自清喝醉了。从铁路上退休的老翟问他,老万,你口口声声说大胆是头牛,到底哪么回事?
万自清迷迷糊糊吐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那个跟万大胆一个模子的黑脸汉子,也是个牛贩子,在一次共同买牛中,万自清的牛发狂,将人家的一头牛追到悬崖,摔死了,他赔不起,只好依了人家的条件,于是有了万大胆,当然罚款也是人家掏的……
狗日的,牛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