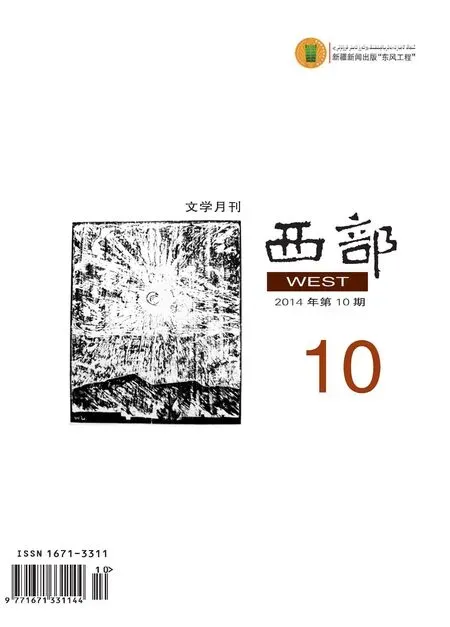小说天下野鱼湖
尹杰
小说天下野鱼湖
尹杰
天还鱼肚子白,河床上的石头就开始发青了。
走了那么久,还没见到湖。倒是不担心迷路,跟着河水走的嘛。河怎么曲折,人就怎么拐弯。在高的地势上看河,就是九曲十八弯的样子。
眼看着水面就开阔了,以为湖到了,紧走两步,却又要拐。拐过去,还是曲曲弯弯的河。
要怪自己。说清楚了的,湖快要干了,怎么可能还有大的水面。应该是要干了,河都缩成这样了。
后爹说,干了,那车就要露出来了。
就简单准备了一下,上路了。可是没到地方,车就不走了。前面没路了,得自己走着去。司机也说,那湖早干了吧。
本来是有路的。车走的路。应该还很宽敞,很平整。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鱼,一车一车地拉来,又七条八条地进了各家的门,又端出来,扎着堆儿地洗?都是一样的鱼,不一样的,是洗鱼的口音、洗鱼的盆和洗鱼的手。鱼腥味飘出来,却不觉得难闻。接着鱼就煎了、烧了、炖了。糖的味道、醋的味道、菜油的味道,红的黄的,扭绕着混在一起,还是有点腥,却又香得让人难捱。
湖干了,就没路了,因为没人去了。路,就让风刮跑了。这不稀罕,就像人,皮肤、头发、牙齿,还有好的身材,被年岁刮跑了一样。
被各式的车轮子碾了千遍万遍,板结得如钢筋混凝土的路,让风刮跑了。先是浮土给卷了去,石子就露了尖儿。风从西北方向刮来,石子背风地方的土又松动了,跟风走了(实在难以想象,石子也有背风的地方,那么小。可是,小就没有背风的地方了吗?)。那么,土又去哪了?自然有地方呆着,聚在一起,多了,就是沙漠。石子就越露越大,到最后,整个儿脱壳而出了,像个吃了肉的桃核。又比桃核多棱角,不规则地四面戳着。路上光剩下这些石子,就像人老了光剩下骨头。路上的石子和戈壁滩上的石子一样多了,路就没了。
路没了,还有河。幸好还有河。河也没了,还有河床。现在,就走在河床上。眼前的河,不叫河也不过分,还没有干了的河床宽,河水汩汩地流着。只有窄和陡的地方,才有白浪花和低吼,还叫人知道是条河。
天依然亮,水却暗了,河床也更青了。
河床上发青的,是石头。比被风刮跑了的路上的石子圆滑,个头也均匀。这些石头,让河水玩弄了那么久,河水退了,棱角锋芒也不能恢复。
就沿着河床走吧。河再怎么曲折,总要流到湖里去。就是中间断流了,干的河床也好认吧。早就想到要走这河床,只是没有想到要走这么久。
把手电从包里拿出来,试。又不敢多亮,怕过不了夜。包里还有水和小半块馕饼。摸手电的时候,又摸到了肉包子,临走时后爹塞进包里的。凉是凉了,弹性还是很好的。
早就知道有那么一回子事。亲爹掉进湖里,后爹就来了,中间没隔太久。自己什么都知道。
亲爹连人带车掉进了湖里,像是安排计划好的。临走,还给家里挑了两担水。
你妈说,他可从不挑水的。这没滋没味的话,后爹说了快三十年了,像是怎么都想不明白。
事儿说久了,就说淡了,像书看久了,就薄了黄了,字迹不再黑白分明一样。
就这么淡了,也很自然,没什么不好。湖,现在就很少有人说起,不再挂在嘴边。不说,谁的脑子里也不会凭空再冒出那湖,因为不再有野鱼。在人们的心里,野鱼和湖,先有野鱼,后有湖,没了野鱼,就没了湖。再说,人们嘴里又不缺鱼,膘肥体壮的鱼,从池里捞上来,在下锅前,还是活的。
人们喜欢鱼是活的。以前见多了死鱼。死的野鱼,帆布盖着,成车地拉来,散发着浓烈的腥味儿。车走一路,就是一路的腥。转上一圈,天都腥了。揭开帆布,有人会晕过去。卸了大厢板,一整车死野鱼就倾泻下来,哗啦啦、白亮亮的一片,地也腥了。
亲爹从拉鱼的车里出来,里外衣服脱掉,光着膀子洗,也洗不掉身上的鱼腥味儿。换了衣服,过上几天,还是有。还没等味儿散尽,又去拉鱼,味儿又再次浓烈。对亲爹,能记住的,就是这鱼腥味儿。
亲爹最后一次去拉鱼,是在冬天。上了年纪的人,聊的时候,是这样开场的,那年冬天,就是克子他爸死的那年冬天,真是怪,下了雾……那年冬天用亲爹命名了。
那年冬天,四九,下了雾。是四九啊!人们奇怪,这地方,夏天干死,冬天冷死,打霜也好,下雪也好,怎么就下了雾?老人们总结了,是因为天不冷,太热了。现在,一遇到暖冬,老人们还会说起那年冬天,好像暖冬就是从那年才开始有似的。
亲爹拉鱼的车就掉进了湖里。要是不掉进湖里,拉回来的鱼就是过年的鱼。人们都在等着吃这一口鱼。
谁都没想到,湖没冻住。连抓鱼的也没想到,还和往年一样,在冰上凿窟窿,下网。亲爹的汽车,也和往年一样,开上了湖,就在冰窟窿边等着。打上来鱼,直接就装车。活下来的人说,那次打上来的鱼可真多,又肥,都有一尺来长。眼看车就要装满了,湖却咧嘴笑了。先是有头发丝儿一样的纹儿,带着好看的冰花。聚在一起,才开了口,笑成了嘴。嘴笑着,咧得好大,又努力地和邻近的嘴接吻。打鱼的,拉鱼的,谁也没注意到脚下的嘴,都看着一网又一网的鱼流口水。一整车的鱼,就掉进了湖里,连着人。
捞了几天都没捞上。开春,又捞,还是没捞上。湖太深了。都想着,除非湖干了。没想到,三十年后,湖真的干了。
知道这事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活着的,也都老了,谁还会听他们絮叨。他们自己也懒得再多说,不如在太阳地里打个盹更好。
一件老事儿,特别是像亲爹这样有头没尾的老事儿,怎么说呢,有点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是不定时,其实是还不到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引线就着了,炸弹就爆了。也可能不爆,永远都不爆。
清明,不是放假了嘛。要是没有这个假,这个炸弹能不能引爆还真的不好说。
几乎每家每户都去上坟了。以前从不上坟的人家,也提前几天就开始张罗了。买菊花、叠黄纸、包饺子。这里上坟一般都供饺子。给放了假,不去上坟好像都说不过去了。不放假,还好说,有个理由:工作忙,离不开,没时间。在心里想想,顶多是在心里想想,也就过去了。有的时候,都努力地不去想,装傻。周围人不说起,就当没这个节。时间一长,就是真忘了。
每家每户都把老底子翻了出来。哪个长辈,哪个亲人,谁谁谁亡故了,哪一年,什么事儿。也不用太费什么劲,本来就是带骨连筋的亲人。一想,就觉得这些年是不是都怠慢了,气氛就凝重了。进进出出的,都稳当多了。
这地方历史不长,几十年吧。有一开始就过来扎根的;也有新人不断地奔过来,在此地安了家,但根子还在别的地方。就有了一个问题:有的人家,后山上就躺着人;有的人家,就没有。可也不是绝对的。扎根几十年的,不见得这几十年家里就有过事儿。才来的新人,也不一定在这儿就太平。
烧纸的,就分成了两拨,一拨是后山有人的,一拨是后山没人的。后山有人的,会在亡故的人脚下摆上菊花、饺子,洒扫一番,烧些黄纸,再哭上一鼻子,磕了头,下山。也有不哭的,高高兴兴地上山,也是洒扫祭奠,再高高兴兴地下山,就当是家庭聚会。
后山没人的,可确实也有要祭奠的亲人,但坟头远在外地,隔着许多个省,或是要坐许多个小时的火车汽车才能到。那就找个地方,荒郊野外,十字路口,摆上吃的,烧几张纸,表示一下。烧纸的时候,还得多带着点小心,管好火,再失了火,就不好了。
照这么说,给亲爹烧纸,就该归后山没人这一拨的,因为后山确实没有亲爹的坟头。
不光后山没有,哪儿都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呀。按现在的说法,亲爹属于失踪人员。不是常说,某起事故重伤多少死亡多少失踪多少吗?
第一个清明假期,就像平常一样过了。第二年的清明,还是后爹先张罗起来的。还是那句话:临走的时候,他还挑了两担水,你妈说,他可从不挑水的。
就买了黄纸,也找个地方烧了。本来烧一烧就完了,可一烧就烧出了眼泪。三十年了,还是第一次为亲爹流眼泪。说来就来了。眼泪这个东西。
水还亮着。一抬头,天却暗了,隐约看得见星星。有水的对比,河床上的石头就青得发黑了。两岸的杨树也模糊了。
凉气就漫开了,潮湿清冽。河水沙土野物的味道,缠绕在一起。
要说,这河也不是头一次来。上小学吧,学校组织夏游,来过一次。光是来,不算回,就是一上午的车程,算得上一个长途夏游了。一路上,吐得不行。只记得见到了一条大河,宽得看不到对岸,一搂粗的树,都长到了河当间儿,岸边全是浓重的树荫,和石头一样,河水也是青色的,有土百灵这样的鸟儿耸着肩,夹着翅膀掠过水面,水很大,河中央有白浪花,应该是大石头,河水就吼起来,岸边的水就安静多了,只有小波浪抚摸着黑土。只记得这些。
眼前的河,就不像河。河水萎缩了,成了溪流。岸边,原本浓黑茂密的树叶失了水养,也焦黄翻卷了。只有河床上倒伏的树干,剥落的树皮,以及散落在河床上的褐色枝杈,还能让人想起这里的水曾经大过。
河老了,像人一样老了,老得露出了骨头。河床上的石头就是河的骨头。走在河床上,就是走在骨头上。
树干枯了,根子还扎在土里。亲爹就这样没了,无踪无影地没了。说是死了,又没找到什么。说是失踪,又确定就在那湖里。湖,是亲爹最后的去处。
祭奠的时候,就朝着湖的方向。可还是觉得缺了什么。是不是该到湖边去一次了?
祭日那天去,恐怕不行,雪大封山,路难走。清明前后,天气还冷,尤其是河边会更冷。中秋应该最合适了,本来就是一家团圆的日子,也有祭拜的讲究;天气又好,刚热过了劲儿,晚上露宿,也不太凉。
家里人却都反对。后爹没说什么。反对的理由,就是事情过去太久了。另外,不能走车,也是个大问题。再说了,清明也烧过黄纸,实在不行,就再烧一次。
一边执意要去,另一边坚决地劝阻,就僵住了。
还是后爹开了口,干了,那车就露出来了。
后爹还说,你和你爹一个倔脾气,十头牛也拉不赢,你爹要是听了劝,我也成不了你爹。过个年吃不吃鱼有啥吗?非要跑那一趟不可,不跑一趟,心里就有猫爪子挠?
后爹老了,越来越喜欢把话说个没完。
亲爹掉进湖里没多久,后爹就来了。来的那天,先挑了两担水。水缸满了,又挑了一担,让桶也满着。又拿起笤帚,里里外外扫了一遍。完了,又扫一遍。扫完两遍,才把笤帚放下。第二天,又扫。天天都扫。不扫地,就干别的,拿块抹布,桌子、凳子、床头、柜子,四处地抹。活儿分男女,这些活儿,后爹干得也顺手。
后爹是带着娃娃来的。是两个姐姐。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走了一个,进来三个,多了张上下床,多了两张嘴。多的人,说话做事却没让人觉得不顺眼,觉得别扭。后爹爱说话,见到啥能说啥。你说这茄子皮咋长的?这么皱巴,像老奶奶的脸。你说这羊是不是也不闲着,有点像我,要不咋这么瘦呢?下次,把我也剌开,看看是不是也这么干巴,不上膘,肯定是……
挤在一个屋檐下,人一多,就过得热热闹闹的。一热热闹闹的,过得就快了,想的事就少了。
天还亮着,月亮就披了薄纱,挂在东边。现在却看不到了。四下里去寻,也不见影子。以为天会黑透,像锅底,却没有。黑是黑,却黑得发蓝,像一整瓶蓝黑钢笔墨水,隔着瓶子看的颜色。
月亮一定还在,一定躲在哪里。
两岸的树干聚在一起,浓重的一坨。看上去,比天还要黑呢。枯死的,茂盛的,都黑黑的,立着不动。
手电打着了,也照不了多远,照得脚下的石头发白,也照不到岸边的树上去。
想找个地方过夜。眼睛跟着手电四处看,看到的都是石头,都是拳头大小。再小一些就好了,躺在上面,也觉得舒坦些。要不,就再大一点儿,像传说中那样宽敞的大青石。
坐下来,喝点水,就不想起来了。关了手电,河水还是白的。眼睛又寻了一圈,还是没见月亮。一定在哪里躲着。
往林子里看,还是黑黑的、重重的一坨,让人不知道深浅。想进去,又怕遇到什么出不来了。
吃了几个包子,身子才暖和些。中秋节气,河边竟会这么凉。
车停下来的时候,都是中午了。司机的意思,找地方歇上一晚,第二天再走。没听劝,就上路了,想的是早去早回。出发前,问过人了,说还好走,只要顺着河走,就迷不了,也没啥大家伙,小的又怕人,河边兴许还有牛栏,喝上一碗奶茶,能提不少劲。
既然这样,那还等什么?还要早回呢。后爹的药,还在单位的抽屉里放着。这药断货了,是托人从外地捎回来的。车子刚上路的时候,把家里的事又捋了一遍,就想起这药了。急出一身汗,才想起家里还剩下一些,没吃完。其实,早考虑过,安排好了的,是自己把自己的安排给忘了。
在这一点上,又随了后爹,爱操心,喜欢把家里的事翻过来倒过去地想。
湖,还有多远啊?
从中午走到现在,天都黑了,还没见到湖的影子。不是说只有八九个小时的路程吗?迷路了?一直是沿着河床走的啊。除非,走到了河岔子上。可这么小的河,会分出岔来吗?也不敢随便地就说不会。杨树都可以开枝散叶,人更不要说了,河当然也可以。不要忘了,这曾经是条大河。
接着走吧!总有个头的。
本来还是干干的河滩路,突然没了,只剩下水。
不会是湖到了吧?
岸只有一人多高,却是陡的。想上去也不太容易。捡石头,扔进水里,听着不像很深的样子。迟疑了一下,就下进去,拿根树杈,前面探着。想着水深了,就退回来。
才没过膝盖,就又浅了。又来到了干干的河滩上,却见到了月亮。月光下,到处都是青白的石头。脸一定也是青白的。
到了一个牛栏旁。没有牛,只有散发着草香的牛粪味儿。
牛栏也还完整。牛再赶来,还能拦住。牛栏旁是块平整的空地。赶牛的人没留下什么,就是一块空地和几块石头。没有预期的奶茶,只能坐在石头上休息一下。确实有些让人失望。
也许,牛已经被赶到了湖边。听司机说,湖干了,却没有干透,还有水洼,牧草肥美,牛羊和石头一样多,到了湖边就好了,什么都不用愁了,说不定还可以吃上好吃的羊肉。
捡几根树枝,架在石头上,再找些干草铺在下面。干草静静地着了,红火苗腾了两下,就隐在烟里,白里透红。呛了两口烟,有微风,火才呼得一下子大了。把手凑到跟前,手心手背地搓。又把屁股底下的石头往前挪挪,让湿了的鞋和半截裤腿也享受温暖。脸感觉已经烫了,摸上去却是凉的。眼睛鼻子嘴巴用力紧了紧,又松开。
喝了两口水,火也小了。心里想着湖,就任凭火小下去。裤腿也没烤干,只是烤热了。火一小,又凉回去了。
火没了,烟又出来。僵着,迈过灰烬。月亮又跑哪里去了?石头黑了不少。
打着手电,就有小虫飞来,迅速地划出一道亮线。消失了,又再来,划出好几个螺旋。能看见水亮,就把手电关了。又看见两个发出幽光的点,忽明忽暗地晃着。脚下自然就慢下来。盯着看,亮点又渐渐地没了。没了,水上的光才照出一个黑黑的轮廓。是个野家伙在喝水,把嘴放进河里,又抬头看。眼睛一会儿亮,一会儿暗。野家伙不再喝了,两个眼睛不动地亮着。只一会儿,就扭身飞快地走了,无声地进了远处的林子。
才松了口气,往林子里看了看,又往前走。捡了个树杈握在手里。想着快些天亮,或者是,天亮前找到湖也好。
只精神了一会儿,走了一段,又坐下来休息。本想就这样坐着,等天亮。看看四周,又起来,继续走。走了没多久,又停下来,喝水,吃包子。走走停停的。
再坐下来,就感到脚痛,想是脚底打了泡。把鞋带松了,凉气就咝咝地往里钻。脱了鞋,打着手电看,还好,就是有些红。
两个赤脚,各放在一块石头上。凉意就从脚心漫上来,到了头顶。赶紧穿好鞋,长出口气,把肩膀塌下来,肚子也松了。眼睛闭上,就不想睁开。
先眯上一会儿吧。就在石头上,东倒西歪地眯着。也不顾什么了,干脆,裹紧衣服躺下。
竟然做梦了。有一大片亮的东西。
干了的湖,在梦里又满了。有水鸟,夜里也不栖息,在湖面游逛,羽毛黑白分明,小的绒毛在风中微微地抖。湖水里不知道含着什么矿物,发亮,像水下装着灯,从湖底往上照着。
赶紧醒了,再赶路吧。却发现,眼睛已经是睁着的。哪里是梦。真的是湖。
湖没有干。干了,又满了。
圆的月亮,安静地挂在天上。月光下,湖、石头、脸,一样的青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