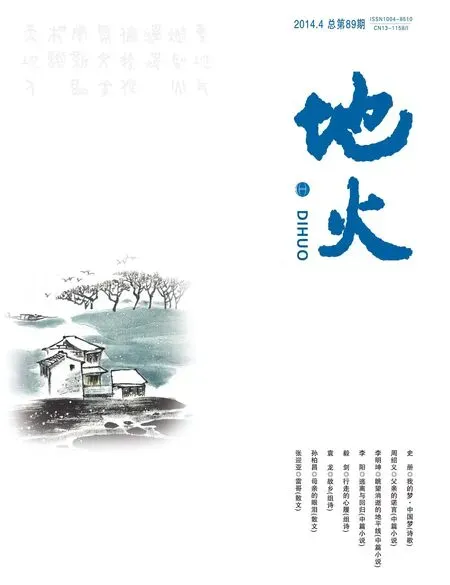母亲的眼泪
■ 孙柏昌
母亲的眼泪
■ 孙柏昌
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流眼泪。
也许,母亲哭过,也流过泪,只是我没有看到过。
堂哥对我说,母亲确实哭过,在父亲的坟头。
直到今天,母亲已经去世三十年了,对于母亲的眼泪,我也只是一种模糊而陌生的感觉。
三哥说,母亲的心真硬,在大姐的坟头,一滴眼泪也没落。
我的大姐早母亲十年去世,在遥远的伊春。母亲一生,唯一的一次远行,就是去伊春为自己的大女儿奔丧。大姐举家北迁的时候,母亲的心里是多么的痛。在我们七兄弟姐妹里,最懂母亲的,应该是大姐。父亲去世后,母亲所有的心里话,只对大姐说。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母亲和大姐在一起商量过,还让不让我继续升学。我尽管还小,不太懂事,也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家境也许真的不允许我再继续求学了。我对母亲说,我不上学了。母亲说,他不想上就不上了吧。大姐也说,不上了,他又能干什么?那时,我长得瘦小单薄。最后,母亲和大姐达成了一个意见:让他去考考吧。
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母亲对大姐说:“越是不想让他考上,偏偏……”
“那怎么办?还是让他上吧。”大姐说。
大姐懂得母亲的心。
大姐去伊春时,有太多的牵挂与不舍。她是母亲的一个肩膀。母女彼此的依靠,才会平安度过那么多艰难。她不愿意走,母亲也不舍得她走。姐夫让我劝劝大姐和母亲,为了外甥男女的前途。
记得的,关于大姐的走,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你别再劝你大姐了。她不愿意走,就不走。”
我也记得,大姐哭了:“俺不愿意。非逼着俺走。”
我不知道,她和母亲单独在一起告别时,母亲流过泪吗?
母亲对我说:“你姐一走,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或许,母亲真的会有什么预感?母亲的话说得那么平静,却忍着太多的痛。
那时,我真的不懂母亲。
当母亲站在大姐刚刚培上新土的坟茔前,她居然没有流下一滴泪。没有泪的母亲,心里储存着多少痛。
母亲回到沈阳大哥家的时候,曾经让大哥给我拍过一封电报,让我去看她。我没有去。刚刚失去自己最爱的女儿,母亲的心是有多么痛。我却不懂。
在我的眼里,母亲总是那样一副宁静的面容。没有眼泪,也极少舒心的大笑。
我能够记得的,唯一一次母亲开怀的笑,是关于奶奶的。奶奶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饺子藏在被窝里,给我的侄子。
“知道吗,你奶奶把饺子藏在哪儿吗?被窝。”
母亲笑得那样舒心、灿烂。此刻,我仍然会听到那笑声。
我每次回家,母亲总是那样静静地看着我:“怎么总那么瘦。”
即使是刻骨铭心的惦念,母亲也说得非常平静。
我真的没有看到过母亲流泪。我不知道,母亲一个人匍匐在父亲坟茔时,泪水会流得多么汹涌……
松的香
故乡的山,散漫着许多好闻的气味。
当暮春或初夏的阳光浩荡在山野的时候,柔和的山风里,就蒸腾着粘稠着太多的芬芳。野菊、苦丁花、瓜篓、刺儿菜、蒲公英、地黄,都会有自己的香味。野草也有的,如山胡椒、苫草、三棱草什么的。香味最浓烈的,应该是松树的香了。
我喜欢闻松香。
故乡的山生长着许多马尾松。疏落、散漫,孤零零的,一律很矮小,高两三米,干不盈握。不知道是因为山的贫瘠,还是因为物种遗传,故乡的松,好像都是一个个不愿长大的孩子。故乡的山,应该是很古老了。裸露的山体,兀立的浮石,都失却了嶙峋锋芒,一律圆韵着斑驳着苍老的模样。暗青色的花岗岩的岩面,隐约着许多岩花的花纹,凋零的,正在开放着的。石头也会开花的。那一棵棵矮小的松,也是上了年纪的。
小时候,我经常去山上拾柴草。干枯脱落的松针,是最好的柴。松的干会分泌松脂。刚刚分泌时,如同一滴滴晶莹的眼泪。据说,受伤感染了的松树,才会流泪。松脂是痛的花。每当发现一棵正在流泪的松,我会坐在岩石上静静地看很久。渗流的过程缓慢极了,一滴眼泪形成珠状,需要耐心等待。山风摇动着松的枝,瑟瑟,那是松的呻吟?当松一阵伤心过后,松脂便会慢慢凝固成晶亮的一团,覆盖住自己那曾经的伤口。松的眼泪散发着馥郁的芬芳。
看过多少次松树流泪,我不记得了。只有一次,我禁不住那芬芳的诱惑,伸出自己的无名指蘸了一滴。眼泪在我的手指上晶莹了许多日子。我偶尔会闻。一闻,我的脑袋仿佛就清亮了许多。
人与气味,是一个很神秘的现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松的香情有独钟。是因为先天遗传的基因,还是在故乡山峦不断攀爬的童年养成的?不闻久了,心底会隐约着一种渴望。
小区花园里,也种着几棵松。也许园丁照料得太细心了,松,没有伤痕,也不会流泪。不会流泪的松,也闻不到纯净的芬芳。
在漫长的流浪人生里,我看到过许多地方的松。我曾先后两次去过小兴安岭的原始红松林。一次,晴天丽日。一次,迷蒙细雨。高耸的红松给了我许多威压,却找寻不回童年的梦境。故乡的松,那一滴滴泪的晶莹。
若干年前,我的脑袋开裂一样痛。我曾经买过一块松香,闻了又闻,没有缓解我的痛。
期间,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他找我写一个专题片,庆祝公司诞生二十周年。
我说,我脑袋疼。
他说,你去兴城,吹吹海风。不急,多久都行。
于是,我就去了关外古城。
我住在兵器工业部的疗养院里,步行二十分钟便可以抵达海滩。海风好像并没给我什么,倒是海边的一片马尾松林让我流连忘返。在那儿,我终于发现了一棵流泪的松。我的脑袋痛居然缓解了许多。
松树的眼泪会变成琥珀。我在俄罗斯看到了普京耗资六亿美元打造的琥珀宫,那金碧辉煌的琥珀宫里,华丽斑斓,却了无泪的鲜亮与晶莹。
故乡那松的香,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成了一个密码或符号。
鸟的巢
少时,我时常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发呆。
发呆时,会数屋梁上的燕子的巢。从东数到西,七个;从西数到东,也是七个。巢,新新旧旧的。我不知道,春景天,一年一度归来的燕子,为什么总会搭一个新的巢。它们是旧时堂前燕,还是旧时燕的一双儿女?
那时,母亲在拉着风箱。风箱咕哒咕哒地响。蹿动的灶火在母亲满是皱纹的脸上一闪一闪的。
母燕飞回时,四个鹅黄小口会趴在巢边喳喳叫。
去吧。慢点吃。
坐在门槛发呆时,我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屋梁上一只乳燕或者屋檐下的一只幼雀,啁啾待哺。
这是我们母子之间的心灵密码。一看到我坐在门槛上,母亲就会为我烧烤点什么。一个烤嫩玉米或地瓜,或者几片地瓜干、十几颗花生。
故乡的老宅,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鸟事兴旺时,家里会先后筑起四个鸟巢。南院的臭椿树上有喜鹊的;正屋屋檐下,有一窝麻雀在趴着探脑;堂屋的梁上燕子,每年都会如期而来;通向街面过道的木棚上,也有过两次燕子筑巢。过道的燕子,燕尾是黄色的,更好看一些。
小时候,我渴望养一只鸟,燕子或者麻雀。
我求父亲。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父亲却摇摇头:不行!
父亲说了不行,就一定不行了。我只好望鸟兴叹。
父亲说,燕子丢了一次孩子,就不会再来我们家了。你也别想再看到燕子了。
新生的乳燕还不大懂规矩,偶尔会把粪便拉到地上、饭桌上。父亲会蹙蹙眉:讨厌。屋檐下麻雀不断筑巢,会漏雨。父亲也会蹙蹙眉:讨厌!有时,父亲会从烟斗里捅出烟油,涂抹在几片草屑上,放到麻雀的窝里。我纳闷,问。父亲说,蛇怕,不会来打扰麻雀了。父亲也常常坐在门槛上抽烟。看燕子在门里飞出飞进,麻雀在屋瓦上抖着翅膀喳喳叫。父亲的皱纹会在弥漫的烟雾里舒展成蝶翼般的模样。
父亲不允,我就去山野里寻找鸟巢。记得的,我曾经找到过一个隐匿在草丛里的鹌鹑巢。河滩上,一蓬三棱丛里的一个云雀的巢。巢是空的,也旧了,没有小鸟或鸟卵。尽管,我每天都会去看,看看那巢的变化与动静。巢依旧。
后来,堂哥送给了我一只麻雀。那只麻雀与我熟稔了,追随了我整整一个夏天。在林丛,在山野,在小河。我逮蚂蚱喂它。它抖着双翼喳喳感谢我。
梦里,我有时又会静静地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发呆,看看屋梁上的燕子,屋檐下的麻雀……我不知道自己那曾经的鸟笼去了哪里。我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只鸟,一只燕子或麻雀,茫然地在雾霾的天空盘旋……
我想有一个巢,有一个温暖心灵的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