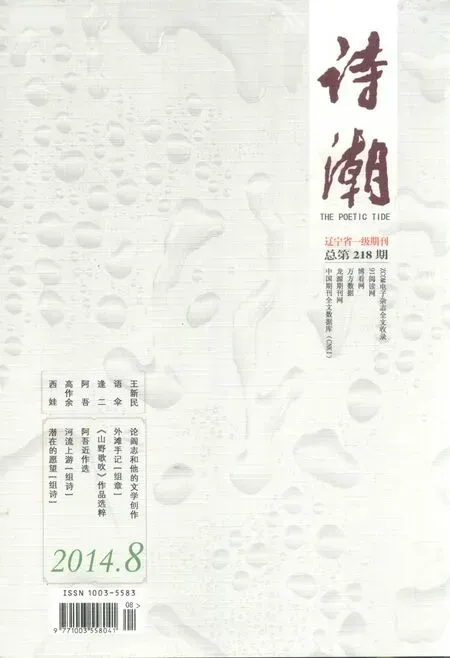它在代替世界,与我交谈
[《外滩手记》创作谈]
它在代替世界,与我交谈
语伞
“一个痴迷黑夜的人。”如果仅用一句话形容自己,我这样说。
黑夜的神秘与诗的神秘,似乎有灵通之处,许是它们无形的生命里暗藏某种血缘关系?它们是不是亲戚,其实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欢喜。当万籁俱寂,大地上的事物由清晰逐渐趋向模糊,目光却可无限辽阔与深远,思维亦可恣意妄行。我必须承认,我写诗,大多依赖于黑夜。
出于好奇,我曾经在夜空下同时观看月亮、星星、霓虹、烟火(如果再有流星、萤火虫等等,我想我会更恍惚),当各种颜色和形态的闪耀汇聚,我确信我已身在另一个世界,我也确信,是黑夜,让我体验到了如此奇异的光。所以,这些光,是黑夜唯一的慰藉。而文字于我,等同或者超越了这些光,它带给我的奇异感和慰藉,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那部分。正如在一个城市的地图上,外滩也是不可或缺的那部分一样。
外滩。写下这两个字,我难以言说此时的心情。或者可以说,在此时,它作为一个潜意识的意象,已经成为我超乎理性之上的“更为重大的现实”。望着萨尔瓦多·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永恒》,我陡然间感到灵魂在强烈地震颤。一种巨大的视觉冲击感,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审美侵袭。几块绵软得快要熔化的钟表,特别是垂挂于树丫上的那一只,让我有着去把它捧扶起来的冲动。但它宁静得可怕。我不敢靠近。抑或,它隐秘的潮涌,像一股狂热的时间的暗流,正在打乱我内心正常的秩序。我因此胆敢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到过外滩的人和没到过外滩的人。”
很多年前,我常常虚构未来的理想栖居地。离开故乡,抵达一个陌生的地域,在某一段时间,显得很急切。后来,渐渐舍不得了,却又真要作别。而今,我眼前的外滩,这水岸相接的画面,是我治疗思乡病的药引子。儿时有一片河滩,叫作“沙石坝”,有着蒲草、艾蒿、沙堆、鹅卵石等纯天然的绿色玩具,比这个城市最顶级的儿童游乐城都充满趣味。但是,回忆只能永远是回忆了。故乡最亲切的河滩,已被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所覆盖,踪迹全无。所以我对外滩,全然有如对故乡那片河滩相似的依恋的感觉。一个写作者的童年记忆和生活经历,是与其文字息息相关的,因此无须细说,便可窥见一斑,更难以掩饰。但诗人对自己的诗作过多地自我定义,我认为是遗憾的。诗人应该将更大的想象的可能,预留给读者。那种因共鸣而心生的愉悦,古人称为知音,今人叫作缘分。人与人,如此;人与景,亦如此。我与上海,岂能例外?这个城市的一切与我,岂能例外?外滩与我,又岂能例外?
外滩,理所当然是上海的代名词。移居上海十余载,一个国际大都市性格里的骄傲与脆弱,被庸常的现实生活逐一而迅捷地体现,让我目不暇接。似乎人人都是渡客,每天都在匆匆碌碌地赶赴渡口。抵达渡口的人,又处心积虑地,想自己手拿双桨掌握方向,成为摆渡自己的人。外滩,在上海无疑有着“光”的磁场,它普照着所有捕梦者去追寻理想之路,同时它又是迷茫者审视自己的镜子,而有时,它还看到某些人在它面前一次一次把自己逼向绝境。我以梦游者的身份,游荡在上海越来越炫目的外在形态之中,对现代人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一览无余。在城市文明病:沮丧、失眠和纠结的作用下,人心常常偏离轨道,甚至扭曲变形。现代人应该如何喘息?连庄子也未曾给出明确回答。我无数次独自漫步外滩,在目光里省去浦江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排除世俗的一切杂念,听风。黄浦江的潮水,被我看出了彩色的魅影和无数生命的在场。我看自己如看他们,我听他们如听自己。漫游在简明的自然之外,接近芜杂的精神的诱惑与危机,我自我存在于内心,也自我存在于世界。很幸运,我面前有一个外滩。它在代替世界,与我交谈。
卡尔维诺在谈到蒙塔莱的诗时曾说:“我把世界的消失,当成是城市的消失而不是大自然的消失。”世界与人类同在,城市永远不会消失。尽管很多时
候,我们内心深处暗藏着从城市逃离的冲动,但我们仍有数不尽的生活在城市的隐秘理由,仍有足够的或主动或被迫修复精神故障的能力。当我们领悟到活着的丰富内涵,便热衷于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光怪陆离,不断征服现实又不断被现实所征服,不断被时间借出又不断被时间归还。城市虚构的魅惑,对向往抽象特征的人心来说,无疑产生着多种奇特的抚慰。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等到另一种理想的城市诞生。
写作,就是实践记忆的经验,用个人的乔装集体的或大众的,无法向自己或他人说尽的那部分,乃写作的秘密。这个秘密属于我的空间,很长一段时间被外滩所占据、所充满,正如几年前被庄子所占据、所充满一样。散文诗让我听到了文字通灵的回声,记下了意念在瞬间缔造的神秘结果。现在,外滩和静默的夜晚,就在我身旁。
我又听见了熟悉的声音。我并不是唯一醒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