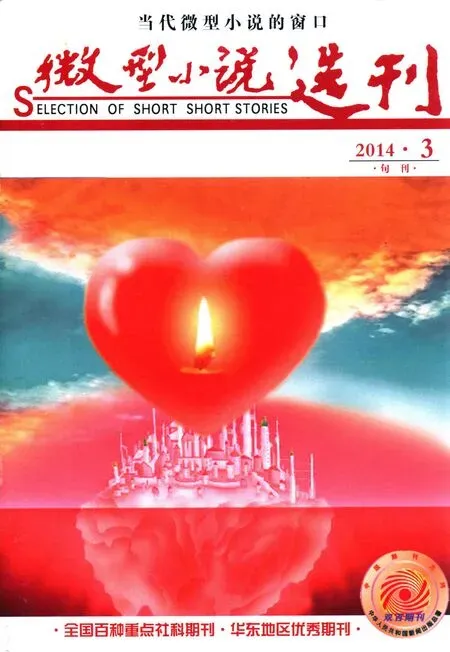黄 昏
□周海亮
黄 昏
□周海亮
兵溜出兵营,只想随便转转。尖尖的屋顶,肃穆的教堂,嬉闹的孩子,安详的老人……风吹来,田野里的香气,将兵醉倒。很多时候兵会忘记他是兵,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村子里的农夫,手里的步枪不过是一柄忠实的锄头。兵坐在田埂上抽烟,发呆,眯着眼,打量或者想象着远方和未来。枪被胡乱地丢在脚边,一只鸽子悠闲地踱着脚步,又停下来,歪着脑袋,用又小又尖的喙,轻啄着兵的枪口。
正是这时候,兵看到了姑娘。
姑娘从晚霞里走来,向晚霞里走去。姑娘用她瘦削并且圆滑的肩膀扛着粗糙的水罐。姑娘走得很慢,却轻盈,腰肢轻摆,扶住水罐的细长手指轻轻跳动,如同悄悄地抚起琴键。看到兵,姑娘笑笑,两颗虎牙微微地闪现,兵的眼睛便亮了,脸也红了。兵站起来,说,我帮你。姑娘说,谢谢。脚步并不停,身体从兵的面前灵巧地闪过。那个瞬间,兵无比幸福又无比悲哀地爱上了姑娘。他呆呆地看着姑娘的背影,他认为那是离他远去的天使。
能够溜出兵营的日子不多,然而每次溜出兵营,兵都会候在田野,等待黄昏里汲水而归的姑娘。能够看到姑娘美丽的脸庞和曼妙的背影,兵就心满意足,他不敢奢望太多。可是那天,鬼使神差般,兵还是将姑娘强暴了。
一切猝不及防,连兵都不敢相信。
兵将随部队离开村子,兵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看姑娘从他面前袅袅飘过。他站起来,说,我帮你。姑娘说,谢谢。脚步不停歇,娇小的身体,散发出醉人的香。兵心跳如鼓,大汗淋漓。他扬开臂,猛地将姑娘搂进怀里。
姑娘犯下一个错误,她不该挣扎。也许让兵静静地抱她一会儿,事情就结束了。或许她还可以让兵吻她一下,甚至,她主动吻兵一下。兵到这里是为保护他们的,兵吻她或者她吻兵,似乎都不过分。可是她竟挣扎。她不但挣扎,还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伴着尖叫,水罐从姑娘的肩头滚落,跌得粉碎。兵害怕了,将姑娘压到身下,又伸出食指,竖到姑娘唇边。兵说求你求你,别叫别叫。姑娘继续扭动身体,尖叫不止。她的尖叫也许足以传回村子,传进兵营。兵恐惧极了。他远比姑娘恐惧百倍。恐惧深处的兵终于失去理智,他表达恐惧的方式,是将姑娘的嘴唇堵住……
兵逃回兵营,发现他忘掉了枪。兵没有枪,就成了农夫。农夫随兵的队伍出发,脸色苍白。
兵看到姑娘。姑娘站在长官身边,缩着身子,抱着他的枪。长官问,是他?姑娘点头。长官问,确定?姑娘说,我在他的胳膊上,咬了一口。长官指指他,他站出来,走到长官面前。他的手中,空空如也。
长官说,你干的?
他点头,身如筛糠。
长官说,是你的枪?
他挺挺身体,说,是。
长官说,拿回你的枪。
他上前,将枪攥紧。抓到枪的他松了一口气,甚至,他开始想象几天以后,他抱着枪,跃出战壕,将一排排滚烫的子枪从枪膛里射出;他还想象战斗的间隙里,他坐在战壕里,吹起口琴。口琴声回荡在硝烟弥漫的黄昏,将埋伏在近处的敌方狙击手的眼睛打湿。
可是他错了。
因为长官说,现在把枪还给我。
他愣了愣,懵懂地将枪递回给长官。
长官说,脱下军装。
他似乎明白一些什么了。他给长官跪下,他说,饶过我。长官说,脱下军装。他转过身体,抱紧姑娘的两腿。他说,饶过我。兵的眼泪在那一刻汹涌而出,一片蒙眬之中,姑娘仍然如同天使般美丽圣洁、妩媚迷人。
长官举起枪,没有瞄准。枪响,兵訇然扑倒。他的嘴唇亲吻到姑娘的脚尖,姑娘感觉到烙铁般的滚烫。姑娘被吓傻了,她笔直地站着,不敢动,不敢叫,不敢哭。然后,突然,她转向长官。她抖着嘴唇,抖着身体,抖着声音,抖着表情,她说,你为什么要打死他?
他强暴了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死他?
这与你无关。长官说,他必须死。
但此时,兵还没有死。他还能闻到姑娘的体香,看到姑娘的脚踝,感觉到姑娘的呼吸。他没有死,但是他正在死去。兵在黄昏里走来,在黄昏里离开,兵的身后,世间的姑娘仍然如天使般美丽动人。
(原载《文摘周报》2013年11月28日 河南李金锋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