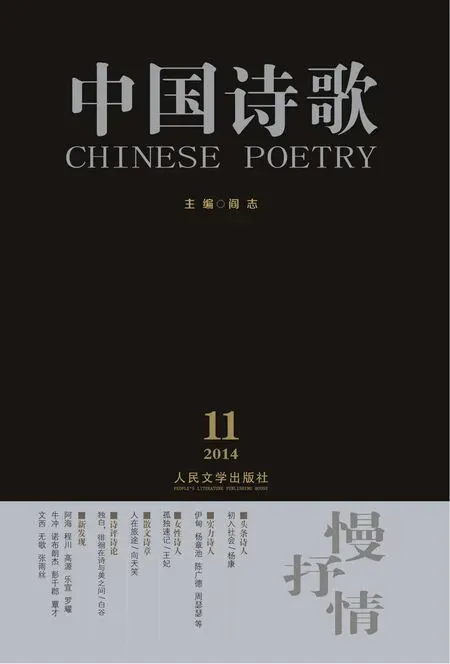诗学观点
□薛晓/辑
诗学观点
□薛晓/辑
●雷平阳认为,抒情性诗歌,在时空感的经营方面有着太多的典范,因为时间与空间可以点石成金般让诗歌语言闪闪发光,并迅速激荡普通读者的心。但它们也是双刃剑,用好了异彩纷呈,用得不好诗歌就会流于空泛和平庸。在优秀的诗歌作品中,此时彼时,此地彼地,也不是说让其产生对比性,以求出其不意,它们是合二为一的,彼此借用身体而存在,或让人难以分辨而产生迷幻从而引出许多无法预知的让人陶醉的误读空间,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出其不意的诗性,而更是以它们为材料,另外再造一片浩瀚星空,万物同宅,天下为量。
(《我只是自己灵魂阅历的记录者》,《诗选刊》2014年第6期)
●草树认为,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派的写作逐渐式微以来,诗人从时代代言人的角色走出来,回到了“个人”,个人化的写作不断缩小诗写的格局和版图,碎片化成为当代诗歌的主要标志之一。大部分诗人的写作,似乎在有意识地远离他们处身其中的时代,沉湎于个人感受或语言游戏,很少有人对时代进行整体性的关照和思考。事实上,对于一个优秀诗人来说,不能做到“整体之心”的清晰,就很难谈得上“细节”的精确,更罔言试图通过“局部”去收获“全部”。
(《象征或语言》,《青海湖》2014年第21期)
●高烈明认为,诗歌的艺术境界简称意境,意境是指作品中诗人所描绘的景物形象、生活画面与其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综合的艺术氛围。它能激活读者的思维,引发读者的想象和联想,让人犹如身临其境,在思想感情上深受感染,进而获得享受和感悟。这也是那些优秀的古典诗词必备的重要特点。我们在阅读古典诗歌时,要结合自己生活经验,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努力寻求诗歌中情景与意蕴和我们的人生经验、生活感悟相吻合的结合点。
(《中国古典诗词的阅读鉴赏问题探析》,《芒种》2014年第6期)
●苏震亚指出,某种程度上,一位诗人及其诗作的成熟与否,很多时候就是看其有无沉思的品格。或者说,诗人的成熟度,就是其沉思品格的成熟度。一个诗人,青春期写作往往是激情洋溢的写作,情感的波浪总是压制着理性的思考。但当到了中年,伴随着理性的天然回归和诗人自身的修养、学养的提升,诗人及其诗作的沉思品格,便理智而又天然地多有增加补充,以填塞青春期因激情过量而留下理性不足的空缺。
(《沉思的品格》,《飞天》2014年6月号)
●哈雷认为,纵观当下诗歌现场,人们似乎让诗歌肩负了太多东西:意识、思想、信念,甚至一个人的功名及生存,都希望通过这小小的诗歌之躯去完成。他指出自己并非不同意诗歌承载这些,古来素有“诗言志”之说,然而,用诗歌表达人的内心,要求我们必须真诚、可信、自然。以人的价值为参照,诗歌可以成为一个人人生坐标的最精致的部分。所以,他赞同以诗歌写生命,而非用生命写诗歌。须让自己成为完整的、负责的生命个体,而诗歌伴随着这种成长自然就会逐步地抵达所要追寻的境界。
(《用心聆听岁月的声响》,《福建文学》2014年第6期)
●郭志杰认为,语言的存在不可能被谁写尽,但是在语言的操作中,诗人必须认识另一种更为大的存在,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那就是哲学。哲学对于诗人,或许应该是存在的根本;当我们的内在世界十分贫乏之时,我们很难进入诗的纵深。是的,存在离不开语言这一本体,但语言并不是诗的终极,诗的终极应是对世界的追问,这一追问将伴随诗人创作的每一步。哲学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制高点,是人类意识的高度概括。时常与哲学相伴的诗人,肯定留下哲学所赋予的那一质地,那不一样的思维与体验。
(《感受道辉》,《福建文学》2014年第6期)
●车前子指出,诗对于思来说,是反思;思对于诗而言,是反诗。诗人看上去总是拙劣地模仿思想家,而他不为自知的杰出之处恰恰是伪币的制造者。诗人因为诗歌而获罪的根本原因是“思想罪”,这并不因为对思想的定罪比对诗歌容易。或许这正是由于诗歌的“诗”与思想的“思”的确不具有相近的品质而带来的后果。诗歌的“诗”这一只手是务虚的,与思想的“思”这一只务实的手相互对抗,保持了语言世界的平衡。这是一种反,在这个过程中,诗思阴阳相荡,呈现某种生命的悲哀,或者死亡的狂喜。
(《无笔记》,《红岩》2014年第3期)
●森子认为,诗歌就是诗人的精神生活,即使诗人写日常生活,也是将其纳入精神领域来考察。诗歌精神的指向不在诗外,而是在语言中,在语言中就是在人类的命运之中。当代诗歌的精神来自语言,也指向语言。诗歌本身就是精神的样式,诗歌之外并无诗歌精神,诗人通过语言能量的注入,传递其精神,诗歌进入阅读、传播领域也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那就是说,诗人的使命与责任感是改变语言(何其难,这几乎是不能完成的任务。改变语言即改变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表达方式),从而生成世界。
(《天赋,强迫与反弹》,《红岩》2014年第3期)
●姚舟指出,在日渐浮华的现代社会里,顾城与海子的诗歌创作却始终坚持着反身自我、本真投入的美学价值。顾城有着如孩子般纯稚的梦幻情绪,海子则坚持敏感而倔强的生命极限抒写。意象,或者说寓意之象,即文人借助物象来寄托其主观情思。由诗歌意象最能了解诗人心中深藏的精神渴望。“梦”意象一直伴随着顾城的诗歌创作,而海子的诗歌创作则用“花”等意象来寻觅与诉说,在梦的世界与花的天地里,世人得以窥视诗人那充满诗意与幻象的心灵世界。
(《由诗之意象考究顾城与海子的诗歌创作》,《芙蓉》2014年第3期)
●张德明认为,诗人的精神视野包括他们的艺术观念、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诗人的审美想象则是诗人想象和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其能力通过诗歌语言而具体体现出来。应该说,诗人的精神视野和审美想象是密切关联着的,二者相互促发,互为因果,共同孕育了诗人的艺术成果。当然二者也有明显的分野,如果说精神视野是隐形的,潜伏状的话,那么审美想象则是显性的,可以在诗歌中确切提取的。
(《当代诗人的精神视野与审美想象》,《山东文学》2014年6月号)
●刘波认为,诗歌不是完全描摹现实的载体,它很大程度上还是语言的飞翔姿态和情感节制出的思想力度。因此,从经验到超验的转化,从语言到思想的过渡,从日常生活到人生可能性的演进,就是诗歌更内在的美学通道。如果诗歌仅仅只限于盲目的语言游戏,难免会陷入轻浮、浅薄、平面化和无力感,终究是走不远的,它必须联于我们的内心现实,达至精神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这就是当下诗歌所匮乏的力量感。
(《尝试、冒险与突围》,《山东文学》2014年6月号)
●罗小凤指出,安石榴通过对移民诗人状态的考察和思考后认为:诗写者在经历彼岸游历之后的聚集,在很大程度上都打破了原生的惯有模式,焕发出另一重写作的魅力;一个诗人可以在某个地方因为某种聚集而获得写作的超越,同时还可以在另一个地方的另一场聚集中获得再次的超越。罗小凤分析,诗人只有在经过游历之后将本土经验和异域文化会聚才能获得写作的超越,因为这种会聚能打破原生惯有模式。安石榴敏锐意识到诗人只有在不同文化的冲撞下才更能意识到区域特性,文化冲撞下的诗人在写作中常常使用比较视野。
(《“他塑”与“自塑”的互文性建构》,《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
●火东霞认为,抒情本来和叙事并行不悖,只是诗歌的形式更擅长于优美的抒情与冷峻的逻辑。正是因为八十年代的激情书写,放弃了日常生活、放弃了对个人经验的关注,才有了九十年代对口语化、个人化的极端鼓吹。不过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忠实于其内心、关注自我的同时,必须关注历史、关注理性、关注人类或者某个族群的现在与未来。
(《那些超验的、悲苦的抒情》,《朔方》2014年第6期)
●张嵩指出,诗是我的精神家园的红色,它热烈,充满着激情,可以信手涂抹。我写作新诗就是这种感觉,自由、浪漫、躁动、狂妄,感性大于理性,一种无序的状态。在我的文学分类中,新诗是鲜红色的,个性张扬,极具魅力。古体诗词形式典雅、神韵诱人,颜色自然也是红色的,是深红色的,古道热肠,意境辽远,含蓄包容,文辞幽雅。
(《搭建精神的家园》,《朔方》2014年第6期)
●黄永健认为,首先,散文诗与非散文诗的边界(那堵看不见的篱笆)是活动的。其次,散文诗语言是诗性语言,散文诗作家的第一要素是情感能力。目前散文诗诗人的情感丰富充实者多(在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前,“来来往往一首诗”的散文诗和散文诗诗人比比皆是),而写出才情、个性,写出具有民族精神、时代群体感受、文化关怀、终极关怀和宇宙意识杰作的不多见。再次,散文诗本来是用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痛楚的,可是到了极讲温柔敦厚的文化中国,又被很多现当代中国散文诗诗人作为美文来曼舞风花雪月。
(《中国散文诗的未来》,《散文诗》2014年6月上半月刊)
●王忠友认为,中国散文诗在繁华背后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散文诗未能走出清浅的抒发与表达。二是创作上的相互因袭,思想与认识上的守旧,导致散文诗“草木人间”的单一与“风景万物”的残缺。三是纯粹思想和哲理的表达,形而上的说教太多,导致大量的散文诗缺乏诗人感情升华的美的形象与美的过程。四是大量存在的小散文鱼目混珠。
(《当下散文诗之现状与未来之走向》,《散文诗》2014年6月上半月刊)
●徐豪认为,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契合的产物。外国散文诗从形式上影响了中国散文诗,中国传统文化从创作思想和创作原则上影响了散文诗作家,因而产生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散文诗。散文诗诗人一旦在主体意识上偏离了散文诗的现代审美意识,其笔下的作品就易流于单向平面性的东西。现在散文诗最明显的进步是散文诗作品整体是“动态”的,情节上,不再是对一事一物的“咏叹”,而是用跳跃式的镜头,向前推移;语言上,对凝练、暗示、跳跃、省略的运用,更富有弹性和张力,更向诗的语言靠拢;内在结构上,情感立体交叉呈网状,不再是平滑的线形。
(《回归散文诗的审美功能》,《散文诗》2014年6月上半月刊)
●冯明德认为,散文诗与现实不可割离。生活是不能高于的,生活只能还原。还原生活不是简单的、肤浅的描摹,而是一种艺术的再现。散文诗肯定会介入生活,但不一定会影响生活。散文诗没那么大的功能。一首纯个人化的散文诗,是生活,有一定的社会性,个体性的凸显导致了社会性的弱化,谈不上影响生活。当然,一首切中时弊、反映现实生活的带广泛社会性的散文诗,却在弱化个体性的同时凸显了其社会性,对生活可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两种走向都是散文诗不可或缺的。
(《散文诗:朝向未来的可能》,《诗潮》2014年6月号)
●黄恩鹏认为,散文诗创作呈立体、复调,更具“文本性”。诗人通过散文式的诗文本创作,隐喻所指。这个隐喻,即是让人能从文本中悟出什么析出什么。它切中现实问题、映射问题本质,其美学特征在于诗人对创作意义的觉醒,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打磨。而“陌生化”意境的创造,必然会带来陌生化意义的生成。这种独特思想,就是隐喻性的诗文本。当下中国散文诗创作,需要诗人具有大视野和大胸怀,要有自由言说、不被意识形态钳制的勇气,要“野一点儿”地写作,不要“规矩一点儿”地写作。
(《散文诗:朝向未来的可能》,《诗潮》2014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