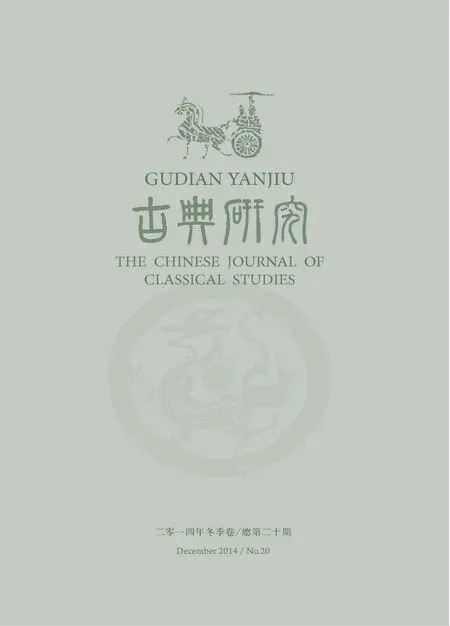由《解老》探韓非的“內聖”學
劉娟
(中山大學哲學系)
由《解老》探韓非的“內聖”學
劉娟
(中山大學哲學系)
“聖人”是韓非的理想人物範型,《韓非子》一書時常在關鍵部分提及,但這些部分多體現“聖人”用世表現出的功效,並非聖人之所以爲聖人的原因。韓非在《解老》篇中,由對《老子》的解釋,闡明對其學說至關重要的“道”論,使得韓非對於“聖人”何以爲“聖人”的重要說明都在此篇中一一呈現。本文以《解老》文本爲核心,先說明聖人探查到“道”“不制不行、玄虛幽冥”和“變化周行,成就萬物”的特點,再說明聖人由“虛靜”的德性領悟“天道”達致“天人合一”,更因“慈”於萬物製作“君道”,使聖人“身國共治”,“內聖外王”。這三方面依次說明了甚麼是“道”,以及聖人如何體“道”,聖人與“道”的關係,體現了“聖人”的“心性”與“工夫”層面,展現出韓非聖人的“內聖”學面相。並同時指出“聖人”的這些內在屬性與“王”貫通的方式,以理解爲何“聖人”方是韓非理想君主的擔當者。
Author:Liu Juan
is Ph.D Candidate a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E-mail:ljfollow@gmail.com“聖人”觀念在先秦諸子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老莊、荀孟、管韓、甚至鬼穀子都時常提及“聖人”,以作爲他們論述某類理想人物的範型。學界對先秦儒道兩家的聖人研究較多,其他學派則較少。本文期望以“解老”爲重點,闡述韓非“聖人”的內在屬性,說明韓非的“內聖”之學。
《韓非子》“聖人”一詞共七十一見,大部分出現在韓非形容“治道”的偏正短語中,以起到修飾限定“治道”的作用,如“聖人之治民”,“夫聖人之治國”,“聖人之爲法也”等等,對這些詞語的分析可以看出“聖人”要麼聖王一體,治理邦國(全書“聖王”一詞九見,“聖主”一詞三見,“聖君”一詞一見,這些也屬於“聖王一體”類型的君主),要麼輔佐在位君主治理。但“聖人”具體的“治道”乃“聖人”之用,並不能體現“聖人”之謂“聖人”的原因。
《解老》中的“聖人”則不同(其中聖人凡十八見),因爲在《解老》中,韓非通過對《老子》一書部分章節的解釋,處理了對其學說至關重要的“道”論,使得韓非對於“聖人”何以爲“聖人”的重要闡述都在此篇中一一呈現,因此我們探察韓非的“內聖”學以《解老》篇爲主。
一、聖人體“道”
“道”的概念在韓非哲學中具有關鍵地位,《韓非子》以“主道”、“明君之道”及“人主之道”等語指涉統治術,《解老》中的“道”乃“萬物之所然”、“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無疑是爲“主道”等具體統治術提供了某種原理性說明。此節分析何謂“道”,以及聖人與“道”的關係。
《解老》中,對“道”的解釋由“理”帶出。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
理規定物、道規定理,道是所有物與理背後的原因。萬物有萬理,道卻唯一,所以具有“化”(演變、變化)的特性,道並沒有永恆不變的規則(無常操)。由此可說道既是一、是普遍,又是多、是特殊。因道盡稽萬物之理不得不化,則生死、愚智、興衰都由道而化,並各符其理(“是以死生氣稟、萬智斟酌、萬事興廢”,是說死生、愚智、興亡都各有各的理,這些理都由道而化)。
接著韓非用三組排比來說明“道”:
(一)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鬥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禦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二)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三)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四)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除(三)是對“道”之特性(“不近不遠、不明不暗、不制不形、柔弱隨時、於理相應”)的描述外,(一)、(二)、(四)都直接說明道,大都用了“得之以”的形式。實際上(二)也可以套用成“得之以”的形式:堯舜得之以智,接輿得之以狂。(一)最先描述了道“周行”“盡稽”於萬物,先講天地、星辰、日月、四時、五常等自然現象,唯獨把軒轅、赤松、聖人歸入其中,而聖人得道正是爲了成文章(禮樂行政制度)”。這種劃分似乎把軒轅、赤松、聖人都歸入“自然”範圍內,且聖人得道所成的“文章”也屬於自然。(二)中的道就多表現在各種王事中,如堯舜、接輿、桀紂、湯武的“智、狂、滅、昌”。需要注意的是從(一)中自然之“天道”過度到(二)中人事之“人道”,中間正好隔著聖人及其“文章”。至(四),道已經具有生死、成敗的特性,區分的標準即是“度”(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與“智”(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從(一)對自然天道的客觀描述,轉換到在(二)(四)中對“王道”“人事”的功過判斷,從天道到人道的轉換帶有了人特有的功用實利傾向和價值判斷屬性。
接下來: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道”本“不制不形,其物冥冥”,不可見聞,但聖人使我們揣摩到“道”的形象(“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中的“狀、象”)。這個被我們見到的道不是原初的天“道”,而是“有功之道”,是聖人通過道所顯現的功效讓我們揣測到了道的形象(聖人執其功以處見其形)。
最後:
凡理者,方圓、短長、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理”制物,物與物因此有了區分,“道”化於每一物中,物分理定似乎就得了“道”。但理定某物的道是某個特殊物所分有的道,是特殊,只在這個物中存在和表現,因而不是一般和普遍,即不是“常道”。道既是一般又是特殊(既盡稽萬物之理,又因萬物各異理而不得不化),所以,道雖然可以“道說”(說是言辭概念的集合,說出的東西呈現出具體的形態)可以“形名”(特殊化),但這個被限定被特殊化的道不是那個普遍的道,不是“恒道”。前面,聖人“執功見形”使我們見到不可聞見的“道”,此處聖人通過觀察“常道”的玄虛,依據道運行時體現出的法則,製作了“可道”之“道”。
從天道的玄虛周行、化而無常操,到君道的幽幽冥冥、君臣異道,君無爲而臣有爲,“道”確實爲韓非建構“勢、術、法”的體系提供了空間與合理性。《揚權》說:
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
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
後之學人批評韓非爲“專制君主”張目,實則真要理解運用並掌握韓非“勢、術、法”的體系,非爲“有道之君”的聖人不可。且先秦諸子考慮政制幾乎無一例外都從君主制入手,諸子設想君主制也從未認爲天下是一家之私天下。後人著意於韓非一斷於法,刻薄寡恩,恰恰是因爲韓非身處聖王分離,“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的春秋之世,因應於“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韓非子·五蠹》)的歷史觀,爲適應“中主”、“庸主”之治,才不斷彰顯法治作爲“當大爭之世”的對策。
二、虛靜與道德
對於“道”,至少可以引申出三個問題。其一,甚麼是道?其二,如何體道?其三,體道後的功效如何。上文著意說明聖人所描述的“道”,此則分析聖人如何體道。
道“無常操”故“化”,“玄虛”而“周行”。天道的玄虛幽冥、神化無常如何才能被聖人體驗把捉到?此即聖人的“修養工夫”。也即通過個人的修煉習養,使自己與天地一統(比如前面論道部分提到的赤松子),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個修煉習養的專門過程就是“工夫”。所謂境界,實是個人通過修煉祛除小我而達到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層次。這個修養過程實質在於溝通天人之際。“天”“人”之間的關係韓非定位如下: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托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
人必須依靠“天明、天聰、天智”“視、聽、思”,憑用一己之私智,則“目不明、耳不聰、智識亂”。如此,體道的修養過程包括兩方面,用韓非的話就是“治人”(指對待人自身的動靜思慮)、“事天”(指憑藉天的聰明睿智)兩端:
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
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故曰:“夫謂嗇,是以早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
“治人”,也就是針對自己的身心修養層面,要“思慮靜”,“用天”則要“孔竅虛”。關於“靜”,韓非並未作過多解釋。《管子·內業》云:“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內業》強調人要正、靜、定,如此精氣也就是道方可停留於身。《內業》同樣解釋了“人主安靜”的原因,人有七情,“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對於道來說,“靜則得之,躁則失之。心能執靜,道將自定。”《莊子·天地》篇云,“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內業》中“憂悲喜怒”指情,《天地》中的“機心”指個人的算計、渴望、欲念。“靜”無外是從聖人治情治欲兩端來理解。所以韓非說,“夫謂嗇,是以早服”是說只有通過“靜”的通道,聖人才能虛無服從於道理,體悟天道。治人與事天,“靜”是前提基礎。“靜”方能空虛靜默,與物爲一,體會領悟天的玄虛周行。天人之際,若靜是準備,是靜默等待,虛則是容納,是接納通融。《爾雅》釋,“虛,空也”。《莊子·天地》云:“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由靜撇除小我的私欲紛雜,從小我到大我到無我,方能由“虛”通融廣納天道的廣漠幽冥。《莊子·人間世》云“虛者,心齋也”,又云“唯道集虛”,皆是此意。關於虛與靜,《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對這兩者間的關係可以用《莊子·應帝王》中的話說明:“至人之用心若靜,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又曰“吾示之以未始出吾終,吾與之虛而委蛇。”
韓非說:“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指明聖人體道必須靠“虛、靜”的工夫修養,修養的程度由“德”來形容,這種德可稱爲“德性”。在《解老》篇首,韓非解“德”曰: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德者,得身也。
德,是“得身”、“身全”,“神不淫於(身)外”。德是自身的精神集中專一於內心的虛靜,不爲物所遷所動,這與“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是一致的。
但這裏我們需要仔細分疏“德”的兩種不同含義。《老子》五十一章云,“道生之,德畜之”。《管子·心術上》云
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謂得其所以然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
天之道有玄虛與周行兩個特點,玄虛,故“道”“濕濕夢夢,未有明晦”,周行,則化育萬物,生生不息。化育萬物是“道”生生不息之功,此功效表現爲“德”。《管子·心術上》云“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韓非在另一個語境說,“德者,道之功”,皆以功用言“德”,實際上以功用言德恰恰對應於“分得”之“得”。“德”是道的功用在不同分殊中表現出的具體形態與結果,當“道”下落萬物以成就萬物之“德”,此“分殊”、此物便“是其所是”,“得其所以然”,此謂物之“德性”。從這個角度說,“德”使“道”顯現顯明,“德”是“道”的歸宿。由此,言之者認爲道與德是一回事,道、德無間,道、德不別。道與德的此種關係,既可以導向本源生成論的闡釋面相,也可以引申出本體體用論的闡釋面相。思想者們累世爭論不休的“無極太極”問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問題,甚至張載形容道體的“一故神,兩故化”的問題,似乎都可追溯到道與德、玄虛與周行的問題中來。只是周秦時人相對於本體論或宇宙論來說,似乎更加關注“天人”關係與“德性”問題:關注天人關係便推天道以明人事,關注物之“德性”便著意於物各是其所是,“得其所以然”。
與此不同,韓非在《解老》篇首說“身全之謂得,德者,得身也”,是把“德”放在聖人修養身心的背景中。《管子·內業》云:“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管子·心術下》云: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冶。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
此中所謂“德”、“內德”皆是從身心修養角度講。“身”作爲連接“道”與“人”的紐帶,其虛無靜默、與天合一的工夫層面可以不斷累積增強,悟道、體道的過程及不斷向“道”趨近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積德”的過程。所以韓非又說
思慮靜,故(舊有的)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重複、不斷)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早服者也。故曰:早服是謂重積德。
區分“德”的這兩種不同用法,不僅是爲了顯示出涇渭分明,也是爲了指出其聯繫。道有生生之德,此大德內涵於道本身,當道散落於萬殊,則有“成物”之美德,此美德表現爲此物的德性,使得物物之間能各美其美。此時,“德”是名詞。當以修養身心論時,“德”是神思聚精於內,不爲物遷、虛無靜默、與道合一,不斷積德修德的過程。此時,“德”是動詞。“日新其德”的動態過程一再更新了“聖人”的由道所“得”,“聖人”的“德”(得的層面)最終因體道而與道合一,聖人的“德性”(是其所是層面)因此也就體現出“道”才有的感而後應、隨物賦形,應物不窮、隨時而變的特點。
虛與靜、德一樣,本身既是工夫,也是德性。當聖人淵虛靜默,摒除小己,虛指心靈空無容納的一面,靜指心靈屏息澄澈的一面,此兩面相使得身心可以通融天道。同時,虛與靜也是道體的德性。在黃老諸篇中,經常以“虛無有”指代“道”或道的德性,《黃帝四經·道原》云:“一者其號也,虛其舍也。”《淮南子·詮言》云:“虛者,道之舍也。”《淮南子·原道》云:“虛無者,道之舍也。”虛無即是道的特性。正因如此,聖人體道才需以“虛、靜”作爲工夫。道體虛無、周行的特點使得“虛”也同時具有了此兩種面相。道體的涵容廣大無所不包是“虛”空、納的一面,道體的周行無怠是“虛”無所制的一面。因此聖人積德體道,自身的德性表現爲道的德性時,聖人即同時擁有“虛”空納和無所制的兩個面相。
三、身國共治,聖王合一
舊德不去,新德日積,積德體道,日新其德,方可與天合一。聖人體天道與自然融爲一體,體道的目的當然不是爲了遠離城邦,作自足的自然哲人。恰恰相反,體道的目的是爲了推天道以明人事,模擬天道周行,執功見形,製作可見、可用之君道。所謂君人南面之術。
通過聖人虛靜的工夫修養,積德在“身”,天道便以聖人得道之“身”爲載體。聖人體天道制君道,君道根據於天道,君道、天道相通的前提依然是聖人得道之“身”。因此,君王能擬天道統治國家,其前提乃是得道之身,有得道之身方有得道之君,有得道之君方有“有國之母”(出於《解老》:“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這體現出古代君王特有的“身國共治”的特點。韓非在解老中對此表述爲: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
其後,韓非多次將有道之君與天下有道,人君無道與天下無道直接聯繫起來闡述,如“有道之君,外無怨仇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這是因爲體道、得道之身方能體天道明君道,體道、得道之身方能身國合一、與道長久與國長久。故人君有道則天下有道,人君無道則天下無道。
誠如司馬談所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與時遷移,因物變化”,聖人身國合一、因物變化,原因在於積德體道。
《管子·心術上》說,“德者得也。得也者,謂得其所以然也”。物物都從道的周行施化中“得其所以然”,“得”乃“德”也,分得此“德”,方可是其所是,成爲自己。古文字中“自然”的“自”,是鼻子的意思,“然”是如此的意思,自然就是自己指著自己的鼻子說:這就是我,這就是我自己。所以,自然就是“自己如此”。當《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時,這個自然就暗含了物物得其所以然、是其所是的意思。不同的物有不同的德性,有不同的自然。聖人體天道,虛無靜默,空納無所不容,周行無所不遷。隨物遷移就是體道的聖人能像“道”一樣跟隨“物”的德性而表現出相應的德性,故能因物變化。如此,身國合一、由聖到王之路就是以“修身積德”爲基礎,不斷跟隨物之德性而隨物所遷、因物變化的過程。德性是一個不斷積累擴大的過程,由聖到王就依次表現爲從修身之德到修家之德,到修鄉之德,再到修邦、修天下之德的擴展。家、鄉、邦、天下的“所以然(亦可說其“自然”)不一樣,其德性也有分別,但修這些德性的基礎都以虛無靜默,積德體道的修身之德爲基礎。這就是《老子》五十四章所謂“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解老》中,韓非將此描述爲:
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眾,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莊子天下篇,分人爲七品,得道者聖人以上尚有至人、神人、天人。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成仙者皆爲得道高人,唯聖人因天道制人道,乃源於聖人的“慈”。《解老》云,“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韓非的“聖人”身處聖王分離的“春秋”亂世,卻因於天下葆有慈母愛子之心而遊於世間。於此亂世中,除修身積德體道之外,必須善於養生(《解老》謂“善攝生”)。
《老子》在第八章曾以水德爲喻,提醒聖人“處眾人之所惡”時,應該“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此一思想在《黃帝四經·道法》中發展成爲“生、動、事、言”四害,云
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生必動,動有害,曰不時,曰時而背。動有事,事有害,曰逆,曰不稱,不知所爲用。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誣,曰虛誇,以不足爲有餘。
《解老》中,韓非繼承了此“生、動、事、言”四害,並分別以之相應的攝生之法。於解《老子》第五十章“出生入死”、“入軍不備甲兵”部分,指出“生害、動害”,分別解之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和“避其域,省其時,塞其原”;並於解《老子》第六十七章“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部分,指出“事害”、“言害”。其中,尤其值得注意韓非對此章的總結部分,云:
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聖人遊於亂世,攝生自全之道爲“盡隨於萬物之理”。能“盡隨於萬物之理”者乃道(前文第一部分描述道曰:“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聖人體道方可如道“柔弱隨時,與理相應”,方能“盡隨於萬物之理”而得全身。亦因聖人體道,與天合一,體道的聖人便猶如“天生”。《管子內業》云:“凡道無所,善心安處。心靜氣理,道乃可止……修心靜意,道乃可得。”“心”是領悟天道的處所,故“天生也者,生心也”。聖人推天道明人事,體天道制君道,“故天下之道盡之生”。“天下之道盡之生”有兩個前提,一要有猶若“天生”的體道之“心”,二是此體道之心要有如慈母爲弱子慮般爲“天下”慮。符合這兩條件者正是“聖人”。只有這兩個條件同時具備,方能“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韓非子·八說》云:“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世人一味責怪韓非“慘核少恩”,“敢爲殘忍而無疑”,
爲何“心”既要體道又要慈愛,方可持國?這又回到道德之意,道虛無周行,德分殊於萬物使之各得其所以然。因此,國有國之所以然,天下有天下之所以然,要認識國與天下的所以然,必須體道。體道方能認識“國”之所以然,方能得治理天下、國家的“外王”之術。
結語
韓非子全書涉及到聖人的,大略可分爲兩種情況,第一種即如本篇所分析的側重於從道與德的內聖角度闡述聖人,此部分大多集中在《解老》中。更多的一部分則涉及到聖人治國的各種方略,多屬於“外王”部分。這些聖人治國之術散落在全書各篇章中,構成韓非“法術勢”體系的一部分。比如:
故聖人之治民,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心度》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詭使》
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八說》
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外儲說右下》
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六反》
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奸劫弑臣》
由於本篇側重以“內聖”角度探討韓非的“聖人”,因此這些部分不再贅述。
綜上,韓非的理想君主必爲“聖人”充當,只有聖人堪爲韓非筆下的“有道之君”。聖王同體的時代早已終結,“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的世風下,聖人當王只能憑靠歷史機運。依然保有“慈”之情懷的聖人若要“幹世”,首先必須面對的是“進說”平平之資的中主,因此而有《說難》,次需面對環繞君主內外的“重人”,如此而有《孤憤》……在險象環生的政治處境下,思想與社會如何互動,理想與現實如何消長,《韓非子》中的思想如何構成了“霸王道雜之”政制歷史傳統的一部分,都是極爲有意思的論題,筆者期待有心人來一起細加琢磨。
參考文獻[References]
陳鼓應注,《管子四篇詮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Chen,Guying.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 Articles of Guanzi.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9.]
陳鼓應注,《黃帝四經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Notes on and a Modern Translation of Huangdi Sijing.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1.]
黎翔鳳校,《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Li,Xiangfeng,ed.Commentary on the Guanzi.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4.]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長沙:嶽麓書社,2010。[Lv,Simian.ASurvey of Pre-Qin Thoughts.Changsha:Yuelu Publishing House,2010.]
宋洪兵,《韓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Song,Hongbing.A Reconsideration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Feizi.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0.]
張覺校注,《韓非子校注》,湖南:嶽麓書社,2006。[Zhang,Jue,ed.Commentary on the Hanfeizi.Changsha:Yuelu Publishing House,2006.]
張舜徽,《周秦道學發微》,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Zhang,Shunhui.An Elaboration of the Daoism of Zhou and Qin Dynasties.Wuha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5.]
周勳初,《韓非子校注》,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9。[Zhou,Xunchu.Commentary on the Hanfeizi.Nanjing:Phoenix Publishing Media Group,2009.]
Exploring Han Fei's Thought of“Self-Cultivation of Sage”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ozi
The idea of“sage,”often mentioned and taken asmodel in discribing the ideal characters by Lao Zhuang,Xun Meng,Guan Han and even Gui guzi,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e-Qin philosophers.It can be noted thatmuch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tudies of sages from the schools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in the pre-Qin period than any other schools.This article will be focused on the Interpreatation of Laozi,elaborating the internal attributes of Hanfeizi's“sage”and his learning of“internal sage.”
The parts in thewhole book of Hanfeizi relating to sage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the first looks the sage from the angle of“internal,”i.e.,his Dao(logos)and De(virtue),mainly express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ozi,while greater emphasis is put on the ruling strategies of the sage,which belongs to the other part of“external king,”in which this article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As themodel of Hanfeizi's ideal character,“sage”is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the crucial parts of the Hanfeizi,which,however principally reflects the effects of the practice of the sage,apparently not the reason that makes the sage sage.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Laozi,Hanfeizi starts from elucidating the book of Laozi to illustrate the theory of Dao,the key to Laozi's doctrine.By focusing on the text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ozi,it can be seen that“the sage”aspires after two characteristics of“Dao,”which are“unconditional and empty,”and“eternally endless in the universe.”Moreover,“the sage”recognizes“Dao”through the virtue of emptiness and stillness to reach the state of“harmony ofmen and heaven.”Furthermore,the sage is“sympathetic”to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to produce“the principle of ruling,”making himself“internal saint and external king.”These three aspects expound in sequence what Dao is,how the sage gives expression to Dao,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age and Dao,reflecting the“inner nature”and“efforts”of the sage and the dimension of Hanfeizi's thought of“internal sage”embodied in the sage.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inner quality is related to“king”is helpful to seewhy it is the sagewho is Hanfeizi's ideal choice of king.
Dao;De;emptiness;stillness;Han Feizi:Interpretation of Lao Zi
關鍵词:
道德虛靜《韓非子·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