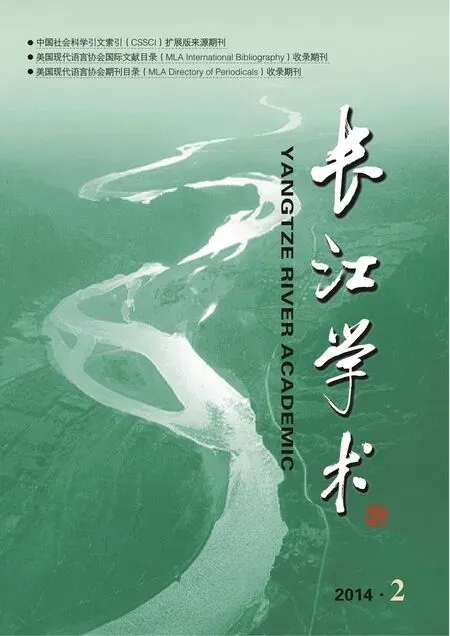“异乎寻常之地”:村上春树的游记中国
刘研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异乎寻常之地”:村上春树的游记中国
刘研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村上春树在游记《诺门罕钢铁墓场》中,一方面以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叙事作为话语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实地考察敏锐洞察90年代中国的问题和特色,建构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文学空间。而这一空间的塑造也是作者个体心理的折射,村上通过中国他者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自省意图鲜明深刻,但同时通过视角、语调、对比等叙事策略的运用,字里行间又闪现出日本的“中国”形象,显示出话语中国的强大规约力。
村上春树 《诺门罕钢铁墓场》 文学空间 叙事策略
1991年村上春树在美国讲学期间,正值海湾战争爆发,日本向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支付了昂贵军费,但因没有出兵被美国舆论讥讽为“支票外交”。加之泡沫经济膨胀,日本经济强势,美国民众反日情绪强烈,波及到了在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村上说:“日本人是什么,哪怕不情愿,也不得不去思考这一问题。《奇鸟行状录》也是在强烈地切身感受着这一外在压力或者压迫的情况下写成的。”村上在异国他乡的美国,进一步获得审视西方、日本与中国的机会,催生了其民族身份的自觉。
《奇鸟行状录》第一部于1992年10月至1993 年8月连载于《新潮》杂志,1994年2月新潮社出版了第一部《贼喜鹊篇》、第二部《预言鸟篇》。1994 年6月村上受《马可·波罗》杂志之邀寻访中蒙边境战争发生地的遗址,发表游记《诺门罕钢铁墓场》,1995年8月《奇鸟行状录》第三部《捕鸟人篇》出版。
1994年的中国之行是村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中国之行。从成田机场经四个小时飞抵大连,从大连挤进“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的硬座车摇晃了十二个小时到达长春火车站,再经由哈尔滨到海拉尔,坐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先到新巴尔虎左旗,又花了三个小时抵达诺门罕村。之后绕道北京,路线经由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来到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从日本到中国四个小时虽说短暂,在中蒙边境上这样漫长的绕行,让村上从感觉上讲,“中国”如《去中国的小船》结尾所言那是“过于遥远的中国”。
村上未来中国前,在《寻羊冒险记》和《奇鸟行状录》一二部中描写了“满洲”,描述了1939年“满蒙”边境的诺门罕战争,“满洲国”成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时空。他构建“满洲”和“满洲人”的话语资源是什么?实地游历,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心到边境,作家感慨万千,认为有关中国的东西都有“异乎寻常”的倾向,作家怎样体现了这种“异乎寻常性”?而这种“异乎寻常性”的背后又折射出作家怎样的视点?
一
中日两国的近代交流始于19世纪70年代,官方以及民间互访颇多,游记骤增,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东洋文库于1980年出版的《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游记解题》(1868—1989)就有四百余种之多。作者身份多样,内容广泛,其中日本人的“中国观”跃然纸上,汇入了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东方学式的话语建构。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人深受中国古典文化浸染,非常重视与中国文化的精神联系。但即便如夏目漱石在《满韩漫游》中也未能完全超越时代,游记中他对中国、中国人的描述并不多,主要是记录了他在满洲各地与同学故友的叙旧。这些同学故友作为日本派往“满洲”的要员、殖民统治的主力军,在“满洲”的生活非常优越,也为作家安排了高规格的接待,而他们正在建设的现代化的“满铁”王国更让作家兴奋不已。
对于当时日本民众来说,中国愚昧落后,中国人是弱国子民。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权后,“满洲”日益成为日本人可以重新开始梦想和冒险的新大陆。构筑他者的真正意义是把握和控制他者,这个把握包括知识上的理解和解释,以及权力意义上的控制和征服。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叙事,既展示了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同时也制造或维护着日本的中国认知。这种认知甚至成为某种文化心理积淀,在不同时期都会听到它的回声。
村上基本是从文学、历史的叙事中了解中国的,村上在《去中国的小船》中说:“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在访谈中他也特别提到了《西行漫记》(又译为《红星照耀中国》)。《史记》是古代中国、中华文明的象征,《西行漫记》是现代中国、革命中国的化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曾幻想从“人民中国”中寻找未来,受法国“五月风暴”等影响,一时之间,中国文革成为“革命”的隐喻,成为批判现有体制的新的思想文化资源。日本人有过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乡愁,对东亚病夫的蔑视,对革命中国宏大理想的追寻。而随后日本实现腾飞,经济名列世界前茅,中国社会却在动荡与混乱中渡过了十余年时光,仍然处于贫困状态。80年代日本人主流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回落到近代的原点上。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综合国力都有所提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发展蓄势待发,蒸蒸日上,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人的中国观也相应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日本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真实再现中国,而是要在中国形象的延续和衍变中体现日本的文化精神和中日力量关系的变化。
村上在阅读大量历史传记材料后创作了《奇鸟行状录》,他说:“在那些描写这些重大事件的书籍里,有我迄今为止仍不知晓的事实,如‘诺门罕事件’,日本人在当时不知情,其结果就是到了今天很多人对此也知之甚少。知道了那如此无意义、残酷、血腥的战斗,我非常震惊。我在小说完成后,去了‘满洲’和蒙古实地考察,多少是有一点奇怪,一般人都是写之前去现实发生地考察,而我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谓想象力,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资质。我不想因为实际去了那里而破坏想象力。”
小说中间宫中尉回忆在“满洲”新京的生活时说,新京虽不是大城市,但富有异国情调,可以尽情寻欢作乐。在肉豆蔻的故事里,她的父亲原本在日本是兽医学校的老师,但觉得在“满洲”更能伸展身手,当新京要求为新动物园派一名主任兽医时,他不顾妻子的反对,主动报名,一家三口来到新京,战败前一直平静快乐地生活在动物园里。对照夏目漱石等近代日本人的文字,这样的描写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村上在《奇鸟行状录》第三部中描写了“满洲”中国人形象。1945年8月,日军即将战败之际,中尉及其士兵奉命射杀动物园中的大型动物之后,中国人杂役向兽医建议由他们处理这些动物死尸,他们想得到值几个好钱的动物皮毛和肉,兽医同意了这个交易,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原文即黑体字)。不一会,十来个中国人用板车拉走了动物尸体,这期间“中国人几乎没有开口,表情也丝毫没变”。第二天两个十三四岁男孩被派来帮忙,两个男孩“黑黑瘦瘦,眼睛像动物般亮闪闪地转来转去”,兽医问两人名字,“两人没答,仿佛耳朵听不见,表情一动未动”,工作一完,两个男孩一声不响地消失不见了。这与《满韩漫游》中一场景相似,夏目漱石一行人到奉天北陵游玩时,一个赤脚中国小孩向他兜售自称捡来的金球,而掌柜好像偷偷以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夏目漱石感慨道:“中国人可真狡猾。”这种丑陋、狡猾、麻木的“中国形象原型”,反复出现在西方和日本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笔下,它不是某一个文本的发明,而是社会文化内在结构的产物。村上的这种中国形象的塑造,应该说也是依据了日本那一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夏目漱石描述炼油厂里“苦力”们劳动场面时说:“从朦胧的蒸汽当中可以看见紫铜一样的肉色因为汗水泛着油光而越发勇猛。当我注视着这个苦力赤裸的身躯时,不由得联想起了‘汉楚军谈’。古时候,让韩信从胯下钻过去的好汉必定是这样一些人。”在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迟钝态度中作家不由自主流露出对中国民众肉体与原始生命力的赞赏。村上在《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中写到中尉和士兵们押来四个穿着棒球服的二十岁上下的中国小伙子重返动物园,这些中国人是“满洲国”军官学校的学生,拒绝接受新京保卫战任务,杀死了两名日本教官逃跑,结果被抓住,当场被射杀了四个,剩下的四个,按照中尉的命令挖下掩埋自己尸体的深坑。中尉觉得弹药要留着对付俄国人,用在中国人身上不值得,遂用刺刀刺杀其中三个中国人。剩下穿4号球衣的中国人因为是主谋,他被处以更加残酷的死刑——用棒球棒打杀。这个中国人“高大魁梧,胳膊有一般人大腿那么粗”,在被击碎了头骨气息皆无的情况下,惊悚的一幕出现了:“4号中国击球手如梦初醒地飒然起身,毫不迟疑地——在众人看来——抓住兽医手腕。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兽医莫名其妙。他的的确确是死了。然而中国人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最后一滴生命力像老虎钳子一般紧紧抓住了兽医的手腕,并且依然双目圆睁黑眼球朝上,以结伴同行的架势就势拉着兽医栽入坑中。兽医和他上下重叠着掉了下去。兽医听见对方肋骨在自己身下折断的声音。但中国人仍然抓住兽医的手不放。”这出人意表的一幕表现了中国人身体的强健和不屈不挠的生命力。数字4在日语中谐音“死”,4号如同死神,这一场景也多少流露出对中国人的恐惧。村上是在反思历史的进程中开始自己的创作的,但从肉体层面关注中国人,与夏目漱石又多少表现出了相似性。
村上踏上中国土地以前对中国、中国人的想象,主要来源于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文本叙事,尽管故事的构筑无不体现了作家个体的想象力和创作个性,但中国人形象显然已经形成一种话语,只要对它进行表述,就不由自主地如此安排素材,在既定的话语体制中参与叙述。同时,我们也不容忽视,这一话语资源既是村上构建小说的资源,也是他游历中国前业已形成的中国印象。
二
村上在《诺门罕钢铁墓场》中按照地理路线图,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又一个文学空间,这些空间不仅是地理场景的呈示、游历过程的“容器”,而且也是一种空间隐喻,在由中国城乡的街道、建筑物、自然景观、社会空间构建的这些空间背后,村上发现了怎样的“异乎寻常性”?
村上发现东北最为发达的城市大连有两大特点:人多,车多。到处是“中国式过马路”:车自行其是地行使,人自行其是地行走。有人横穿马路,车速也不减,由于太可怕,天黑以后不敢出宾馆。他还非常精准地预测道:“倘若行驶在中国大地的汽车数量进一步增多,那么出现的恐怕是异乎寻常的噩梦(有关中国的东西似乎都有异乎寻常的倾向)……势必有一天中国全境——从越南国境到万里长城——被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烟头、BENETTON招牌所彻底覆盖。”
到长春去了动物园,这个动物园便是《奇鸟行状录》中写到的“新京动物园”。动物园始建于1938年的日伪时期,是日本著名的东京上野动物园的20倍大,当时其面积之大,展出的动植物品种之多,号称“亚洲第一”,兴盛一时。1940完成首期工程,1944冬因美军空袭将园中的非洲狮、东北虎等猛兽处死。日本战败投降后到1949年,成为国民党军队的“练兵场”,几成废墟。解放后直到1987年才以“长春动植物公园”为名重新开放。村上眼中1994年的动物园,面积大得不得了,动物却少得可怜,“钢筋混泥土建筑物的墙壁像久经岁月洗礼一般凄惨黑乎乎的,到处布满令人想起李尔王皱纹的深度裂纹,有的地方甚至已开始崩毁。”让人无法想象这是七八年前建的,相比较而言,倒是“满洲国”时期建造的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他“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也是如此:电梯装饰板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有空洞,浴室阀柄分离,墙壁有漏雨污痕。问起来不过去年刚刚建成。在海拉尔参观的三年前建的观光设施“望回楼”也呈“轻度废墟”状,看来都是出自和长春动物园一样的建筑师的手笔。
在哈尔滨村上因眼睛进了异物去了医院,医院“便宜、便捷、技术好”,和日本医院大为不同的是,空空荡荡,光线幽暗,“整体上笼罩在卡夫卡式的郁闷气氛之中。蓦地,我产生一种超现实主义恐惧——假如不小心开错一扇门,那里面说不定又有中国式异乎寻常的情景展现出来。”
在去往内蒙海拉尔的火车上,自然景观相近:牛猪牧群,红砖小镇,蔚蓝天空,喷吐白烟的工厂烟囱,电视天线丛生的村落,这里那里流淌的河流,踩着自行车等待道口开闸的朝气蓬勃的红脸蛋年轻女子,同汉字一起书写的仿佛勃然翘起的胡须的蒙古文字……这里虽然较为落后但与充满经济动感的大连和长春相比散发着一种野性,位于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村的夏日日暮时分的草原风景也极为美丽,但此地道路泥泞不堪,蚊虫众多。住在解放军招待所,因为缺水,厕所无法冲水,“刚进建筑物时还以为进了巨大的公共厕所”。
村上以印象素描的笔法真实记录了1994年的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急速开始了落伍多时的现代化进程,90年代是中国经济最为迅猛增长的时代,道路交通、城镇建设规模空前,但尚处于起步阶段,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建设杂乱无章,各种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城镇很多地方正如村上所言,“街上行人不分场合地扔烟头、吐口水、大吼大叫、胡乱买东西或硬卖东西”。较之90年代,今天中国的城镇景观大为改变,但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并未有太大改观,中国公民在世界自由旅行甚至有些炫富的同时也因此受到诟病。也就是说,经济上“富起来”的中国人,在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上并没有“富起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在游记中多次将厕所作为透视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象征物,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以尖锐而悲悯的语言描述了孟买贫民区可怕的卫生现实。厕所卫生某种意义上体现的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关注。而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也让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汗颜。在新巴尔虎左旗,村上坦然已经不把住在“巨大的公共厕所”这类事情放在心上了,这是一种无奈,而长久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对肮脏的适应与麻木,不更是对尊严和自由的放弃吗?
在长春动物园,村上也听到了一些趣事,一是从工作人员口中听到了“日伪时期”的情形,至于内容是什么,村上一字未提;二是因为园里树多且密,有很多情侣在此男欢女爱。“性”在中国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革命时代都是比较避讳的话题。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同时,人们也越发正视自己的欲望,如果说80年代“性”还是被包裹在爱情、理想和政治中压抑性地加以表达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性”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呈现出来。有意思的是,1990年漓江出版社和北方文艺出版社就将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打造成低俗艳情小说加以出版,而在游记中村上也注意到了中国那个“性趣盎然”的时代。
在赶赴海拉尔的软卧里,村上遇到了一个在中俄边境的满洲里做个体贸易的四十岁左右的中国男子。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完成,村上在火车上遇见的这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活跃的“个体”,将成为中国社会中全新的“大众”。所以村上十分好奇:他此前的生命轨迹怎么样,此后又有怎样的生命轨迹呢?
在中国短暂的旅行,村上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当时的问题和某些特色。在中国人眼中,1994年的中国,尽管问题良多,困难重重,但基调应该是充满生机的。然而,在村上的笔下,中国的城市街道混乱、建筑物犹如废墟,乡镇虽天空蔚蓝,空气清新,但对于人居而言,生存环境无比恶劣。在巨大的“文明”落差中,诸如此类消极、负面的描写构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景观空间。
三
每一个景观不仅仅承载地域、场景和建筑,也是重要的社会空间,是人们活动和精神交流的场所,而对每一景观、每一场所的所观所思,又明显地刻上了作者的思想特征,是作者个体心理空间的折射。
游记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村上此行的目的——寻访旧日诺门罕战役的战场引发的种种思考。在来中国之前,通过阅读史料,村上发现了这场战役失败的要害之处:这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以极差的效率杀害了”,即便战争结束后在经济繁荣中,日本人也并未从作为无名消耗品被抹杀掉的命运中挣脱出来,“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在蒙古一侧的诺门罕遗址上,55年前的武器密密麻麻扔得到处都是。深夜醒来,村上在战场上感觉到的某种“气息”猛烈摇晃房间,他意识到摇晃的是“我本身”。村上的中国之行是他对诺门罕战役认识的进一步确认,同时也发现这是不该忘、不能忘,是融入自身血肉中的民族记忆。有日本学者概括说,“以春树描写中国的作品群为中心来看,可以从中了解,春树自身以遍布20世纪日本社会的险恶事件为背景,展现了日本这个国家本身长期以来具有的社会构造中的扭曲与波折,让不得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构造中的人们进行冷静和深沉的思考。”
村上极为深刻地审视自我历史,意识到了“为了使日本这个贫穷国家生存下去而在‘维持生命线’这一‘大义’之下侵略中国这个更穷的国家,真是无可救药”,那么他是否能够跨越那一封闭国家的组织或观念,塑造富有积极性和新意的“中国形象”呢?
村上对两位女医生的描写耐人寻味。第一位是“武斗派肌肉发达型体质”的中年女医生,一边向他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叫着,一边为他治疗;第二位也是一位中年女医生,很文静,但非常疲惫,“脸上浮现出像是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凄寂的微笑”。这样的特定比喻作家要暗示什么?村上在海拉尔沿途小站目睹一个企图扛自行车上车的男子被警察逮住打一顿带走了,翻译说此地人性情暴躁,文革期间很多人在这里遇害。村上说:“死多少人我没问,既然中国人说‘很多’,想必真的很多。”文革是中国当代最为沉痛的集体记忆之一,1994年距文革结束已近20年,小站暴力让我们中国读者警醒:文革虽已成为历史,但对文革的反省和思索还远未结束,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各种各样暴力的践踏。然而,村上看到每一位女医生,强悍抑或温柔,都能让他联想到文革,这一先入之见令人诧异。
村上还记录了中国人充满“异物感”的目光。在长春动物园村上花十元人民币抱虎崽照相,顺嘴问中国人虎的名字,“给对方空漠的神情看了片刻,仿佛在说‘你这个傻瓜蛋,哪能给虎一一取什么名字’。”这种令村上不快的目光再次出现在新巴尔虎左旗,此地居民都象看异物似的“眼盯盯地注视着我们”。乡民的盯视固然有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看客”的性质,或者说缺少最起码的礼仪,但“目光”是无形的,即使在当时也不能确定它的涵义,更不要说事后回忆了,这一目光完全是作家的自我感受。
中国异乎寻常的“人多”让他进一步联想:在书上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和“万人坑”等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屠杀事件,虽然对于事件可以大体把握,但从数字上总是难以置信,实际到了中国才有实感,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有一拨拨的人涌来,“长时间面对如此光景,难免产生类似恐怖的感觉,觉得数量陡然差了一位数。甚至觉得,使得日本兵的感觉发生根本性错乱的,说不定也是这种压倒性的物理数量的差异”。因为中国人多而让日本兵神经错乱感到恐怖而杀人?尽管村上用了一种戏谑调侃的口吻,但此说很难让中国读者在情感上接受。
当年日军为修筑大规模永久性工事征用了大量中国劳工,死者众多,在山头附近有万人坑。这里村上解释,这是当地导游说的,“他所说的在何种程度上属于正确的历史事实——就是说是否果真杀了一万人——我当然无法充分证明,但至少住在海拉尔的中国人至今仍确信那是史实(从当地几个人的嘴里听到过大体相同的内容),归根结底,我想那恐怕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据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干的实在太多海拉尔式行为加以类推,那样的事在这里也确实(或以相当高的概率)发生了。当时致死的中国人数字一万也好五千也好两千也好,此时存在于此的事态本质都不会因数字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化。”8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如有人用推理法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其中的论据之一便是人数问题,因为无法确定准确人数,细节不可靠,如果细节不可靠,那么整体就无法相信了。村上在此的修辞耐人寻味,关注到受害国一方的感情问题,但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质疑;既认为中国导游提供的数字不太可信,又指出事态的本质不能因数字变化而有大的变化,日本在中国的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一万也好五千也好两千也好”如此数字递减的叙述,潜台词便是中国方面未免夸大其词。质疑与肯定的叙事语调在反复之间使叙事充满张力。
除了叙事语调很有特点外,游记里还暗含对比叙事。卫生观念、洁净一直是近代以来日本大力宣扬的民族性之一,中国90年代的“脏乱差”潜在参照系便是日本的“整洁、文明和优良”,中国的“废墟”式建筑对应的便是五十年前的“伪满洲”殖民统治时期的坚固的建筑。中国形象的另一参照系是蒙古国。同夏目漱石的《满韩漫游》一样村上游记中出场的中国人亦没有名字,而陪伴村上的蒙古国的三个军官,每一名字都记录在案。村上谈及中国境内诺门罕村的博物馆之所以俨然是小学里的遗忘物玻璃柜,是因为在对面的蒙古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军营里夜间熄灯禁酒,蒙古兵不当回事,照例开灯饮酒,军队里也没有人说三道四。说给中国人听,中国人则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绝对没有那种事”。实则与村上前文描述的中国新巴尔虎旗街头当兵人的形象形成对比:“年轻士兵大多邋邋遢遢,或解开衣扣,或歪戴帽子,或叼着烟卷,活像从前日活电影里的阿飞。”同样是违反军纪,蒙古兵显得率性天真,而中国兵则如此表里不一。文中有一大段详细记录了蒙古军官杀狼的经过,虽然最终落脚点是人类能占一时上风却永远无法与自然抗争,但是明显是对蒙古人所保有的生命力的褒扬。与日本人的文明、蒙古人的彪悍相比,中国人呈现出令人惊惧的现代性怪胎的形状。
萨义德指出:“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夏目漱石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创作了游记《满韩漫游》(1909),村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创作了游记《诺门罕钢铁墓场》(1994),时隔近八十年,两位作家看待中国、书写中国仍然有很多相似体验。战后传统的“自我图像”和“他者图像”(强大的日本帝国与低劣野蛮的近代中国)解体,日本人当代“自我图像”和“他者图像”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与深藏的民族“精神创伤”有关,村上通过中国他者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意图鲜明,但在新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和反差基础上孕育出的中国这一“他者图像”更为微妙与复杂,字里行间不断闪现的日本的“中国”形象,显示了话语中国强大的规约力。
“Exoticland”:ChinainMurakami’sTravelogue
LiuYan
(SchoolofChineseandLiterature,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Jilin,China)
ThroughhisfieldvisitsinNomonhanSteelGraveyard,MurakamiHarukiconstructsan“exotic”spacebasedona discursiveresourcesincemodernJapanesenarrative,andwithakeeninsightintotheproblemsandcharacteristicsofChina inthe1990s.Atthesametime,theconstructofthisspacealsoreflectstheauthor’sindividualpsychology.Ontheonehand, itisdistinctandprofoundthatMurakamireflectsonJapan'smodernhistory.Ontheotherhand,China'simageoftheprototype flashingbetweenthelinesshowspowerfulforceofdiscourseChinathroughtheuseofnarrativestrategiessuchasperspective, tone,contrast.
MurakamiHaruki;Nomonhansteelgraveyard;LiterarySpace;NarrativeStrategy
责任编辑:汪树东
刘研(1970—),女,辽宁葫芦岛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树论”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BWW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