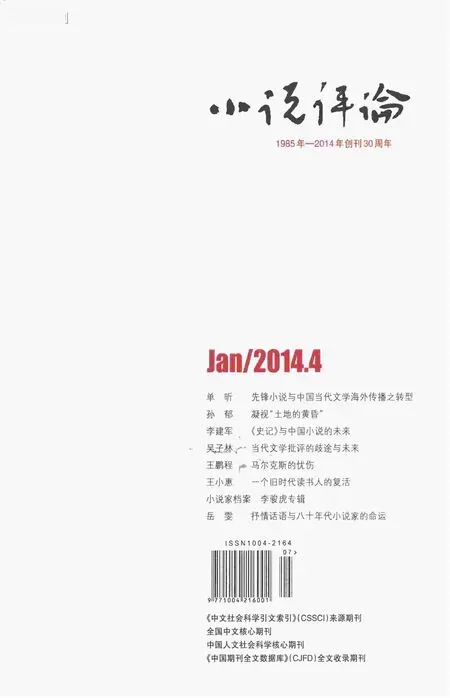高鸿:从题材到叙事的审美自觉:《农民父亲》、《血色高原》、《青稞》走读
杨焕亭
在生机勃勃的陕西中青年作家群中,高鸿以多产、活跃而受到文学批评界广大读者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以来,他相继推出了《沉重的房子》、《农民父亲》、《血色高原》三部长篇小说后,论家都从不同视角给予了见仁见智的评论,认为“高鸿的写作是有根的,有原乡的,所以它的苦难的美感来自生存和生命的深处。”这里所说的“根”和“原乡”,从广义而言,乃是指酿造作家作品的宏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狭义上说,就是指作家生命起始点——梁峁逶迤、苍茫浑厚的陕北高原。然而,当他以青藏高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青稞》问世后,那种强烈的时代感,那种弥漫在作品中的“精神乡愁”,都引发我们关注他从题材选择到叙事方式所体现的审美自觉。
一
对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关注,既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内在要求,又是高鸿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这不仅因为复杂而又交织着矛盾冲突的环境是塑造艺术形象的鏊钵和基础,更因为它使得作家“在写自己本人的过程中,也就写了他的时代”(艾略特语),据此构建起自己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艺术认知。
然而,无论我们跟随着《农民父亲》的足迹,去解读北方农民沉重而又苍凉的生命历程,还是目光掠过《血色高原》,去观览中国乡村在历史演进中的斑斓画面,抑或是追逐着《青稞》的芬芳,去体味西藏新一代生命族群丰富的精神世界,都会发现作家在题材选择上的个性视角,这就是在多元的历史背景下,将艺术的笔触伸向中国社会底层,将审美的目光投向那些名不见经传,却被鲁迅视为民族“脊梁”的普通人物,而且以悲剧的色调,悲悯的情怀,去刻画一簇簇生命群体,或被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所驱使而被动的颠沛流离,或为了某种梦想和目标而主动的背井离乡,穿越苦难,抑或是走出羁绊的生命态,从而完成经过灵魂熔冶,最终确立人格自我、人性自我的“归去来兮”的审美表达。
从创作实践的意义说,题材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选择题材却是一种主体行为,它不仅考验作者对于生活本质的把握程度,更是见证作家审美视角的向度坐标。如果我们以故事发生的年代顺序而不是依照作品发表的先后将高鸿的三部小说做一个排列,就会发现,它构成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新世纪之初,长达七十多年西部中国社会沧桑变迁,转型变革的多色影像。从《血色高原》中以外婆为核心的“逃难者”族群到《农民父亲》中的“讨饭者”组合,其间切换着外族入侵,战火弥漫的煎熬;旧生产方式解体、新生产方式生长;旧体制消亡、新体制诞生的风云变幻,这两次“迁徙”都打着咀嚼“苦难”的烙印。《血色高原》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在一种灰色基调下,拉开了“外婆”一家流浪的序幕。作家以凝重的笔墨,刻画了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在民族危亡与个人生存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时刻,是怎样跨越昔日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将迁徙的历程演绎为一支心灵的“安魂曲”。一场水灾,把外婆和她的儿女们驱赶进逃荒的人流,在外婆踉跄的步履背后则是战争阴云下的流浪潮。灾难让情感冲破了血缘的藩篱,宗族的羁绊。外婆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地收留了被父母丢弃的孤儿铁蛋;她在坚持抗日的祝老爷罹难之后,以博大的母性襟怀接纳了祝俊;她把一个女人的爱给予了负伤的抗日将士老吴,而且在老吴牺牲后依然生下了他们爱情的结晶“抗战”。外婆的行为方式,就像一道紫色的光,因了她的照耀,周围一切“共生态”下的生命群体,都改变了固有的单一色度,燃烧着希望的温暖。这种理想力量和人格自尊,成为作品中的人物走过一个个艰难时世,在非正常秩序造成的惨淡人生面前,在各种邪恶势力面前从不屈服,从未低头的意志力量。外婆和她周围“迁徙”的人们身上所携带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饱经沧桑,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它甚至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在漫长的岁月里,医治“自我”创伤,走向伟大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坚实的抗体。有了这一方可以供灵魂栖居的精神家园,任何物理状态的“迁徙”都不可遏制地会到达理想的彼岸。
如同一部剧的上下本,“迁徙”在《农民父亲》中演绎出另外一幅图景。与《血色高原》相比,《农民父亲》中跨地域的迁徙,虽不排除自然灾害的直接原因,然而最根本还在于那种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制过度,那种人们对于以“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式的“共产主义”的幼稚解读,那种对于“大食堂满足供应,人人有饭吃”的虚幻浪漫憧憬,那种“没有人怀疑这一切的逻辑性”的文化蒙昧,它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力动摇了人们从初生的人民政权那里获得的稳定秩序和愉悦安逸。于是,一场乌托邦式的梦幻终于被严酷的现实打碎,“大梁庄人唯一的食物源被切断了,一些人于是就开始逃荒”。作家就在这样的氤氲下,铺展开“父亲”一家千里乞讨的曲折旅程,那画面是悲怆而又沉重的:“大翠拉着两个妹妹,父亲背着奶奶,小叔跟在后面,一家人乘着夜色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离开了大海。奶奶一路上啜泣着,父亲不时地回头看,到处一片荒凉……”。
从生物形态说,“迁徙”是人的求生本能必然孕育的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各种关系失衡催生的“副产品”,是灾难所导致的一种超稳定的生态现象。然而,它在高鸿的笔下一旦被赋予“诗意”的悲悯,就给这动荡的旋律涂上了恒定的精神理性。
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大翠“发现高粱已经吃完了,还没有到目的地,所以就不吃东西了”,她死后,“父亲”看到了她贴身“那个用裹肚做的袋子,袋子里面装满了东西,高粱、干萝卜、花生皮、地瓜蔓等等,还有一块粘乎乎的东西”,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而把死亡留给自己,这个普通的“憨憨的”乡村女人的人生因此而其华灼灼,而为其他继续向前的人们赢得了机遇,“大翠留下的食物使父亲一家人有力气继续前行”。诚如尼采所说,在悲剧中,肉体毁灭了,“而意志的永恒生命却仍然没有受到影响”。
题材选择反映着作家的思想境界和情感世界。对于“流浪者”群体的关注,表现了高鸿从艺术视角对生活投入的反思。“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马克思语)“哲学家只是在理论中预料到的真理”,“作家却能够从生活中把它把握住。”(杜勃罗留波夫语)桂花由安定走入“迁徙”的命运遭际是这种思考的切入点。它形象而又质感地告诉读者,贫困的根源在于社会深层的矛盾,当我们不能从体制的层面上找到疗治这种创伤的途径,当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不安和躁动时,一个“大刘庄”没有力量去结束被“饥饿”驱赶着的“迁徙”。很快,“大刘庄的‘粮仓’宋桂花开始讨饭了”,从河南到徐州,直至流落到陕北鹿县,“父亲”一家和桂花的行程是一个时代“切片”,使我们得以透过这个“疤痕”,更深切地释读曾经的那个激情与狂热相交织、幼稚与幻想相伴随、对自然蔑视与人的极度意志膨胀的岁月。数十年后,我们在一种开放的氛围中品味高鸿在作品中“复活”了的远逝年华,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如果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恩格斯语)那么,“对于一个民族所能发生的事情”,没有比小说这种文本的表达更具历史价值了。
题材选择也考验着作家对时代旋律的艺术敏感。如果说,“迁徙”作为一种生命态,在《农民父亲》和《血色高原》中,被涂以悲剧的色调,那么,我们就从《青稞》中看到了新世纪阳光下的另外一种“迁徙”。无论是从西藏本土上成长起来的,还是被内地城市养育大的一批80 后的生命群体,在市场大潮的感召下,有的毅然走出父辈固守了多少个世纪的草原,去寻求一种新的价值支点;有的则告别楼房鳞次栉比的城市,走进神秘的雪域高原,去体验传统的、外来的、新生的文化在这里演绎出缤纷如云的撞击和交锋。喝惯了酥油茶,吃惯了青稞糌粑的主人公央金和巴桑,在城市品尝到牛毛毡帐篷里从未接触过的“啤酒”,而且很快习惯了吃“西餐”。根在内地的毕建、吕秀、韩力、雷阳等,基于人生价值的自我认知,心灵世界的对外开放,从而将生命的“迁徙”演奏为一首拥抱现代文明的进行曲。他们走入现代文明的步履并不平坦,有过肉体的痛苦,央金在翻越卓嘎山遇难,被巴桑搭救时起,从此修正了巴桑的人生轨迹;她在进入拉萨后,不但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开放和多彩,也经受孤独和寂寞的流浪和漂泊;有过彷徨和迷茫,面临的不只是新文化的绚烂多彩,还有对金钱崇拜、对地域文化的褒贬,对传统道德的疏离等媚俗文化的挑战,央金的弟弟平措以寻亲为目的的拉萨之行,很快地就陷入了热衷于喝酒、飙车的文化迷茫,以致酿成酒后驾车,撞死拉姆的丈夫;有过刻骨铭心的濯洗,老援藏干部雷平的女儿雷阳为了兴办希望小学而壮烈牺牲,与其说,他们为了寻找“梦中的橄榄树”而“流浪”、“漂泊”,毋宁说他们在经历一场形象的再塑,灵魂的重铸和价值理念的重建。
闻一多说:“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续”,“没有选择,并没有艺术。”我看到有不少论家在评价高鸿的创作时,都使用了“乡土写作的一次突围”、都觉得“这种刻画中国农民的坚韧、厚朴、善良、忍辱负重的作品已经不少了”,高鸿的乡村叙事却仍然“大有新意”。我想,它的新意不在别处,正在于在作家对题材的选择题材从自在进入自觉,从“共时态”中捕捉差异;从既在中寻求突破,从而把视角聚焦在代际人的“迁徙”和“漂泊”这种动态的生存时空,写出了人的另一类的“诗意栖居”。
二
与作家题材选择的视角相一致,高鸿在小说创作实践中,比较理性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作家思维与艺术表现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叙事方式上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嬗变。
叙事方式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言说的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文体去结构故事、去塑造人物、去推进情节,去勾勒细节的实践过程。它在读者面前呈现的是一个多维、多彩、多视的再现和想象的世界,它不仅取决于题材对创作主体的要求,也取决于作家的时代方位与生活本源的的距离和区间。
就作家所站的时代方位来说,高鸿是一位在新世纪进入写作高峰期的作家。因而,《农民父亲》、《血色高原》中人物所经历的风雨春秋,浮云苍狗,沧海桑田,无论对于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对于创作主体个人,都不过是一种人的生存方式的“曾在”。也就是说,即使在高鸿的生命册页中,有过亲历的体验,但一旦置于艺术的审美视域,就成为一种历久弥醇的“文化记忆”。故而,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都打着深刻的“生命回溯”的烙印。也许是基于此,作家在叙事方式上采取了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法,把故事引入主体自身。但这种引入又与那种主体自身与故事同步的新体验小说有明显不同。在《农民父亲》中,作品一开头就写道:
“父亲一辈子经历过四个女人”。
显然,这是一种时间距离下的审美。作品中的“我”是以追忆似水年华的心绪切入故事的。由此而展开父亲与大翠、桂花、母亲、继母四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线,众多的人物在这条轴线下,以“迁徙”为经,以各自的生存空间为纬,拓展出千姿百态、迥然相异、悲欢离合的命运风景。不论父亲对于与他命运交织的四个女人的爱怎样的浓淡参差,或被动接纳,或心灵交融,或若即若离,或基于伦理的同情,还是奶奶、母亲、继母与姐姐、小叔等如何被生活的激浪时而抛向波峰,时而坠入浪谷;不管“我”与花茸怎样从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到最终分手,还是与“菲菲”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衍生的理念冲突,所有这些,都是通常乡村叙事中常态的展现。关键在于,当高鸿以“追忆”的情绪咀嚼过往时,这种时空错位下的审美和“生命记忆”式的的叙事背后,就始终流淌着作家的情感湍流,贯注着作家诠释这些“曾在”的历史理性,隐寓着主体对于人的情感和思维的价值评估,闪烁着他看待这万千世相的独特的目光,传达着他对于人生、社会的哲学梳理。
这种主体回溯式的叙事,带来高鸿创作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散点式透视”的审美效果。因为要对“曾在”进行回眸,做出“反思”,使之提升到生命诗学的意义,就要求作家必须从人的现实存在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去发现他同这个世界的联系。“人在其现实性上,从来就不是单个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读《血色高原》,会发现,作家审美的视角并不固定在一个人物或者单一的环境,而是从故事的时空、节奏,人物的活动区间出发,不受视域的限制,横向地去扫描生活的各个点面。在许多情况下,他为我们勾画的多色背景不只是宏观的历史和现实投影,还有着地域自然涂抹在人物生命底板上的色素。战争硝烟的灰色、时代标识的红色,黄土高原一望无际的黄色以及它孕育的农耕文明特定的生存方式、文化生态和心理生态,都在作品中的母亲贾张英和丈夫抗战、儿子福海与女友、柳叶、二儿子福才和女儿福云身上烙下文化的烙印。外婆“超越自我”的“神性”,养育了坚守人性自我的贾张英、抗战,以至绵延到福海、福才、福云,却没有能够在两个孤儿身上“对现实起意志,去掌握现实”,祝俊堕落和离家出走,铁蛋后来“魔化”为折磨外婆的打手;福娥向往个性自由,追求个人幸福,表面看来。似乎打着思想解放的痕迹,然而,当这种追求因了长期封闭和道德准备的不足,使得她同时代的旋律产生了一种价值的错位,从而陷入了郑老师的色情陷阱。这样,作家通过《血色高原》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丰富充盈的社会风情画卷,不仅大大拓展了作品的横向广延,更重要的是,它在美学意义上强化了读者的心理视觉、意识形态视觉和时空视觉(福勒语),使得读者得以跟随作者的文本,去感知故事赖以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氛围,去读解作家通过人物语言和行为外化的价值和信仰维度,在纵与横的交点上形成对故事、背景、人物、情节的想象性建构。
作家的这种审美追求,在《青稞》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与前两部作品相比,《青稞》尤其注重“此在”——“人”的生存境遇亦即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联。作品虽然以主人公央金逃婚,去千里之外的拉萨寻找男友多吉开篇,然而,多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意象,他只存在于央金对幸福和爱情的憧憬中,是作家走进西藏新生代生命群体的一个入口。而接下来,高鸿以大量的笔墨去铺叙央金的坎坷历程,巴桑的人生遭际、拉姆的悲欢离合,平措的沉浮颠簸。在许多章节中,作家追求一种同构异质的审美效应,在同一时间内切换出不同空间的故事,从而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宏阔的、立体的叙事信息架构。于是,我们看到,“现代”这个概念,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打破旧的模式,催生新的生活范式的同时,必然导致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分化。拉萨,这座离太阳最近的城市,在信息社会化的岁月,早已不是单纯的钟磬远播、香烟袅袅、经诵悠悠所在,她在沐浴着现代文明春风微雨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各种不同生存方式和文化理念的浸淫和濯洗。诚如以色列籍美国著名文体学家浦安迪所说:“叙事文体中的节奏感的产生主要地存在于故事层面,表现为色调的变化、场景的更替、事件的转移以及表现这些内涵的诸如视点和语态等形式与手段的变幻上。”
对于高鸿的这种结构意识,批评界的看法仁智各异,有些论家以为高鸿这种“散点透视”的审美取向,使得作品的结构松散。这个评估,在一定的层面是有道理的,尤其在《农民父亲》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然而,我在读了高鸿的三部重点长篇小说后,就发现它与出版商“原汁原味大西北原生态小说”品格体认不尽相符,而是贯穿在作家作品中的一种自觉的追求。
首先,它没有影响故事主线在作品中的主导位置。在《农民父亲》中,“父亲”从屈服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动的与大翠结合,到在流浪途中遭遇桂花,碰撞出真爱的火花;从“救起一位落难的少女”,“ 看到母亲的第一眼就觉得很面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那年“腊月最后一天结婚”,成为“我的母亲”到继母走进“父亲的生活”,他与四个女人之间的情感冲突和情感起伏,始终牵动着读者的情怀。作者在讲述父亲梁海东与每一个女人的情感纠葛时,都倾注了饱满的笔墨。既有一波三折的情节推进,又有婉转细腻的心理描写,既有感荡心灵的矛盾冲突,又有和风细雨的起承转合。埋葬了母亲后,父亲一个人去了山东,寻找当年掩埋大翠的地方;在桂花最后的那段日子,父亲不顾村里的流言蜚语,毅然将自己的铺盖搬了上去,同桂花住在一起;父亲帮继母找回了被卖的女儿黑女,又把她的两个儿子接到家里。当继母遭到前夫的骚扰后,他以一个男人的刚烈和大度去呵护一个与自己生命交织的女人,所有这些,构成了《农民父亲》情感主线有机而又绵密的链接。
其次,它没有影响作家对作品中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黑格尔说:“凡理想的艺术典型形象,理应做到把人物的精神气质的质的规定性、性格的表现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情致的始终如一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在高鸿的作品里,人物形象的丰满与人物性格的丰富是协调而又统一的。读《血色高原》,除了外婆是作家赋予了创作激情,倾注了酣畅笔墨的形象外,母亲贾张英是作家为读者奉献的一个性格主导性鲜明的人物。在贾张英的行为方式中,“自我”首先是确立人的尊严的一种价值自觉,这成为她“活人”的一条稳定的基线。在奶奶歧视外婆的时候,她宁愿舍去新婚燕尔的温馨也要随着外婆搬到破窑里去住;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为了改变穷困的生存窘迫而顶着环境的压力到镇上摆摊卖饭;即使在劳教农场也仍然挺直着“人”的脊梁,并且冒着坐牢的危险而把开水泼在王三蛮脸上;为了呵护儿子的一份为“人”的权利,他甚至冲破后来成为法院院长的王三蛮的阻挠而直接去找县长。但只要走进作家的叙事结构,就不难发现,贾张英性格的丰富性与奶奶的坚韧和宽怀构成承继关系、与祝俊、王三蛮的庸俗、霸道相比较,与福海、柳叶的抗争相矛盾而得以呈现的。正是这种多侧面的群体刻画,烘托起主人公的绚烂和多彩,使得人物凸出了“散点透视”下人物群像的平面而显现出“浮雕”的魅力。
再次,它没有影响作家对作品的深度开掘。《农民父亲》、《血色高原》和《青稞》,虽然讲述的是不同历史条件、不同人文环境、不同自然地域下发生上的故事。然而,作家主导这三部作品的价值取向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有机联系。这就是呼唤人作为“人”存在的尊严和地位、人作为美的主体,他的本质力量的美学价值,而这恰恰是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所缺失的。如果说,在《农民父亲》和《血色高原》中,作者以文化批判的姿态鞭挞那种对人的生存地位的蔑视行为,期待在反思中为构建一个“属人”的现实提供了历史的启示;那么,在《青稞》中,作家则以与故事中人物命运同步的创作姿态直面复杂的生活。作品中主人公央金、巴桑和雷阳等一代年轻人所面临的困惑恰恰是新世纪中国在走向复兴历史进程中矛盾的“普遍性”反映,它告诉读者,人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尊严的最终确立,不仅有赖于物质的丰富,更在于人文生态的改善,在于构建使“人”得以消除工业时代或者后工业时代“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建立起传统与现代相交融、民族性与开放性相协调、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这样,人才能最终摆脱“人”的生物学意义的存活,而在对历史的切近中绽出生命辉煌。
三
高鸿的审美自觉,不仅仅体现在对题材的解读,对叙事结构的构建上,也在技巧的层面得以充分的展示。
阿根廷著名诗人胡安·拉赫曼说:“创新往往是以痛苦的方式开始的。因为一方面要打破以往的执着积累下来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寻求新的、与以往不同的执着,在掌握新的表现工具的时候,原有的执着会熄灭。在我的写作中,这几乎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其中也有低潮,有写不出来的时候……”高鸿是追随着陕西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变革和繁荣的足迹登上文坛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对于他的侵染,既为其攀升提供了可供参照的坐标,也把如何走出旧的窠臼,走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创作道路,打造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提到他的面前。令人欣慰的是,他以坚实的脚步,寻求着新的突破。
从创作《农民父亲》开始,他就比较关注小说审美表达的文学意象特征,并试图借以隐涵人物命运的走向,如在第一章,大翠娘家为大翠做陪嫁枕头,“鸳鸯是大翠的娘央人绣上去的。先是绣了一只,那家的女人突然得了急病,殁了。大翠娘于是又央人绣另一只。村里的女人都劝她重新拾掇一对枕头,大翠娘左看右看舍不得,就将就了。”结果,不但新婚第二夜爷爷就死了,而且大翠与“父亲”的婚姻也没有到头,在与一家人“迁徙”中饿死。在大翠妹妹去世的前一天,“太阳似乎也开始捉弄人了。一会儿是三个,一会儿又变成了两个,它们在父亲的头顶盘旋。”在“父亲”带着一家人暂时于大刘庄栖身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作家满怀激情地写了一段《蒿草颂》,热情地讴歌生命的倔强和坚毅:
干枯的荒蒿紧贴着地皮,都蔓到台阶上了。这种植物具有超强的生命力,无论在哪里,不管自然条件有多么恶劣,你都会看见它们的身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它们生命的赞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不能蔑视它们的存在。它们和古老的中华民族一样,具有超级忍耐力和超强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维系着几千年的岁月,支撑着一个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
散文笔法的介入,赋予作家笔下所讴歌的客观物象以浓郁的象征意义,引发读者的审美视域在联想的时空自由翱翔,在精神和信仰的坐标前,实现超越具象的升腾。
对于象征艺术的运用,在《青稞》中表现出高鸿的艺术自觉。作家之所以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青稞》,正是因为它是贯穿在作品始终的象征体,是走进作品人物心灵世界的一把钥匙,是西藏人精神国度里的神祗圣物。作家在第六章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关于青稞的传说。而讲故事的主角却是一位80 后的青年巴桑。这个设定,就赋予这个美丽的神话以强烈的当前性和在场感。它的“喻指”在当今而不在过去,承载这个美丽神话的是两个重要的意象,一个是青稞,它使得西藏人改变了古老的食物结构,“养育了一代代藏民”,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青稞是西藏人生命的符号,是西藏民族精神品格的象征。一个是“黄狗”,它蕴含着为偷取青稞种子被蛇王惩罚而演变成“黄狗”的阿初的悲剧命运。尽管阿初在获得了公主俄满的爱情后得以回归“人类”,然而,“黄狗”却成为藏民崇拜的图腾。它们的象征意义远远地超越了它作为一个古老故事的存在。青稞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更闪烁着熠熠的人文光彩。于是,我们看到,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在西藏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被赋予“属人的本质”。
高鸿的艺术探索不止这些,他的创新的足迹在他的其他作品里都留下深刻的笔痕墨迹。
当然,作为一位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中青年作家,他的作品也有需要打磨的空间,他对于生活的深入和解读也还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如何实现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的自然统一,也是待思考的问题。例如,在还原历史面貌时,有误读的现象。“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概念是在“学大寨”运动开始以后才有的,1958年代它还没有出现;又如女人被轮奸后,用擀面杖檊肚子,也是有违生活常识失真细节。这些,当然不影响我们对于高鸿小说创作价值的美学认定。期待他有更多的好作品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