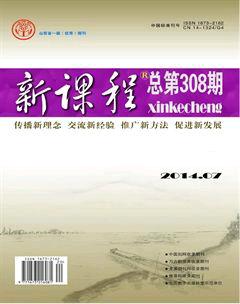论郁达夫作品中体现的西方文学
张倩
摘 要:郁达夫的《沉沦》描写了一个有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充满清醒的病态心理解剖意识,成为新文学史上自觉描写灵肉冲突的二重人格形象的优秀名篇。郁达夫与一般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不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此为榜样,而是把他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更多地接受西方个性主义的忏悔意识。
关键词:西方文学;忧郁;感伤;忏悔主义
郁达夫的《沉沦》是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精神积于一个深受着时代压迫,染着当时忧郁伤感的“时代病”的留日中国学生身上。小说深刻地剖析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他酷爱自由,热望着真正的生活,却受着社会的严重压抑;他希望祖国的强盛,而看到的却是祖国的日渐“陆沉”。他那多愁善感的性格使他终日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他把自己的精神寄予虚幻之中。他那孤冷的性格,忍受着残酷的现实。《沉沦》包含大量的对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引用。与一般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不同,郁达夫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此为榜样,而是把他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
郁达夫的《沉沦》则代表了更多地接受西方个性主义的忏悔意识,现代文学的忏悔意识存在从“人的忏悔”到“忏悔的人”的转化过程,忏悔主体从抽象的人转移到具体的人即作者自身,产生了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这种转换俄国文学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罪孽和良心的痛苦自谴思想的深远影响,也深刻反映了政治大变动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忏悔的人”演变为知识分子的“自我作贱”,忏悔意识原先具有的人文主义因素和现代意识丧失殆尽。
现代汉语中的“忏悔”意为:认识了过去的罪过或错误而感到痛心,是一种良心与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反省行为。从词源上看,“忏悔”原本是佛教语词,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忏”是梵语“忏摩”的音译,“悔”是意译。《晋书·佛图澄传》也有佛图澄弟子佐“愕然愧忏”的说法。据说“忏悔”一词的合成始于南北朝,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梦见如来说法说到忏悔之言,醒后向萧衍转述了梦境。后萧衍当了梁武帝,做“忏悔”文以“忏六根罪业”。“忏悔”成为文学批评的常用概念则是在80年代以后。新时期文学产生了社会批判精神和自我审判意识,“忏悔”就是良心与良知的自我反省。
郁达夫的《沉沦》,小说中只有“我”的视角,小说展现的首先是“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我”眼里的世界。现在作家强调的是“我”在世界中,若“我”不在世界中,那么“世界”就没有意义,过去那种全知全能的客观性叙述人消亡了,叙述人不再是超脱于事件之外的冷观者、宣教者、审判者,而是事件的参与者、故事中的行动者。他是普通的,是一个“我”,个体的人。“五四”个体性文学时代的小说叙述人是角色化的。个体性文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感性的优先地位的确立,在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对立中个体性文学的作家无一例外地选择感性世界,作家首先认定自己是独立个体,然后再把自己的个人的经验世界呈现出来,这是一种身体的哲学,它确认人的身体的经历的正当性,身体的法则是私人性的、非理性的、欲望化的,它同我们过去所重视的灵魂的法则是对立的,灵魂的法则是禁欲的、理性的、伦理的。过去的哲学基本上都是灵魂哲学,几乎都在终点上将自己归结为伦理学,而个体性文化时代的哲学是身体的哲学,是对以往一切灵魂哲学传统的一个颠覆,个体性写作的时代作家对自己的身体是肯定的,《沉沦》作品中,作品中的悲观主义是身体的悲观主义,作品中的痛苦是身体的痛苦,作品的绝望是身体的绝望。
郁达夫小说塑造了一个处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留日青年。他在“五四”狂飙和西方新思潮的感召下业已觉醒,热切地渴望恢复刚刚意识到失去的自身价值,向往异化于己的真正的性爱。然而,在这文明的现代社会,尤其是他这样一个身处异邦的弱国子民,他的所有追求都“已成为一种观念”,成了他的理想。他的清醒终究成为他愈加苦恼、愈加悔恨的深渊。终于,伴着个人理想的彻底幻灭,他走向投海自尽的绝路。小说中这个拼命挣扎的生灵被黑暗势力张开的魔网所吞噬。然而,他的精神又是耗尽于无尽的忧郁和感伤之中。在那社会为他张开的吃人的魔网里,他也用自己的忧郁感伤束缚了自己的意志,在无法摆脱的苦闷中了结了年轻的生命。因此,有人说“作者心灵深处对爱情的呼唤,使他听不到革命的金戈铁马声。面对黑暗社会,只能发牢骚、泄私憤,通篇弥漫着因国辱权丧引起的哀愁……”(《试论郁达夫创作中的消极思想》宋聚轩)。
鲁迅曾说过:“即使所讲的,只是个人的事,有些固然只看见个人,有些却也看见背景和环境。”生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进步作家郁达夫,时代的闪光也必然在其作品中得到折射和体现。众所周知,“五四”精神就是反帝反封建。由于时代的黑暗、祖国的贫弱,郁达夫因此饱尝着长期的痛苦,使他的忧郁感伤情绪与日俱增。正如郁达夫自己所说:“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面……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概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丧失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那时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郁达夫《忏余独白》)。他这由于切肤之痛所发出的忧郁感伤的基调,就必然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反映。另外,郁达夫忧郁感伤格调的形成,还深受当时某些文学流派的影响。无论是他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还是他自己提出的文学主张,都要求大胆、率真地暴露自我。一则在这丑恶现实的压迫下,使他产生无穷尽的苦闷忧郁,一则他那日益觉醒的意识又不甘死灭,而这种内心的矛盾只有对自我进行大胆剖析才能宣泄出来。
郁达夫作品中的忧郁感伤基调也有一定的消极性,表现出了那一时代所特有的矛盾:“追求幸福”与享乐主义,“性的解放”与纵欲放诞。郁达夫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曾以“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为武器猛攻旧道德、旧传统,并热烈地幻想拯救民族,复兴祖国。可是当“五四”退潮之后,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思想变本加厉地窒息着中国大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勾结在一起,使中国社会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而这些业已觉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由于他们清醒了,正是他们曾有过好梦,所以就更加痛苦。正如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尽管他的作品是忧郁感伤的,但他那大胆破坏的精神却是主旋律,尽管他从“自我”来触及那个时代,但他却体验着那个时代里受苦受难者的疾苦,尽管他的作品有着一些缺陷,但他始终是前进着的。他是具有“特异的人格”的人。同时,郁达夫创作还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持和群众结合在一起而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他将永远苦恼、永远忧郁,因为他无法踏上真正解放的道路。
虽然郁达夫没能把西方文学的文本放进他的小说后做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但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出另一个现代主义写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