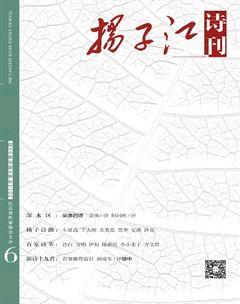反抗,何以成为失败的一部分?
何同彬
从前,诗歌通过回顾词语记忆并从中萃取出感性时光,一直都懂得大声说出对自由意志的愿望。在我们隐约感觉到衰落或至少是不确定的时代,追问一直是惟一可能的思维方式:一种尚存生机的生命的标志。
——克里斯特娃
宿命的节日
数年前,朵渔凭借“凝视个体内部的黑暗”而在一个名流云集的光亮舞台上领受了那个重要的,或者可有可无的荣誉。彼时彼刻,在那束被簇拥的赞誉和诡异的朗诵声塞满的公众性的光里,朵渔涌动着怎样的诚实内心、如何安置自己体内的黑暗?不得而知,我只能以一个冷眼看客的狩猎似的心态,妄自揣测着诗人将如何“被他低水平的对手扼住”……伯恩哈德面对纷至沓来的文学奖时的自责心态——蔑视文学奖但没有拒绝、憎恶仪式却又不得不参加——在中国的场域中是不合时宜的,以至于秉持“反抗的诗学”的朵渔在那篇名为《诗人在他的时代》的获奖感言中,无法免俗地悼念了死者、代言了“沉默的大多数”、感谢了评委。然而更具悖谬的宿命意味的是,他声称:“只要在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苦难和不公,还有那么多深渊和陷溺,还有那么多良心犯、思想犯被关在笼子里……那么,诗人的任何轻浮的言说、犬儒式的逃避、花前月下的浅唱低吟,就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恰如他在描述自己“羞耻的诗学”时为自己布置好的“圈套”:“诗歌写作如果仅仅是与精神生活有关,那么它很可能是一种狂热的、高烧的精神巫术,它的归宿往往是虚无的、蒙昧的。我看一个人的作品,往往会联系上他的生活,如果他的写作和生活是分裂的,我会对此人的写作保持怀疑和警觉。”(《羞耻的诗学》)在一个诗人沦为戏子、靠谎言和表演制造诗歌的灾难性的繁荣的时代,朵渔极力制造的诗人主体或诗歌的“小小的孤独游戏”与日常生活的对峙关系,将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拖入一个廉价的“耻辱”不断累积、不断重复却又毫无意义的“失败”之中。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不是分裂的,没有任何严肃的写作形态不堕入虚无,诗人、诗歌不依赖虚构的“精神巫术”将难以维系自身的存在和认同。于是,诗歌对朵渔而言就成了他所谓的“自己与自己的较劲”,而这一较劲也难以避免地震荡出鲁迅意义上的“颓败线的颤动”。
“你有没有勇气成为失败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它的邻居?”(《问自己——你要诚实地回答……》)事实上,失败是不需要勇气的,它是朵渔这样的在“扩大了的精神”(康德)的维度上逆流跋涉的诗人的可怜“宿命”。阿伦特把极权主义的倾向概括为“使人变得多余了”:私人融化在公众之中,个体被随意处置,而思想变得无能,对权力之成败没有任何影响。正如她在描述“黑暗时代的人们”时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借用:“任何真实或本真的事物,都遭到了公众领域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闲谈的压倒性力量的侵袭,这种力量决定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预先决定或取消了未来之事的意义或无意义。”这和朵渔在柔刚诗歌奖“受奖辞”中描述的困境一致:写作是对羞耻感的回应,而这一回应无所谓成绩,所有的成绩都只是失败。当年,阿多诺声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如今,日常的欢愉之后写诗是羞耻、失败、再羞耻、再失败的无意义之循环。因此,朵渔的近作《这世界怎么啦》(组诗)毫无疑问地仍旧深陷在这种“失败”的诗学范畴和政治困境中:
总感觉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在靠近,其实
又没有什么不同。……
……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幻听的毛病始终未愈,宿命啊
我们在期待中迎来的每一次失望
都在磨损着我们的意志
当我试图用爱来装扮这个世界时
总有角落里的哭声在低声抗议
——《宿命的节日》
朵渔在一个他愈发无力应对的时代坚持着“追问”:这世界怎么啦?这一追问在他这样的“征服者阵营里的逃亡者”(西蒙娜·薇依)的黑暗心脏里,是应对召唤的必要的诗学反应。但这一追问形式在强大的日常生活的“闲谈”和“不可理解的琐屑”那里,无疑将显得渺小和可笑。早在2008年朵渔就“突然觉得诗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成了一件可疑的事情”,“也许‘怀疑的苗头早已深藏于我的内心,它随时会鬼魅般跳出来。我甚至觉得诗人的现实存在有了某种晦暗性,包括诗人的身份、手艺、精神、创造等等”,“我必须对现代汉语诗人的身份危机做一番自我辩驳——对诗人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现代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合法性问题进一步追问:你在现代社会中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你说你在创造,那么你到底创造了些什么?你有没有自知之明?”(《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样的怀疑和一系列追问无疑会把诗人的主体认同推向溃散的边缘,只是那个时候他对自我辩驳还充满信心,能够开出这样的处方:重返最初的开端,经由超越(自我修炼)与沉入(爱),返回自我的实存。几年后,他亦提出“无论时代真相如何,一个诗人都应该无惧于希望的幻灭,秉持永不衰退的激情,使人、使世界变得美好起来”,要相信“文学的伟大性”(《我等》)。而如今面对《这世界怎么啦》(组诗),我们却触目地看到朵渔所曾经反复警惕的“虚无主义的惬意”和“道德主义的自我感伤”,以及弱化了的“恨”的主题:“批判、怒火、抗议、鄙视、绝望,哀悼的气质、反讽的嘴角……”如“自由,以及自由所允诺的东西,在将生命/腾空,如一只死鸟翅膀下夹带的风”(《稀薄》)、“不知不觉的,像是一种荒废/如此来到人生的高处/不可能再高了”(《损益》)、“都散了吧,屋檐下的海已结冰/空气中到处是废墟的味道/阿克梅的早晨不会再来临”(《银子》)……低徊在诗歌中的是浓厚的衰败与悼亡,而精致的平衡感营造的沉静也隐匿不了虚无、绝望的潜流。
如此颓唐的朵渔的到来毫不意外,仍旧属于那个“失败”的宿命。“当我试图用爱来装扮这个世界时/总有角落里的哭声在低声抗议”,朵渔与当代那些纠结在拯救与逍遥、自由与关怀的永恒矛盾中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一样,始终无法轻松地把自己安顿在威廉·布莱克所批评的“幽灵自我”中,守着一个叶芝描述的超越性的梦:诗人通过不断的自我争辩,可以向更高级的生命状态飞跃。那些低声乃至高亢的“抗议”始终纠缠着诗人的内心,只要你诚恳而严肃地回应,就绝对无法飞跃,相反,你将被抗议俘获并紧紧压在身下。时代的“深渊和陷溺”如此迫近,而“轻浮的言说、犬儒式的逃避、花前月下的浅唱低吟”又那么的“亲切”,失败自然如约而至。朵渔在描述自己写作的“耻感”时所苦心经营的“两种力的平衡”(《“其实你的人生是被设计的”——朵渔访谈》)既成功了,也失败了,他固然没有“走火入魔”、陷入过分的偏执和黑暗,但却因此失去了部分的激情和力量,开始徘徊在中年写作的微妙智性的退路上。endprint
危险的中年
感觉侍奉自己越来越困难
梦中的父亲在我身上渐渐复活
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沉沦
更多时候管不住自己的骄傲
……
假意的客人在为我点烟
一个坏人总自称是我的朋友
我也拿他没办法……多么堂皇的
虚无,悄悄来到一个人的中年
——《危险的中年》
菲茨杰拉德认为,没有人应该活过30岁。我从不认为这是危言耸听的怪谈,相反,我坚信成长、成熟经常是衰退、世故的代名词。就像朵渔在诗歌中描述的,“父亲”在自己身上“复活”,莫名的“沉沦”与“傲慢”不可遏制,那些曾经的“坏人”成为自己的朋友……60后的很多诗人在描写中年的时候涌动着更多自我辩解、自我戏剧化的意图,如于坚那“最高的轻”:“中年是幽暗的杜甫/之后在落日中散去/什么也不是了/满足于最高的轻”(《一朵白云》),潘维的淡泊或孤独:“人到中年,一切都在溢出:亲情、冷暖、名利。……人到中年,是一头雄狮在孤独。”(《中年》),还有黄梵广为流传的“好脾气的宝石”:“它是好脾气的宝石/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中年》)朵渔虽然明确意识到中年的危险性,但某种程度上仍然出于一种平衡感的需要,没有把“羞耻”和“个体内部的黑暗”全部挤压出来,而是以退为进,把中年的“荒废”作为不能再高的高处,衰老或流逝被淡化为“生命中的自然损益”:
接下来,要准备一种
临渊的快感了——
死亡微笑着望着你,那么有把握
需要重新发明一种死亡
以对应这单线条的人生
——《损益》
欧阳江河在提出中年写作的时候同样以创制一种新的死亡叙事为开端的,“反复死去,正如我们反复地活着,反复地爱。死实际上是生者的事,因此,反复死去是有可能的:这是没有死者的死亡,它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亡灵。……对中年写作来说,死作为时间终点被消解了,死变成了现在发生的事情。”(《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而朵渔的中年写作依循的是同样的路径,《这世界怎么啦》(组诗)如同一个遍布死亡的复活节,以至于我们在频繁而反复的死亡话语那里丢失了它:死亡、死者、死鸟、痛哭、哭声、泪水、葬礼……
到底是新生还是死亡?也许只是一次轮回
一个旧我被清空了,死亡徒有其表。
人生其实就生在这死里。并相信这是善的。
——《善哉》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已经习惯于以这样一种审美主义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s)方式“调侃”死亡,这一“趣味”在中年写作的书写形态中更甚,诗人们像是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一盒牛奶那样,把琳琅满目的死亡话语塞进自己的“购物车”,毫不顾忌日常、审美和脆弱的人性对人的惟一绝对性的损伤,相反,死亡的失重或稀薄化被一种看似超越的姿态“奉承”为“教育”:“稀薄也是一种教育啊,它让我知足”(《稀薄》)、“必须在死亡中/重新学习活了,真好,死亡还很年轻”(《银子》)。这一切对朵渔而言无疑意味着一种特别的虚无主义的降临,死亡被淡化的同时,所有曾经的“愤怒的诗学”、“反抗的诗学”中那些反叛、冲突、对抗、怒火都渐趋平抚、熄灭,或者就是新的羞耻的逼近。当然,与死亡的失重同理,羞耻的诗学在耻感的反复到来中变得稀薄,乃至沦为朵渔厌恶的“符号化”的自我辩护。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生活是被杀死的或已故的认同的墓地,朵渔如今的诗歌就根植在这样的墓地之上,他感激“日常之欢”,抛弃“读者”、“理解”和“赞美”,不为“荣誉”也不为“监狱”写作(《致友人》);他时常责备自己,为不能回到“真实无邪的生活”而哭泣(《我时常责备自己》);他用最后的咳血告别尘世,去另一个世界寻找“咳血的友人”(《道路在雪中》);他梦想如树一样活着,忘记什么是不幸,无欲无求的淡定(《树活着》)……
当然,朵渔的虚无主义不是克里斯特娃所否定的那种虚无主义:“摒弃了旧的价值标准,转而崇拜新的价值标准却不对其提出疑问”,“两个多世纪以来被视作‘反抗或‘革命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放弃了回溯性追问。”(《反抗的未来》)朵渔对时代的追问和对自我的怀疑从未停止,《这世界怎么啦》(组诗)始终盘绕着针对存在与写作的诸种形态的深刻的省察,只是这种省察过于潜隐和低沉,不似以前诸如《2006年的自画像》、《妈妈,你别难过》、《不要被你低水平的对手扼住……》、《凶手的酒》等诗作那么明确、激烈和决绝。如果这仅仅是一种美学调整倒也无可厚非,毕竟“抵抗诗学”或“文学知识分子化”所经常装点的“独断论的道德气氛”和“痛苦诗学”(臧棣《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论当代诗歌的抵抗诗学和文学知识分子化》)。的确有其矫揉造作的一面,但事实上任何美学嬗变都无法与个体的政治心理的变化完全剥离,对朵渔而言就更是如此。从朵渔近期出版的作品来看,无论是诗集《最后的黑暗》,还是散文随笔集《我的呼愁》、《生活在细节中》、《说多了就是传奇》,历史性书写已经成为他文学书写的主要支撑,这与当前诸多诗人、作家对历史的“迷恋”是一致的,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历史作为一种“危险的疾病”(尼采)的灾难性,或者忘记了别尔嘉耶夫的警告:历史是精神的蒙难,上帝王国不出现在历史中。当然,历史性写作可以帮助朵渔保持认同的延续性和心智、美学的平衡,但这一平衡是以某种程度上的怯懦和自私为代价的,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行动”。因此,朵渔的虚无主义也不是海德格尔总结的尼采式的虚无主义:一种摆脱以往价值的解放,即一种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解放。《这世界怎么啦》(组诗)所显现的是,历史及那些知识(知识分子)的谱系性梳理并没能帮助朵渔实现解放,相反,他陷入一种束缚性的沉溺,而这一沉溺还之所以值得期待,就在于追问的对峙性并没有被彻底放弃。endprint
在期待中
就这样,我也来到这里
在期待中领受孤寂的教益
神恩不降,孤寂便没有价值
天使不来,记忆中的情人
也没有意义,和那些同样
不具意义的玫瑰在一起
——《在期待中——里尔克在慕佐》
多年前,朵渔还写过一首同样意味但风格大相径庭的诗,充满了对诗人及诗的浓重的质疑:
诗的虚伪 诗的狭隘
诗的高蹈和无力感
已经败坏了我的胃口,让我
想要放弃
我放弃得已经够多,时光、尊严
无穷无尽的耻辱,仿佛一堵
竖起的墙 我越来越
与世界无关,与这座
虚无的城无关。
——《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
如今,朵渔的自我怀疑换了另外一副中年写作的面孔,即“历史纵深和记忆深层”的“知性的质地”(霍俊明),但虚无感却更为彻骨:价值、意义只能寄希望于“神恩”和“天使”,而这也许就是那羞耻、失败的宿命的根源。严肃的诗人谁都无法避免遭遇里尔克所说的“古老的敌意”,如何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实现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已经成为当代诗人、诗歌的“斯芬克斯之谜”,而认识自己(诗人、诗歌)又谈何容易。朵渔曾经相信的“文学的伟大性”是否真的存在?我们是否对诗歌的见证(米沃什)和纠正(希尼)功能深信不疑?玛莎·努斯鲍姆提出的“诗性正义”、唐晓渡所说的“内在的公共性”是否可能?或者相反,做一个喧嚣中的逃遁者、在孤独中“领受孤寂的教益”是否就是柯勒律治所批判的“享乐主义的自私”呢?我想朵渔以前与现在都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些根本无法真正解决的问题。阿伦特认为,能够在艺术家与行动者之间进行斡旋的是cultura animi,“即一个受过充分培育教化,从而有能力照料好一个以美为尺度的现象世界的心灵”,甚至应该是那些“天生自由人中的最高贵者”(《过去与未来之间》),朵渔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诗人乃至现代人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无信仰的个体,为了赋予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意义,将会发现自己被困在自我专注的强迫症、沮丧与焦虑之中——精神病(psychopathology)成为疾病的现代形式。事实上,‘精神—病(psycho-pathology)这一术语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灵魂的受难,而在现代用法中,以人格(personality)——实质上是自我(ego),取代了灵魂。”(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诗人不过是无信仰的现代人中的一员,他的所有的希望/绝望、光荣/羞耻都只是把自己限定在“自我关注”中的疾病;他误以为自己的灵魂在受难,但往往只是与那个褊狭的自我有关。因此朵渔也就不会等到“神恩”和“天使”,他的一切的书写也不过是宿命的“失败之书”,他的一切或隐或显的“反抗”也就无法避免成为失败的一部分。
我的缠绕往复的论证得到的是朵渔早已明了的虚无的宿命,但他也许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世界怎么啦》(组诗)及其目前的创作所暗藏的危机与生机。一方面,一种越来越沮丧、焦虑的自我关注的强迫症(或中年写作心态),让他离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和“行动”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他内心永远涌动的自由意志的愿望,支撑着他永不放弃的追问:黑暗、羞耻、失败……这种尚存生机的标志,保证他在“自我”与“灵魂”之间始终没有放弃向后者的推进。“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鲁迅《颓败线的颤动》)朵渔永远摆脱不了“失败”的梦魇,因为他在梦中也本能性地把自己沉重的手放在胸脯上……某种意义上,《这世界怎么啦》(组诗)属于朵渔的转型期的作品,既有一以贯之的诚实的、抵御性的人性逼问,也有一种混杂的、虚无的犹疑,此时我们不妨从希尼对赫伯特的评价中期待一个更具当代诗歌典范性的朵渔:“由平衡、步调和韵律所给予的确定性,则不可否认地是他成就的关键;他迂回的形式和编织隐喻以与意识圈套相称的方法,则有一种根本性的力量;但是只有当这种精神受到远远超乎平常生活所谋求的道路的召唤时,只有当呼喊或狂喜从那种精神中绞拧出来,飞入其自身的孤独与明确的某种意外的形象中时,只有在那时,赫伯特的作品才以其最无可比拟的精致而树立了诗歌纠正的典范。”(《诗歌的纠正》)endprint